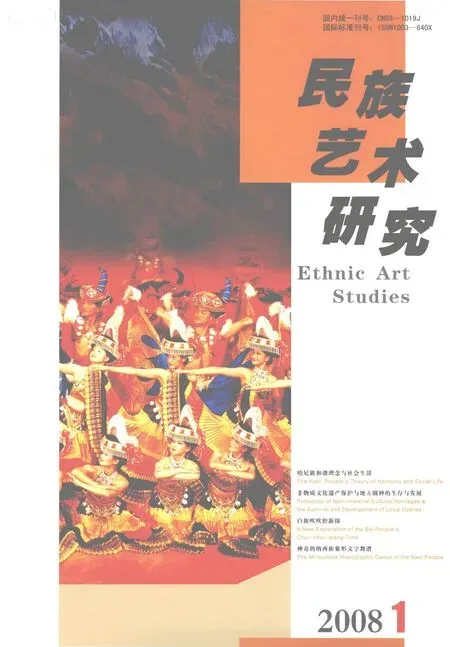當下中國藝術電影發展面臨的困境與選擇
丁亞平,王 婷
進入21世紀以來,第五代和第六代導演持續發力,年輕一代導演則不斷涌現,國產藝術電影無論是在電影內容,還是形式的探索上,都獲得了新的進展。互聯網對社會生活的重構作用于電影生態,影響深遠,原本概念和范疇并不那么清晰的藝術電影進入了一個更復雜、混融和多元的空間里。近年來,對國產藝術電影發展的選擇、困境和對策的檢視與討論的聲音一直存在,然而,面對當今多義復雜的新語境和日益被拓展的結構空間,中國藝術電影如何自處和良性發展,值得思考和探討。
一、國產藝術電影譜系:“看”與被選擇
(一)何為藝術電影
在電影的評價序列中,一直存在著對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抑或文藝片和商業電影的涇渭劃分。然而,在真正對具體電影文本進行仔細甄別時,其間卻充滿模糊性和曖昧性,分明的涇渭似乎無法被辨識,它們之間的區別仿佛只存在于抽象的概念空間中。何為藝術電影?一直以來,其各種定義聚訟紛紜,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有學者談到文藝片、藝術片、商業片之間的關系時,如是言:“商業片其出發點是票房,從創意、編撰、表演和宣傳發行都圍繞著這一目標進行,與市場存在一種妥協和合謀的關系。文藝片則不僅僅是為了商業價值,還有電影人的某種文化追求。如果它再走遠一點,也就變成實驗性質的藝術片或者 ‘藝術電影’。”①厲震林:《關于電影文藝片的概念誤區及其發展通道》,《藝術百家》2016年第5期。商業電影、文藝片和藝術電影的區別源于其追求目的的不盡相同。《電影藝術詞典》為藝術電影下了這樣的定義:“藝術電影專指那種觀念新穎、趣味高雅、技巧考究、不以贏利為目的的影片。”至于它與商業電影的關系,獨具意義:“(藝術電影)在觀念上的創新突破、在藝術技巧上的大膽探索,常很快為一般商業電影所采用,從而帶動整個電影藝術的發展和提高。”②許南明、富瀾、崔君衍主編:《電影藝術詞典》(修訂版),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頁。臺灣學者廖炳惠的 《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匯編》一文認為:藝術電影 “在技巧的實驗與敘事手法上,都有其自主性與企圖,而這些和主流的商業電影 (特別是美國的好萊塢電影)是有所區隔的。”①廖炳惠:《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匯編》,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頁。顯然,藝術電影無論是形式和內容上,都不乏對 “新”的追求,從表達訴求方面偏重作者性,而這也決定了它與商業電影的本質區別。
“藝術電影”作為一個術語的出現,可追溯至20世紀初。1908年,一家名為 “藝術電影公司”的制片公司在法國成立。當時的電影作為一種新式的玩意出現了約十多年,被視為下里巴人欣賞的玩意,趣味低級,更遑論 “藝術”二字。于是,藝術電影公司以藝術為主要追求,專門請著名作家和演員拍攝有高雅趣味的影片。隨著電影的不斷發展,現今藝術電影的概念和一百多年前的顯然不完全相同,然而其中的精神內核卻存在一定的一致性。《黨同伐異》作為早期世界電影史上的藝術電影代表作之一,它的出現顛覆了大眾對電影常規的認知,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導演格里菲斯均完全打破了往常的表現手法,自然逃脫不了觀眾在觀影時感到被“冒犯”的命運,最終票房的巨大虧損,亦印證了藝術電影和票房原生的抵牾關系。大衛·波德維爾則從其他維度定義藝術電影,他認為:“藝術電影是以注重人物性格刻畫、淡化因果邏輯關系和對寫實與逼真表達性的強調為特征的。”他還從和觀眾的關系出發去解釋藝術電影的特征:“對于觀眾來說,藝術電影的主要標志就是它的不確定性”②轉引自游飛、蔡衛:《世界電影理論思潮》,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頁。。和不確定性相對應的是確定性,確定性是類型片的內在敘事邏輯。觀眾在觀影時,對影片敘事的發展有潛在的期待視野,這是好萊塢類型電影之所以長盛不衰的秘密。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當故事的發展和觀影心理完全一致時,會出現相應的觀影疲勞——故成功的類型電影或言商業電影可以做到精確把握大眾微妙的心理需求,在確定性的基礎上賦予其不確定性,產生預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確定性意味著連續、完整、清晰,反之,不確定性則意味著斷裂、破碎、模糊。在藝術電影中,不確定性成為影片的基調,觀眾的期待視野從觀影伊始就被打破。影片的觀看作為一種沉浸的藝術,電影和觀眾之間的最佳縫合來自人們對于它的認同感,當認同感無法建立時,觀眾心里會出現自然的排斥機制,這大抵是藝術電影和大眾之間長久以來無法避免的關系怪圈。不同于商業電影中對觀眾心理的迎合,藝術電影導演往往在影片中執著于個人對世界、對社會、對人本身的觀照和表達。導演刁亦男在接受采訪時曾談到他對電影中不確定性的理解,為藝術電影的不確定性做了最佳注解:“我就想抓住一種永遠的不確定感,直到結尾”“男人和女人關系的不確定性是最有張力和最有意思的……我要的是不確定性,這就是我對情感的認識”。③刁亦男、李迅、蘇洋:《〈南方車站的聚會〉:復原怪誕現實的審美追求——刁亦男訪談》,《電影藝術》2019年第4期。
無論在世界電影史還是中國電影史上,藝術電影往往受制于諸多因素,然而它們的發展并未因此止步。從 《公民凱恩》到 《低俗小說》再到 《小丑》,從 《小城之春》到《霸王別姬》再到 《南方車站的夜晚》,藝術電影拓展了電影形式上的邊界,其內核指向敘事之外的精神修辭,它們通過各自的方式為觀眾提供了某種理解世界的方式,每部藝術電影自有其法則,成為廣義電影序列中的“嚴肅藝術”,脫離了看世界的慣常方式,從而通過一種更復雜、更曖昧的再現,進入更真實的現實。
(二)現狀:被看見的和被偏好的
日本電影導演是枝裕和曾表達過 “電影只分有趣和無趣”的觀點,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眾對電影的態度。電影從誕生伊始,迄今有百年的歷史,“第七藝術宣言”為它的藝術性發起辯護。從巴贊 “電影是什么”的拷問直至今日,想必并沒有人會質疑 “電影是藝術”這一類似于公理的存在。同時,電影的傳播和流通方式決定了其大眾性和商業性。藝術性和商業性對電影而言,像一對雙生花,相互背離,又彼此依存。
從歷史的維度看,藝術電影并不是一個完全靜態的概念,它隨著歷史背景、歷史文化的變化而變化發展。新時期以來,國產藝術電影先后在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的努力實踐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第四代”力圖突破傳統電影觀念的桎梏,拉開了新時期藝術電影創作的帷幕。“第五代”顛覆了影像語言,讓中國電影開始被世界認識和關注。如果說 “第四代”和 “第五代”的作品是作為一種集體記憶的藝術電影的話,“第六代”則在影片中聚焦于個人記憶、顛覆個體的精神世界。實際上,藝術電影在票房上始終無法與商業電影抗衡。第五代導演何群曾說過:“《黃土地》的拷貝賣得并不是特別好,大概30多個。從普通觀眾的層面來看,《黃土地》并不是非常通俗的,從形式上、從影片的節奏上,對大多數觀眾來說,《黃土地》是一部藝術片,而非商業片。從導演和創作手法上來說,我們也的確沒有考慮去迎合觀眾的趣味,而是更想通過影像來表達思想和追求。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電影整體都呈這種狀況,那就是對藝術的追求和創新要遠遠大于對市場的欲望。”①轉引自饒曙光:《中國電影市場發展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402頁。進入21世紀后,隨著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國電影進入產業化時期。面對電影市場中的商業大片熱潮,藝術電影的生存空間岌岌可危,其聲音日漸被掩蓋,甚至消失在一片商業營銷中,如何被觀眾 “看到”成為這一時期藝術電影面臨的困境。2014年,電影 《白日焰火》在 “金熊獎”的加持下收獲億元票房,很多人認為藝術電影的春天已來臨。但是,《白日焰火》的成功首先倚靠其類型電影的外殼,其次來自廖凡、桂綸鎂等主演的明星號召力,它的成功并不具有普遍意義。事實證明, 《白日焰火》之后的國產藝術電影之路走得并不順遂。2016年,吳天明導演的遺作 《百鳥朝鳳》上映,首日票房27.7萬元,排片僅2%。制作人方勵的 “驚人一跪”為該片增加了話題熱度,隨之而來的是排片率的上升, 《百鳥朝鳳》最終以超過8500萬元的票房成為藝術電影的一個經典營銷案例。在這一話題的帶動下,藝術電影再次被大眾關注和討論。也是從這一年開始,中國電影市場逐漸被細化,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成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標志。
婁燁、王小帥、賈樟柯作為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縱觀他們的導演生涯,無不經歷了從 “地下”走向 “地上”,再面向大眾的艱難歷程。2015年,王小帥導演帶著電影《闖入者》回歸大熒幕,結果卻無法 “闖入”電影市場。同期上映的電影有 《赤道》 《何以笙簫默》 《念念》等。其中, 《何以笙簫默》從排片和票房上以壓倒性的勝利拔得頭籌;張艾嘉導演的 《念念》則和 《闖入者》一樣,陷入 “無人問津”的處境。最終,《闖入者》收入1005萬元票房, 《念念》收入1389萬元。2019年,王小帥的新電影 《地久天長》上映,在柏林電影節影帝影后之譽的助力下,最終票房為4471萬元。2014年底,婁燁的 《推拿》上映,票房為1285萬元。2019年,他帶著 《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回歸觀眾,經過一系列宣傳后,獲得6432萬元票房。《山河故人》是賈樟柯的第一部公映的作品,當時收入3010萬元票房。2018年,他為了宣傳新片 《江湖兒女》竭盡全力,甚至請 “101女孩”楊超越為其站臺,最終獲得9000萬元的票房。由此,藝術電影開始漸漸被更多的人 “看見”。但是,這一現象也從另一個角度體現出中國電影市場的非常態。隨著互聯網環境的變化,越來越多的投資和發行公司將重點放置在電影的宣傳營銷環節,藝術電影亦難逃這一命運。
面對嚴峻的電影市場,某些藝術電影選擇另辟蹊徑,結合現今觀眾的多元喜好和互聯網傳播,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鄭大圣導演的 《村戲》、范儉的 《搖搖晃晃的人間》等電影即屬于這一系列。它們依托大象點映這一平臺,實行眾籌放映,進行了對目標觀眾相對精準和長線的營銷,為藝術電影的生存探索出了有示范意義的新路。事實上,藝術電影面臨的嚴峻窘境在短時間內無法改變,尤其是那些成本低、知名度低的作品,在電影市場的流通階段,依然嚴重水土不服。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國產藝術電影文本呈現出多樣化特點, 《黃金時代》 《路邊野餐》《長江圖》《羅曼蒂克消亡史》《心迷宮》《八月》《不成問題的問題》 《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南方車站的聚會》《平原上的夏洛克》《冥王星時刻》等作品都從形式和內容上拓展了電影的表現空間,導演個人風格凸顯,這標志著當代中國藝術電影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曲高并非均要和寡,然而往往和寡,從某種意義而言,藝術電影最具代表性的特點決定了它們不被觀眾偏好的處境。如何讓它們被更多觀眾 “看見”,如何從被 “看見”到被“偏好”,是國產藝術電影當下面臨的難題。
二、國產藝術電影的困境:錯位與焦慮
(一)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宿命怪圈
無論是作為文本本身的藝術電影,還是作為電影傳播載體的藝術影院,幾乎在殘酷的市場面前都難以和主流的商業電影抗衡,最終往往陷入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怪圈中。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的負責人楊洋曾說過這樣一段值得玩味的話,有的藝術電影在宣傳發行時并不 “愿意”和藝術影院掛鉤,盡管如北京百老匯電影是品質電影放映地的代名詞,但是其放映活動背后隱含的意義是藝術電影與主流觀眾之間的割裂,如果在這里宣傳,則意味著失去 “大眾”。因此,穿著商業類型片宣傳外衣的藝術電影在具體營銷中往往贏了票房,失了口碑,電影 《地球最后的夜晚》即是如此。它的宣傳以抖音為主要平臺,在 “一吻跨年”的營銷口號下,預售票房高達1.5億元,首日票房甚至超過了2.6億元,這個驚人的票房數字確實令大多數藝術電影甚至商業電影望其項背。可是,第二日它的票房迅速下滑,縮水達95.7%,打破內地電影有史以來次日票房跌幅的紀錄。最終,《地球最后的夜晚》以2.82億元的票房結束了它的票房征程,其中2.6億元是首日票房。和電影宣傳時的高調相比較,電影的潦草下檔,則顯得異常落寞。從票房數字來看,藝術電影拿2.82億元的票房是一個新的紀錄,但是這一紀錄卻是扭曲電影市場的縮影。湯唯、黃覺在 《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用心演繹不敵觀眾的睡意,觀眾調侃 “地球最后的夜晚”變 “地球最困的夜晚”,批評其沒有底線的宣傳手段,對電影文本本身的討論卻少之又少。從 《路邊野餐》到 《地球最后的夜晚》,畢贛表達了個人對電影近乎自戀式的激情,可其晦澀的表達沒有在觀眾心中得到呼應。《地球最后的夜晚》以其粗放式的商業型宣傳令票房在短短幾天內被反噬,這一現象恰好說明了藝術電影和大眾之間存在的距離。當一部藝術電影變成一場鬧劇,它的中國式原罪也盡顯無疑。
傳統的商業電影宣傳模式貪多求大,藝術電影的宣傳生搬硬套只會引起觀眾的不適感。藝術電影的宣傳發行困境本質上由文化差異決定,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的鴻溝是難以被抹平的。賈樟柯導演曾說:“藝術電影最大的商業性就是藝術性”,可是將藝術“成功”轉化為實在的票房則異常艱難。“普通老百姓進電影院不是來消費文化的,他們先看的還是明星或者熱鬧,他們走進電影院主要的目的是消費電影的娛樂功能,消費電影中的社會話題。”①陳舊、陳剛:《類型片框架下藝術電影的營銷》,《當代電影》2014年第9期。《地久天長》中的王源,《風中有朵雨做的云》中的井柏然,為 《江湖兒女》站臺的楊超越,《南方車站的聚會》中的胡歌,均是吸引觀眾消費的符號。當偶像明星胡歌和流量明星李佳琦出現在同一直播間時,《南方車站的聚會》瞬間賣出25.5萬張電影票。可是,當大眾對電影的討論集中于胡歌的肌肉時,藝術電影的精神似乎被消解殆盡。如何保持正確的走路姿勢,是國產藝術電影面臨的困境。
曾執導電影 《巫山云雨》的導演章明和賈樟柯、婁燁、王小帥等導演同屬 “第六代”序列,相較于其他幾位,章明的 “邊緣感”更加持續和徹底。2018年底,他的新片 《冥王星時刻》上映,作為入選第7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 “導演雙周”單元的唯一華語作品,同時也是章明的第一部公映的大銀幕作品,在這部電影中,沒有流量明星,沒有鋪天蓋地的營銷,僅上映九天,最終以57萬元的票房收尾。盡管票房成績不盡如人意,在談到藝術電影的市場時,章明依然感到樂觀,從沒有資本到漸漸有資本開始主動找他,是國內藝術電影市場良性發展的結果。2019年12月8日,在第二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上,電影 《氣球》奪得最佳影片獎和最佳女演員獎,導演萬瑪才旦再次進入大眾視野。從 《靜靜的嘛呢石》《塔洛》到 《撞死了一只羊》《氣球》,萬瑪才旦始終鐘情于藏語電影的拍攝。如果說藝術電影的生存空間狹窄的話,那么少數民族語言的藝術電影則面臨更加艱難的處境。盡管之前有 《岡仁波齊》的成功營銷,但不可否認,“情懷營銷”和 “奇觀化觀影”是它戳中票房的根本原因,沒有廣泛的借鑒意義。不過,萬瑪才旦在談到觀眾、市場和票房的關系時,和章明導演樂觀的態度不謀而合,在他看來,現在的電影市場環境正在往好的方向發展。事實上,萬瑪才旦的作品從小眾的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進入 “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藏語電影從沒有任何市場到開始走入一部分觀眾的視野,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是中國電影市場向好的一個側影。但是,無法忽視的一個事實是,國產藝術電影會在較長時間內很難改變被冷遇的局面。大眾的觀影審美習慣不會一蹴而就,藝術審美源于感受力,電影的本質在于感受,而非理解,藝術電影尤甚。只有在良性的電影生態環境下,藝術電影才會得到更多的生存空間,才可以真正面向大眾。
(二)風格化的形式迷狂
從 《風中有朵雨做的云》 《地久天長》到 《地球最后的夜晚》《撞死了一只羊》《南方車站的聚會》,國產藝術電影中獨特的視聽語言往往帶來觀眾分裂甚至兩級的評價,其中多集中于對影片風格的推崇或消化不良。隸屬于 “第六代”的婁燁、王小帥、賈樟柯等導演的影片體現出共同的 “時代記憶”傾向。正如 《風中有朵雨做的云》上映時的宣傳語:“電影會幫助我們記住,我們和我們的時代”,時代成為 “第六代”的電影主題,命運的無常則成為其中的表達主旨。在時代的裹挾下,無論是堅守的人,抑或出走的人,都無法獨善其身,猶如持續搖晃的鏡頭一般,最終被洗禮為時間的灰燼。從拍攝 “地下電影”到向商業靠攏,“第六代”經歷了從獨立制片到完全合法化制片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的作品漸漸消解了敘事性,體現出對形式的迷戀。而這種形式的轉向,在畢贛、萬瑪才旦、刁亦男等導演的作品中,體現得更徹底。
和婁燁、賈樟柯等導演不同,刁亦男、畢贛等導演在執導筒伊始,出于電影作者的“游戲性”,在電影語言運用上具有高度的自覺性,對形式的注重直接在電影中表現為文本的跳躍性,這也是他們的藝術電影之所以被詬病的根本原因。如果說,民族和國家是“第五代”關注的敘事母題的話,第六代則大多聚焦于大時代下的個人情感和遭遇。到了畢贛等人,他們似乎在風格化和個人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他們的作品中,形式成為表達主旨的根本,深層的社會思考亦寓于形式的背后。以2019年上映的藝術電影為例,從年初的 《地球最后的夜晚》及至年末的《南方車站的聚會》,對形式的迷戀和探索,是近年來國產藝術影片的共同轉向,構成當下藝術電影生態的主要景觀。
從成名之作 《路邊野餐》到褒貶不一的《地球最后的夜晚》,畢贛作品中對 “夢”的追尋始終如一。他在 《路邊野餐》中的自我表達彌漫著一種隨意的野生氣質,這也是電影的迷人之處。及至 《地球最后的夜晚》,畢贛在形式上大膽創新,用2D轉向3D的革命性觀影經驗和一鏡到底的3D長鏡頭,試圖創造一種全新的電影結構方式,以一種超現實視角將觀眾帶入迷幻的夢境中。一直以來,“講故事”被認為是電影最重要的部分,人們對一部影片的評價也常常基于文本,這就導致電影中的表意功能往往被忽視。顯然,導演畢贛更注重從電影的視聽角度表現人物情感。面對觀眾對電影前后兩段中混亂的質疑,畢贛堅持認為 “如果前半部分像后半部分那樣流暢、準確、清晰的話,前半部分形式上的意義就會被大打折扣”①畢贛、李迅等:《源于電影作者美學的詩意影像與沉浸敘事—— 〈地球最后的夜晚〉主創訪談》,《電影藝術》2019年第1期。。然而,無法忽視的一個事實是,影片因敘事的斷裂和劇情的跳躍無法給予觀眾合理的想象空間,從而造成對文本本身理解的無法延伸。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電影美學傾向并不是僅存在于畢贛作品中的偶然性。作為一名藏語電影導演,從 《塔洛》到 《撞死了一只羊》,再到前不久剛獲獎的 《氣球》,萬瑪才旦從寫實進入寫意的維度,其作者性和風格化越來越突出。在 《撞死了一只羊》中,故事顯然不是電影的主體,無論是4∶3的畫幅,還是人物的刻意設置,抑或夢的營造,意在凸顯一種不安的荒誕感。正如那句藏語諺語所言:“如果我告訴你我的夢,也許你會遺忘它;如果我讓你進入我的夢,那也會成為你的夢。”觀眾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跟隨金巴進入他的夢中,經歷了一場朦朧的夢境旅行,旨在傳達 “世相荒誕,以夢慈悲”的意味。誠然,對形式的追求必然帶來敘事的語焉不詳,亦同時形成了某種風格。導演刁亦男說道:“風格是抵抗所有庸常和腐敗的武器。”《南方車站的聚會》集中體現了這種觀念及風格化的極致。從 《白日焰火》到 《南方車站的聚會》,刁亦男的作品里始終存在作者意義上的某種統一性。和 《白日焰火》相比較, 《南方車站的聚會》承襲了刁亦男一以貫之的黑色電影風格,卻在包括暴力表現等方面具有更多的儀式感。例如那柄雨傘在暴力鏡頭中呈現出的形式美,是導演故意為之的結果。影片的形式感體現出導演對形式迷狂的高度自覺,片中大量城中村的奇觀表現對敘事并沒有直接的影響,導演對這些閑筆的執著表現是其對形式迷戀的表征之一。如果說 《白日焰火》中的感情線依然有跡可循的話,《南方車站的聚會》中感情的不確定性則是阻礙觀眾進入其故事和接受故事的核心要素,對此,導演刁亦男坦言電影形式和內容的矛盾性。他認為,只有持對形式的警覺,才會完成對風格的追求。
從觀眾的經驗來看,感官愉悅往往建立在內容上,對形式的極致追求結果往往會造成內容的斷裂,這符合畢贛所指的 “詩的邏輯”②畢贛、李迅等:《源于電影作者美學的詩意影像與沉浸敘事—— 〈地球最后的夜晚〉主創訪談》,《電影藝術》2019年第1期。,符合刁亦男所說的 “激發理智”功能的原理,卻與觀眾閱讀電影的習慣相悖。恰如塔可夫斯基所言:“為了營造效果去拍攝一場美麗的戲,也的確并不困難……但是只要你朝那個方向跨出一步,你就迷失了。”③畢贛、李迅等:《源于電影作者美學的詩意影像與沉浸敘事—— 〈地球最后的夜晚〉主創訪談》,《電影藝術》2019年第1期。對形式的探索有可能會跌入畫地為牢的形式主義陷阱中,只剩下空洞的能指。電影的形式與內容之辨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當內容生產無法自由時,形式的轉向似乎變得順理成章。這種新的電影觀看方式需要觀眾在一定的理解力和接受力基礎上完成,對電影形式外的理解層次決定了對影片本身的認同程度。
三、中國藝術電影的發展策略:多維度與新景觀
(一)分眾時代下的跨圈層傳播
20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開始勃興,隨著它的不斷發展和普及,其對人們社會生活的滲透愈來愈深。在21世紀初的十年內,互聯網從不同層次對傳統媒體產生沖擊,隨之而出現的是移動互聯網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進而影響其思維方式。由此,傳統意義上的 “大眾”被解體,人們進入分眾時代。電影作為大眾文化,其與分眾時代無法有效匹配的矛盾凸顯出來。在此背景下,一種圈層文化現象逐漸形成,成為新型的社會結構方式。
在網絡中,人們會根據愛好、趣味本能選擇適合于自己的圈層,同時,圈層原初的區隔特點反過來鞏固其本身的偏好,隨著圈層輪廓越來越清晰,逐漸形成某種文化潮流和趨勢,建立小眾共同體,豆瓣、知乎等網絡社區成為圈層的主要聚集地。尤其在90后、00后逐漸成為觀影主要群體的今天,圈層文化進一步鞏固了電影分眾的局面,無論是藝術電影的放映,還是營銷,找到 “正確的”觀眾是首要問題。實際上,分眾化不僅利于藝術電影找到合適的觀影對象,也會促進商業電影在電影生態中找到更合理的位置。基于這一發展趨勢和電影創作的多元化,傳統的粗放式電影放映市場顯然已無法適應時代的訴求。無論是從區域性的上海藝術電影聯盟 (SAFF)、百老匯電影中心到輻射地區更廣的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還是從后窗放映到大象點映,藝術院線在政策扶持和民間行為的維度上,都獲得了長足發展,它們旨在找到藝術電影的觀眾,在分眾發行的基礎上,采用長線放映模式,在此過程中,藝術電影和藝術觀眾的關系會越來越匹配和穩固,從而挖掘出藝術電影的市場潛力。《岡仁波齊》《八月》《撞死了一只羊》《長江圖》《路邊野餐》《不成問題的問題》《老獸》等電影,即在這樣的放映機制下,被更多觀眾看到,在找到目標受眾的同時,也活躍了藝術電影市場。
但是,在圈層效應發揮作用的同時,也應警惕圈層的僵化。文化圈層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傳統的時空關系,圈層之間的關系類似于平行運行的宇宙之間的關系,加之大數據和算法推送的出現,其公共性更指向圈層內部,而非圈層之間。因此,適時地和適當地 “破圈”是藝術電影的重要生存策略,只有圈層之間的流動,才會帶來電影的多元化發展,否則將會掉進另一重狹隘主義中。從營銷層面而言,《地球最后的夜晚》盡管是一則失敗的營銷案例,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在商業營銷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一小部分觀眾,這也給予藝術電影在 “破圈”宣傳時一定的啟示。事實上,當李佳琦的“帶貨”直播成為一種現象時,傳統的營銷模式已不再占有優勢,藝術電影作為一種虛擬產品,在這種新的營銷模式中,如何找到更“對”的受眾,是國產藝術電影宣傳路徑的一個重要方向。近年來,小眾文化的 “破圈”現象并不只是局限于電影的范疇,民謠、嘻哈音樂、街舞、脫口秀等小眾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試圖突破原有的圈層。所以,國產藝術電影的宣傳在有效吸納核心觀眾的同時,應通過其他合理手段獲得更高的觀眾覆蓋率,實現跨圈層傳播。
(二)藝術電影 “自來水”的力量
2016年,國產藝術電影迎來了新的生機,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 (簡稱 “藝聯”)和大象點映平臺的建立標志著國產藝術電影進入全覆蓋的放映時期。在此之前,成立于2013年的上海藝術電影聯盟主要依托政策的扶持,在加盟影院中進行藝術片的常態放映,但是僅局限于少數影院。同年,“后窗放映”組織發起藝術電影放映活動,主要在上海、南京、廣州、深圳、成都等17個城市進行藝術電影的巡回點映。后期的“后窗放映”實際上是一條虛擬藝術院線,但是由于加入城市的限制,其放映活動依然屬于小眾范圍的放映活動。隨著時代的發展,觀影趨向日常化,數據顯示,觀影主體力量從之前的一線城市慢慢向二三線城市轉變。與此同時,商業院線在二三線城市的覆蓋更加廣泛,然而,藝術電影院線在這些地區卻相對處于真空狀態。按照分眾理論和圈層效應,藝術電影觀眾在這些地區有很大的發掘潛力,這也是“藝聯”和大象點映必然出現的原因。 “藝聯”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的支持下成立,其背后的主要支撐力量是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國電影資料館是國內藝術電影最早的官方運營單位,從1996年開始常規放映藝術電影,愛好藝術電影的觀眾去小西天看電影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節目。2016年10月15日,“藝聯”正式成立,旨在 “希望中國電影創作多樣化發展,群星璀璨;希望中國電影放映特色化經營,枝繁葉茂”①“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宣言,中國電影資料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https://www.cfa.org.cn/tabid/587/Default.aspx。。它的成立一定程度上標志著中國電影放映呈分眾化、多元化發展態勢,改變了藝術電影放映止于北京地區的局限性,為國產藝術電影提供了更多生存空間。截止到2018年11月,全國有1260家電影院加盟 “藝聯”。從 《海邊的曼徹斯特》的發行放映開始, “藝聯”不斷發展壯大,培養了眾多藝術電影觀眾,從而形成了國產藝術電影發展的良性循環。如果說 “藝聯”的形成和發展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政策扶持的話,那么 “大象點映”則通過 “自來水”的力量自下而上為藝術電影的發行放映開拓了新的路徑。
“自來水”一詞作為一個概念出現于電影《戰狼》的營銷上,主要指那些自愿為某部作品做宣傳的影迷。2015年,電影 《大圣歸來》在 “自來水”力量的助推下收獲近10億元的高票房,“自來水”一詞也因此被大眾廣泛使用。雖然,“自來水”作為概念始于商業片的宣傳,但是藝術電影的 “自來水”力量同樣不可小覷。尤其是近幾年,在互聯網的助推下,這一力量逐漸壯大和集群,成為藝術電影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大象點映平臺的創始人吳飛躍的另一重身份是紀錄片導演,他是紀錄片 《我的詩篇》的導演之一,從這個意義來說,他本身也是藝術電影的 “自來水”。吳飛躍對藝術電影面臨的 “難發行,發行難”困境有切身體會,因此大象點映平臺的建立初衷旨在突破發行局限,為國產藝術電影開辟新的生存空間。大象點映平臺的基本運營模式為 “一人發起,大家參與”,屬于眾籌觀影的一種。在這種放映模式下, 《村戲》《搖搖晃晃的人間》《冥王星時刻》《冬至》《出路》《八月》等多部藝術電影和紀錄片得以長線發行,表現出持續的生命力。除此之外,大象點映平臺還有包括 “百城首映禮”、超前點映在內的放映模式,并組織線下主創深度交流活動,在較快的時間內為電影找到最佳受眾,從而形成最早的口碑宣傳。電影 《村戲》上映前,吳飛躍在多個宣傳活動中提到該電影是一部 “特別挑觀眾”的影片,認為:“主流觀眾還沒有準備好去欣賞這類影片,它找尋的是對電影有要求的人,對現實處境有問號的人。”①何國威:《文學性與新時代藝術電影—— 〈村戲〉學術研討會綜述》,《電影新作》2018年第4期。由此,對藝術電影觀眾的 “尋找”和培養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百老匯電影中心作為國內最早開始運營的獨立藝術影院,滋養了最早的 “迷影”文化,培養了一批穩固的藝術電影 “自來水”觀眾。坐落于北京的百老匯電影中心于2010年成立,脫胎于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其經營模式與香港的百老匯電影中心類似,連同庫布里克書店構成北京獨特的文化交流風景線。它的成立初衷是為更多的人能夠看到藝術電影,因此為國產藝術電影開辟了新的生存空間。作為一個民間藝術影院,其自負盈虧的性質決定了它運營的艱難處境。于是,“百老匯”采取 “以商養藝”的策略,無論是在放映藝術電影的同時兼映商業影片,還是書店及電影周邊的經營,其目的都是為了使更多藝術電影進入觀眾視野。同時,其電影主題展映也是重要的藝術電影傳播方式之一,從成立之初開辦 “世紀的美麗與哀愁——阮玲玉電影回顧展”,到 “父輩的青春——謝晉電影回顧” “法國新浪潮回顧展”“臺灣文學電影展” “香港主題電影展”,再到2019年的 “北野武導演回顧展”“歐盟電影展”“日本動畫大師回顧展”,北京百老匯電影中心已走過十個年頭。此外,它還以策展放映、電影圖書館、b·SEE觀影團、影人專欄等其他形式吸引觀眾,使更多藝術電影可以在這里和觀眾見面。除了北京以外,另一家百老匯電影中心于2017年在深圳落戶,為藝術電影的發展注入新的生機和力量。實際上,隨著電影觀眾群呈 “下沉性”特點的聚合,百老匯電影中心的運營模式或許可以在其他城市被借鑒和轉化,為多區域的藝術電影 “自來水”構建文化交流空間。自媒體是互聯網發展最鮮明的表征之一,隨著微博等自媒體大V的形成,意見領袖擁有的話語權不可小覷,其 “觀影團”依舊主要來自“自來水”的力量。例如在電影 《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前,微博昵稱為 “次等水貨”的運營者做了一個跨年場觀影團活動,該活動和大象點映的類似,采取眾籌觀影模式,在全國19個城市同時進行,幾乎所有的電影票都售罄,以至不斷加場。
(三)媒介融合下的新景觀
在互聯網急遽發展的今天,電影的觀看實現了多樣性,除了傳統影院的展演形式,流媒體電影收看成為大眾的另一主要選擇方式。與此同時,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下,媒介融合的趨勢勢不可擋,電影和美術館、博物館的互動成為一種新景觀,形成新的文化場域。從藝術史的維度看,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技術的變革,當代藝術的出現打破了傳統藝術認知的桎梏,也模糊了藝術種類之間的分野和界限,藝術家的多重身份亦在斜杠式地轉換。
電影走進美術館、博物館可以追溯至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紐約,當時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建立了電影圖書館,以保存電影和展示電影為主要目的,并因此延展了電影的閱讀模式。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術館、博物館 “精英” “正統”的地位受到沖擊,這激發了電影保存和閱讀的形式變革,實驗性、先鋒性的電影開始出現,試圖重新定義電影的形式和意義。及至20世紀末,數字技術的發展和影像的普及化再次挖掘了電影的生命力,其實驗性為藝術電影拓延了生存空間的寬度。在美術館、博物館中,電影的放映形式有兩種:
一種是將美術館、博物館作為放映空間的相對傳統的形式,諸如 《塔洛》 《路邊野餐》《心迷宮》《清水里的刀子》《黑處是什么》《村戲》等藝術電影都曾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行過首映及映后主創和觀眾的座談。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作為電影放映的美術館重鎮,一直致力于藝術電影的推介,其中包括 “藝術家的電影”“四季影展”“新亞洲影志”等多個推介活動。正如中國電影資料館策展人沙丹所言,各個藝術影院的選片原則不盡相同,“尤倫斯”的選片往往會在滿足主流藝術影迷的基礎上 “再選擇一些非常小眾的、甚至一般人聞所未聞的作品”①《訪談錄:培育期的北京藝術電影放映》,微信公眾號:“幕味兒”,2014-09-15。,這樣的選擇盡管冒險,卻豐富了其文化層次,也是特定美術場館特有的文化經驗。
除了在放映空間中放映,電影和美術館結合的另一種形式則是將電影納入美術館、博物館的展示系統中,產生新的解釋行為。如果說藝術影院屬于商業院線外的小眾序列的話,那么美術館、博物館則提供了其 “再次小眾化”的閱讀模式。2002年以來,導演蔡明亮開啟了電影走進美術館、博物館的先聲,造型感和形式感成為其以這種方式展演的關鍵詞,傳統的觀看習慣和經驗在這一空間中被自然地消解,對電影的閱讀模式更加接近美術館、博物館的觀看經驗。傳統的電影觀看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觀眾在看電影時隱性的心理期待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電影觀看的自由性,美術館、博物館則賦予觀看行為更大的自由度和隨意感。顯然,這種媒介融合下新的電影觀看方式遠離了傳統的、主流的電影生產和電影語言,將電影的邊界推向另一個維度。
由此生出的問題是,影像裝置是否屬于電影的序列,例如,在2019年first國際電影節上引起爭議的影片 《動物方言》,全片的素材來自公共影像、照片等,摒棄了線性敘事,且使用聲畫分離的處理方式,是一部實驗性非常強的作品。面對這樣一部作品,即使是藝術電影觀眾也會產生觀影的不適感,普通觀眾則更自不必言,這似乎又回到那個原初的問題——何為藝術電影,或許這也正是今天討論藝術電影的價值所在。
(四)播出場域的復調多元:從影院放映到線上發行
盡管電影人使出渾身解數,卻依然無法改變藝術電影市場整體低迷的客觀事實。新媒體作為一種中介,將觀眾吸引進影院,是電影傳播的重要渠道。實際上,通過新媒體傳播,同時也產生了另一種電影的觀看方式。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重構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交行為,國內移動視頻用戶的數字已相當可觀,在線視頻市場亦發展迅猛,觀看付費視頻的習慣正在被接受和形成,這其中屬于藝術電影的觀眾力量值得挖掘,尤其是在大數據的力量下,屬于藝術電影的受眾會在觀看習慣的影響因素下,更快被找到和聚合。“柯首映”是電影和新媒體結合的產物之一,由導演賈樟柯作為主要投資人于2016年建立,是全球電影短片的首映平臺,以微信公眾號的形式運營,每周舉行兩部短片的線上首映,實現 “‘電影短片’和 ‘電影首映’形式在新媒體端口的一次相遇”①賈樟柯:《賈樟柯:108次短打》,微信公眾號:柯首映,2016-05-07。,是觀眾與藝術電影接觸的新平臺。另外,“柯首映”還與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知乎、騰訊等多個機構合作,旨在連接線上和線下,形成復調多元的電影傳播形式。
電影與新媒體的結合,還包括通過視頻網站傳播等。以愛奇藝為例,它作為較早感知到藝術電影生存困境的視頻平臺,首先以試水的姿態與 《路邊野餐》 《暴裂無聲》等藝術電影的出品方進行合作,主要以網絡版權采購的形式完成具體操作。2017年,愛奇藝直接買下了 《北方一片蒼茫》的版權,在平臺播出的同時,還將它推到 “全國藝聯”發行,使觀眾可以同時在線上和線下觀看該片。其后,《狗十三》 《四個春天》 《八月》等藝術電影仿效此法,都獲得了良好的收益。不過,其在具體影片的版權購買時,往往進行精準分析和差異化操作嘗試。例如 《四個春天》,愛奇藝并沒有采取一次性將版權費支付,而是采用單點付費和分賬的方式播出此片。時至2019年,在 “first影展”奪得最佳劇情長片和最佳導演的 《春江水暖》也在和愛奇藝嘗試合作發行,網絡發行逐漸成為藝術電影的又一生存渠道。
縱觀國產藝術電影的發展,它作為電影生態的一部分,和商業電影的發展形態關系始終關聯。由一個國家或地區藝術電影的現狀,可以看出其整個電影生態的成熟度和發展態勢。2020年, 《第十一回》 《詩眼倦天涯》 《氣球》 《拉姆與嘎貝》 《少年與海》《第一次的離別》 《春江水暖》 《英格力士》《鳥鳴嚶嚶》《熱湯》《不浪漫》《平原上的摩西》《椒麻堂會》《回南天》《蘭心大劇院》等國產藝術電影將陸續上映。提高藝術電影的傳播量至關重要,但同時要注意到,這并不是使藝術電影走出陰霾天的根本方法。在當今行易知難的時代,藝術電影自身的造血功能非常關鍵,如何恰當地處理好藝術電影、藝術影院、藝術電影觀眾三者的關系,使大眾在以往草履蟲式的觀影經驗中,重新獲得思考的能量,是中國藝術電影可行的未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