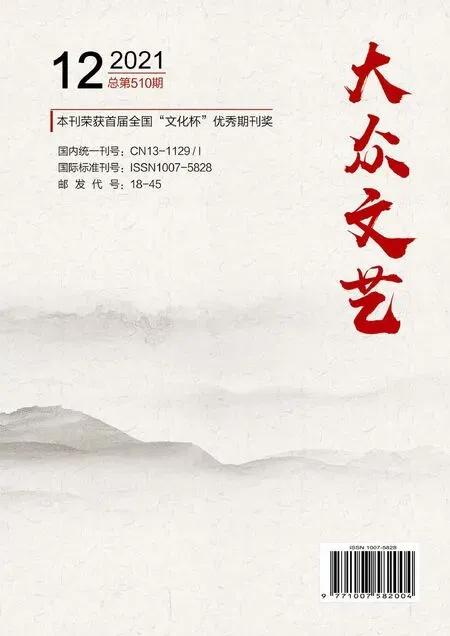制器尚象
——談遼瓷仿生造型
(內蒙古師范大學,內蒙古呼和浩特 010000)
一、前言
遼代陶瓷在中國陶瓷史中占有重要的篇幅,具有鮮明的契丹民族造型風格,在結構形式方面也獨具匠心。同時,契丹人運用其觀察、思維和設計的能力,對自己在游牧過程中、與自然相處中產生強烈關系的事物進行模仿,并對其進行改造,出現了許多運用仿生手法制作的器皿造型,達到“寄物以情”的目的,體現了契丹人“天人合一”的造物觀。遼瓷仿生造型中模仿對象的選取與遼代社會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這也是遼代陶瓷仿生造型的獨特性。契丹人運用“象形取意”的方法將生活中的元素加入器皿設計中,這是一種原始的、本能的創造,遼瓷仿生造型的設計結合了對被模擬事物的觀察、感受、內在含義,既有功能又有寓意,體現了制器尚象的造物觀,也是契丹人的文化與自然達到高度統一的體現。
二、遼瓷仿生造型中的“象”
“象”一詞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形象,《系辭傳》說:“象也者像也”,意思是“象”是宇宙間眾生的傳神寫照,是根據人們對自然現象和生活現象的觀察與模仿,從而創造出來的。二是意象,即寓意之象,在《易傳》中提出了“觀物取象”,延伸出著重再現事物的內在特性,表現深奧微妙的寓意。轉化到造物方面,仿生設計中的象生器一詞,其中的“象生”即指模仿生物,是人通過對自然之物改造,創造出的器物,也是“象”這一概念在器物設計中的具體體現。仿生造型中的“象”不僅是對形象的模擬,還有對形象內在特性的再現。遼瓷仿生造型中的模仿對象不僅包括有生命的生物,比如花、樹、魚;還包括了無生命的人造物,比如皮囊壺、神話動物等,且都有各自的制器寓意,遼代陶瓷的仿生設計在對事物的直接感受上進而概括、創造,按照形態的基本分類可以分為具象仿生和抽象仿生兩大類:
具象仿生即把被模仿對象以最直觀的方式呈現出來,并附加一定的實用功能,模仿的類型包括自然界中的事物以及人造物,具象仿生一定是在具備了一定的形態把控能力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因物賦形,給人以直觀的感受,也是遼瓷中所占比重較大并且風格極具契丹特色的一類。雞冠壺,遼瓷中獨樹一幟的雞冠壺,形制取材自皮囊壺,其釉色也有仿皮的肌理質感,色調和光澤度的呈現與皮的質感別無二致。早期的雞冠壺保留了完整的皮囊壺形制,并且對皮頁縫制的肌理也進行復原,較有代表性的雞冠壺有綠釉劃花塑貼火珠雞冠壺(圖1),藏于遼寧省博物館,在壺身泥片拼合處甚至可見針腳,與原本皮囊壺不同的是,添加了塔式蓋、雙孔系,并做底足,在保留游牧風格的同時,結合日用瓷的使用需求,方便置放。在雞冠壺的細節裝飾上也有仿生設計的體現,如科右中旗遼墓出土的綠釉雕塑龍粱雞冠壺(圖2),在壺的環梁上,將龍的身子轉化成了雞冠壺的提梁,頗具巧思。雞冠壺寄托了契丹人對游牧生活的感情,映射出一種對過去生活的懷舊情緒,遼代工匠對皮囊壺形態的仿制也是對皮囊壺功能的復制,皮囊壺一直用于儲存水、酒、奶,而根據此制作的雞冠壺的功能也是儲存這些東西,所以在器型的體量上像儲存器的體量靠攏,且因為便于放置的原因,通常比皮囊壺的存儲量更大,保質時間更久;摩羯壺,摩羯在印度神話中代表“河水之精”,與佛教一同傳入我國,至遼代,其形象已經逐漸定型。摩羯造型的陶瓷器皿在遼代出土很多,如1976年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烏蘭套海蘇木出土的白釉人首摩羯形壺(圖3),壺身是魚形,流部為龍形,魚背處有注水口,宛如花瓣,和魚身相得益彰,魚身前方是一女子,手持龍形流口,從造型到構思都稱得上是遼瓷中的代表作。在象征意義上,筆者認為,一是摩羯法力無窮,具有祈福的意愿,這樣吉祥且有崇拜色彩的形象便自然而然地運用到造型設計中。二是其形象猶如大魚,從河中而生,仿佛可吞噬一切,作為壺的造型元素具有水源源不斷用之不竭的意味;龜形壺,1989年內蒙古寧城縣天義鎮郊區出土的遼代三彩龜形壺(圖4),這件龜形壺龜首上仰,龜嘴留一壺口,前后都用穿孔,方便攜帶。是宋遼時期較為流行的款式;鴛鴦壺,鴛鴦在契丹人生活中是很常見的鳥禽,以鳥獸為造型的器皿從原始社會就有,遼代瓷器中以鴛鴦為題材對象的也不在少數,1977年內蒙古赤峰松山區遼代墓葬出土的三彩陶鴛鴦注壺(圖5),這只注壺腹部為容器,鳥身背部留一口,口部稱花狀,鴛鴦頭部為流,腹部還有蓮花裝飾,羽翼形態逼真,栩栩如生。以鴛鴦為題材的仿生造型體現了遼代人對自然之美、生活之美的追求,鴛鴦又有象征幸福,出雙入對的寓意,將這樣的形象轉變為實用器,可以給當時的人們以平和恬淡的感受。
抽象仿生將復雜的模仿對象逐漸提煉概括,復歸于樸,抽象仿生不像具象仿生那么直觀,需要人們的聯想補充,遼瓷中的抽象仿生造型多模擬常見的花卉,比如八曲海棠長盤,遼代三彩海棠長盤出土非常之多,且海棠長盤的形制只見于三彩器物上,如遼寧省新民縣遼墓出土的三彩海棠長盤(圖6)遼代工匠借鑒金銀器造型中的海棠盤樣式,深入提煉概括,將三彩長盤中的海棠花凝練為四角尖尖的口沿、流暢的花瓣曲線,富有張力,高度體現了遼代工匠的造型概括能力。

三、遼瓷仿生造型與契丹社會文化
《文心雕龍·詮賦》中提到“情以物興”,“物以情觀”。仿生設計最大的優勢在于可以令使用者實現“睹物思情”“物我交感”,這也是中國傳統造型設計中的一個常用的手法。創作者運用一些外部的符號或者帶有寓意和寄托的物象,從而把自身的情緒傳達出去,所以模擬離不開對被模擬事物原有的情緒感受。古代仿生設計的萌芽都遵循著一定的造物文化背景,契丹人自古與大自然為鄰,蘇頌的《契丹帳》寫到“行營到處即為家,一卓穹廬數乘車。千里山川無土著,四時畋獵是生涯。酪漿羶肉夸希品,貂錦羊裘擅物華。”以及契丹的捺缽習俗、漁獵方式,向我們生動地展示了契丹人生活起居方式。花草、游魚、牛羊鹿昔日與之為伴,帶給他們的感官豐富的體驗,與之相關的形態、審美感受在心中潛滋暗長,也成為他們精神世界里不可缺少的養料。
契丹人自古“馬逐水草,人仰湩酪”,并且“食牛羊肉酪而衣其皮”,可見皮制品在契丹人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以皮為原料做成的皮囊壺不僅方便攜帶而且具有很好的儲存奶制品等液體的效果。契丹人建國后,逐漸放棄了靡有定居的生活,并且開始學習中原工匠的制瓷技術,大量生產精美瓷器,可以推測最開始中原的制瓷工匠為迎合遼統治者的審美趣味,皮囊壺造型作為契丹人傳統的日用器很自然地就應用到了陶瓷設計中,從而創造了獨具契丹特色的雞冠壺。這種仿皮囊壺裝飾的處理與契丹人對游牧生活的依戀十分契合,代表了契丹人的民族文化,因此在遼代燒制不絕。除了皮囊壺外,捺缽文化也對遼代仿生造型有很大影響,契丹人四時捺缽習俗由來已久,從徐昌祚的《燕山叢錄》可窺見:“漷縣西有延芳淀,大數頃,中饒荷芰,水鳥群集其中,遼時每季春必來弋獵。”此處的每年春天必來弋獵就是指的我們所說的春捺缽,遼人在外時常見到游魚、鴨鵝,所以遼瓷中不乏見到這些題材的裝飾,比如鴛鴦注壺的出土地赤峰松山區,就是遼代人春捺缽弋獵時的主要地帶,古時為遼上京,《北蕃地理》記載“東至長泊十五里,西南至上京二百里……泊多野鵝鴨,戎主射獵之所。”可見鴛鴦注壺在此地的出現與春捺缽的文化背景不無關系。遼瓷的仿生造型也有受漢文化的影響。遼與宋同時期占據南北方,期間有對立也有和平,不可否認的是文化交流不絕如縷。對于這一時期遼地流行龜形壺而言,雖然其具有和扁壺類似的形制,有實用性因素,但是遼代工匠是如何產生模擬烏龜的形態運用到器物造型中的想法?在中原地區,烏龜自古就為四靈之一,《宋書·符瑞志》也有記載:“靈龜者,神龜也,王者德澤湛清。”印證烏龜有祥瑞神獸的寓意。同時,烏龜作為道教神物,其紋飾在遼代出土物中也所見良多。遼代境內有不少來自中原地區的漢人生活在此,所以根據不同地區文化實行“因俗而治”,同期契丹人也廣泛學習漢文化,對于宗教文化的吸納也采取兼收并包的政策,這讓道教在遼域內得以廣泛傳播。由此可見,烏龜作為祥瑞、神物這樣的概念應該也被遼代人所廣泛接受,且龜形壺的形制符合游牧民族一貫的使用需求,可以推測是遼代盛行龜形壺的原因。
四、結語
契丹人作為游牧民族,有與自然相融的天性,對于身邊自然物的模仿是其與自然長期相處的必然結果,遼瓷仿生造型的模仿對象也隨著遼代社會的發展、工藝的精進不斷豐富。遼瓷工匠的仿生設計一方面體現了“功用至尚”的樸素傳統功能主義觀念,另一方面從遼瓷器物中不僅可以看到遼瓷中的仿生造型體現了其精妙的功能性、裝飾美特征以及文化象征的寓意,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的物化符號,從中可以感受到遼瓷造型帶來的巨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