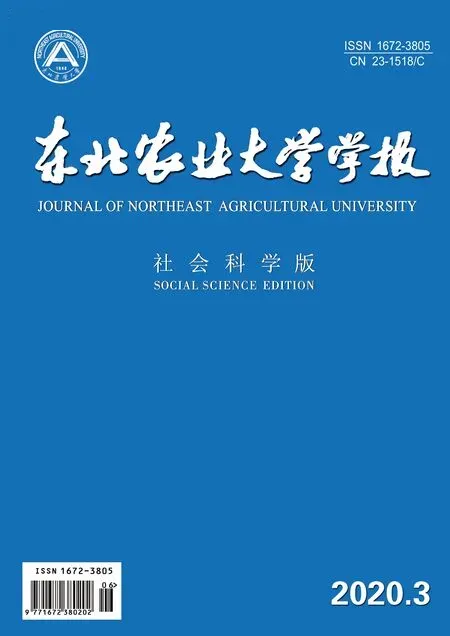數字普惠金融減貧效應存在空間異質性嗎?
——基于空間計量模型的實證分析
王剛貞 陳夢潔
安徽財經大學,安徽 蚌埠 233030
引言
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新時期做好“三農”工作總抓手。農村地區是中低收入人群和貧困人口集中地,中國社科院報告顯示,我國有近7億農村人口因傳統金融機構服務“最后一公里”問題導致金融需求無法滿足,“三農”金融缺口逾3萬億元①中國社會科學院:“三農”互聯網金融藍皮書:中國“三農”互聯網金融發展報告(2017),中國社會科學院,2018年5月11日。,合理金融需求被抑制。金融供需求不均衡是制約農村金融“普惠化”最大障礙,加之風險規避與逐利特點,資本較難流入農村地區,致使區域性貧困未完全破解。
普惠金融是為農村貧困人口、小微企業等社會群體有效提供融資產品和服務的體系,相較于傳統金融,普惠金融更強調服務對象包容性、服務方式便利性、服務內容同質性及商業模式可持續性。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普惠金融融合數字技術,提升金融服務便捷度和可獲得性,緩解融資約束和金融排斥,促使“三農”政策落地。
金融發展減貧效應是重要研究課題。研究觀點可歸納為:一是金融發展帶來積極減貧效應。阿馬蒂亞·森認為貧困歸因于缺乏權利與能力,保障貧困群體獲取金融服務的權利將有助于減貧[1]。反之會加大區域經濟發展速度和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減貧[2-3]。二是金融發展減貧效應十分有限,甚至存在負面影響。Arestis等人認為資金流入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部門不利于優化資源配置,貧困人口收入進一步減少,加劇貧困[4],加之金融“逐利”特點,貧富差距將加大[5-6]。
已有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可通過提高覆蓋廣度、增加金融服務可獲得性等提升減貧效應[7-8],但不同區域和群體減貧效應存在差異。如Kondo等指出普惠金融更有助于輕微貧困家庭減貧,對極端貧困家庭減貧效應并不明顯[9]。朱一鳴、王偉指出普惠金融緩解縣域低收入群體信貸約束程度有限,高收入居民獲益更多[10]。王剛貞等人運用門檻模型驗證普惠金融減貧效應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制約[11]。故普惠金融發展可改善金融資源分配不公現象,但減貧效應可能存在異質性。
信息通信技術和互聯網蓬勃發展為數字化金融服務提供極大便利[12]。部分學者認為城鄉收入隨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逐漸收斂,達到減貧效果[13-14]。黃倩等從收入增長和分配視角驗證數字普惠金融具有良好減貧效果[15]。張子豪等運用空間計量模型驗證數字普惠金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機制,認為減貧效應受本地區及周邊地區普惠金融發展影響[16]。
綜上,由于現實稟賦及地理環境制約,數字普惠金融減貧效應存在異質性。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時間序列數據模型和普通面板數據模型,忽視空間同質性假設的缺陷。鑒于此,本文采用空間計量模型研究數字普惠金融減貧效應空間溢出作用。結合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衡量31個省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利用2011—2018年省級時空面板數據測度數字普惠金融空間相關性,實證分析其減貧效應空間異質性。
本文貢獻在于:第一,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更貼合我國現狀,研究其空間分布相關性對推進我國普惠金融數字化建設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第二,空間杜賓面板模型可綜合時空雙維度數據,令研究結論更精確。第三,運用靜態和動態模型從長短期兩個角度研究數字普惠金融減貧效應直接與間接影響,分析不同時期空間溢出效應,有助于明確數字普惠金融未來建設方向。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數字普惠金融是在成本可控、模式可持續前提下,以數字化技術為實現條件,為農村貧困群體等社會各階層提高服務,擴展“三農”金融服務覆蓋廣度。縱觀國內外研究成果,數字普惠金融分布具有空間相關性,其減貧效應顯著且具有空間異質性,可輻射周邊地區。
(一)數字普惠金融空間相關性理論假說
數字普惠金融空間相關性已有部分研究成果。郝云平等人運用空間自回歸模型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空間相關性及減貧效應在不同地區具有異質性[17]。徐敏運用變異系數和Moran’s I指數得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逐漸趨向高水準統一,存在空間集聚現象[18]。吳金旺指出數字普惠金融水平整體提升且各省差距逐漸縮小[19]。胡宗義等人利用Kernel密度估計法分析中國普惠金融發展動態演進過程,認為普惠金融具有顯著空間相關性且絕對收斂[20]。綜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打破空間維度限制,與周邊省份交互影響。
假說1: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存在顯著空間相關性,局部傾向于集聚分布,且存在冷點區域。
(二)數字普惠金融減貧效應理論假說
數字普惠金融減貧效應可從宏微觀兩個層面敘述,其作用機理如圖1所示。從宏觀層面看,數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推動經濟增長,縮小收入差距,提高貧困地區就業創業機會。Oliver Wyman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可推動印度尼西亞等國GDP增長,促進低收入人群增收10%[21]。國內學者普遍認為,提升數字普惠金融水平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16]。張勛等指出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農村家庭收入,促進家庭創業,實現減貧效應[22]。
從微觀層面看,數字普惠金融可降低農村貧困群體金融服務門檻,緩解發展生產、教育醫療、平滑消費等多維流動性約束。楊艷琳提出農村普惠金融可提高該地區金融產品和服務可獲得性,改善農村人口貧困程度[23]。部分學者提出數字普惠金融對平滑城鄉居民消費有明顯促進作用,使低收入家庭擺脫貧困[24]。此外,普及數字普惠金融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長期顯著促進作用,為減貧效應打下堅實基礎[25]。綜上,通過宏微觀雙路徑,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長尾人群”擺脫貧困。
假說2:數字普惠金融具有顯著減貧效應,其減貧效應隨數字普惠金融水平提高而增強。
(三)數字普惠金融減貧空間異質性
根據地理學第一定律,各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可能相關聯。國內學者利用不同方法探析數字普惠金融減貧效應空間異質性特征。呂勇斌、肖凡基于縣域面板數據和空間誤差模型證明普惠金融具有“倒U型”減貧曲線[26]。錢鵬歲、孫姝認為提高數字普惠金融水平可降低本地區及周邊貧困程度,即數字普惠金融對周邊區域有正向空間溢出減貧效果[27]。汪曉文等認為普惠金融減貧效應存在異質性,呈現東強西弱區域特點[28]。綜上,由于地理位置、信息、資本、技術等存在異質性,各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相互依賴,其減貧結果存在空間溢出效應。
假說3:數字普惠金融減貧效應存在空間異質性,發達地區可通過空間傳導機制輻射周邊地區,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二、模型、變量和數據說明
為驗證上述假說,本文選用2011—2018年31個省份相關數據,測算數字普惠金融莫蘭指數和Getis-Ord指數,使用LISA聚集圖探析其空間分布特征;采用空間杜賓模型綜合時間空間雙維度信息檢驗數字普惠金融減貧效應顯著性;構建動態空間杜賓模型,在考查被解釋變量時空滯后項基礎上,探究長短期減貧效應,進一步比較減貧效應空間溢出情況。
(一)計量模型設定
1.空間權重矩陣。本文以中國31個省份(除港澳臺)為研究對象,省份i與省份j有共同邊界,則wij為1,反之wij為0,形成31×31空間權重矩陣W1。其中,按慣例假定海南省與廣東省相鄰。
2.空間相關性檢驗。空間面板數據中若某一特定指標高-高值或低-低值相聚集,則具有“正空間自相關”,反之為“負空間自相關”。運用“莫蘭指數”(Moran’s I)測度空間相關性,表示如下:
Getis and Ord提出的“Getis-Ord指數G”可辨別“熱點”(高-高值地區聚集)與“冷點”(低-低值地區聚集)區域。G*指數標準化后服從漸近標準正態分布,若G*值大于1.96,空間自相關且為熱點區域的概率為95%,反之為冷點區域。表示如下:
3.空間計量模型。本文選用空間杜賓模型(SDM)、空間自回歸模型(SAR)和空間誤差模型(SEM)三類空間計量模型。其中,SAR衡量被解釋變量空間溢出情況;SEM測量擬合誤差項空間效應;SDM檢驗以上兩種情況。空間模型形式如下:
當θ=0時,模型(1)簡化為SAR模型;當θ+δβ=0時,模型(1)簡化為SEM模型。POVit為模型被解釋變量,表示t年i省貧困率;IFIit為核心解釋變量,衡量t年i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X1為控制變量向量;μ1為個體固定效應;λt為固定時間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n為樣本數31。δ、β1、β2、θ1、θ2為待估參數,δ為各省貧困率空間溢出效應強度;β1、β2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和模型控制變量的直接效應系數;θ1、θ2為空間溢出效應系數。
動態空間杜賓模型在靜態模型基礎上納入變量時間空間滯后項,可同時解決內生性、時間自相關性和空間依賴性問題,使模型估計結果更加精確。模型設定如下:
POVt=τPOVt-1+ηWPOVt-1+δWPOVt+βX+θWX+vt
其中,X為31×7向量,由核心解釋變量(IFI)與 6個控制變量(LNPGDP、GAP、CZH、CE、TO、EDU)構成,參數γ、η為被解釋變量一期滯后項對當期解釋變量的直接影響和空間溢出影響系數,同時將解釋影響分為長短期效應。模型(2)可改寫為:
對X向量第k個解釋變量對應的POV期望值求其偏導,視作短期效應,表示如下:
(二)變量說明
本文相關變量如表1所示,借鑒肖挺研究方法,以民政部門公布的各省農村低保人數與農村總人數之比評價減貧成果[29];核心解釋變量為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18),表示各省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由于致貧因素較多,引入以下六個控制變量提高實證結果精準度。
1.被解釋變量(POV)。選取各省農村低保人數與農村總人數比值衡量貧困率,反映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度量數字普惠金融減貧效果。
2.解釋變量(IFI)。以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表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指數涵蓋數字金融覆蓋廣度、使用深度、數字化程度3個綜合指標,細化指標如圖2所示。

表1 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3.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LNPGDP)衡量各省份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城鄉收入差距(GAP)以各省份泰爾指數衡量城鄉收入差距;城鎮化率(CZH)衡量城鎮化進程對貧困率影響;財政支出規模(GE)衡量政府支出規模對貧困作用;貿易開放水平(TO)表示進出口水平的貧困率效應;受教育程度(EDU)衡量本專科教育普及率對貧困緩解程度。
(三)數據說明
本文以2011—2018年31個省份時空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統計性描述如表2所示。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數字普惠金融空間相關性分析
1.全局莫蘭指數檢驗。運用Stata軟件對2011—2018年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貧困指數空間作相關性莫蘭檢驗。
由表3可知,大于0表示在1%顯著性水平二者均具有顯著正向空間相關性,擁有全域范圍性空間集聚效應。即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及貧困率的空間自相關均得到驗證,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實證分析較為合理。

表2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3 全局莫蘭指數統計值
2.局部莫蘭指數檢驗。由于全局Moran’s I無法度量特定區域空間集聚情況,本文利用局部Moran’s I和LISA聚集圖分析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和貧困指數省際分布特征。Ii>0,LISA落于第一象限(高—高區域)和第三象限(低—低區域)內,即存在正空間相關性;Ii<0,LISA處于第二象限(低—高區域)和第四象限(高—低區域),即空間負相關。本文以2011年和2018年為例作局部空間自相關性分析。
從圖3可知,2011年和2018年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分布基本一致,多數省份落在第一、三象限,約占總樣本79%,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高水平集聚和低水平集聚。2018年除經濟較發達的中東部地區外,湖北、山東、安徽等省份也進入高—高聚集區域,說明這些省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態勢良好,并帶動周邊地區發展;低—低聚集區較2011年分布更集中,且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區。
從圖4可知,2011年和2018年貧困率落入第一、三象限占比82.3%,低—低聚集區主要為中東地區,高—高聚集區多為西部欠發達地區。即各省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貧困指數均存在較顯著空間集聚效應,東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較快并促進鄰省,西部地區及鄰省貧困率較高。
3.“Getis-Ord指數G”檢驗。對2011—2018年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和貧困指數空間相關性作“Getis-Ord指數G”檢驗。
根據檢驗結果可知,G均小于-1.96,可在5%水平上拒絕數字普惠金融無空間自相關性假設,總體呈顯著空間相關性,局部傾向于集聚分布,即存在正向空間相關性和冷點區域。
(二)數字普惠金融減貧效應分析
采用省份為聚類變量的聚類穩健標準誤,結果如表4所示。
靜態空間面板杜賓模型的回歸結果見表5。spatial rho系數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采用空間杜賓模型分析較為合適。表5中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與貧困指數主效應系數為負數,說明數字普惠金融可有效降低貧困率,減貧效應隨數字普惠金融水平提高而增強。數字普惠金融可整體減緩貧困,但空間溢出效應會抵消部分直接減貧效應,說明隨著數字技術發展,數字普惠金融跨越地理界限產生“涓滴效應”,影響周邊地區貧困水平。

表4 數字普惠金融減貧效應模型設定檢驗
(三)數字普惠金融減貧空間異質性分析
動態模型同步考慮貧困指數時間和空間滯后項,體現模型變量長短期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采用偏誤修正的動態空間杜賓模型重新估計樣本數據,結果如表6。其中,貧困指數時間一階滯后項系數為0.8724911,且在1%水平下顯著,即減貧效應具有持續性,上期貧困程度會對本期產生一定影響。

表5 靜態空間杜賓模型的估計結果

表6 動態空間杜賓模型估計結果
將動態空間杜賓模型分解為長短期效應,分解結果如表7。由表7可知,分解后減貧效應系數并不顯著,提高數字普惠金融水平在長短期均可直接減緩本省貧困,但長期間接空間溢出效應逐漸萎縮,甚至產生負面影響,歸因于各省金融資源仍存在競爭關系。間接效應不利于減緩貧困歸因于中西部幅員較為遼闊,其整體性貧困未完全破解,空間溢出效應不利于東部省份經濟發展。
從控制變量來看,提高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城鎮化水平及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長期均具有正向減貧效應,提升政府支出水平短期總效應在5%水平下顯著為正,不利于減貧。歸因于提升政府支出會加劇通貨膨脹,導致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另外,我國農民多從事農業或家庭小規模生產,產業鏈較短,進出口貿易量激增將擠占我國農產品市場份額,對減貧效應產生負面影響。
(四)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結論穩定性,替換被解釋變量及回歸方法,最大程度緩解結果差異。通過Husman檢驗后確認選用固定效應(FE),回歸檢驗方法選用空間自回歸模型(SAR)和空間誤差模型(SEM),被解釋變量替換為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指數,結果見表8。數字普惠金融項系數符號不變,Z檢驗均通過,減貧效應依然存在。故本文結果并不受回歸方法及指標影響。

表7 動態空間杜賓模型估計結果的分解效應

表8 穩健性檢驗估計結果
四、基本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莫蘭指數、LISA聚集圖和動靜態空間杜賓面板計量模型對2011-2018年31個省份數字普惠金融空間相關性及減貧效應空間作異質性分析,研究表明:
第一,全國數字普惠金融水平總體呈上升態勢,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和貧困水平存在顯著正向空間相關性,具有空間聚集效應和顯著冷點區域。
第二,數字普惠金融可顯著破解區域整體性貧困;數字普惠金融空間溢出效應會抵消部分直接減貧效應,即隨著數字技術發展,數字普惠金融跨越地理界限影響周邊地區。
第三,數字普惠金融長期間接空間溢出效應逐漸衰落,甚至對減貧有負面影響,歸因于各省金融資源存在競爭,長期來看仍需發展本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實現減貧目標。
第四,提高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城鎮化水平及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在長期均具有正向減貧效應,但政府支出、進出口比率對減貧效應影響并不明顯,說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凸顯,數字普惠金融政策需進一步升級。
綜上,研究結果驗證了本文三個假設合理性。
(二)政策建議
數字普惠金融可降低金融服務成本和門檻值、拓寬金融服務覆蓋面,滿足貧困人口資金需求,但需因地制宜制定特色化數字普惠金融政策,適應其空間異質性。結合上述結論,提出政策建議如下:
第一,加強區域合作,充分利用數字普惠金融空間輻射作用,擴大金融服務范圍。利用其空間聚集效應實現技術、市場、資本等資源共享互通,形成中心輻射區域。對于東部地區,著力提升金融產品及服務創新能力,提高數字化金融服務可獲得性。對于中西部,由于經濟基礎薄弱,缺少開發式扶貧,應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政策激勵金融機構向偏遠農村及金融發展滯后區域增設網點,提高網點覆蓋率,有效提高中西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
第二,著力提升貧困群體金融素養,加強消費者保護和宣傳教育。將能力扶貧與教育扶貧相結合,構建多元化數字普惠金融教育體系,提升減貧效果。首先,在欠發達地區推進數字技術建設,提高數字技術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解決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問題,使“長尾人群”享受優質金融服務。其次,金融機構積極革新數字化金融服務,探索低門檻、高效率數字金融服務,提高用戶忠誠度。最后,政府適當增加資金投入,加速偏遠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破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增進人民福祉。
第三,依據區域特征實施異質性瞄準機制,提高長期減貧效應精準性。依據各省貧困程度及地理條件選擇適宜金融機構輔助扶貧開發,形成“政府前瞻指引,市場自發運行”雙輪驅動機制。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打破潛在金融壁壘,進一步釋放數字普惠金融減貧空間異質性,實現鄉村振興和全面脫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