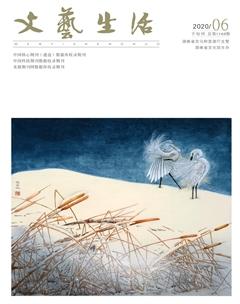“自我與傳統”矛盾背后的時代悲痛
劉銀求
摘要:穆旦是中國現代新詩史上一顆熠熠生輝的明珠,其詩具有鮮明的現代性以及強烈的主體意識。《鼠穴》一詩,使用了反諷、意象壘砌、矛盾修辭等手法,描繪了在如“鼠穴”一般的封建社會中被扼殺人性、庸碌麻木、明哲保身并異化為“老鼠”的現代青年人的猥瑣之態,表達出詩人內心對于“自我與傳統”矛盾的折磨人的痛苦,流露出深沉的時代悲痛。
關鍵詞:自我;傳統;時代悲痛
中圖分類號:11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20)18-0014-02
穆旦,本名叫查良錚,是中國現代詩歌史上極為重要的人物。他與何其芳的詩歌作品于1952被編選入《世界名詩庫》,可謂是“世界級”的華人詩人。穆旦處于社會變革與戰亂頻發的時期,經歷坎坷。生于“書香門第”世家,他自幼就接觸古典文化,且在少年時期就已開始詩歌創作。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穆旦隨校南遷至昆明。西南聯大時期,他受到了英美現代派詩歌的影響,其現代主義詩歌創作逐漸成熟起來。
穆旦的詩歌是帶有清晰的主體意識的,這種自我的重新覺醒與五四新詩喚起人的覺醒具有一致性。“五四”給中國帶來了啟蒙精神和個性主義,但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文化過于強大,使得人性“永遠被圍在百年前的夢里,不能出來”,廣大民眾繼續受著封建主義的壓迫,“五四”個性解放精神二十年米并沒有改變民眾愚昧、懦弱的精神狀態,穆旦意識到了這一點,“黑暗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是誰,誰噬咬它受了創傷?”(《野獸》)。這個社會依舊還是“吃人”的社會,而“被吃”的廣大國民卻在這個如“鼠穴”一般的社會中茍且偷生,麻木庸碌。穆旦作為新一代青年意識到了自我與傳統的矛盾,他意識到“我們已是被圍的一群”,他對傳統與集體有著懷疑、反抗精神,卻又實實在在的受到傳統勢力的桎梏,隱藏在背后的則是巨大的時代悲痛。
下面以對其名作《鼠穴》一詩的細讀米作具體分析:
我們的父親,祖父,曾祖,
多少古人借他們還魂,
多少個骷髏露齒冷笑,
當他們探進豐潤的面孔,
計議,詆毀,或者祝福,
雖然現在他們是死了,
雖然他們從沒有活過,
卻已留下了不死的記憶,
當我們祈求自己的生活,
在形成我們的一把灰塵里,
我們是沉默,沉默,又沉默,
在祭祖的發霉的頂樓里,
用嗅覺摸索一定的途徑,
有一點異味我們逃跑,
我們的話聲說在背后,
有誰敢叫出不同的聲音?
不甘于恐懼,他終要被放逐,
這個恩給我們的仇敵,
一切的繁華是我們做出,
我們被稱為社會的砥柱,
因為,你知道,我們是
不敗的英雄,有一條軟骨,
我們也聽過什么是對錯,
雖然我們是在啃嚙,啃嚙
所有的新芽和舊果。
“我們的父親,祖父,曾祖/多少古人借他們還魂”—一“父親、祖父、曾祖”指一代又一代,傳承著古人延續下來的“靈魂”,傳統的思想與文化一輩又一輩被延續下來。“多少個骷髏露齒冷笑/當他們探進豐潤的面孔/計議,詆毀,或者祝福”—一“骷髏”喻指已經逝去的古人,豐潤的面孔”喻指仍舊活著的當代青年人,這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古人對當代青年人露齒冷笑,是多么不屑與輕視的意味,似乎在謝“我們永遠借你們還魂,你們擺脫不了我們的思想侵襲”,所以不管青年人如何反叛傳統,古人還是探進他們豐潤的面孔,對他們“發出的抗議”進行計議、詆毀或者祝福,新生的希望總是被傳統的、封建的勢力抵制、打壓,并逐漸將他們同化,讓我們不由自主地想起魯迅先生發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喊。第一節就展示了戕害廣大中國國民的封建傳統的強大力量,能夠使畸形的社會一直循環下去,正如詩人在《裂紋》中所說:“四壁是傳統,是有力的/白天,扶持它一切勝利的習慣”。
“雖然現在他們是死了/雖然他們從沒有活過/卻已留下了不死的記憶”一死了,從沒有活過,不死的記憶,這三者看似相互矛盾,卻蘊涵著更深層次的意義。第二句是對第一句的否定,因為只有“活過”才能“死了”,這些已經逝去的古人雖然曾經活過,但從未活出自己的聲音,他們是被一代又一代的古人“靈魂附體”,被迫繼承傳統的思想文化,所以說他們沒有活過。第三句是對第二句的否定,因為只有活過的人才會留下記憶。雖然他們沒有活出過自我,但他們繼承了古人的“靈魂”并且一代又一代傳承下來,“留下了不死的記憶”。接下來筆鋒一轉,由“他們”過渡到“我們”。“我們”指的是有個體意識的現代青年人,所以才去“祈求自己的生活”,“我們”想要掙脫傳統的桎梏,獲得自由,但古人“留下的不死的記憶”卻又是使我們得以形成的客觀體。當自我與傳統產生矛盾時,個體的生命永遠是被扼殺的對象,“改變明天的已為今天所改變”。“我們”想要反抗傳統卻又不得不依靠傳統,自我與傳統的矛盾反映了當代青年人對自我身份定位的艱難,傳達了失落、迷茫的時代沉痛。“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絕望/永遠是自己,鎖在荒原里/仇恨著母親給分出了夢境”(《我》)。處在這個四壁是傳統的鼠穴里,脫離了群體,沖出了樊籬,“我”是誰,“我又該何去何從?
“我們是沉默,沉默,又沉默”——連續三個“沉默”蘊含著對包括自己在內的當代青年人茍且偷安、膽小怕事、不敢發聲的憤怒與控訴。“在祭祖的發霉的頂樓里/用嗅覺摸索一定的途徑/有一點異味我們逃跑/我們的話聲說在背后”——詩人用“老鼠”象征著被異化的人類,在這個如“鼠穴”一般的發霉的戕害人性的傳統社會,用嗅覺摸索著前往祭祖的頂樓的途徑,因為這些鼠輩膽小卑怯,不敢違背傳統。“我們”只敢走那條無數古人走過的路,而在路的終點等待著“我們”的是祭祖,因為古人要借我們“還魂”。“異味”指的是不同于傳統的精神品質,即背離集體與封建的個人意識的覺醒。“我們”不敢要求變革,而是“逃跑”,“傳統”對“我們”充滿著敵意,我們只能“把話聲說在背后”。這是怎樣被壓抑的人性啊,傳統社會“把我們這樣切,那樣切,等一會就磨成同一顏色的細粉/死去了不同意的個體,和泥土里的生命”(《城市的舞》)。選擇逃跑的青年人最終能夠在這個社會生存了下來,但對個體自由的追求已經被摧毀,“我們”已經形成集體的“無個性”,在這個巨大的發霉的如網一樣的封建社會隨波逐流,繼續留下“不死的記憶”,而真實的靈魂卻在單調疲倦中失去了生命,有誰還記得那首高喊“突進”的“玫瑰之歌”嗎?
“有誰敢叫出不同的聲音/不甘于恐懼,他終要被放逐/這個恩給我們的仇敵/一切的繁華是我們做出/我們被稱為社會的砥柱”一這個傳統社會將放逐敢叫出不同聲音的人,扼殺每一個“不甘于恐懼”的生命,因為這個社會只容許一種聲音。所以“新生的希望被壓制,被扭轉/等粉碎了他才安全”。詩人在描寫自我與傳統的對抗中帶著深深的無奈與憂慮,因為“年輕的學得聰明,年老的/因此也繼續他們的愚蠢”,沒有人“顧惜未來”。所以有著歷史意識的詩人,對處于這個時代的孩子感到悲痛、嘆息:等長大了你就要帶著罪名/從四面八方的嘴里/籠罩來的批評”。而最終被同化的年輕一代成為了那個“吃人”社會的“砥柱”,做出“一切的繁華”。我們在這個社會有了一席之地甚至成為了砥柱,而這個恩情是我們的仇敵給的,好不諷刺!詩人在這里使用了反諷的技巧,諷刺隨波逐流、不分對錯、同流合污的鼠輩們。
“因為,你知道,我們是/不敗的英雄,有一條軟骨/我們也聽過什么是對錯/雖然我們是在嚙齒,嚙齒/所有的新芽和舊果”——憑著那“一條軟骨”,我們成為了“不敗的英雄”,在這個如“鼠穴”一般的社會,“我們”寄生其中,唯唯諾諾,以茍且偷生。詩人繼續采取反諷的技巧,將“英雄”和“軟骨”這一對矛盾的客體放在一起,突出了趨炎附勢的“我們”的猥瑣之態。“我們”明明聽過什么是對錯,卻像老鼠一樣有著十足的破壞性,在封建勢力的主使下,嚙齒、扼殺新事物的萌芽,摧毀曾經取得的傳統優秀文化成果。傳統最終戰勝了自我,而隱藏在這種矛盾背后的卻是沉重的時代傷痛!
總之,穆旦的這首《鼠穴》以“老鼠”作為核心意象,象征在封建社會中壓制自我,茍且偷生,最終被封建社會同化,并.‘協助”封建勢力一同摧毀個體價值,失去“自我”的現代青年人。“鼠穴”則象征了整個黑暗、破舊、庸俗、落后的封建社會,并以“頂樓”、“骷髏”、“軟骨”等意象疊加壘砌,豐富了“鼠穴”的內涵,加強了諷刺的意味。在描寫軟弱無能的“鼠輩”背后,則是詩人強烈的“自我”與“傳統”的矛盾情緒,隱藏著時代的無言的悲痛。
參考文獻:
[1]彭廣見,穆旦詩歌的符號學解讀[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10.
[2]吳小東,“突進”與‘退回”[D].重慶:西南師范大學,2001.
[3]李興嶺,詩人主體的詩意投射[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15.
[4]唐詩詩.穆旦早期詩歌中的象征系統研究[D].開封:河南大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