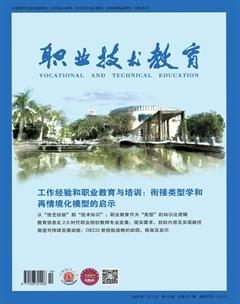從“技藝經驗”到“技術知識”:職業教育作為“類型”的知識論邏輯
徐平利
摘 要 職業教育的誕生和發展建立在“實驗的經驗主義”知識論基礎之上。職業教育對于經驗知識的探究過程,是從“技藝經驗”“技能知識”到“技術知識”的遞升過程。“技術知識”具有層級結構和獨立運行體系,在技術的遞歸和迭代過程中不斷演進。“技術技能”是經驗知識復雜性的政策性表達,可以清楚描述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遞升性特征。理解職業教育的知識論邏輯,有利于職業教育在實踐中厘清關系、樹立自信、輕裝前進,也有利于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實現“互通共長”。
關鍵詞 職業教育;技術技能;技術知識;知識論邏輯;技藝經驗;經驗知識
中圖分類號 G71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0)19-0016-06
不同國家的學校職業教育制度各有特色,但各國基本趨勢都是不斷打通職業教育的上升通道,并通過學分制和彈性學制等方式實現“職普融通”。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也處于這一基本趨勢中。2019年《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指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其意義在于,從“類型”發展上建立國家職業教育的“遞升體系”,以使職業教育擺脫傳統的“低賤身份”。本文所要討論的是: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之所以能夠建立遞升體系的知識論邏輯是什么?回答這一問題,必須涉及以下問題:如何理解“知識”,不同的知識論會產生怎樣的教育觀,職業教育的知識論如何影響職業教育的國家政策?
一、什么是知識:知識論與教育觀的演變
什么是知識,哲學家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知識就是證實了的真的信念(knowledge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1]這個判斷表明,“知識”有三個必要條件:一是“信念”,即對某事某物表示相信;二是“真”,即信念與其對象完全一致;三是“證實”,即有充分證據能夠證實信念是真的。根據知識來源和檢驗標準的不同,哲學史上出現了不同的知識論,主要有兩種:一是先驗主義或理性主義知識論,認為某些信念是證實知識真實性的“元信念”或“天理”;二是經驗主義或外在主義知識論,認為信念與其對象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只要知覺確認之后其就是真的。從歷史發展的眼光去看,“徹底的經驗主義和徹底的理性主義立場都是片面的”[2]。康德率先對這兩種片面的立場進行綜合,不過他的“物自體”概念仍然站在傾向于理性主義的立場上。與康德相反,杜威從現代科學的實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出發,站在傾向于經驗主義的立場上,他稱之為“實驗的經驗主義”。
康德的知識論把論證的信念體系從天上的神靈拉回人間的理性,對后世的教育觀產生了根本性影響,無論是赫爾巴特的科學教育理論,還是泰勒的目標主義課程模式,都可以在此找到知識論的源頭。然而,杜威對此批評指出:“康德的所謂革命,只不過是使早已隱藏在古典傳統思想中的東西明顯化罷了。”[3]杜威認為,關于知識論的徹底的“哥白尼式的變革”,必須打碎理性主義知識論的信念體系,即“我們并不需要把知識當作唯一能夠把握實在的東西”,因為“我們所經驗到的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實在的世界”[4],而認知所要做的工作是把經驗從不可靠的“原始狀態”變成可靠的“認知狀態”,其手段是動手實驗與效果檢驗。杜威開辟了知識論的新道路,對后世教育觀也產生了根本性影響,例如人本主義教育理論和“做中學”課程模式,即以此為源頭。
杜威認為,人類之所以要把知識作為一種“確定性尋求”(證實真的信念),是因為早期人類“逃避危險”的必然要求。逃避危險有兩種途徑,一是祈求“神力”,二是發明“技藝”。由于“技藝”不能保證確定性,因此唯有“相信神力”。久而久之,“神力”就演變為“元信念”(先驗),進而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理性”,這就是先驗主義知識論的起源。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就認為,知識屬于“超感覺的永恒世界”,只有“那些看到了絕對永恒與不變的人們則可以說是有知識的”[5]。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的知識論雖然比柏拉圖進步,他不反對實用,卻否認奴隸勞動的精神性價值,認為工匠技藝是“卑陋的”,顯然也不承認奴隸勞動的技藝經驗可以產生知識性意義。在西方哲學史上,由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學家中最有影響的人”[6],所以他們的知識論思想深深植入了傳統的貴族教育觀。
貴族教育觀排斥“勞動”教育或“職業”教育。這是因為,貴族教育觀以先驗主義知識論為理論基礎,把理智和行為分開,認為理智活動與尋求絕對不變的確定性具有本質聯系,而行為活動“須冒著風險”,所產生的技藝經驗是變動不羈的。這樣一來,貴族教育就只能局限在“自由的”“閑暇的”“勞心的”層面,大部分勞力者是沒有受教育權的。事實上,在人類社會早期,“知識”和“教育”都不普及,屬于稀有的“精神產品”,是統治階級的專利。至于“器具制作”,由于其中的技藝經驗不具有普遍意義——制作同樣的器具可以有不同經驗,有的還是難以言傳的個性化“絕活”,因此,技藝經驗不能作為“知識”來把握,也不被允許進入學校教育中,只能通過“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在匠人家族中世襲下來。比如,孔子在教育中要求“君子不器”,意思是器具太狹隘,不能作為君子教育的目標。
杜威正是站在民主教育權力的基礎上反對傳統的貴族教育觀的。他提出,民主社會需要“經驗”的知識理論:“民主代表自由互換,代表社會連續性,所以必然發展出一種知識理論,在知識中找到使一種經驗得以可用,從而為其他經驗提供方向和意義的方法。……它們在教育上,則體現為學生在學校中獲取的知識與在共同生活的環境中所進行的種種活動或作業之間的關系。”[7]為此,杜威在當時特別強調職業教育的意義,他說:“當前有意識地強調職業教育,傾向于把過去隱含的職業內涵明確地顯現出來。”[8]今天,教育民主化和大眾化深入人心,職業教育已經成為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類型,而杜威的“知識論”作為職業教育的哲學基礎,也已經成為學界共識。
二、“經驗知識”的傳授與職業學校的誕生
17世紀,歐洲的科學革命使傳統的先驗主義知識論受到挑戰,因為“科學本身,借助于數學,把證明性的知識體系帶到了自然對象的領域中”[9]。以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為代表,“抨擊舊有的學問和邏輯學”,提出“應該訴諸經驗以發掘自然的底蘊,求助經驗表示對權威的反抗,……而不是沉迷于系統地收集和整理傳統的觀念”[10]。王陽明似乎與培根遙相呼應,他在東方提出:“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11]在這樣的時代里,“借助皮匠在皮革上打洞,或者使用蠟、針、線之類的活動,人們獲得了對世界的充分知識。”[12]自此,“經驗”不再作為“知識”對立面,而是即將以一種“經驗知識”的面貌登上歷史舞臺,正如杜威所指出的:“由此產生的邏輯結果是一種新的經驗和知識的哲學,即不再把經驗放在理性知識和解釋的對立面的哲學。”[13]
必須指出,純粹的技藝經驗并不意味著一定會成為知識,因為沒有經過證實的信念不能說是“真的”。但是,絕對經驗主義(或感覺經驗主義)卻在此時把“感覺的后果當作‘心理的或精神的狀態或過程”[14],這種絕對經驗主義知識論從純粹理性直接跨入純粹經驗,其實質是一樣的,在教育觀上必然導致知識權力的肆意妄為。顯然,絕對經驗主義并沒有解決知識信念的論證問題,因為“一切知識都是特殊探究行動的結果”[15]。即是說,“技藝經驗”要成為具有確定性的“經驗知識”,必須“采取動作、從事操作,就是切割、區分、分隔、擴大、堆壘、接合、聚集與混合、積累與分派;總之,就是選擇和調整事物,使之成為達到后果的手段”[16],簡言之,必須經過實踐效果的檢驗。
杜威在批判傳統的先驗主義和經驗主義知識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實驗的經驗主義”知識論,這一知識論為國家職業教育制度的誕生建立了哲學基礎。當國家職業教育制度誕生之后,傳授“經驗知識”的“學校教育”就與傳授“技藝經驗”的“師徒制”區分開來,并且“知識學習”的規模化和標準化也與“技藝模仿”的個體性和模糊性區別開來。以廚師做饅頭為例,好廚師憑經驗知道做一籠饅頭需要多少面粉、冷水、酵母、老面和堿面,但這種技藝經驗并不具備確定性,對徒弟來說只能依靠觀察和模仿,無法定量。因此,個體性和模糊性的“技藝經驗”無法作為職業學校教育的“經驗知識”進行傳授。在工業社會,大機器生產強調的是效率第一,“師徒制”教育方式無法滿足效率經濟的要求,所以技藝經驗的模仿在職業學校教育中必然被經驗知識的探究所取代。
17世紀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發表論著《泛智學校》,指出“所有人都應學習一切知識”,“必須訓練我們的學生進行操作,這也應列入認識的內容,即認識事物必須加上實踐活動。”[17]這是現代職業教育制度得以孕育的轉折點,夸美紐斯在這里表達了三點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偉大主張:第一,所有人有權力接受一切教育,教育可以擴大至勞力者階層;第二,操作實踐也應列入認識內容,承認經驗探究的知識論意義;第三,實踐活動可以進入學校教育,打破了傳統學校教育的封閉思想。而且,為了適應新時代的規模化教育需要,夸美紐斯提出了“大班授課”思想,奠定了工業社會學校教育的基本組織形式。
18世紀后期,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創辦學校,他把“教學做”結合起來,帶領孩子們在農場進行專門的生產訓練,男孩子學習園林種植和手工制造,女孩子學習紡織、縫紉和廚藝,以及其他職業勞動[18]。19世紀之后,開設實踐科目并專門傳授“經驗知識”的職業學校在歐洲各國紛紛出現,并且逐步進入國家教育制度體系。德國教育家凱興斯泰納用勞作教育思想改造了德國的國民學校,他把“心智活動”和“實踐活動”看作同等重要,指出“心智技能的培養同勞動技能的培養,在專業課上結合得越緊密,國民學校的發展就越興旺。同時,心智技能的發展也就隨之越加自覺,越加穩定”[19]。
20世紀初,杜威在《民主與教育》一書中總結了現代職業教育誕生的五點理由:一是在民主社會中,體力勞動和一切生產實踐活動受到尊重;二是工業性的職業使學校教育必須重視工業生產和就業問題;三是工業生產需要技能知識;四是知識追求變得更有實驗性;五是操作、探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20]。總之,在杜威看來,經驗知識的登場成為學校職業教育誕生最重要理由。
三、從“技藝經驗”到“技術知識”的遞升之路
“技藝”這個詞在現代漢語中通常稱作“技能”。不過,“技能”與“技藝”不同。“技能”指工業社會圍繞機器生產的標準化工作能力,而“技藝”是指小農社會中手工藝勞動者的個性化工作能力。“技能”比“技藝”前進了一步,但是其卻失去了“匠人之道”。從上文分析可知,“技藝經驗”還不具備作為知識的條件,但是,“技能”已經是“經過特殊探究行動的結果”,具備成為“經驗知識”的條件。
同樣,在英語詞匯中,“technique”的意思是“技藝”,也可以是“技能”,不過“技能”還有一個詞是“technology”,即“技術”,它的意義更為豐富,既包括“技藝經驗”“技能知識”,也包括更為復雜的知識內容。我國技術哲學家吳國盛對此有一段分析:“‘技術這個詞(英文為technology,德文為technik,法文為technique)大體包含著四個方面的意思:第一,與個人身體實踐相關的技巧、技能、技藝、技法;第二,體現在行動和做事情之中的方法、手法、途徑;第三,物化了的工具、設備、設施、裝備;第四,工業技術、工程技術、應用現代科學的現代技術。”[21]
可以明確的是,從“技藝經驗”到“技能知識”,再到“技術知識”,這是一個遞升的過程。首先,“技藝經驗”是純粹的活動,還不是“經驗知識”,用杜威的話來解釋,“純粹的活動并不構成經驗,因為它是發散的、離散的、彌散的。作為嘗試過程,經驗涉及變化,但除非變化被自覺地和由它產生的結果的反饋關聯起來,否則,變化就沒有意義。”[22]接下來,當技藝的活動經過不斷探索、累積、反思和確認之后,一種初級的“經驗知識”就形成了,這就是“技能知識”。但是,這個階段的知識還不完美,所以常常受到傳統觀念的鄙視。事實上,在先驗主義知識論的慣性作用下,“技能”甚至不被看作“知識”,比如,人們將兩者并列稱為“知識與技能”。長期以來,職業教育處于初等和中等教育層次,在傳統教育觀的眼中,培養的是缺乏“知識”的“技能”人才,所以是“卑賤的”教育。對此,杜威的解決辦法是,為“技能”賦予更多的意義,“使工人們知道,他們職業的科學的和社會的基礎”[23]。
不過,當我們進入“技術知識”層面的時候,就會發現“技術知識”其實具有豐富的內涵,而且已經賦予“技能”很多意義。當代美國技術哲學家皮特(J.Pitt)對“技術”的特殊定義是:“‘技術是工具(tools)、技能(techniques)以及工具和技藝的系統,‘技術,是工作中的人性(Technology is humanity at work)。”[24]這個定義不僅把“技能”包含其中,而且賦予其“人性”的意義。如今,數字技術正在改變傳統的工業技術,技術的遞歸和迭代升級越來越快,工業技術的知識特征受到“有效率的個性化”和異質性的巨大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技術知識的結構、特征和意義必然越來越復雜,我們在下文將有詳細論證。
在杜威的知識論產生之后,英國科學家和哲學家波蘭尼創造了一個新的概念,即“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也有人翻譯為“隱性知識”“緘默知識”),專指那種在行動中發生的難以言傳的知識。波蘭尼的理論建立在格式塔心理學基礎之上,雖然不同于杜威的機能主義心理學,但是對認知活動的解釋是相同的,兩人都強調動作的連續性和整體性[25],即強調“知行合一”。可以認為,波蘭尼對杜威關于技藝經驗的“探究”作了細化。波蘭尼發現,經驗的探究是“連續上升”的過程:“首先上升到生理功能的植物層級,接著進入到主動的、有知覺的、有欲求的行為層級,接著上升到智力和創造性的層級,最后到達有責任的人的層級。”[26]波蘭尼說:“個體性從低級到高級的這一前進包含著被觀察的個體和作為觀察者的我們自身之間關系的一個變化。”[27]可見,波蘭尼的“默會知識”是一個認知過程,其體現在經驗的探究與證實(確定性尋求)過程中,或者說,“默會知識”只有在經驗的探究與證實過程中才能發揮作用,這個過程具有“連續上升”的特性。
四、“技術技能”是經驗知識復雜性的政策性表達
從2014年國務院下發《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開始,到2019年《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技術技能”作為一個特別的專有名詞,在國家政策文件中隆重登場。問題是:“技術”與“技能”為什么要作為一個聯合詞組而出現?它們之間是什么關系?站在“實驗的經驗主義”知識論的立場上,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用杜威的實驗經驗主義知識論分析發現,“技術技能”這個詞實際上是對“經過探究和實證的經驗知識”的整體性描述,包括“技能知識”和“技術知識”兩個部分。在“技術技能”這個概念中,“技術”和“技能”構成聯合詞組,具有遞進關系。如果從“遞升”角度看,使用“技能技術”這個詞組似乎更為合適。但是,“技術技能”是一個政策性的專有名詞,意在強調職業教育傳授經驗知識的復雜性和高等性,因而將“技術”置于“技能”之前。
“技術技能”可以直觀地體現職業教育傳授經驗知識的復雜性特征,與之相應,“技術技能”也可以用來直觀地描述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遞升性特征。我國高職教育的“高”字體現在什么地方,一直以來這一難題總是令人抓耳撓腮。現在,“技術技能”這個能夠體現經驗知識復雜性和高等性的概念出場了,其不僅從國家政策層面給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搭建了遞升的階梯,而且具有實驗經驗主義的知識論邏輯。
職業教育不僅培養“技能(高技能)”人才,而且培養“技術”人才;職業院校的畢業生不僅能夠有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文憑,而且能夠有高等教育的本科和研究生文憑。這是“技術技能”這個概念在國家政策落實層面的具體表達。不過,有人會提出疑問:職業教育培養“技能(高技能)人才”很好理解,但是如果把職業教育提升到培養“技術”人才層面,那么它的知識論邏輯到底是什么?“實驗的經驗主義”知識論能夠對這種“技術”人才作出不同于“學術”人才的合理解釋嗎?事實上,“職業教育”在敘事上常常與“應用技術”連結在一起,比如“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等,但在人才培養目標的具體描述上,似乎很少把“技術”(特別是“高等技術”、“復雜技術”)作為關鍵詞。人們一般把“高深”“復雜”“知識”這些詞匯用于學術教育,比如“學術性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等。
國家文件并沒有對“技術技能”這個概念作具體解釋,其只是一個具有指向性的政策表達。但是,當從實驗經驗主義知識論的角度去分析的時候,卻發現“技術知識”具有豐富的層級結構,足以支撐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遞升需求,或者說,“高深”“復雜”“知識”這些詞匯并不是學術教育的專利,它們同樣可以用于職業教育。
從筆者所掌握的有限資料看,關于“技術知識”內部結構和本質特征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只是在技術哲學家那里有一些比較宏觀的分析。可喜的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復雜性科學奠基人布萊恩·阿瑟(W.Brian Arthur)完成了一部解剖技術知識的經典著作,即《技術的本質》(the Nature of Technology),而且阿瑟的研究立場正是實驗的經驗主義,他認為“技術是對現象有目的的編程”,這個觀點與杜威關于“一切知識都是特殊探究行動的結果”完全一致。阿瑟將復雜性技術理論用于解釋變動不羈的經濟現象,重視偶然、異質的經驗元素,呈現了與古典主義經濟學完全不同的面貌。同樣,我們可以借助阿瑟關于技術知識結構與特性的分析,解讀職業教育培養技術技能人才的遞升性和復雜性特征。
五、“技術知識”的層級結構與特征
在《技術的本質》一書中,阿瑟指出,技術是一個復數概念和集合概念,是“實踐和元器件的集成”,是“在某種文化中得以運用的裝置和工程實踐的集合”[28]。具體來說,技術是由許許多多大小不同的零部件構成的系統或模塊,技術進步表現為零部件的“集成化過程”。比如一只手表有1000個零件,如果每次組裝都要重復1000個零件,效率就很低,但是當1000個零件被組合為10個模塊之后,新的制造就產生了,這就是“技術進步”。這說明,技術系統內部有零散和整體、簡單和復雜之分,這種區分是動態的,即隨著技術進步和時間推移,有些零件組合可能會“凝固”成簡單的“獨立單元”,此時原來的“繁瑣”變成了現在的“簡易”。比如,制作電子玩具的某種工作流程,以前由于技術內部零件很多很細,流水線上需要安排100個人,后來許多零件“凝固”成“獨立單元”,流水線上只需要安排10個人就可以了。
由此可見,如果把“組裝”零散的和簡單的零件看作“技能”的話,那么這種技能就是技術構成的基礎和出發點,由此出發,技術的“獨立單元”得以形成,這是一個認知過程、探究過程和證實過程,當然也是“技能知識”向“技術知識”的遞升過程。然而,由于探究與證實的復雜性,其中必然不斷有錯誤和糾錯的發生,這就使得“遞升”之路不可能是線性的,而是具有“遞歸”的特點。
阿瑟揭示了技術的兩個特征:第一,“技術具有層級結構”;第二,“技術具有遞歸性”。“遞歸”原是數論概念,如今主要用于數據編程,其包括“遞推”和“回歸”兩個要點。首先是把復雜問題的遞推到比原問題簡單一些的問題進行求解,其次是當簡單問題得到解決后,逐步返回,依次得到原問題的那個最復雜的解。由此可知,所謂“技術知識”,正是在技術問題的求解過程中發生的,問題逐步化解,效果得以證實,技術知識的真的信念體系就建立起來了。
技術的“遞歸性”和“層級結構”相輔相成。因此,技術的“層級結構”是動態的,始終處在不斷遞推、回歸、修正和完善的過程中。比如,我們把飛機制造看作“大技術”,其包括機翼機尾、動力系統、控制系統等“子技術”,每個“子技術”又有很多“小技術”,比如動力系統就包括進氣系統、壓縮機系統、燃燒系統等。而每個“小技術”又可以繼續細分,直到“最基礎技術”或“單個元素”。對于“大技術”來說,其內部所有技術都有相似性,技術人員因這種相似性,可以“進入”其中任何一個技術來認識飛機。無疑,這個過程就是技術知識的探究過程。與之類似,在職業教育中,技術知識的學習也是“一個可執行的層級結構”。
阿瑟說,技術是“流動的東西,永遠不會靜止,永遠不會完結,永遠不會完美”[29],這是由技術的結構與特征決定的。的確如此,技術在數字化時代更加體現了它的復雜、多變和敏感特征,技術的結構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擾,猶如一只蝙蝠的病毒很可能摧毀全球經濟一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可以在技術知識的探究過程中,增加迭代性特征。“迭代”是利用外界變量值不斷演進、不斷升級的過程,比“遞歸”的效率更高,可以代替“遞歸”。
總之,通過阿瑟的分析表明,技術有其完整的獨立運行的結構特征,技術知識是動態發展和復雜多變的,但技術知識的特征有其可認知的確定性。而且,技術的“獨立運行”使其與科學能夠并立而行。技術不是科學的附屬物和應用品,雖然技術依賴科學,但是科學也依賴技術,兩者是“共生關系”。阿瑟說:“科學和技術以一種共生方式進化著,每一方都參與了另一方的創造,一方接受、吸收、使用著另一方。兩者混雜在一起,不可分離,彼此依賴。”[30]
六、理解職業教育知識論邏輯的意義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一是職業教育的誕生和發展有其知識論邏輯。杜威奠定了職業教育的哲學基礎,他提出的“實驗經驗主義”知識論,成為職業教育的基本理論之一。二是人類關于經驗知識的“確定性尋求”,表現為從“技藝經驗”到“技能知識”再到“技術知識”的探究過程,這既是一個不斷遞升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回歸和證實的過程。三是把“技術”和“技能”聯合為“技術技能”這個概念,是我國新時代職業教育關于人才培養目標的政策性表達。“技術技能”可以直觀反映職業教育傳授經驗知識的復雜性特征,也可以清楚描述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遞升性特征。四是技術知識涵蓋技能知識,具有層級結構和獨立運行體系,在技術的遞歸和迭代過程中不斷演進、不斷升級、不斷淘汰。技術知識的演進需要科學原理,也需要技藝經驗。
分析可見,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培養“技術技能”人才,有其清晰的知識論邏輯,或者說,職業教育必然有其自己的“生命意義”和“生長空間”。理解職業教育培養人才的知識論邏輯,有利于職業教育在不同教育類型的“彼此依賴”中找到茁壯生長的理由。
過去,人們根據舊有習慣,很容易在理論與實踐、學術與職業之間找到區分的邏輯,但是對于“技術與應用”和“技能與應用”“技術與職業”和“技能與職業”之間的區分卻比較模糊,簡言之,人們對于“技術技能”這個概念當中的知識論邏輯還沒有弄清楚,以至于在實踐中很難在“應用技術本科”和“職業技術本科”之間作出區分。事實上,職業教育實踐中有許多“剪不斷、理還亂”的概念,比如“科學技術”“應用技術”“職業技術”“職業技能”等,它們直接影響人們對不同教育機構及其人才培養類型與目標的認識。
十多年前,潘懋元曾把當代世界主要國家的高等教育歸納為“學術理論型”“專業應用型”和“技術實用型”三大類,并結合中國實際,將中國高等學校分為“學術型大學”“應用型本科高校”和“職業技術高校”。他認為,學術型大學培養“學術人才”,應用型本科高校培養“不同層次的應用型專門人才”,職業技術高校培養“不同層次的生產、管理、服務第一線的技能型人才”[30]。學術人才從事科研工作,專門人才從事技術應用工作,技能型人才從事技能服務工作,三類人才只有“目標不同”,沒有“層次之分”。不過,根據我國職業教育政策文件中關于“技術技能”的提法,“專門人才”和“技能人才”產生了交叉地帶,進而產生了職業院校“升本”和本科院校“轉型”的困惑和爭論。因此,潘先生的分類在當下的職業教育實踐中已無法清晰“劃界”。其實,這并不奇怪,按照布萊恩·阿瑟的觀點,如果我們把教育看作“技術”,這種現象正是技術復雜性的體現。
理解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的知識論邏輯,有利于我們在職業教育實踐中理清關系、明確位置、輕裝前進。如今是“跨界”和“融通”的時代,職業教育在人才培養中既要有獨立運行、不斷遞升的“知識自信”,也要與普通教育的人才培養實現“互通共長”,因為兩者“不可分離,彼此依賴”。
參 考 文 獻
[1][2]胡軍.知識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66.358.
[3][4][9][13][14][15]杜威.確定性的尋求:關于知與行關系的研究[M].傅統先,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271.278.24.165.180.145.
[5][6]羅素.西方哲學史[M].何兆武,李約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153.131.
[7][8][10][12][19][21][22] 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九卷)[M].俞吾金,孔慧,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274.250.216.221.250.116.251.
[11]王陽明.傳習錄[M].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3:132.
[16]夸美紐斯.夸美紐斯教育論著選[M].任鐘印,選編.任寶祥,等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35.
[17]Fredalene B. Bowers. Thorn Gehring,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8th Century Swiss Educator and Correctional Reformer[J].The Journal of Correctional Education, 2004(4):309.
[18]凱興斯泰納.凱興斯泰納教育論著選[M].鄭惠卿,選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4.
[20][23]吳國盛.由史入思:從科學思想史到現象學科技哲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374.371.
[24][25][26]邁克爾·波蘭尼.認知與存在:邁克爾·波蘭尼文集[M].李白鶴,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5.111.112.
[27][28][29]布萊恩·阿瑟.技術的本質[M].曹東溟,王健,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26.42.68.
[30]潘懋元,等.關于高等學校分類、定位、特色發展的探討[J].教育研究,2009(2):3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