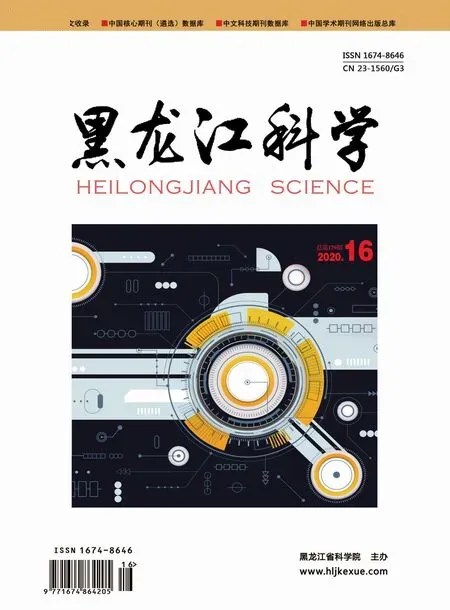腹針療法治療腹型肥胖糖耐量異常的臨床效果觀察
阮 勤,謝 敏
(1.遵義市中醫院,貴州 遵義 563000; 2.貴州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貴陽 550000)
糖耐量減低(IGT)是1999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專家委員會提出的血糖異常類型,它是所有2型糖尿病(T2DM)患者發病前的必經階段。《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3版)》指出:超重、肥胖、腹型肥胖是糖尿病的重要危險因素。《內經》中有脾癉、消渴、消癉的記載。“脾癉”是指糖尿病前期狀態,脾虛是糖耐量異常發生發展中的始動因素和關鍵環節。糖耐量異常的主要病機為脾虛,故脾虛所致的肥胖與“致消”更為密切。“引氣歸元、調脾氣”方,從調理臟腑功能入手,調補脾胃,運化水濕,通調氣血,從而達到健脾化濕、調節“脾虛致消”的目的。本研究通過分析腹針療法治療脾虛痰濕型腹型肥胖IGT患者臨床效果,為患者提高更好的治療方案,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5年1月—2016年1月來貴陽中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針灸科、治未病中心、內分泌科就診的58例患者,隨機分為健康教育組21例(男9例、女12例),運動組18例(男8例、女10例),腹針組19例(男10例、女9例)。三組患者中年齡最大的60歲,年齡最小的39歲,平均年齡(51.13±5.54)歲。各組人數、年齡、性別等情況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
IGT:根據2010年美國糖尿病協會(ADA)診斷標準:空腹靜脈血糖(FPG)<6.1 mmol/L、口服75 g葡萄糖耐量試驗(OGTT)檢查餐后2 h靜脈血糖(2 hPG)為7.8~11.1 mmol/L[1]。
超重及腹型肥胖:根據《中國成人超重和肥胖癥預防控制指南(試用)》診斷標準,超重:體重指數(BMI)≥24;腹型肥胖:腰圍男性>85 cm,女性>80 cm[2]。
1.2.2 中醫診斷標準
參考1995年衛生部《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第二輯)》對脾虛痰濕型證候的標準作評定。具備主癥3項(舌苔必備);或主癥2項(舌苔必備)加次癥1項;即可診斷。
主癥:食少納呆,脘腹痞悶,食后或午后腹脹,大便塘泄,舌苔白膩或白滑。
次癥:頭身困重,腹滿或腹痛腸鳴,肢體浮腫,惡心欲嘔,婦女帶下量多色白,面色萎黃,浮腫,脈濡緩或細緩。
1.3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符合IGT、超重、腹型肥胖以及中醫脾虛痰濕證診斷標準;(2)年齡18~60歲;(3)腹針治療前1個月及治療期間未接受其他減肥、降脂藥物治療,無器質性病變的患者。
排除標準:(1)年齡小于18歲或大于60歲;(2)各種器質性疾病引起的IGT;(3)藥物引起的IGT;(4)妊娠、準備妊娠或哺乳期婦女;(5)合并甲狀腺功能亢進癥、急慢性胰腺炎及嚴重的五臟功能不全,近期有感染、創傷、手術等應激狀況;(6)依從性差的IGT患者及精神病患者;(7)有針灸禁忌癥者;(8)已接受其他有關治療,可能影響本研究指標觀測者;(9)腹部檢查有肌緊張、壓痛、腫塊以及肝、脾腫大或有觸痛者。
剔除標準:(1)凡不符合納入標準而被誤入的病例應予剔除;(2)依從性差的受試者,療程中自行退出者,或本實驗實施過程中自行使用其它治療方法者;(3)未按規定時間接受檢查,資料不全者應予剔除;(4)發生嚴重不良反應或并發癥,不宜繼續接受治療而被中止試驗的病例。
1.4 治療方法和療效觀察
1.4.1 治療方法
(1)健康教育組(A組)。對患者進行IGT及DM知識宣教,使患者了解兩種疾病的基礎知識,包括IGT及糖尿病的診斷標準、病因,了解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的重要性,宣傳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對IGT的影響,將宣傳資料打印發放給受試者,或發送到受試者的QQ或微信上。(2)運動組(B組)。運動組以中等強度的有氧運動為主,用智能手機下載益動運動軟件,根據患者的自身情況選擇跑步、騎行及步行三種模式中的一種,每周總運動量為700 kcal,每次運動時間以達到上述運動量為標準。每天運動所消耗的熱量值通過益動軟件上傳到微信朋友圈,以監督患者的運動量。堅持運動4周。(3)腹針組(C組)。選穴。引氣歸元穴組,中脘、下脘、氣海、關元。調脾氣,雙側大橫穴。患者仰臥位,皮膚常規消毒后選用0.22×40 mm或0.22×50 mm毫針,進針時避開毛孔、血管及瘢痕,對準穴位直刺,針尖抵達預定深度后,采用只輕捻轉不提插的手法。針刺深度為中刺,留針30 min,每周治療3次,隔天1次,共治療4周。
1.4.2 療效觀察
入組治療前、治療后、隨訪1個月、隨訪2個月時監測患者的空腹血糖(FPG)、口服75 g葡萄糖耐量試驗(OGTT)檢查餐后2 h血糖(2 hPG)。入組治療前及隨訪2個月時檢測空腹胰島素(FINS)、甘油三酯(TG)、總膽固醇(TC)、糖化血紅蛋白(HbA1c),計算胰島素抵抗指數(HOMA-IR)。見表1。
1.5 統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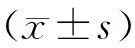
2 結果

表1 三組患者FPG、OGTT2 hPG、BMI、WC實驗結果Tab.1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FPG, OGTT2 hPG, BMI and WC of three groups

表2 三組患者TG、TC、HbA1c、FINS、HOMA-IR實驗結果Tab.2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G, TC, HbA1c, FINS and HOMA-IR of three groups

表3 三組患者治療前、治療后中醫癥狀評分比較Tab.3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mptom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three groups
上述實驗結果表明:腹針療法對腹型肥胖型IGT患者FBG、OGTT 2hPG、HbA1c、TG、TC、FINS、HOMA-IR、BMI及WC具有調控作用,能降低血糖、血脂、體重以及改善胰島素抵抗,提高機體對胰島素的敏感性。
3 結論
腹針療法對血糖、體重及腰圍的調控作用有較好的持續性,可以改善脾虛痰濕型腹型肥胖糖耐量異常患者的中醫癥狀。
4 討論
現代醫學認為IGT的發生主要與胰島素抵抗(IR)和胰島β細胞功能缺陷密切相關。肥胖會加重胰島素抵抗,并隨著胰島素抵抗程度的加深而損害胰島β細胞功能。肥胖狀態下脂肪細胞分泌以細胞因子如腫瘤壞死因子-a(TNF-a)為代表的各種炎性因子,引起胰島素敏感性(IS)下降,產生IR,使胰島β細胞功能代償性分泌增多,以代償IR所造成的胰島素相對缺乏,隨著胰島素的過度分泌,β細胞功能逐漸下降,更高的IR狀態伴隨IS功能嚴重失代償而出現IGT,進一步發展為糖尿病[3]。腹型肥胖患者的腹部體脂積聚,內臟脂肪增多,導致脂代謝紊亂,使過量游離脂肪酸(FFA)在肌肉、肝、脂肪組織中儲留,降低組織細胞對胰島素的敏感性,減少了胰島素受體數目結合位點,進而引發胰島素抵抗[4]。
腹針療法主要針刺腹部的穴位,針刺對神經通絡和神經遞質產生影響,激活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信號傳導途徑[5],增加葡萄糖的轉運和攝取。也可以通過刺激穴位調節患者自主神經系統[6],降低血清瘦素水平,抑制胃腸運動,減少胃酸分泌,增加機體對葡萄糖的利用,降低脂肪蓄積程度,使機體代謝趨于平衡。有研究顯示,針刺能增加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含量,降低一氧化氮合酶(NOS)的含量,增加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7],即清除超氧陰離子(O2-)保護β細胞免受損傷,改善肌體的代謝狀態,減輕胰島素抵抗,從而保護胰島β細胞。
腹針組各項觀察指標均顯示出優越的療效。雖然目前西藥有大量研究證明了其療效的確切性[8-9],但因其嚴重的副作用,目前對IGT的治療主要以非藥物治療方法為主。腹針療法通過大量臨床試驗證明其療效確切,并且無毒副作用。與傳統針刺強調“酸、麻、重、脹”得氣針感相比,腹針療法不強求“得氣”的針法,能夠提高患者的依從性。本研究結果提示,腹針療法在調控血糖、血酯、體重、胰島素抵抗程度方面具有很好的調控作用,并具有較好的持續性。
糖耐量異常屬祖國醫學“脾癉”范疇。《內經》中有脾癉、消渴、消癉的記載。脾癉對應的糖尿病前期狀態,即對應現代西醫診斷的糖耐量異常階段。《靈樞本藏》指出:“脾脆則善病消癉”,由此可見,脾虛是糖耐量異常發生發展中的始動因素和關鍵環節。糖耐量異常的主要病機為脾虛,尤其是肥胖患者,與“脾虛致消”關系更為密切。飲食不節損傷脾胃功能,脾胃功能受損則運化水液功能失常,水濕津液失于輸布,聚而生痰,脾喜潤惡濕,痰濕加重脾虛,從而形成惡性循環。脾胃失調,飲食不得節,脾失健運,聚濕生痰,痰濕困脾,阻遏氣機,脾化輸津液和布化精微的功能失常,使水谷精微及津液不能進一步轉化而發病。
通過腹針治療后,患者的各項中醫癥狀明顯減輕,證明腹針療法通過調理“脾胃”的功能,以“后天養先天”,能夠達到調理臟腑、氣機條暢的目的,使脾主升清、主運化的功能得以恢復,提高脾化輸津液和布化精微功能,從而達到健脾、化痰、除濕的目的,改善患者食少納呆,脘腹痞悶,腹脹,大便塘泄,頭身困重,腹滿,舌苔白膩或白滑等癥狀。
運動組治療結束后出現持續反彈趨勢,說明運動量減少后干預作用降低。有研究顯示,運動60 min后血糖開始下降,隨著時間的推移,其降糖作用存在逐級遞減的趨勢[10]。本課題研究結果也提示運動對降低血糖有較差的持續效應。針刺治療具有持續效應,是經大量臨床與實驗研究證實的[11]。腹針組療效能維持到治療結束后1個月,說明腹針療法具有較好的持續效應。
本研究從治療療程及針刺間隔時間兩方面討論腹針治療腹型肥胖糖耐量異常的持續效應。針刺持續性效應的產生與疾病種類、針刺手法、針刺時間、針刺穴位、針刺強度、針刺療程、針刺間隔時間等有著密切的聯系。針刺效應會隨著針刺時間的延長而增加,當刺激積累到一定量的時候達到最大值,此時再增加刺激量及刺激時間可能無效,甚至會起反作用,如何選擇合適的治療時間才能保證針刺的即時效應和遠期效應是臨床工作中應探討的問題。
本課題選擇1個月為1個療程,腹針組治療結束后患者的相關指標得到改善,并且在治療結束后1個月仍有較好的持續效應。然而,隨著隨訪時間的延長,持續效應開始減弱,及時給予再次刺激,制定合理針刺間隔時間,選擇恰當的再次介入針刺治療時機,對臨床治療慢性疾病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本課題研究結果也提示了用腹針治療IGT,可以在結束治療后2個月繼續下一療程的治療。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應延長隨訪時間,以尋找最佳時機再次介入腹針治療,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