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耶卜·薩利赫:清醒的蘇丹文化守護者
曾劍穎

塔耶卜·薩利赫(1929—2009)是蘇丹當代現實主義作家,被英國廣播公司BBC評為20世紀最著名的阿拉伯小說家。他懷著真摯誠懇的態度描寫蘇丹現實生活和文化,曾獲得阿拉伯小說界最具權威性的開羅創意獎。
薩利赫出生在蘇丹北部麥爾沃區的凱爾麥考林——一個屬于盧凱賓部落的村莊。他的父母都是農民,家族中出過商人和伊斯蘭教學者。他的第一個學校是一所伊斯蘭宗教學校,在這里他學習了宗教的基本教義和讀寫的基本原則。而后,他在自己的村子里上了由當時統治蘇丹的英國當局建立的小學,接著到蘇丹港市完成了初中學業,畢業后進入全國僅有的兩所高中之一——瓦迪·瓦德納學校。高中期間,他參與了豐富的文化活動,學習論文寫作,閱讀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等作家的文學作品。盡管校長準備幫助薩利赫獲得獎學金去牛津或劍橋留學,但薩利赫的家人并不愿意將他送到國外,因此他繼續在喀土穆大學學習。對人文學科感興趣的他卻選擇了理科專業,認為這些學科對于國家建設更為實用;然而他并不喜歡科學,花了很多時間在文學課上,最后選擇離開喀土穆大學。
1952年,23歲的薩利赫申請了BBC的職位,于次年冬天離開蘇丹前往英國。然而,新的生活起初并不順利,直到他認識了一個蘇丹朋友,生活狀態才開始慢慢轉變。他倆合作建立了一個小型的蘇丹社區——“蘇丹之家”,作為來自蘇丹同胞的寄宿之地。除了為BBC工作外,薩利赫還在倫敦大學學習政治學,同時專注于英國文化,參加了很多社會文化俱樂部,經常去看包括莎士比亞在內的許多戲劇。
1956年,英國、法國和以色列發動對埃及的進攻,薩利赫作為通訊員前往幾個國家進行報道,并且在當地辦事處工作。1960年他去貝魯特旅行時,由于過度勞累而病倒,不得不住院3個月,康復后與英國女孩兒朱莉結婚,后育有三女。此外,他還曾為倫敦的一家阿拉伯語雜志《麥加拉》撰寫每周專欄長達10多年,此間他探究了各種不同的文學主題,還擔任過喀土穆大學校長。在生命的最后10年,薩利赫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擔任顧問。
從北方省馬爾維縣到恩圖曼、喀土穆、倫敦,豐富而多變的生活是作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童年對農村家鄉的回憶和體驗,往往是他最初客居倫敦時撰寫短篇小說的素材。當然,他也以同樣的熱情研讀阿拉伯古今文壇之杰作,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阿拉伯小說家納吉布·邁哈福茲。
薩利赫的第一部小說《溪畔的棗椰樹》(1953)創作于他初到英國時,英國寒冷的天氣以及狹窄的房間、平淡的食物使他并不能很好地適應英國生活,他幾乎多次想回國。然而就在這個困難時期,他的第一部小說出版了。這個故事講述的是一個富有的商人從一個貧窮的農民那里買棗椰樹的故事。故事發生在大旱的一年,因為旱災,村民們收成不好,勉強度日,但是在這個時候要舉辦宗教慶典,每個人都要為慶典出一份錢。小說的主人公瑪據布是一個貧窮的農民,他沒有錢可以出,只能賣掉自己的棗椰樹來換取,他十分不舍,因為他對樹有著深厚的情感。正當他一籌莫展的時候,他很久之前去了埃及后杳無音信的兒子給家里寄了一筆錢,解了瑪據布的燃眉之急。整部小說細致地刻畫了小人物的喜怒哀樂,表現了薩利赫對于貧苦農民的深切同情。
薩利赫的作家生涯真正開始于1960年,這一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說《瓦德·哈米德棕櫚樹》,這個故事最初發表在雜志《聲音》上,后來成為薩利赫本人乃至當代阿拉伯文學最重要的短篇小說之一。故事發生在瓦德·哈米德的村莊里,這個地點在薩利赫的小說中也頻繁出現。小說的敘事結構類似《一千零一夜》,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將發生在這個小村莊的四件大事串聯起來,組成一個有機整體。小說呈現了村民和政府之間的沖突,政府想要砍掉被村民賦予神圣意義的杜姆樹來修建停泊口岸和農業設施,而村民們卻堅持守護習俗和信仰。這場持久的沖突是與三次事件相結合的,每次都是由政府挑起,政府執著地想要幫助農村進行革新,推動農村現代化,但是這種引導并不是一步一步的,顯得急于求成,因此政府三次砍掉杜姆樹的嘗試都遭到了村民們的抵抗,以失敗告終。在這個故事中,薩利赫的態度就像結尾老人告訴年輕人的那樣,無論是杜姆樹、墳墓、水泵或是蒸汽機,這里的空間都可以容納。薩利赫通過老與少、樹與蒸汽機、村莊與城市、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來探索變革的方式,他理解村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欣賞現代化的優勢,他以一種寬容的態度面對變化,對變化的復雜性有深刻的理解。
中篇小說《宰因的婚禮》(1964)出版后被譯為英、德、意等多國文字在歐洲發行。這部作品以蘇丹這個伊斯蘭國家的鄉村生活、風土人情為背景和色調,生動表現了蘇丹鄉村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系,概述了蘇丹獨立后的若干變化,因此得到阿拉伯乃至國際文壇的高度評價。蘇丹國內的評論家認為該作是研究蘇丹社會關系和民族精神的一部重要參考書。故事發生在一個村莊里,主人公宰因不英俊也不富有,但他心地善良,幽默感十足。他會對村子里漂亮的姑娘一見鐘情,并到處宣揚自己愛上了她,而被他喜歡上的姑娘也會因此而變得遠近聞名,最后竟都嫁給了鄉紳或當地名流。村民們發現了宰因這一“長項”后紛紛籠絡他,讓他認識自己的女兒,然后對外宣揚。于是,宰因就這樣日復一日地幫忙成全著自己喜歡的人和他人的愛情。最后因為自己的善良和幽默俘獲了村里最美麗的女孩兒尼阿瑪的心,兩人戰勝村里人的非議,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宰因的婚禮》展現了薩利赫的希望和夢想:在一個平靜、穩定、和諧、幸福的社會中,所有的問題都能以和平方式化解。有人覺得這是奇跡,而薩利赫在訪談中談到“奇跡”時稱,自己非常尊崇村民們的信仰,他不能肯定世界上沒有超自然的力量,所以如果小說中的一些人物相信這些形而上的信念,作為一個作家,他不會排斥這些信仰、視它們為神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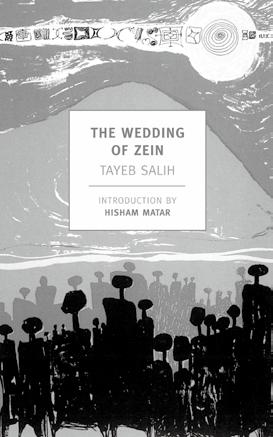
《一捧椰棗》(1964)的故事同樣發生在那個叫瓦德·哈米德的小村莊里。敘述者是一個家庭富裕、聰明又受人喜愛的男孩兒。村里有一個叫馬蘇德的農民因為多次的婚姻而欠下許多債務,為了償還債務,只能將自己家里祖傳的林地賣給男孩兒的爺爺。男孩兒在陪爺爺去監督馬蘇德和家人收獲椰棗的時候,目睹了他的悲慘處境,感受到爺爺和椰棗販子的冷酷無情,對爺爺的行為產生深深的反感。他開始改變對爺爺的看法,不再像從前那樣對爺爺懷著深深的崇敬之情,以至于因為吃下爺爺給的一捧椰棗而感到十分不舒服……
兩卷本的《班達爾·沙哈》仍然以瓦德·哈米德村莊為背景,而這一次薩利赫運用了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將村莊的平淡日常與有關村莊的神話、想象融合在一起。敘述者梅亥梅德從一所公立學校的教師崗位退休后,遵循祖父的遺愿回到自己的家鄉成為一個農民。該書的第一部主要講述的是村莊里的日常生活,比如村長馬祖步年事已高,逐漸失去了治理村子的能力,其位置被人取代;還有傳說中的班達爾·沙哈與他孫子的故事。第二部則主要表現梅亥梅德對于人生的思考與求索。他年輕時愛上了瑪利亞姆,但祖父卻沒有同意他們的婚事;時過境遷,他想象著自己當時如果抗爭而不是順從,或許生活會完全不同……小說中,祖輩與孫輩(比如梅亥梅德祖孫倆、班達爾·沙哈祖孫倆)形成了一種鏡像,薩利赫意欲傳達出一種歷史觀念,即未來似乎永遠在重復著過去。而梅亥梅德回到故土尋根,也體現了蘇丹人對于民族身份根源的找尋。
《移居北方的時節》(1966)被阿拉伯文學學院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阿拉伯小說”,也被挪威圖書俱樂部評為“世界最佳100部小說”之一。《紐約時報》給予它極高的評價:“《移居北方的時節》是阿拉伯人民和非洲人民困境的一個絕妙縮影,他們深陷于對民族文化棄之不忍和對殖民文化受之不甘的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因此這篇小說被認為比任何學術文本都更具指導性。”
小說以“我”從歐洲返回蘇丹的小村莊開始——曾經默默無名的“我”重返家鄉時已拿到了英國一所大學的英語文學博士學位。“我”注意到村莊里有一個名叫穆斯塔法的人舉止言談都與村莊格格不入,他偽裝成一個普通農民,卻在酒醉后背起了英文詩。后來在“我”的詢問下,穆斯塔法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他是第一個移民到倫敦的蘇丹人,24歲就獲得了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并且留校擔任經濟學講師職務。在學術上他十分成功,但卻遭受了新文化的沖擊——他是外來的阿拉伯人,受到人們的歧視。待在倫敦期間,穆斯塔法與許多女人糾纏不清,他隱瞞自己真實的身份,用阿拉伯人特有的異域風情、才華、學識和魅力,使那些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的歐洲女人為他癡迷,甚至為他自殺。他覺得自己用這種方式征服了歐洲女人,他絲毫不為她們的死亡而愧疚,他覺得英國是他要征服的對象。然而,他在瓊妮·莫里斯那里受到了挫敗,他之前引誘女人的招數全都失效,最后他親手殺了瓊妮·莫里斯。穆斯塔法服了7年刑,刑滿釋放后返回蘇丹,結婚生子,在村子里安定下來,過上了隱姓埋名的生活。接下來的故事是,隨著穆斯塔法的神秘失蹤和離奇死亡,“我”成為穆斯塔法孩子的監護人,同時被穆斯塔法的妻子哈賽娜所吸引,但已婚的“我”不能向她表達愛意。一個名叫瓦德·利斯的當地人打算向哈賽娜求婚,哈賽娜的家族強迫她嫁給利斯,但哈賽娜發誓絕不改嫁,最后選擇與企圖強暴她的利斯同歸于盡。“我”對發生的這些事感到震驚,想起了穆斯塔法的密室,發現密室里有全套英式設備的壁爐,四面墻壁擺滿了各種各樣的西方經典著作,連《古蘭經》都是英文版,里面還有油畫和詩稿……穆斯塔法對西方文化的推崇讓“我”深受觸動。
穆斯塔法的人生悲劇反映了當時到歐洲求學的阿拉伯人普遍的困境。在歐洲,他們這些外來者遭受各方面有意無意的歧視,無法獲得歐洲人的真正認同。而回到故鄉之后,他們也并不輕松,回鄉對于他們來說也是一種文化轉變的過程,相當于重新適應一種文化,而這種重新適應的過程同樣無比艱難。他們雖然熱愛自己的故土,卻為它的落后而深感失望,經受過歐洲文化洗禮、對歐洲文化始終無法真正放下的他們也無法融入故土文化;夾在兩種文化中間,他們無法確認自己的文化身份,像一個流浪者無處皈依,穆斯塔法最后的自殺也是一種自我放逐的選擇。
薩利赫在《移居北方的時節》中運用了很多西方現代派的手法和技巧,還用電影手法推動情節發展。比如故事通過兩條平行的敘事線索展開,一條是穆斯塔法過去的經歷,一條是“我”的生活。除此之外,意識流、閃回倒敘、內心獨白、時空交錯、象征等手法的運用,使小說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上看,都是當代阿拉伯文學中的重量級作品。整個故事講述的僅僅是發生在作者故鄉蘇丹小鎮上的一個悲劇,但卻引起了世界性的反響。小說中融進了很多元素,比如阿拉伯景點、伊斯蘭歷史、莎士比亞戲劇、弗洛伊德思想、古典阿拉伯詩詞等等,這些展現了薩利赫強大的語料庫,他仿佛把整個圖書館的知識都裝進了腦子里,呈現于作品中;加之各種戲劇因素如突發事件、激情犯罪、施虐受虐等,使他的作品變得更加鮮活。

《移居北方的時節》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象征和隱喻手法的運用,這為小說提供了一個意義無限豐富的語境。比如,小說中穆斯塔法與白人女性的關系實際上隱喻了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關系,而穆斯塔法的報復性行為暗示了被殖民者與殖民者身份的轉變。此外,小說標題中的“北方”也暗含隱喻,這里的“北方”并非蘇丹的北方,而是指世界的北方,即西方世界。小說鞭笞了西方殖民主義及其“文明”的罪惡,表達了作家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同時也蘊含了對當時蘇丹政府的不滿,對女性解放的期待,深刻剖析了后殖民時期的阿拉伯知識分子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的心路歷程,對阿拉伯文化邊緣化現象進行了反思。
薩利赫熱愛自己的家鄉,贊美樸實的鄉村生活,卻不固守成規,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故鄉的落后和存在的問題。他意識到世界的潮流就像尼羅河北流注入大海一樣不可抗拒,因而理智地看待現代化,不盲目排斥西方文化。他也承認殖民主義和反殖民主義之間存在著歷史深淵,但他知道無休止的爭吵并不能解決問題,因而更傾向于對話與溝通。他以包容的胸懷、溫和的目光注視著蘇丹,關注著蘇丹人民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