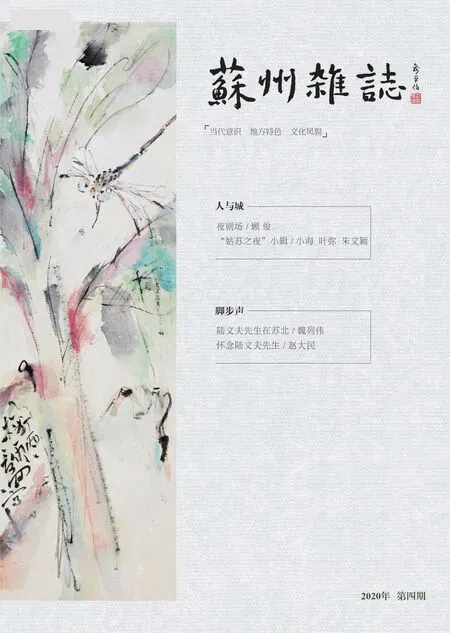夜劇場(chǎng)
顧俊
今年的黃梅季不好過,淫雨霏霏,疫情反復(fù),整個(gè)蘇城陰沉沉濕漉漉,墻角磚縫的青苔快蔓到了胸口。暮色將至,驟雨初歇,一個(gè)人帶把傘出門,穿街走巷地看幾場(chǎng)戲,有點(diǎn)久別重逢的感覺。
因這雨天,掌燈后的古城愈發(fā)顯得氤氳。巷子里石板路上,人是帶著仙氣飄過的。有的看似行色匆匆,一轉(zhuǎn)眼不見了,或許拐進(jìn)一道石庫(kù)門,也看戲去了。以前沒留心,一場(chǎng)雨后,各種“江南小劇場(chǎng)”的演藝如同林間的蘑菇,忽然冒了出來。
何謂“江南小劇場(chǎng)”?顧名思義,就是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小場(chǎng)合文藝演出。強(qiáng)調(diào)兩個(gè)點(diǎn),一是地方風(fēng)情,二是有別于廣場(chǎng)、體育館、大劇院等,屬于規(guī)模較小的演藝活動(dòng)。這也是疫情發(fā)生后,為促進(jìn)消費(fèi)回補(bǔ),繁榮夜間經(jīng)濟(jì),圍繞“姑蘇八點(diǎn)半”推出的文化品牌項(xiàng)目。
我手頭有份蘇州“夜經(jīng)辦”的匯總材料,羅列了“江南小劇場(chǎng)”首批21場(chǎng)劇目的情況。其間,有昆劇、評(píng)彈等傳統(tǒng)劇目,也有兒童歌舞劇、滑稽戲、相聲等,還有一些具有創(chuàng)意的、帶來“沉浸式”體驗(yàn)的綜藝表演。演出主體除了國(guó)有劇團(tuán),還有不少民間團(tuán)隊(duì)和個(gè)體藝人。演出場(chǎng)所也不局限于正規(guī)劇場(chǎng),古宅、園林、會(huì)所、茶館,甚至城墻上、古道邊、石橋頭、假山側(cè),因地設(shè)場(chǎng),自由切換。應(yīng)該說,這些是當(dāng)前蘇州所能見到的,比較主流的劇場(chǎng)演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連著看了幾場(chǎng)演出之后,頗有感觸。涉筆成文,算是一個(gè)本地觀眾劇場(chǎng)外的一些思考吧。
一
鈕家巷潘世恩故居里上演的《金榜題名時(shí)》是“江南小劇場(chǎng)”的劇目之一,也是我今年看的第一部戲。觀演之前,朋友向我推薦,這是蘇州首部室外沉浸式喜劇,創(chuàng)意頗多,笑點(diǎn)滿滿。而且,此劇改編自夏荷生的長(zhǎng)篇彈詞《描金鳳》。狀元府里演錢篤笤,對(duì)蘇州人來說,無疑具有極大的感召力。這個(gè)看點(diǎn)抓得妙。
蘇州盛產(chǎn)狀元,老百姓茶余飯后也愛聊狀元。近的如“紅狀元綠狀元”(指洪鈞與陸潤(rùn)庠),遠(yuǎn)點(diǎn)的如申時(shí)行,他的故事還被編進(jìn)了彈詞《玉蜻蜓》。潘家更了不得,潘世恩是狀元宰相,其孫潘祖蔭又是探花尚書,有清一代,家族中竟有16人折桂,人稱“祖孫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過去遇到潘姓的,蘇州人會(huì)多問一句,倷是“貴潘”呢,還是“富潘”?這“貴潘”就是指做官的潘世恩一族。
現(xiàn)在鈕家巷的潘世恩故居作了狀元博物館,里面有個(gè)紗帽廳,曾經(jīng)是個(gè)書場(chǎng),老蘇州都知道,里面肯定也說過《玉蜻蜓》《描金鳳》。我隨家里大人去聽過書,說的什么早忘了,打了個(gè)瞌銃就聽得醒木一拍下回請(qǐng)?jiān)纾缓笙锟诔粤艘煌胄○Q飩,篤悠悠蕩回家。那時(shí)候,平江路不是旅游地,河埠頭上還有居民洗衣淘米。
沒聽過《描金鳳》的蘇州人大概不多,我外婆以前住吳門橋堍,常有人打趣說,你家和錢篤笤隔壁相鄰!為啥呢?《描金鳳》里交待得清楚,錢篤笤就住在吳門橋堍第三家。要注意,錢篤笤的“笤”字要念成“招”,而且必須用吳音,普通話讀不準(zhǔn),聽起來也別扭。《描金鳳》是部老書,解放前彈詞名家夏荷生把它說活了,人稱“描王”。后來這部書作為蘇州評(píng)彈經(jīng)典書目流傳至今。蘇州滑稽劇團(tuán)還以此改編成大型滑稽戲《錢篤笤求雨》,名噪一時(shí)。
可以說,潘世恩也好,錢篤笤也罷,兩個(gè)人物形象雖然一個(gè)真實(shí),一個(gè)虛構(gòu),但經(jīng)過漫長(zhǎng)的歷史沉淀和文學(xué)勾畫,在蘇州早已深入人心。心里有了這些鋪墊,對(duì)《金榜題名時(shí)》的期待自然不言而喻。
平心而論,當(dāng)天的演出氣氛不錯(cuò),編劇蠻有創(chuàng)意,演員也很賣力,觀眾跟著演員,隨著劇情發(fā)展移步換景,穿堂過院,達(dá)到了互動(dòng)效果,一些小朋友被逗得樂不可支。作為一個(gè)文創(chuàng)劇目,或者一個(gè)娛樂消費(fèi)產(chǎn)品,這部戲本身無可非議。不知道那天的觀眾中有沒有蘇州本地人,是否也和我一樣無法“沉浸”?這種迥然不同的感受,或者說心理的落差究竟因何而來呢?
心理學(xué)有個(gè)理論叫認(rèn)知失調(diào),失望無非來源于期望。這是部相聲劇,演員一開口,就是帶著兒化音的京片子。戲里走出來的錢篤笤等,又與既有概念里的人物形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僅這兩點(diǎn),對(duì)于熟悉這段歷史背景,特別是懷有深厚鄉(xiāng)土感情的觀眾而言,恐怕一時(shí)難以適應(yīng)。
打個(gè)比方吧,元大昌拷冬釀酒、采芝齋買粽子糖、松鶴樓點(diǎn)松鼠桂魚,要的是什么?當(dāng)然就是地道的蘇州味道。創(chuàng)新可以,哪怕是變個(gè)口味也成,不過,千萬慎用老字號(hào)。這倒不是說只有蘇州的好,但既然用了蘇州文化的包袱皮,最好表里一致。何況,演出的地點(diǎn)在蘇州狀元的老宅。蘇州人說這話,似乎有點(diǎn)敝帚自珍。然而,一個(gè)地方的文化積累,形成鮮明的個(gè)性,肯定有堅(jiān)守的東西。一部《描金鳳》最終磨成經(jīng)典書目,傾注了幾代說書藝人的心血。
觀眾隨著劇中的人物穿過廳堂,我止住了腳步。這宅子讓我感覺有點(diǎn)陌生了,茫茫然不知今夕何夕。院子里一株白玉蘭開得正好,清香沁人,這是蘇州初夏的味道。
劇還在演著,越來越熱鬧,我折回潘宅門廳,大門已經(jīng)掩上,外面就是喧囂的街市,不遠(yuǎn)處平江路的夜生活已經(jīng)開始。

☉ 昆劇表演
偌大的門廳里,此刻空落落的,就我和演出方的一位負(fù)責(zé)人。我看到有幾幅海報(bào),是這里上演或合作的劇目,有趙志剛的越劇表演,還有“聲入平江”的項(xiàng)目推介。那位負(fù)責(zé)人告訴我,利用蘇州老宅優(yōu)勢(shì),盤活文化資源,是他們一直致力的方向。《金榜題名時(shí)》的推出就是一種嘗試,希望這里成為戲劇人才的孵化器,打造出更多的蘇州文化旅游品牌項(xiàng)目。
這種嘗試是有積極意義的,繁榮文藝應(yīng)該兼容并蓄。不過,我也直言不諱,說出了自己的感受。接下來,我們的對(duì)話很有意思,觀點(diǎn)有認(rèn)同,也有碰撞。散場(chǎng)之后,他說的幾句話還在我腦海里盤旋。現(xiàn)在的蘇州已是一千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外來人口占比較大,以昆劇、評(píng)彈為代表的的地方曲藝,知音幾人?又有多少新戲可看?再過20年,每天花5塊錢去泡書場(chǎng),這還會(huì)是我們這代人老年生活的消遣嗎?
問題很尖銳,這也正是大家所擔(dān)憂的。其實(shí),莫說20年后,看看身邊的小朋友吧,能講好一口蘇州話已屬難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同時(shí),科技改變生活,各種外來文化如潮涌來。留給蘇州的時(shí)間真不多了。這是危機(jī),也是責(zé)任。為此,我更要說:在蘇州,錢篤笤還是講蘇州話的好。
二
春呵春!得和你兩流連。春去如何遣?恁般天氣,好困人也……
杜麗娘游園身倦,于水榭倚欄而坐,低眉緩緩吟出,昏沉沉睡去。燈光漸暗,樂聲跟著輕了下來。
雨還在下,風(fēng)來,樹葉嘩嘩作響,幾絲細(xì)雨從廊檐前吹過,落在臉頰上,涼颼颼的。《山坡羊》笛聲起,劇中人又唱道:沒亂里春情難遣,驀地里懷人幽怨……此景此身,是在夢(mèng)中,還是園中呢?
那天,我在校場(chǎng)橋路的昆曲傳習(xí)所欣賞《游園驚夢(mèng)》,就在夜雨綿綿的庭院里。所謂“實(shí)景版”戲劇,它與傳統(tǒng)室內(nèi)劇的區(qū)別之一,大概就是與春夏秋冬、雨雪陰晴有個(gè)應(yīng)和吧。演出結(jié)束,我采訪了劇中杜麗娘的飾演者、蘇州昆劇院的青年演員劉煜。我問她,你在這里演戲,與傳統(tǒng)劇場(chǎng)表演的感受有何不同?她告訴我,在這園子里,她已演了7年,觀眾有“沉浸式”的體驗(yàn),演員也是如此。這樣的環(huán)境更容易入戲,與觀眾距離更近,對(duì)演員的表演要求也更高。
其實(shí)“實(shí)景版”“沉浸式”并不時(shí)髦,過去家班演戲也有在室外花園的,只要有一方氍毹,踏進(jìn)去便是戲中人。早在幾百年前,到了八月中秋夜,蘇州人群集虎丘鼓吹弦歌,這邊唱來那邊和,唱的自然是昆曲,不也是實(shí)景演出么?一直唱到夜半三更,“月孤氣肅,人皆寂闃”之時(shí),還有人樂不思?xì)w,登場(chǎng)競(jìng)藝。明代的張岱在《陶庵夢(mèng)憶》里有詳細(xì)的記述。幾年前的虎丘曲會(huì)上,我遇到一個(gè)臺(tái)灣蘭庭昆劇團(tuán)的曲友,她好奇張岱筆下的“聲出如絲,裂石穿云”,特地跑到千人石上試唱了一段,結(jié)果有點(diǎn)失望。實(shí)際達(dá)不到那個(gè)效果啊,難道明代人有麥克風(fēng)嗎?
這當(dāng)然是句玩笑話。反過來說,昆曲的藝術(shù)特性決定了它的欣賞方式,小場(chǎng)合演出,近距離觀摩,是最為適宜的。用蘇州昆劇院原院長(zhǎng)蔡少華的話說,一個(gè)水袖甩出來,就在你的眼門前。或許,就是一個(gè)轉(zhuǎn)身,一個(gè)回眸,讓你一輩子愛上了昆曲。你能感受到“聲出如絲”,我想距離不會(huì)超過五米。我聽到過的最美的聲音,不是在劇場(chǎng),而是在排練廳里。“沉浸式”小劇場(chǎng)演出,就是抓住了這個(gè)特性。

☉ 蘇州昆曲傳習(xí)所園景
現(xiàn)在的昆曲傳習(xí)所是在五畝園原址重建的。20年前,這里還是林機(jī)廠的倉(cāng)庫(kù)用地。蘇州昆劇院接管時(shí),只有礎(chǔ)基和兩個(gè)廳堂的遺構(gòu)尚為舊物,其余幾成廢墟。蔡少華說,這個(gè)地方意義不凡,它是近代昆曲的復(fù)興之地,也是中國(guó)第一所專業(yè)昆曲學(xué)堂。當(dāng)時(shí)就產(chǎn)生了一個(gè)夢(mèng)想,如果真能修舊如舊,不僅為昆曲留下一個(gè)物化的遺產(chǎn),而且還能把昆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把昆曲傳承的形態(tài)展示和保存起來。就為了這個(gè)夢(mèng),一做就是18年。話說起來容易,個(gè)中艱辛,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昆曲傳習(xí)所修葺一新之后,機(jī)緣巧合,引入了北京蘇州商會(huì)加盟,為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市場(chǎng)化運(yùn)作注入了活力。每周六的晚上都會(huì)有一場(chǎng)《游園驚夢(mèng)》在此上演,10年做下來,已成為蘇州昆劇商演的典范之作。企業(yè)方告訴我,即便是最近受到疫情影響,上座率還是維持在七成以上,有時(shí)候甚至一票難求。除了《游園驚夢(mèng)》,接下來他們還將推出《玉簪記》。同時(shí),昆劇高雅的藝術(shù)品位也提升了企業(yè)自身的品牌形象,形成疊加效應(yīng)。這讓他們更有信心,繼續(xù)將小劇場(chǎng)商演運(yùn)作下去。
在昆曲傳習(xí)所,演員拍曲、化裝和道具等,都有開放式的展示,觀眾在看戲之余,能更直觀地了解昆劇歷史,加深了文化體驗(yàn)。對(duì)專業(yè)劇團(tuán)來說,這里作為演出基地,既滿足了日常研習(xí)和排練的需要,也實(shí)現(xiàn)了昆劇的活態(tài)傳承和藝術(shù)呈現(xiàn)。聯(lián)合國(guó)前秘書長(zhǎng)潘基文來傳習(xí)所看過演出,感嘆這是一生中最難忘的文化體驗(yàn)。
守護(hù)歷史文化遺產(chǎn),遵循藝術(shù)發(fā)展規(guī)律,在資源配置上找到最佳的契合點(diǎn),這是劇目運(yùn)作成功的關(guān)鍵。
誠(chéng)然,“江南小劇場(chǎng)”的劇目不可能都有如此高的起點(diǎn)。各自條件不同,劇本是否經(jīng)典,團(tuán)隊(duì)是否專業(yè),場(chǎng)地是否適宜,經(jīng)費(fèi)是否充裕,種種因素都會(huì)影響最終呈現(xiàn)。這里有個(gè)定位問題,不同的定位滿足不同的文化需求。比如說,時(shí)下不少園林和景區(qū)推出的“實(shí)景版”戲劇表演,滄浪亭有《浮生六記》,耦園有《耦園夢(mèng)憶》,還有《尋夢(mèng)山塘》《木瀆往事》等等,這些劇目通過對(duì)當(dāng)?shù)貧v史人文故事的挖掘和演繹,豐富了景區(qū)的文化內(nèi)涵,也增加了游客的觀光體驗(yàn)。這也是一種定位。蔡少華說,“江南小劇場(chǎng)”既為“江南”,還是應(yīng)該體現(xiàn)地域文化特征,說到底是姓“蘇”的。
說句題外話。好幾位朋友對(duì)我講,現(xiàn)在看一場(chǎng)演出,票價(jià)動(dòng)輒幾百,甚至上千元。一家三口過來旅游,一個(gè)月工資看不了幾場(chǎng)戲。“江南小劇場(chǎng)”的劇目消費(fèi)若能貼近民生,顯然更有利于地方曲藝的保護(hù)與傳承。由此,我想起多年前與顧篤璜先生閑談,戲劇如何吸引觀眾,顧篤璜先生說“大世界”的模式可以借鑒。以前白相上海大世界,里面有許多小劇場(chǎng)和小舞臺(tái)。買一張門票進(jìn)去,各種地方戲曲都能看到。不僅消費(fèi)低廉,而且觀眾能有選擇,在有限的時(shí)間里看到許多自己喜歡的戲。
那么,僅靠低廉的票價(jià),是否就能把人拉回劇場(chǎng)呢?時(shí)代發(fā)展到了今天,相比過去的“大世界”,手機(jī)上“刷抖音”還不用花錢呢,手指輕輕一劃就“秒換關(guān)注”了。文藝插上科技的翅膀,似乎一切的需求都能瞬間滿足。將來還有什么不可替代呢?大概唯有親身的體驗(yàn)。這么一想,小劇場(chǎng)的價(jià)值倒是凸顯了。因?yàn)樾。嚯x互動(dòng)交流成為可能。
三
不去劇場(chǎng)看戲,也可到平江路的茶館坐坐。花幾十塊錢買杯茶,能看呂成芳表演兩個(gè)鐘頭。呂成芳調(diào)侃自己屬于隨茶贈(zèng)品。

☉ 呂成芳戲曲表演
很難界定呂成芳的表演形式,反正一個(gè)人一臺(tái)戲,從古琴?gòu)椀脚谩⑷遥汕俑璩嚼デ⒃u(píng)彈,中間各種穿插,吳地歷史、戲曲知識(shí)、時(shí)尚文化、網(wǎng)絡(luò)笑話無所不包,說得興起,她還會(huì)再附贈(zèng)你幾曲,山歌、小調(diào)、地方戲、流行歌任君挑選。“江南小劇場(chǎng)”的劇目單上,稱之為昆曲清口表演,我覺得也不確切,這大約是從周立波的所謂“海派清口”引申過來的。在游客看來,這種形式更像脫口秀。有人慕名跑到平江路,嚷著要找“蘇州的郭德綱”聽?wèi)颉?/p>
茶館說唱,本就為博人一樂。若用專業(yè)藝術(shù)的眼光去看呂成芳的表演,顯然過于嚴(yán)苛,也沒有必要。呂成芳心里清楚自身的價(jià)值在哪里,她說,我不是科班出身,屬于半路出家。我是用說書的方式在推廣昆曲,傳播我所熟悉和了解的蘇州文化。僅此而已。
我那天早早地去了茶館,見她跨進(jìn)門,感覺就是鄰家大姐的模樣,衣著大方,素面,大嗓門,快人快語。我們面對(duì)面坐著,她化裝還是老法做派,蘸了刨花水刮發(fā)片。她一邊貼鬢角,一邊述說著自己的經(jīng)歷。年少時(shí)喜歡文藝,但命運(yùn)坎坷未能如愿。吃過很多苦,也做過很多行當(dāng)。在這茶館里說唱,已近十年。
她粉墨登場(chǎng),立馬變得神采奕奕。臺(tái)上唱念做打揮灑自如,才做了白娘子,又去串許仙,一個(gè)人調(diào)動(dòng)起整場(chǎng)的氣氛。
她的串場(chǎng)詞不全是戲謔打諢,似乎有意在傳遞一些文化信息。比如唱完一段《月圓花好》,她會(huì)告訴觀眾,這歌的詞作者是范煙橋,是伲蘇州人,再講一段范煙橋的軼事。見觀眾來了興趣,她接著說,想找范先生的故居嗎?好,離這里不遠(yuǎn),你到觀前街打聽“啞巴生煎”,范先生以前就住在隔壁。還有,蘇州的點(diǎn)心有特色,有機(jī)會(huì)要嘗嘗哦……
一場(chǎng)演出下來,已經(jīng)十點(diǎn)鐘了。茶客陸續(xù)散去,呂成芳還在簽名售書,幾個(gè)外地過來的“粉絲”搶著與她合影。我贊她是才女,一個(gè)人一臺(tái)戲真不簡(jiǎn)單。她笑了笑說,為了生活。
她告訴我,最近因?yàn)橐咔榈年P(guān)系,一天只演一場(chǎng)。去年端午節(jié),她從下午兩點(diǎn)唱到深夜十二點(diǎn)半,連著加了三場(chǎng),當(dāng)中只歇一刻鐘,吃一塊大餅充饑。那天連軸轉(zhuǎn),最后喉嚨唱啞了。盡管辛苦,一年要演好幾百場(chǎng),但也有收獲,那么多觀眾喜歡她,現(xiàn)在常有人邀請(qǐng)她去講課。
呂成芳曾是文學(xué)青年,當(dāng)年的不少文友現(xiàn)在成了知名作家。她說自己本也可以走這條路,至少不用像現(xiàn)在這樣,每天風(fēng)里來雨里去。我說,蘇州不缺作家,單槍匹馬在茶館里唱十年戲的蘇州女子,你大概是唯一。
她又是苦笑,為了生活。
知道她是“60后”,我們聊起這代人的經(jīng)歷,他們身上似乎有種特質(zhì)。
她點(diǎn)頭,對(duì),都是讀朦朧詩(shī),被崔健“催大”的一代人。我們唱的是《一無所有》,年輕時(shí)想學(xué)吉他,去做流浪歌手,去黃土高原,走得越遠(yuǎn)越好。現(xiàn)在回轉(zhuǎn)來想想,還是蘇州好,越老越愛蘇州了。
她話鋒一轉(zhuǎn),我現(xiàn)在對(duì)生活很感恩,最困難的時(shí)候已經(jīng)過去。用這個(gè)方式補(bǔ)貼家用,還能尋找有緣人,很滿足了。
我看著她卸妝,繡花戲袍脫下,掛起,明天繼續(xù)。
茶館打烊了,我們?cè)陂T口道別,她跨過青石橋,消失在夜色之中。除了才情,除了艱辛,此刻我又想起一個(gè)詞,勇氣。
很多人說呂成芳的《驚夢(mèng)》唱得比《游園》好聽,她自己也這么覺得。我看到一首她寫的詩(shī),其中有這么幾句:你是梅,你是柳/是牡丹亭畔芍藥欄邊癡情的湖山石/是似水流年里不曾移動(dòng)的那一道光。
我喜歡后面一句。她寫這詩(shī)為紀(jì)念已故昆劇藝人金繼家。
呂成芳學(xué)戲轉(zhuǎn)益多師,金繼家與她有緣,曾教過她小生身段,示范七步路該怎么走。就教過這么一次,老先生就駕鶴西去。而今昆劇繼字輩尚存幾人?細(xì)思不免悲涼。去年俞中權(quán)先生過世,我也寫過一篇文章。他是彈詞作家,上世紀(jì)60年代起就開始評(píng)彈創(chuàng)作,許多開篇至今還在傳唱。可惜一生不得志,晚年想將作品結(jié)集付梓費(fèi)盡周折。有些人,沒來得及告別就匆匆離去了。
呂成芳說得沒錯(cuò),昆曲和評(píng)彈那么美好,一定會(huì)和人類同在。無論大舞臺(tái)的綻放,還是小劇場(chǎng)的堅(jiān)守,總有人會(huì)成為似水流年里不曾移動(dòng)的那一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