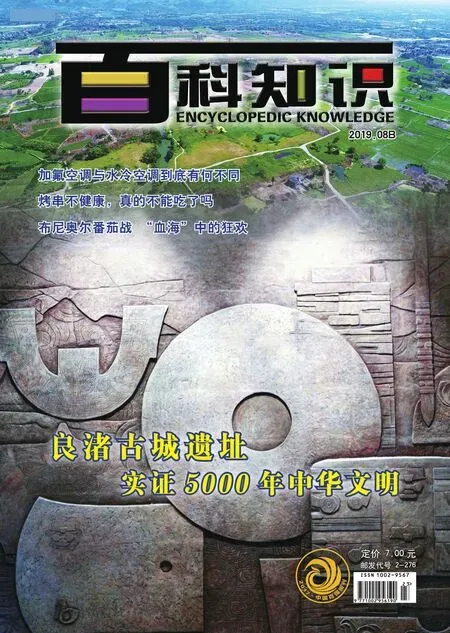石頭是咋形成的
馬志飛
石頭算得上是我們生活中最普通的東西,隨處可見,很少有人真正去留意它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石頭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對于這樣一個看似極其簡單的問題,在地質(zhì)學史上曾經(jīng)掀起過“水火不容”的激烈紛爭。
古希臘的水火之說
在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當科學還沒有成為一種有效的工具時,很多人試圖從傳說中尋找答案。關(guān)于巖石的成因,很多學者一開始就是從傳說中的大洪水來研究的,如女媧補天、大禹治水、諾亞方舟等,在諸多古代文明中都出現(xiàn)過類似的傳說,只是關(guān)于洪水災害發(fā)生的時間不同而已。盡管傳說撲朔迷離,亦幻亦真,但仍有很多人堅信不疑,并努力從傳說中尋找科學的答案。
在回答“萬物的本源是什么”這個哲學問題時,古希臘著名的思想家、科學家和哲學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世界的本源。泰勒斯極度崇尚水,他在對埃及尼羅河水每年的漲退記錄進行研究后發(fā)現(xiàn),每次洪水退去都會留下肥沃的淤泥,還有無數(shù)的幼蟲。于是,泰勒斯得出了這樣的結(jié)論:“萬物源于水。”即水是世界初始的基本元素,地球也是漂浮于水上的。按照他的觀點,地球的巖石也是由水生成的。
后來,古希臘又出現(xiàn)了一位名叫赫拉克利特的著名哲學家。他認為,萬物的本源是火,世界萬物都是由火產(chǎn)生的,即使萬物消亡,也要復歸于火。從他的觀點來看,地球的巖石應該也是由火生成的。
第二次“水火之爭”
如果說,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的爭論屬于第一次“水火之爭”的話;那么,伍德沃德與莫羅的爭論就算是第二次。

伍德沃德(1665—1728年)是英國格雷山姆學院的一位醫(yī)學教授,也是一位地質(zhì)學家。在1695年出版的《地球自然歷史試探》一書中,伍德沃德以傳說的摩西洪水說為依據(jù)論證了水成作用。他認為,洪水曾經(jīng)把地球沖擊得分崩離析,地表的巖石、土壤以及各種雜物都被沖垮,所形成的汪洋大海就是一片包含著各種物質(zhì)的混合物。當洪水退去后,這些物質(zhì)慢慢沉淀,現(xiàn)在的地層也是從洪水中沉積下來的,重的物質(zhì)沉淀到底層,輕的東西沉淀在上層,之所以還能在高山上發(fā)現(xiàn)海洋生物的化石,正是由于它們比較輕。
安東·拉扎羅·莫羅(1687—1764年)是意大利威尼斯一所修道院的院長。他認為,地質(zhì)變化的原因在于地球內(nèi)部熔巖的運動,正是由于熔巖的運動,引起了火山爆發(fā);待熔巖冷卻之后,包裹著其中的生物遺骸堆積成了新的巖層;所以,高山上發(fā)現(xiàn)的海洋生物化石并不是洪水造成的,而是火山作用的結(jié)果。

用現(xiàn)在的觀點來看,伍德沃德與莫羅的認識都存在明顯誤區(qū),但與之前古老的哲學觀點相比已經(jīng)有所進步。盡管他們二人都過于強調(diào)水或火在地質(zhì)變化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但都承認世界物質(zhì)的復雜性和變化性,突破了把世界的本原簡單地歸結(jié)為水或火這樣具體的物質(zhì)形態(tài)的局限性,這種思想與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的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
這兩次爭論都為第三次爭論,即維爾納和赫頓的爭論做好了鋪墊。
維爾納的“水成論”
英國著名的化學家波義耳曾發(fā)現(xiàn),鹽能從溶液中結(jié)晶出來,這為德國弗賴貝格礦業(yè)學院的亞伯拉罕·戈特洛布·維爾納(1749—1817年)教授的新觀點提供了理論支撐。維爾納出生于礦業(yè)家族,從小就對礦物學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不僅狂熱地收藏各種礦物,還對巖石進行過深入研究。通過對巖石的觀察,維爾納認為,地球上所有的巖石都是從大洋深處“結(jié)晶”或“沉淀”出來的。這就是所謂的“水成”觀點,該觀點支持的理論便是“水成論”。
“水成論”的主要觀點認為,地球上的一切巖石都是在水中沉積形成的—注意,這里說的是“一切巖石”。維爾納認為,在地球早期,地表全部被原始海洋(混沌水)所淹沒,從海水中不斷沉淀、結(jié)晶出來的物質(zhì)慢慢形成了巖石。它們按照先后順序進行沉積,早沉積的位于下面,越往上的沉積越晚。首先沉積的是花崗巖,被稱為“原始層”,它們是覆蓋在地球表面的第一批巖石,也是地球上數(shù)量最多的巖層。后來,原始海洋的水位逐漸降低,“原始層”露出水面,遭受侵蝕,然后再次沉積,這便是第二批巖石,主要為粗砂巖、石灰?guī)r等,為“過渡層”。最后,“過渡層”上面再沉積下來一些含有化石的巖層,為由松散泥沙組成的“沖積層”。


總而言之,在維爾納的觀點里,水是形成巖石的根本力量。可是,火山活動又該如何解釋呢?維爾納解釋說,那是因為煤和硫磺在地下燃燒,玄武巖則是它們?nèi)紵蟮幕覡a。
維爾納是一位能言善辯之人,他不僅是一位科學家,還稱得上是一位演說家,他總能自圓其說,滔滔不絕,妙語連珠,讓聽眾沉浸于他的理論中如癡如醉。據(jù)說,當年很多人慕名而來,投奔到其門下學習地質(zhì)科學。維爾納由此培養(yǎng)了一大批人才,當然,基本上都是自己學術(shù)理論的追隨者以及維護者。維爾納被后人尊稱為“德國地質(zhì)學之父”。
實際上,維爾納是一個只注重理論思考而不善于進行野外考察的地質(zhì)學家,這也可能與他一生體弱多病有關(guān)。維爾納的一生幾乎都是在弗賴貝格度過的,他的腳步從未踏出過德國薩克森州以外的任何地方。對于地質(zhì)學家而言,如果不到野外進行實地考察,只憑自己的想象和空泛的理論去解釋地質(zhì)現(xiàn)象,總會出現(xiàn)一定的偏差,甚至是錯誤。
根據(jù)現(xiàn)代地質(zhì)學的觀點,說巖石是水成的確實具有一定道理,只不過,并非所有的巖石都是水成的。地質(zhì)學界曾經(jīng)有過“水成巖”的稱呼,但現(xiàn)在我們稱這種因沉積作用形成的巖石為沉積巖。它們的覆蓋范圍很廣泛,大約占地球表面的73%;但沉積巖只是地殼上部薄薄的一層而已,實際上,它們占地殼巖石總體積的比率很小,只有8%左右。
赫頓的“火成論”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水成論”統(tǒng)治著學術(shù)界,不過,還是有一些問題用該理論無法解釋清楚:既然巖石是洪水和海洋沉積的結(jié)果,那么,洪水過后,這些水都去了哪里呢?
1726年,在蘇格蘭一戶富裕的家庭里,一位名叫詹姆斯·赫頓(1726—1797年)的男孩誕生了。這是一位怪人,他在少年時期就表現(xiàn)得與眾不同。最初,他喜歡的是醫(yī)學,學了不久就心生厭倦而改學農(nóng)學。在繼承了父親的一座農(nóng)場之后,赫頓有了大量的時間到野外進行觀察;于是,他對地質(zhì)學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興趣,經(jīng)常好奇地觀察見到的每一個洼坑、溝谷和河床。最終,赫頓將自己的目光盯在了地球的巖石上。到了晚年,赫頓最終自學成才,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785年,年近60歲的赫頓在蘇格蘭高地的凱恩戈姆山進行考察時發(fā)現(xiàn),這里的花崗巖呈巖脈狀,具有從一個大巖體向外侵入圍巖的分枝,圍繞著花崗巖的圍巖石灰?guī)r還出現(xiàn)了變質(zhì)現(xiàn)象。這表明,當時的花崗巖是在上覆巖層形成以后才侵入的。也就是說,花崗巖的年齡應該比圍巖年輕,而且這里出現(xiàn)了熔融現(xiàn)象。這說明,花崗巖是熾熱的熔巖冷卻之后形成的,而不是從水中結(jié)晶出來的。這與當時流行的“水成論”明顯不符。
經(jīng)過詳細的研究,赫頓寫了一篇很長的學術(shù)論文,并在愛丁堡皇家學會的會議上宣讀,題目是《地球?qū)W說,或?qū)﹃懙亟M成、瓦解和復原規(guī)律的研究》。遺憾的是,沒有人對他的論文感興趣,原因并不是赫頓的研究內(nèi)容沒意思,而是他的語言表達實在令人著急。赫頓那蹩腳的文字和枯燥的敘述讓每一個聽眾都昏昏欲睡,沒有人聽得懂赫頓到底在講些什么,甚至有人毫不客氣地說他“幾乎完全不懂得怎么使用語言”。
后來,赫頓的朋友勸他將自己的理論再豐富一下,講得更透徹一些。于是,赫頓花了整整10年時間,于1795年寫出了兩卷本的巨著《地球的理論及其證據(jù)和解說》。沒想到,事情還是很糟糕,這部將近1000頁的鴻篇巨著依舊沒有人能讀懂—確切地說,是沒有人愿意去讀。就這樣,直到1797年赫頓病逝,也幾乎沒有人理解他的偉大理論。

要不是后來赫頓有一位文筆極佳的好友來幫忙,恐怕我們永遠都不知道他的成就有多么重要。愛丁堡大學的數(shù)學教授普萊費爾(1748—1819年)稱得上是赫頓的人生知己,為了傳播赫頓的學術(shù)思想,他對赫頓的著作進行了深入研究,并親自到很多國家進行野外考察,重新整理了赫頓的理論,普萊費爾在1802年寫出了著作《關(guān)于赫頓地球理論的說明》。這是一本數(shù)學家所寫的關(guān)于一位地質(zhì)學家的地質(zhì)理論的簡寫版,竟然比原著者本人闡述得還要清楚,其中還著述了一些普萊費爾自己的地質(zhì)發(fā)現(xiàn),可謂是一部奇書。從此之后,赫頓的理論才被慢慢傳播出去,不僅形成了“火成論”的系統(tǒng)學說,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和繼承者,而且為赫頓帶來了巨大的榮譽,后世尊稱他為“現(xiàn)代地質(zhì)學之父”。
“火成論”的主要觀點包括:火成作用是主要的地質(zhì)作用,陸地上的花崗巖和玄武巖是由巖漿形成的;水成作用也是一種重要的地質(zhì)作用,陸地上的巖石受到風雨和流水的侵蝕,然后流向海洋并沉積下來,固結(jié)以后形成巖石,升出海面以后才形成了陸地。這也就意味著,雖然赫頓提出了“火成論”的觀點,但并沒有完全否認“水成論”。
地質(zhì)學的研究過多地依賴于觀察,缺乏實驗研究,所以當某種新的理論提出以后很難得到證實。不過,在“火成論”提出后,有人通過實驗幫了赫頓一個大忙。蘇格蘭的詹姆斯·霍爾(1761—1832年)原本是赫頓的反對者,雖然曾與赫頓一起多次到野外考察,但他仍然懷疑赫頓的理論。后來,霍爾做了一些實驗,逐漸轉(zhuǎn)變了原來的看法,成為赫頓的重要支持者。
維爾納“水成論”的追隨者認為,熔融的巖石不會結(jié)晶,只能像火山噴發(fā)那樣,變成玻璃狀的東西。但是,霍爾在玻璃廠中觀察到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如果讓熔融的玻璃非常緩慢地冷卻,它就會變成白色不透明的結(jié)晶體;再次熔化之后,如果讓其快速冷卻,它就會變成透明的玻璃狀態(tài),重新恢復玻璃光澤。霍爾由此認為,熔巖應該也是這樣。他從火山附近取回來一些暗色的巖石,放在鐵廠的高爐里熔化,結(jié)果正如他所料:如果讓其緩慢冷卻,這些巖石會結(jié)晶成與原來一樣的暗色巖;如果讓它們快速冷卻,巖石會變成玻璃狀的東西。霍爾的實驗證明了那些暗色巖就是熔巖緩慢冷卻的產(chǎn)物。
維爾納“水成論”的追隨者還認為,石灰?guī)r在受熱時會分解,而不會變質(zhì)成為其他巖石。針對這樣的觀點,霍爾花了六七年的時間,做了500多次實驗,證明了石灰?guī)r在低壓加熱時并沒有分解,而是的確變成了別的巖石—大理巖。
根據(jù)現(xiàn)代地質(zhì)學的觀點,地球上的巖石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火成巖,它們是巖漿在地下或噴出地表后冷卻凝結(jié)而成的,大部分為結(jié)晶質(zhì),只有小部分為玻璃質(zhì)。火成巖是組成地殼的主要巖石,從地面到深達16千米的地方,火成巖的體積幾乎占了90%。
究竟誰是勝利者
“水成論”與“火成論”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特別是在1790—1830年間,爭論最為激烈。在1807年成立的倫敦地質(zhì)學會中,13名會員無一贊同“火成論”;第二年,該學會增加了4名會員,也只有1名會員支持“火成論”。后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支持赫頓的陣營。據(jù)說,這兩種學說各自組成了學派,為了一爭高下,他們在蘇格蘭愛丁堡的一座古堡里展開了現(xiàn)場辯論。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場學術(shù)辯論最后竟然演變成了一場“罵戰(zhàn)”,雙方相互指責和謾罵,甚至還發(fā)展到了斗毆的地步。這場看似可笑和有辱斯文的爭斗,其實恰恰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執(zhí)著的科學追求。正所謂“亂世出英雄”,當時的確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地質(zhì)學家。
德國著名的科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1769—1859年)當年在弗賴貝格礦業(yè)學院學習時曾是維爾納的學生,深受老師的影響,原本是“水成論”的堅定支持者;然而,隨著參與野外考察的次數(shù)越來越多,洪堡對火山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刻,最終意識到自己老師的觀點存在問題,于是洪堡拋棄了原來的觀點,成為“火成論”的支持者。
克里斯蒂安·利奧波特·馮·布赫(1774—1853年)也是維爾納的學生。在進行野外考察時,他親眼目睹了火山噴發(fā)時熔巖從火山口流出的情形,后來還發(fā)現(xiàn)了熔巖流普遍存在的事實。這些現(xiàn)象都無法用維爾納的“水成論”進行合理的解釋,最后,布赫也不再堅持維爾納的觀點,轉(zhuǎn)而支持“火成論”。他還因此被人譏諷說:“1789年,以一個‘水成論者離開了德國;1802年,卻以一個‘火成論者回到了家中。”
多比松(1769—1841年)是另外一位“倒戈”的科學家。他先前也極度推崇維爾納的觀點,但是后來,他觀察到玄武巖直接覆蓋在花崗巖之上,根本沒有什么煤層的存在,順著這些玄武巖查找源頭,最后發(fā)現(xiàn)的就是火山口而已。后來,多比松公開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勇敢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在真理與師生情誼面前,這些科學家并沒有被學術(shù)權(quán)威嚇倒,而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真理,因為真相只有一個。在科學研究面前,在自然、客觀規(guī)律面前,一時之間出現(xiàn)錯誤認識在所難免,如果能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并及時糾正,而不是固執(zhí)己見,才算是掌握了科學的真諦。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水成論”一度占據(jù)下風,差點被完全擊敗。在這關(guān)鍵的時候,德國著名文學家歌德(1749—1832年)站出來幫了它一把,補充和發(fā)展了“水成論”。歌德的文學造詣很高,他創(chuàng)作有《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等享譽世界的偉大作品;不過,很多人未必知道,他也是一位喜歡探索自然的科學家。在歌德的文學作品中,我們經(jīng)常能夠看到他對山川的描述,言語之中滲透著他對自然變化的認識和思考。在他的代表作《浮士德》中,就突出描繪了水神和火神的矛盾沖突,借此來表現(xiàn)“水成論”與“火成論”的斗爭。歌德是“水成論”的支持者,在他寫作的《論花崗巖》這篇論文中,花崗巖被認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巖石,是“原始巖石”,早于一切生命,超越一切生命,亙古以來毫無變化,其他一切巖石和地形都是在圍繞著原始花崗巖的海洋退去以后由剝蝕的碎片沉積而成的,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海水廣闊的懷抱里”發(fā)生的。不過,后來,隨著地質(zhì)學知識的不斷拓展,歌德開始覺得,“火成論”似乎也有些道理,于是,他就試圖調(diào)和這兩種對立的觀點。
從表面上看,地質(zhì)學歷史上的“水火之爭”以“水成論”完敗而告終,但實際上,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水成論”為何能夠長期占據(jù)優(yōu)勢?一方面,這主要是受到了當時某些勢力的壓抑,畢竟,“水成論”的觀點更符合“神創(chuàng)論”思想,關(guān)于遠古洪水的傳說大多來自于這些思想;另一方面,赫頓對他的理論解釋和宣傳做得不夠。維爾納和赫頓的故事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道理:在關(guān)鍵時候,“能說會道”是多么重要。

那么,“火成論”真的勝利了嗎?用現(xiàn)在的視角來回顧一下他們的觀點,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實,這些觀點都存在片面性,都是從不同側(cè)面揭示了一些地質(zhì)現(xiàn)象的成因而已。以維爾納為代表的“水成論”過分強調(diào)地球的外力作用,甚至把花崗巖和玄武巖都理解為原始海水結(jié)晶的產(chǎn)物,忽視了地球的內(nèi)力作用;“火成論”則強調(diào)內(nèi)力作用,即火山和地震的作用,就連地表的起伏與地殼變遷都被理解為洋底在地球內(nèi)部地下火的作用下上升運動的結(jié)果。
這場“水火之爭”真的結(jié)束了嗎?其實并沒有。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搞明白了,地球上的巖石不僅僅只有沉積巖和火成巖,還有第三大巖類—變質(zhì)巖,它們彼此之間可以相互轉(zhuǎn)化,不斷循環(huán)。雖然現(xiàn)在地質(zhì)學界已經(jīng)沒有純“水成論”和純“火成論”的說法,但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還存在著爭論,巖石學中的“花崗巖化論”和“巖漿論”之間,礦床學中的“熱液礦床”和“同生礦床”之間的爭議,也還是“水火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