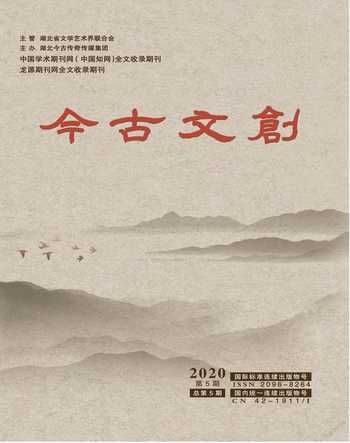衡陽抗戰文化的歷史淵源
【摘要】 衡陽抗戰文化內容豐富、歷史淵源深厚,充分吸納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抗戰文化、湖湘文化的精華,在衡陽保衛戰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因為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兼具衡陽本土吃得苦、霸得蠻、耐得煩、不怕死的蠻勁、狠勁。衡陽軍民在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時,不畏強敵、不懼犧牲與日軍鏖戰四十七天,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激發了中華民族的抗戰斗志,并導致東條英機內閣垮臺,創造了中國抗戰史上的戰爭神話。雖然戰爭已經過去76年,但那場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寶貴精神財富,是先烈們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鑄就的,也是中華民族在歷經磨難和艱苦斗爭中凝聚起來的,在今天仍然值得弘揚和傳承,銘記歷史、警鐘長鳴。
【關鍵詞】 文化;抗戰文化;抗戰精神;衡陽保衛戰;湖湘文化
【中圖分類號】G12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05-0059-03
自近代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里,中華民族屢遭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和難以磨滅的記憶。中國社會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別是日本對中國的瘋狂侵略,給人們帶來了慘絕人寰的災難,所到之處盡是荒涼凄慘的景象,燒、殺、搶、掠無所不用極致,國破家亡、民不聊生,中華大地狼煙四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中華兒女擰成一股繩,形成合力,結成最廣泛的愛國抗戰同盟,齊心協力、共赴國難與日本侵略者死戰到底,譜寫出一曲極其悲壯而慘烈的贊歌。中華民族的抗戰史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偉大的斗爭史,改寫了自鴉片戰爭以來被侵略、蹂躪的屈辱歷史,增強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捍衛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成果。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仍然要銘記這段痛苦的記憶,感知中華民族的今天來之不易,珍惜當前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繼續弘揚抗戰精神、斗爭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一、抗戰文化的相關理論闡述
(一)文化的理論闡述
文化的含義很多很廣,內涵十分豐富,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見解,目前中外學者對它的解析和定義有多達300多種,尚無統一的定義,普通人對“文化”的理解為通過了解自然和人類社會各種現象而對天下民眾實施教育感化的一種方法。寓意社會狀態、風土民情、人倫規范、社會關系等。文與化兩字合用最早追溯到漢朝,在西漢劉向的《說宛·指武》中說:“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1]其寓意就指古代君王圣人對國家的治理,首先是依靠文化和道德使民眾臣服歸順,不服者,然后才通過武力給予鎮壓來臣服。這不難看出文化作為國家治理的一種工具或者方法。這也是我國古代文獻資料中最早出現文化一詞的出處。在中國古代,文化更多的體現在“文治教化”的層面,其中的精神內涵遠遠大于物質內涵。中國現代意義上有關“文化”的概念,出現在清末明初時期,從日本流傳回來,經過日文而翻譯成漢語“文化”,大學者梁啟超是中國近現代以來最早使用文化一詞的學者之一,其在1901年發表的《義和團有功與中國說》一文中就兩次提到了文化一詞,如“當往昔文化未開之代,爭城爭地……風教之盛,文化之隆”。文化的定義在1996版辭海里對文化的解釋,廣義解釋為人類在社會實踐中獲得的物質、精神的生產能力和創造的物質、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解釋指精神生產能力和精神產品,包括一切社會意識形式: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社會意識形態。文化是由人類創造并傳承的,并有其自身的特點,是人在與自然界交往的過程中不斷進行能量與信息的交換,將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不斷地融合形成特有的生產生活形態、風俗習慣、行為思想、語言、文字、宗教藝術等,既有物質方面也有精神方面,還有意識形態等方面,其內涵、外延豐富多樣。
(二)抗戰文化的理論闡述
抗戰文化形成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全民族面臨空前危機,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入侵,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打擊日本帝國主義而產生的一切有利于抗戰的文化。“它以民族大義為前提,以多元政治為基礎,多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文化,既真實地反映了中華民族、中華大地所經歷的生死浩劫,也熔鑄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偉大靈魂。”[2] 通過文學、戲曲、新聞、電影、音樂、美術等等各種形式,最大限度地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支持和加入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野蠻入侵的歷史洪流之中,喚醒人民群眾的覺醒,為積極抗戰、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它具有特定的時代性、階層性、地域性、黨派性等特性。它看不見、摸不著,但卻能夠突破地域、民族、黨派、國界的間隙與隔閡,在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期,發出時代最強音,鼓舞士氣、振奮人心、凝心聚力,團結起國內外一切中華兒女以及支持和擁護中國抗戰的國際友人。它具有強心針和助推劑的功效,對全社會抗戰氛圍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對抗戰的貢獻是巨大的,也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精神文化財富。
(三)衡陽抗戰文化的理論闡述
衡陽抗戰文化產生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衡陽保衛戰前后,一切為抗日或者有利于抗日的文化,是文化領域開展抗戰的一種表現形式,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衡陽保衛戰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被譽為東方的莫斯科保衛戰,在中國抗戰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在敵眾我寡,敵強我弱,敵我軍力對比十分懸殊的背景下,能夠堅守47日之久,難能可貴,守城時長在中國抗戰史上僅次于淞滬會戰的92天,雖然失敗了,但它的影響力和戰力是驚人的,大大延緩了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戰略步伐,死死拖住日軍主力,為大后方組織備戰和進行戰略大轉移贏得寶貴時間,同時也為太平洋上的盟軍對日作戰贏得最佳戰役期,不僅在中國抗戰史上有驚天的影響力,放在整個二戰期間也有重要的影響力,有利地推動了中國抗戰的勝利。衡陽抗戰期間的抗戰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文化存在,反映出廣大人民群眾為追求民族獨立解放,抗擊日本侵略的迫切愿望,主要表現為新聞、理論宣傳、文藝作品、戲曲、電文、電報、通訊稿、舞蹈、演講、游行等多種形式,堅持以“抗戰、團結、民主”為旗幟,團結衡陽人民一致抗日,掀起了一股文化抗戰的新浪潮,極大地鼓舞了衡陽廣大人民踴躍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洪流中,將衡陽人民面對強敵時共赴國難,面對災難時同舟共濟的霸蠻血性展現得淋漓盡致。
衡陽抗戰文化孕育著衡陽抗戰精神,為衡陽抗戰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和支撐,抗戰后成為衡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建設文化強市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歷史意義。[3]衡陽抗戰文化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傳承和發展而來的,充分吸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基因,[4]同時也吸收了湖湘文化的精華,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抗戰時期的不斷發展,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衡陽抗戰文化的歷史淵源
(一)動力來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
衡陽抗戰文化的發展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在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發展的歷程中,逐漸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優秀傳統文化,如團結愛國、和平友愛、自強不息、勤勞勇敢等文化標識。特別是在幾千年的文明進程中,遭受到無數次外來侵略,中華大地遭遇到空前災難,在挫折和災難面前,中華民族變得越來越勇敢,越來越團結。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踐踏中華大地,草菅人命、無惡不作,用大炮轟開了中國大門,同時也喚醒了沉睡的雄獅。一批不平等的喪權辱國的條約,深深地刺痛了中華兒女的敏感神經,喚起了人們對祖國的熱愛、對列強的痛恨,列強的每次瓜分,都讓大家不斷成長和團結。在災難降臨時,中華民族不再沉默,用自己的吶喊和行動喚醒無知和愚昧。經過歷史的錘煉,逐漸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精神品格之一,衡陽抗戰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愛國主義精神的熏陶,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直是中華文明不斷前進的動力和紐帶。回顧人類文明發展歷程,四大文明古國,唯有中華文明沒有斷流和消失,這與愛國主義精神的傳承和延續存在一定的關系。在愛國主義旗幟下,各民族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共同維護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統一,雖然在歷史長河中有合有分,但終究歸于一統。愛國主義始終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動力,推動中華民族薪火相傳,代代延續。面對強敵入侵,人們奮不顧身、踴躍參戰,給敵寇沉重地打擊。近現代以來涌現出一大批民族英雄如林則徐、馮子材、關天培、左宗棠等。他們的英雄壯舉激發了中華兒女反抗強敵入侵的斗志,推動了愛國主義運動的高漲,這也是衡陽抗戰文化發展的原動力和來源。
(二)思想基礎:中國抗戰文化的蓬勃發展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華大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災難,日本帝國主義打開了侵略中國的大門,中華民族遭遇到了空前的民族危機。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加快了侵華戰略步伐,并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妄圖三個月消滅中國,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一大批城市淪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盧溝橋事變點燃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烽煙,在事件發生的次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華民族的危機意識和危機感得到了極大的喚醒,全國性的抗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1937年8月,國共兩黨達成協議,形成廣泛的共識,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全民抗日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戰進入新時期,形成了全體中華兒女摒棄前嫌、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奮勇殺敵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國運動的熱潮,工、農、商、學各界紛紛舉行抗日游行示威和罷工、罷課、罷市等活動,號召全民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全國各族人民。衡陽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相繼成立衡山、衡陽人民抗敵后援會和衡陽人民敢死挺進隊、湘南赤色游擊隊,為支持抗戰興建湘桂鐵路,為宣傳抗日救亡運動開設“讀者書店”(后改為“湘江書店”),一大批報紙來衡陽出版,如《正中日報》《大剛報》《新階段旬刊》《獅子吼》《開明日報》《力報》《青年界》等,極大地宣傳了抗日主張,激發了衡陽人民的抗戰熱情,為衡陽抗戰文化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三)個性特質:湖湘文化的熏陶
衡陽地處衡山之南,謂之陽,故稱衡陽,位于湘江中游,湘江、耒水、蒸水合流處,故有“三道水口鎖大江”的美譽。衡陽是湖湘文化重要的發祥地之一,相傳“北雁南飛,至此歇翅停回”,故又雅稱“雁城”。衡陽擁有2000多年文字可考的歷史,積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湖湘文化是源自荊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南下經過激勵的碰撞、交融、吸收而形成的。由于湖湘大地處在群山懷抱之中,交通閉塞,本土的苗蠻、荊楚文化鑄就了湖湘人的民風、民俗、心理個性, 其特殊封閉的地理環境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了——忠直、倔強、剛烈、偏執的湖湘民性。這種民性與湖湘封閉、保守的特殊地理環境有關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閉性與非理性的生存特征。在宋代以前湖湘大地沒有正統的思想體系和思想學派,這與中原思想文化的思想學派形成巨大的反差,湖湘文化只能以較低端的民俗文化形態存在。[5]到宋代中原文化對外傳播以后,中原文化南下湖湘大地,自宋代周敦頤提出湖湘理學概念以來,胡國安胡宏父子在南岳創立了湖湘學派,并迅速成為主流統治性文化廣泛傳播,經過程氏二兄弟(程顥、程頤)、朱熹、張栻、王船山等人的進一步發展和傳承,形成了完整的湖湘文化理論體系。
湖湘文化既融合了中原文化,也突出了楚文化底色,楚文化是一種重情感、重想象、重浪漫理想的文化,比較重視家鄉情節,戀鄉、戀家情節較濃重,更多地表現為崇祖、忠君、愛國的文化特質。屈原在《離騷》中寫道:“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豪邁的詩句一直流淌在湖湘人的血脈里,代代傳承,激勵一代代湖湘人忠君愛國、誓死護國的霸蠻血性,塑造了湖湘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寧死不屈、血戰到底的霸蠻個性。在西漢司馬遷所著的《史記·項羽本紀》中記載楚國的南公的一句名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真實地反映出楚人無比堅強的抗敵意志。乃至近代湘人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有“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驚世絕句,勁敵當前湖湘人以命相搏、誓死抗爭的意識極為強大。湖湘文化中的“天下”情懷和敢想敢干不怕犧牲的殉道精神推動中國革命不斷前行,戊戌變法后,譚嗣同拒絕逃脫勸告,決心一死,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就是湖湘文化的特有基因“犟”勁和血性,認死理,一條道路走到黑,不撞南墻不回頭,不到黃河不死心,心憂天下、舍我其誰、敢于犧牲的英雄氣概讓人血脈僨張。“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書。每當中華民族面對空前危機時,湖湘人胸懷天下、心憂民眾、吃得苦、霸得蠻、不怕死、耐得煩的秉性,剛強與血性展現得淋漓盡致。
衡陽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一部分,也稱之為衡湘文化,既繼承了湖湘文化的所有特點,又具有鮮明的地域特性,既具有湖湘文化經世致用、心憂天下、敢為人先、實事求是、兼容并蓄的共性特點,也有自身文氣重、霸氣足、蠻氣足、骨氣強等個性特質。并且擁有濃烈的愛國情懷和憂國憂民的責任擔當,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特質比較強烈。涌現了一大批為民族、國家勇于犧牲的英雄事跡,1276年衡陽人李芾(任潭州知州)誓死抵抗元軍對潭州城的進攻,率三千殘兵弱將堅守三個月,在最后時刻,全家33口人主動殉國,自己也自焚身亡, 忠烈敢死的性格,最終感動元軍將領阿里海牙免予屠城。這些為國為民的英雄壯舉在衡陽大地上隨處可見,夏明翰、唐群英、羅榮桓等一批具有強烈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特質的代表人物,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激勵著衡陽人民世世代代沿著救國愛民、胸懷天下的湖湘文化精神一直走下去。
四、結語
衡陽保衛戰已經距今76年了,它給衡陽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下,衡陽城變成一片廢墟,全城只剩下幾棟完整的房子,到處是荒涼衰敗的景象,災情全國第一。它給人們帶來的傷痛記憶至今也無法抹去,歷史是一面鏡子,只有不斷反思歷史、總結經驗教訓,才能不挨打,不被欺凌,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天正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所面對的各種風險和挑戰依然十分艱巨,國際國內環境日趨復雜,國際反華遏華勢力從未停止對中國的圍堵打壓。回望歷史,不懼怕威脅,展望未來,有信心和能力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自己的戰略發展布局,必然能戰勝各種困難險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1]劉向.說苑校正[[M],北京:中華書局,1987.
[2]范松.論抗戰文化遺產的定義分析及其他[J],貴州社會科學,2010,(8):135.
[3]羅娟.衡陽抗戰文化研究[D],南華大學,2017:13.
[4]張文.桂林抗戰文化及其當代價值研究[D],山東大學,2018:31.
[5]羅宏,許順富.湖南人底精神:湖湘精英與近代中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作者簡介:
彭志剛(1985-),男,湖南祁東人,中共衡陽市委黨校、衡陽市社會主義學院公共管理教研室講師,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抗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