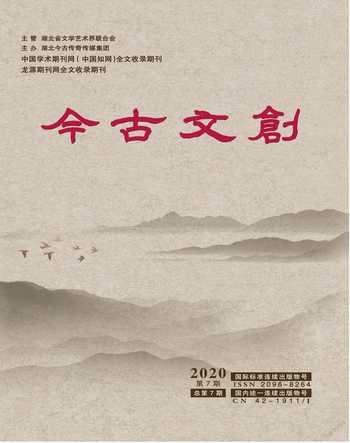晚清民初繼承傳統的《史》《漢》接受研究
【摘要】 晚清民初《史記》《漢書》接受研究與之前的研究呈現出不同的特征,白話寫作和文言研究專著并存;傳統研究方法如考據和評點仍然存在,如陳衍、李景星等人的研究;另外,也出現了新的研究視野和方法,如林紓、梁啟超等人的開拓。本論文重點探討晚清民初傳統派的《史》《漢》比較和接受。
【關鍵詞】 晚清民初;史記;漢書;接受
【中圖分類號】I20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07-0037-02
本論文系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晚清《史記》接受研究”(14YBA070)研究成果。
接受美學興起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聯邦德國。該理論認為,文本的存在意義和價值依賴讀者的闡釋,文學作品內涵的體現和豐富取決于讀者,因而將讀者置于第一位,提出了以讀者為中心的文學理論。堯斯、伊瑟爾、鮑列夫、伽達默爾等文論家都對接受美學進行過闡述和完善,雖然接受美學至今仍然存在各種矛盾,但興起之后,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中國古代文學也引入了接受史理論,學者們對諸多經典從讀者接受的角度作了精到的分析,擴展了研究視域。2002年俞樟華、虞黎明《走向<史記>接受史研究》一文,提出從效果史、闡釋史、影響史三個方面來研究《史記》的接受。
晚清民初《史記》《漢書》接受研究與之前的研究呈現出不同的特征,白話寫作和文言研究專著并存;傳統研究方法如考據和評點仍然存在,如陳衍、李景星等人的研究;另外,也出現了新的研究視野和方法,如林紓、梁啟超等人的開拓。傳統研究與現代視野相互交融,互為糾偏,為《史》《漢》研究增加了新的風貌。總體上看來,這一時期研究者人數有限,專門的研究者不多,但與西學東漸下的其他學術研究一樣,他們的觀點體現了傳統研究與現代研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背離,因而值得關注,姚苧田、陳衍、李景星、劉咸炘、梁啟超等都對《史記》或《漢書》發表過自己的看法。本論文重點探討晚清民初傳統派的《史》《漢》比較和接受研究。
一、姚苧田的《史記菁華錄》
姚苧田的《史記菁華錄》運用傳統的評點式研究方法,作者并沒有對《史記》進行全部評點,而是“抽挹菁華,批導窾卻,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有針對性的選取部分篇章和文字,作細致的研究和評價,他擇取的列傳共三十三篇,世家為九篇,本紀、表、書各為三篇,相當于原著的五分之一。對于這些選中的篇章,他做了大量的刪改,卻沒有說明刪改理由,有學者評曰:“經過刪節后的文字,并無割裂支離之病,而依然脈絡貫通、首尾圓融、神氣完足。”姚氏的刪節本及其評點因此具有可讀性,他的評點方式跟傳統評點并無什么不同,眉批、夾批和篇末評語共為一體,相互補充,對章法結構和字詞句法都有涉獵。值得注意的是,姚氏對敘事時間頗為在意,如在評《平準書》“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民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時,姚氏點出:“先提明而后倒敘其事,此史家絕頂妙法,自遷創之”,明確指出司馬遷運用了倒敘手法,并認為是司馬遷獨創,給予高度評價。此外,姚氏對于插敘手法也密切關注,如他指出《項羽本紀》中7處使用插敘、夾敘,《封禪書》6處使用插敘、夾敘,對敘述手法諸如此類的評點在《史記菁華錄》中多達20多處。
二、劉咸炘的《太史公書知意》六卷和《漢書知意》
劉咸炘作為近代四川史學巨擘,對《史記》《漢書》均有涉獵,他著有《太史公書知意》六卷和《漢書知意》一卷,他從史學角度出發,探究史著之體例,開啟了兩書的宏觀研究。他認為讀史不僅要知其字面意思,更要洞悉兩書的文本和思想內涵,摒棄了死摳字眼的考據法,注意從文脈和歷史沿革的角度作宏觀觀照,如他指出自從韓愈舉漢代人的文章不涉及班固之后,后人盲目跟從,批評歸有光以《史記》為宗、方苞詆毀班氏的行為。《太史公書知意》卷一為緒論,其他諸卷按《史記》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五種體例順序編排,分篇評論。“吾既撰《漢書知意》,復究《太史公書》,亦作《知意》六卷,體與《漢書知意》同,偶涉考證、論事、論文,必與義例有關”,可知其評論重心在于“義例”。劉氏評語慣用手法是匯集前人之語,再略加批評,如:與上“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文相對,此乃史文用意處,而歸、方皆未指出。大抵歸、方偏于論文氣,往往于義無關,文順說者,以頓挫密標之,而于此等,反不留意。梁曰:“虞卿嘗再相趙,則其著書非窮愁之故”,按此說可怪,嘗為相,即定不致窮愁邪?
前者劉咸炘認為歸有光和方苞偏重文氣,對于史學要緊的地方卻未加留意,后者批評梁玉繩的說法奇怪,認為虞卿的窮愁并非為相的緣故。由此可知劉氏注重史料的真實性,偏重史法研究,對于前人論點多所批判,少有附會,體現出其不拘泥于前人觀點、獨立思考的可貴品質。對于《史》《漢》優劣,劉氏也有簡要評論,如清人趙翼認為《漢書》多錄經世致用的文章,肯定班固為“辭賦之祖”,劉氏一方面肯定班固,但不認為這是《漢書》優勝《史記》的地方。因為《史記》是通史,不能盡詳,《漢書》為斷代史,應該詳。
三、陳衍的《史漢文學研究法》
與其他專著相比,陳衍的《史漢文學研究法》最早打出“文學”研究角度的口號,書名明確了兩書的文學性特征,陳氏評價:“《史記》長者,《漢書》短之,《史記》短者,《漢書》長之”,對于《史》《漢》詳略的不同和用意評點到位,事實也是如此,班固在參考《史記》時有所選擇,對于《史記》敘述詳細的地方,《漢書》盡量簡述,而對于《史記》語焉不詳之處,《漢書》則予以擴充,陳衍以兩書對鴻門宴的敘述為例,指出《漢書》將《史記》中所有描寫神情言語的敘述都予以刪除,沛公所言“孰與君少長”“項王項伯東向坐”,以及張良見樊噲、樊噲撞擊的動作,項王賜彘肩等相關段落和情節,統統刪除,在樊噲相關傳記中也不涉及,并得出結論:“大略馬欲恣肆,班欲謹嚴”。以此從文學角度評價兩書的寫作特色,點出司馬遷站在私人寫作的角度,敘述放肆,描摹色彩濃重,場面歷歷如見,班固作為官方史家,寫作更為嚴謹,盡量避免主觀敘述,務求客觀寫實。此外,陳衍慣以大量舉例的方式證明自己的觀點,如評價兩書 “是時”“當是時”的用法時,大量舉例,富有說服力,體現其學術研究的嚴謹。然而,陳衍的研究法除去“文學”研究的旗幟,與明代以來的評點路子并無大的不同。
四、李景星的《四史評議》
李景星的《四史評議》包括《史記評議》《漢書評議》《后漢書評議》《三國志評議》,1932年濟南精藝公司刊印發行了3000冊,1986年韓兆琦和俞樟華共同校點《四史評議》,由岳麓書社出版,是研究前四史的重要專著。《史記評議》《漢書評議》對《史》《漢》做了比較多的綜合對比。作者自述書名含義:“評者,謂持平之理;議者,謂定事之宜也”。與清人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不同的是,李氏拋棄了札記式的評論,他對前四史逐篇點評,大到篇章結構、命題主旨、歷史材料的甄別、各個版本記錄的異同,小到字詞句法、人物地名的考證,他都有細致評論,其用心之勤,考證之精,令人嘆服。《四史評議》對于初讀前四史的人是一部很有用的書。此書行文時用的是文言,注重考訂,對于《史記》《漢書》敘事異同的研究尤其具有參考價值,如《史記》《漢書》均有高帝本紀,李氏認為《史記》“以奇肆勝”,《漢書》“以莊嚴勝” ,雖然講同一個人,但命題用意大不相同,因為風格迥異。
李景星對于敘述結構的分析尤其精彩,如評《魏公子列傳》:“通篇以客起,以客結,最有照應。中間所敘之客,如侯生,如朱亥,如毛公、薛公,固卓卓可稱;余如探趙陰事者,萬端說趙王者,與百乘赴秦軍者,斬如姬仇頭者,說公子忘德者,背魏之趙者,進兵法者,亦皆隨事見奇,相映成姿。蓋魏公子一生大節,在救趙卻秦,成救趙卻秦之功,全賴乎客,而所以得客之力,實本于公子之好客。故以好客為主,隨路用客穿插,便成一排絕妙佳文。”將一篇列傳的結構章法分析得淋漓盡致,切中肯綮。
除以上四人外,崔適、李笠、郭嵩燾等人也是走傳統研究的路子,此外還有以新的視角系統研究《史》《漢》的林紓、梁啟超。古文家和翻譯家的雙重身份使得林紓在翻譯時往往將外國小說與《史記》相比附,充分展示了他對中國傳統敘事作品的自信。同時,西學東漸為《史記》的研究輸入新觀念,如經濟學思想滲透在梁啟超的《貨殖列傳》等研究中。
五、小結
《史記》 《漢書》在晚清民初的接受與傳統的《史》《漢》接受既有相似之處,又有明顯的不同,這取決于晚清民初這一特定時代背景的復雜性和獨特性。《史記》《漢書》發展到晚清,人們的接受更多的屬于自發自覺的行為,基本上剔除了統治者的因素以及科舉制度等文化政策的因素。同時,晚清民初復雜多變的政治局面顛覆了傳統的史學觀,也顛覆了考證為主的史學研究法,傳統的史學受到質疑,其中觀點主要以梁啟超為代表。而晚清民初文學對《史記》《漢書》的接受一樣貫穿在詩歌、散文、戲劇、傳記等多種文體中,閨閣之中也有熟讀《史記》《漢書》者,詠史之作常有。這一時期有關《史》《漢》的研究既有傳統的音譯注釋、考證評點,也有借用西方新觀點進行研究者。要之,晚清民初的《史記》《漢書》接受體現出強烈的時代性和復雜性:即傳統之中孕育新變。此時期的研究并無太多的創見,其主要意義在于繼往開來,真正的突破尚有待于后來者。
參考文獻:
[1]姚苧田.史記菁華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2]劉咸炘.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3]陳衍.史漢文學研究法[M].無錫民生印書館.民國23年.
作者簡介:
曾小霞,女,漢族,湖南衡陽人,湖南城市學院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