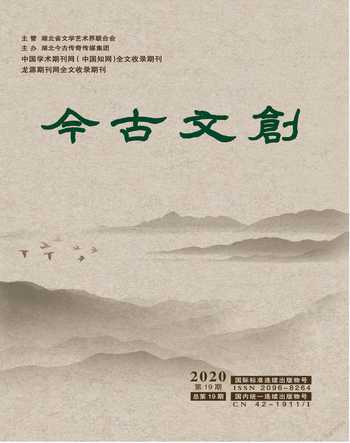尋根,促進對“美”的認同
任懿行 陳婭婷
【摘要】 舞蹈是所有藝術之母,是人類的第一語言。隨著時代的發展,舞蹈也在不斷地進行著自身的演進與發展,比如原始時期有表現圖騰崇拜、生殖崇拜的舞蹈;夏朝出現了奴隸女樂;西周利用舞蹈進行制禮作樂的禮樂制度;漢代有出現了表現星象意識的“盤鼓舞”以及少數民族的四夷樂舞等等。歸根結底,是由于人類的意識在隨著實踐的改變而發生著變化,而文化的出現又是由于人類“審美”意識的出現。中國的《易經》中講:“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舞蹈隨著人類對“美”的不斷認識與再認識而進行著演進。本文以海陽秧歌為例,解讀其中所包含的“美”的現象。
【關鍵詞】 舞蹈;海陽秧歌
【中圖分類號】J72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19-0075-02
一、“美”的多元性與多意性
“美”的認識是推動人類文化進步或使得人類進步的一種抽象的認識。因為不同的地域、文化、風俗、審美,導致每個地域的人都有其各自對“美”的不同認識與理解,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的進步、時代的發展,“美”也逐漸在進行著自身的發展。比如漢代的藝術講究“天圓地方”,實行“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魏晉時期出現了唯美的風格,社會大變革、政治風云變幻,面對生命的變滅,流行于魏晉名士間的虛無放誕,便對漢代群體生活架構起的倫理產生了徹底的懷疑,這時的“美”,是回來做自己,所以,“美”的概念從無絕對的定義。
二、何謂海陽秧歌
秧歌是中國漢族古老的民間藝術形式之一,它起源于插秧、耕耘時所唱之歌,它與古代祭祀農神祈求豐年,祈福禳災時所唱的頌歌、禳歌有關,在發展過程中以民間的農歌、菱歌作為基礎,由東北、華北、西北農村演出的秧歌、扮演人物的小戲逐漸擴展為漢族最普遍的民間舞蹈形式。
海陽秧歌為中國漢族民間舞蹈,屬中國四大秧歌流派之一,同時也是山東三大秧歌之一。海陽秧歌源于漢,創于明,興于清,它的真正產生距今已有500余年的歷史。它在當地又稱“唱秧歌”“跑秧歌”“扭秧歌”“逗秧歌”,生長在黃海之北,牙山之南的海陽,屬農耕文化與海洋文化相互交織的區域。它流傳于山東煙臺市海陽及周邊的乳山、萊陽、棲霞一帶,以其莊嚴肅穆的禮儀制度及靈活自如、收放有致的動態特征于齊魯文化中獨樹一幟。海陽秧歌是一種集歌、舞、戲于一體的民間藝術形式,以性格鮮明的角色扮演、多彩豐富的表現形式、靈活即興自由的內容及古樸豪放的風格著稱。早在明朝1425年間已有文字記載,興盛于清朝中期,即1736年設海陽縣后。
傳統海陽秧歌最早出現于新年燈節中人們的祭祀娛樂,秧歌隊一般從臘八節就開始進入組織和排練,正月開始搭班演出。秧歌隊由三部分組成,出行排在最前列的為執事部分,由三眼銃、彩旗、香盤、大羅組成。其次為樂隊,由大鼓、大鑼、大鈸、小鈸、堂鑼等構成。第三為舞隊,伴有各類角色,其中指揮者稱為“大夫”;集體舞表演為“花鼓”“扇女”;雙人舞表演為“翠花”與“貨郎”,“老頭”與“老婆”“王大娘”與“錮漏匠”,“丑婆”與“傻小子”,“大頭和尚戲柳翠”,單人舞表演為“老婆抱母雞”“濟公挑花燈”“豬八戒背媳婦”等,均在“樂大夫”指揮下完成。
三、秧歌中的“美”
(一)理性之美——祭祀,禮儀
海陽秧歌之所以在眾多秧歌中獨樹一幟,它與其他秧歌不同的時其十分嚴謹的結構與程式以及禮儀的規范。海陽地處齊魯文化的發源地必然離不開孔孟之道,由于儒家學說的影響,古代中國政治以禮為中心,“禮”包含了仁、義、智、信、忠、孝、悌、廉等倫理范疇,孔子十分重視禮與樂,東周時期試圖恢復西周的禮樂制度,同時用其一生去推廣“禮”,傳播“禮”,并認為符合“禮”與“善”的事物才是美的,同時也是區別人與獸的主要標志。李澤厚在《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中提出了“度”的哲學,認為“美是人對‘度’的自由運用”。于是中國漢族人的舞蹈多要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理性之美。
海陽秧歌中的“禮”體現在拜進、拜廟與拜出之時。首先,拜進又稱為“三進三出”,是海陽秧歌的重要禮儀形式,由祭神、祭祖的“三拜九叩”簡化而來,是進村前與東道主的會首見面,以及與東道主的秧歌隊迎面相遇時互表敬意的禮節。出村的叩拜儀式為“拜出”,無論拜進或拜出,都采用“三進三退”的形式,拜進為逐步遞進,拜出則為遞退。按傳統要求,拜廟后才能正式演出,于是秧歌隊在“串街”后的第一個目的地則是前往東道村的宗祠家廟,來訪的秧歌隊向東道村祖宗牌位行“三拜九叩”大禮,即每進一次叩三個頭。所以在海陽秧歌中要對“人”進行“三進三退”之禮,在拜廟時要對“神”與“祖先”進行“三拜九叩”的大禮。同時我們在祭拜時的陣勢中能看到祭孔的遺風,其特點為動作少,儀式性強。
(二)情感宣泄——演場
海陽秧歌雖然有嚴謹的結構與肅穆莊嚴的禮儀程式,卻在“演場”中彰顯了無限的人文情懷,凸顯出其原始性與自由性。舞蹈是身心合一的有意識的肢體表現,越是極致的身體動作越能體現舞者強烈的情感表達,因此舞蹈難于“言”。德國表現主義舞蹈家魏格曼說:“如果可以用語言來表現,就沒有必要用舞蹈表現。”所以當語盡意不盡,意盡情不盡的時候我們才用舞蹈來表達。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響,使得漢族始終活在農業倫理當中,漢族便不擅歌舞。農業社會是將種子放到土里,等待其發芽。只要是農業,一定是穩定的,譬如農業中的文化講究安土樂天,重恒輕變;農業中的舞蹈講求法古守成,不喜變動。那么穩定同時也可能是保守的、封閉的,在農村,人們的道德觀念一般十分保守,因為必須穩定,那么對新事物的接受非常難,于是在漢族的舞蹈中少了許多少數民族的豪放與自由。但海陽秧歌不同,它講求動作的極致,在大開大合中感受生命的律動,這也與海陽地區在春秋戰國時期隸屬齊國有關,姜子牙封地齊國,倡導“尊賢尚功”,文化思想開放,較少受到繁文縟節的束縛,因此,海陽文化具有較強的開放性、包容性,大多能表現人物性格的文化元素皆被海陽大秧歌吸收。比如各類角色扮演中盡顯人文主義情懷,王大娘的扮演者——民間藝人王發,最經典的動作就是與錮漏匠的對舞中表演的“大閃腰、大撲身、大翻身”的動作,然而每一次的表演也都會因不同現場氣氛刺激下產生出豐富的情感變化,導致其動作的多段變化、風情萬種,極大的能量釋放使得動作達到了“極致”的美。他能在瞬間啟動爆發力,使其舞蹈動作似排山倒海般不可阻擋,卻又能霎時轉入緩動之中,就在這一開一合,一張一收,一實一虛中將“王大娘”的萬種風情的神韻體現得淋漓盡致,恍惚間仿佛真的看到了那只狐仙。
(三)“圓”——完滿,輪回,循環
方與圓在中國文化與西方人所理解的概念是不同的,自漢代開始中國文化講求“天圓地方”,道家認為:“圓”指天, 動蕩不定, “天圓”指心性上圓融,才能通達;“方”指地,收斂,“地方”指命事上要嚴謹條例。“天圓地方”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陰陽學說的一種體現,不僅代表中國人格取向的“外圓內方”,更有“天人之際,方圓之間”的中國人的生命觀。
中國人對于“圓”的追求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生活中的桌子是圓的,過年時講究“團團圓圓”,傳統戲劇最終總會以一個“大團圓”的完滿結局作為結束,還有“上元節”“中元節”“中秋節”等,都與月光的圓滿有關。那么海陽秧歌作為中國漢族民間舞蹈,其中不乏包含了大量“圓”的形態與軌跡,主要表現為體態上的彎、曲、疊、直,動態中的擰、磨、裹、探、繞、旋等等;扇花中的圓表現為:盤扇、纏頭扇、遮陽扇、磨拐扇、五花扇等,都是“圓”的思想于肢體上的外化體現。關于海陽秧歌蘊含的“圓”之美可從以下幾點做進一步解釋:
1.仁者愛人,天人合一——圓滿
儒家文化除孔子提出的“仁”與“禮”以外,最重要的為一“和”字。“和”包含了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代表經典之作——《禮記》在自己特有的基本華語和理論架構的人道思想的基礎上,以“中和”為審美原則,在禮與樂、情與理、美與善、內容與形式等矛盾對對立因素之間,構建某種均衡中和的關系形式,體現出“和”的審美智慧和理想。其中闡明了孔子中庸思想本體論化的過程。《禮記·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這里,天人相通又相和,“中庸”成為天地宇宙和萬物發展的根本,“中和”則是這一本體在萬事萬物間生生不息與圓融完滿的體現。此思想影響了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于是“和”思想在海陽秧歌中轉化為了動作造型,動勢動律以及隊形調度上“圓”的符號。
2.陰陽激蕩,循環往復——循環
傳說盤古開天,劈開無極,輕的上升,重的下降,然后有兩儀,兩儀即陰陽。陰陽學說產生于夏朝,稱宇宙間萬物皆可分為兩類,即陰與陽。“陰”指柔弱、向下、收斂等意;“陽”指剛健、向上、外向等。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講道:“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生焉。”世間任何一事物都有陰陽兩面,即陰中有陽,陽中帶陰,二者又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形成陰陽調和之態勢以及對立統一中生“圓”的意象。道家提出陰陽五行學說,分“陰陽”與“五行”,“五行”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基本物質運行和變化所構成,它們相生又相克,成圓而循環往復。
綜上所述,雖然海陽秧歌屬于“俗”舞,但其中包涵了大量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值得思考的哲思的理念,學習海陽秧歌的目的,不僅局限于四肢,更希望學習者能從海陽秧歌的身體律動中發現中國多樣的傳統文化,以及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做到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在傳統文化的肢體表達上,發現美,延續美,發展美,使“美”成為屬于我們民族的一種跨越一切障礙的精神紐帶。
作者簡介:
第一作者:任懿行,女,漢族,北京人,碩士,研究方向:舞蹈編導。
第二作者:陳婭婷,女,漢族,甘肅人,碩士,研究方向:舞蹈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