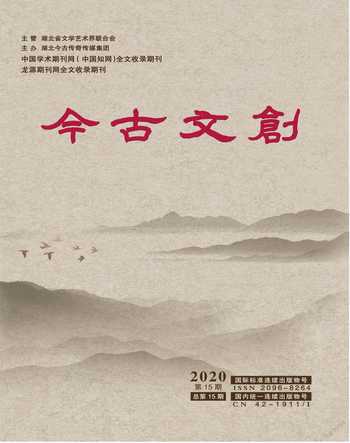文學作品中的“女扮男裝”現象研究
【摘要】 “女扮男裝”是中外文學作品中一個經典而獨特的母題,它是指作品中女性人物喬裝成男性的情節,此外,喬裝后通常還伴有一系列社會活動。關注這一話題時,除了情節設置外,更需要注意其背后的性別意識。本文以英國作家莎士比亞和明代作家徐渭的劇作進行比較,以此來管窺不同文化背景下對于兩性關系的認知與思考。
【關鍵詞】 女扮男裝;性別意識;兩性關系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15-0035-02
一、前言
在文學作品里,女扮男裝往往作為一種出其不意的情節而設置,作者常將此描寫為女性裝扮成男人的模樣進行(其本性別會受阻的)活動,“扮男裝”被作為達成某種目標的方式。它通過換裝打破了“男”與“女”兩者間固有的界限,在造成喜劇效果的同時又引人深思,令行文更跌宕,故多見于戲劇創作中。隨著性別平權意識的進步,尤其是女性的活躍和發聲,文學作品中的這一母題也逐漸為學者重視,并開展分析研究。本文以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皆大歡喜》以及中國明代劇作家徐渭的《雌木蘭替父從軍》《女狀元辭凰得鳳》為例,綜合這些作品中的一些形象進行探討。文章將分為五個部分,在具體的文本分析之前加入了性別研究方面的理論,嘗試更全面把握這一主題。
二、性別與服裝
在女扮男裝的情節中,服裝作為一類重要的媒介而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后世大眾趨向中性化的服飾選擇,莎士比亞及徐渭作品的創作年代(16世紀)將服裝與性別關聯得更加緊密,服飾在這里成為人們對自我性別認知的外化表現,此時它的區分功能格外顯著。人們的穿著打扮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生活需要,更成了某種象征——例如褲裝、長袍等通常被認為是陽剛的,代表著男性氣質。正是這樣,兩性之間的界限被劃分得相當明確,服裝相當于一種權力場,尤其是對于傳統社會中的女性而言。
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表演”理論中,提到性別乃至一切身份都具有表演性,“所謂性別表演就是‘我’在扮演或模仿某種性別,通過這種不重復的扮演或模仿,‘我’把自己構建為一個具有這一性別的主體”。這實際上指出人們對于“性別”的連帶反映(認為男性堅強,女性柔弱等)其實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世代積累的主觀建構,而后來者為了符合這樣的建構,會有意識地將自己打磨成“認定中”的樣子,這便形成了一場表演。在出現女扮男裝情節的作品中,人物往往是為了求得認證而選擇變更服裝;而在服裝變更之后,她們又會通過模仿來進一步偽裝,完成從表面到深層的全方位“改變”,這可以說是一次愚弄。服裝為兩性認知劃出界線,然而也正是因為它們在觀念中的綁定關系,才讓作品中的“跨越”成為可能。
三、出走與回歸
在涉及具體情節描寫時,發現“女扮男裝”作品的一個共通之處,它們均以“認可——出走——回歸”這條脈絡進行。這明確展示出部分女性嘗試追尋自我,但在最后又返回到從屬地位的過程,這是突破之舉,亦是無奈之舉,以下綜合文本詳細闡釋。
(一)認可:女性身份的接納
“女扮男裝”情節在作品中通常作為一個重大轉折點出現,借此營造出一定的戲劇性。轉折前,女主人公們對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受限的社會權利是很悅納的。《威尼斯商人》中的鮑西婭縱然有顯赫家世與可觀財富,但面對擇匣而來的丈夫,她仍然先把自己放在低位—— “我只是一個不學無術、沒有教養、缺少見識的女子”,《雌木蘭替父從軍》中花木蘭上戰場前也暗自思忖“回來俺還要嫁人,卻怎生?”木蘭父母因她是女兒身而憂愁,她反過來勸慰二老“您盡放心,還你一個閨女兒回來”。
這些女性主人公們確有優越的自身條件:從羅瑟琳、花木蘭的勇猛到鮑西婭、黃崇嘏的智慧,可以說是文武兼備。但這些品質展示與否,依舊要以女性身份能否允許作為前提條件,她們自己也認知、并接納這一點。這一認可是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的正常想法,不過也為后文女主人公們回歸家庭埋下了伏筆。
(二)出走:釋放的閥門
莎士比亞與徐渭的兩部劇作里,女主人公們都是在緊急情況下而不得不扮作男人的:為親人解圍,或是出于保全生計的需要。此前,她們的才能受到女性身份的壓抑,而突如其來的狀況卻像一個引子,點燃了其展露的愿望。鮑西婭在換裝前曾夸口:“我會學著那些愛吹牛的哥們兒的樣子,談論一些擊劍比武的玩意兒,再隨口編造些巧妙的謊話,這些愛吹牛的娃娃們的鬼花樣兒我有一千種在腦袋里,都可以搬出來應用。” 黃崇嘏應考前亦有言:“咳,倒也不是我春桃賣嘴,春桃若肯改裝一戰,管倩取唾手魁名!”可見她們對自己的實力是相當有自信的。往日囿于限制不得發揮,今時女扮男裝,獲得了外部認可后,相當于打開了一處閥門,她們借助更為強大的男性身份,得以參與社會事務,充分釋放自我。
“女扮男裝”,可以說是一種出走,它偏離了傳統社會對于兩性的劃分和認知,在“灰色地帶”創造可能。劇作里還描寫到女主角變裝后對男性的戲弄和考驗:如鮑西婭執意要巴薩尼奧的指環作為報酬,還囑咐尼莉莎“我們回家以后,一定可以聽聽他們指天誓日,說他們是把指環送給男人的;可是我們要壓倒他們,比他們發更厲害的誓”;花木蘭在營地哄二軍“我花弧有什么真希罕,希罕的還有一件。俺家緊隔壁那廟兒里,泥塑一金剛,忽變做嫦娥面”,讓對方驚奇不已。如此安排調侃了男性主導的環境,女性角色從被凝視、被安排的客體轉變成了可以表露自我的主體。盡管她們最開始易裝是出于被動,但在換裝后,反而能夠抓住主動權,這種在特殊環境下所表現出的機智正是女扮男裝情節最吸引人的地方。
(三)回歸:不完全叛逆
易裝無疑是富有創新性的巧思,不過它們呈現的仍然是一場不完全叛逆。危機后,劇中女主角的結局依舊是回歸家庭,相夫教子。考慮到當時的普遍觀念,這是符合常理的,然而相比她們身著男裝大放異彩的場景仍稍有遜色。羅瑟琳在出走前曾道:“現在我們是滿心的歡暢,去尋找自由,而不是流亡!”易裝如同一次冒險,通過這一大膽舉動,她們得以實現自我價值,這份經歷彌足珍貴。以回歸作為結局縱然使劇情閉合成圓,但站在女性權利意識的角度上看,不免有一些遺憾。
盡管總體上四部劇作女主人公結局相似,但其中過程各異,最為突出的便是心理層面的不同。在莎劇里,鮑西婭和羅瑟琳的故事圍繞愛情展開,其心理狀態并未發生太大改變。與此相異,在徐渭的劇作中,主角的心理則更加復雜。花木蘭從軍時暗道“萬般想來都是幻,夸什么吾成算。我殺賊把王擒,是女將男換。這功勞得將來不費星兒汗”;黃崇嘏回詩于丞相:“相府若容為坦腹,愿天速變作男兒!”正是由于性別壁壘出現了缺口,花木蘭才會發出“都是幻”的感慨,黃崇嘏更是抱有“作男兒”的祈愿,并不滿足于安坐閨閣了。親身感受到男女權利的區別劃分,讓她們或多或少地產生了一定反思。在文本里,這樣的反思尚處于初步無意識的階段,并未改變傳統意義上的大團圓結局,不過相較于莎劇,花、黃二人的心理變化更具有進步的色彩。
四、結語
“女扮男裝”作為一個經典的文學母題,具有文學和社會雙重價值。它是性別易裝現象的一部分,又因傳統社會環境下兩性話語權的巨大差距而帶有更為深刻的含義,變得特殊,故在文學作品中出現頻率更高。兩性關系中,女性常常處于從屬地位—— “幼子們在選擇配偶方面有最多的自由,女性則很少有這種自由,因為男性家長遺贈給女兒嫁妝的條件就是,他們必須接受父親遺囑的執行人為她們聘定的婚姻”。女扮男裝情節之所以會有如此廣泛的受眾,是因為它在一定意義上打破了男權環境的壟斷——過去只有男人能夠參與的工作,現在出現了女性的身影,雖然這是特殊情況下的極個別現象,但也邁出了從無到有的一步。本文所述四部劇作中的主人公也是如此,雖背景各不相同,但都以其地點、工作的特殊來反襯出女性群體之智慧,故更具有代表性。
“女扮男裝”這樣的舉措在文學作品中出現,可以看作是某種對現有父權中心的反抗,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反抗規則的過程,也是服從規則的過程,只有當女性打扮成男性模樣時,才能拿到對擂的入場券,這如同一個悖論。在莎士比亞和徐渭創作的年代,由于大環境沒有改變,人們的傳統觀念仍占上風,因此這個悖論得不到突破口,只能是未解。縱然能夠在部分片段中覓得女性自我意識的萌芽,也會發現它是不完備的。美滿團圓的結局背后,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們思想的局限,而作者的局限,也是時代的局限。
參考文獻:
[1](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2]牛文馨.女性視角下16-18世紀英國兩性關系的變革[D].西華師范大學,2017.
[3]楊世明.論中國古代的“色性說”及兩性之不平等[J].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5):20-23.
作者簡介:
黃淼兒,女,蒙古族,河南開封人,中央民族大學,本科學歷,研究方向:比較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