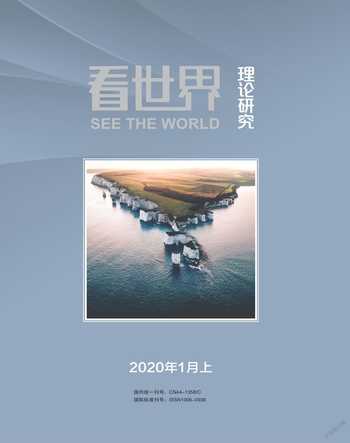戚繼光讀書之道
羅洪
古人講“立德、立功、立言”,能于三者之中立其一者已為不朽,戚繼光則三者兼而有之,實屬難得之典范。立德上,生時福建、浙江人民為其立碑刻銘,尊稱“戚我爺”,死后為其立宗祠,永享香火;立功上,東南創建“鴛鴦陣”掃平倭寇、北上御虜首創空心臺、車步騎三兵種聯合作戰以不戰之功而屈虜之兵十六年;立言上,其有《止止堂集》《練兵實紀》《紀效新書》,其中四庫全書所收錄的十部兵經中,其中兩部即為《練兵實紀》《紀效新書》。
縱觀中外古今之名將、統帥,探究其成功背后的原因,善于學習、一生學習、學以致用無不是其之所以能彪炳史冊、光耀千秋的規律所在。默觀戚繼光所著兵書、詩集,考察其后人為其所編《戚少保年譜耆編》,不難發現戚繼光戰斗的一生也是其學習的一生,學習內容始終圍繞著“為何而學”“以誰為師”“學以致用甚至是創用”三個問題展開, “為何而學”是其靈魂與根本,“以誰為師”則是其學以成功的方法關鍵,“學以致用甚至是創用”則是其由疑惑而得真知,由真知而真信,進而更行于學的動力之源。一言以蔽之即為“勝戰之學”。
一、真心尊賢與師賢
經典是否已經過時?古圣先賢是否還可學?如何學?這是從古及今任何一名立志于學的人所面臨的共同課題,也是一個理解戚繼光學習方法的關鍵所在。就此問題,戚繼光在《練兵實紀·儲練通論上》之《正習訛》篇專門有所論述,他認為致力于軍事的人都為孫子之徒,但今之人“自夫世好(注釋:世俗所愛好)之不同也,試文之馀,每于篇中,必肆詆毀譏誚其師,無所不至。試使今日之毀師者,受國家戡定之寄,而能攘外安內如孫、吳者,幾人哉?夫業彼之業,而詆彼之短,是無師矣。以無師之心,而知忠愛之道,有是理乎?”。此外在其《止止堂集·愚愚稿上》中談到“近世人輕易看書,辭日繁,道益晦,只是欠身體力行四字耳。但將數圣賢真儒說過的話頭,字字認真體貼,來我身上行之,只一良知,便可徑到圣賢地位,便可日日見堯舜”。無獨有偶,千古一帝康熙、毛主席曾給予極高評價 “余以近人,獨服曾文正” 的曾國藩,對經典與圣賢的看法也同為尊崇備至并注重實踐體認,康熙有言“帝王之治,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盛”]“學問無窮,不在徒言,要惟當躬行實踐,方有益于所學”];曾國藩《挺經·英才》中對何以成才的方法歸納為“今世人皆思見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誠能考信于載籍,問途于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效,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通,才亦漸立。才識足以濟世,何患世莫己知哉?”[5]。
戚繼光出生于1528年、康熙出生于1654年,、曾國藩出生于1811年,四書五經、《孫子兵法》距離他們不可謂不遠,但三位不同時代名垂青史的歷史人物對古圣先賢的認知卻畫出了同心圓,并都在學圣賢中建立了各自時代的不朽功勛。
后人視今亦由今之視昔,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之大變局,世界新軍事革命加速發展,軍事技術和戰爭形態發生革命性變化,空地一體戰、目標中心戰、超限戰、各種各樣的作戰理論疊出不窮,各種各樣的武器眼花繚亂,哪種軍事戰略是符合新時代政略的良方?哪種武器裝備屬于作戰所需,而非巧立名色、逞意浪造?哪種戰法符合新時代之所需?古圣先賢所著的經典中是否還會有答案?
二、學為勝戰
如果以上軍事戰略之問,武器裝備之問,戰法之問為當下之所問的話,那么遠在15世紀的明朝,這些問題也仍然是戚繼光所問!
“北方原野空闊,必以眾成功;南方田徑縈紆,必以寡制勝,固常道也。”]然而,考之史傳,“范蠡伐吳,戰于姑蘇,尤南方之至隘而田者也”。其伐吳之軍“計且五萬矣,沿河魚貫百里以外,設使身處其事,如何施展?”,“岳飛御金,戰于中原,尤北方之至曠而陸者也”,考之史傳,“汜水以五百勝,穎昌以八百勝”,“設使身為之將,如何分應?”,“用兵之法,不過寡與眾,眾寡之用,不過奇與正”],然而古之將領皆有眾以奇用和寡以正用之效,與兵法所論相反而成功者,其戰法的要領于何?
“或謂策論、弓馬不足以得真才,或謂保薦甄取獵民而非正轂。然歟,否歟?及其試之以事,或謂掣肘不能展布,或謂摧挫不得行志。是歟?非歟?”,為何國家求將愈密,得之愈艱?
戰法之問,帶兵之問,兵器之問,求將之問?以上諸問皆可以歸結為一問,那就是“勝戰”之問。察查戚繼光勝戰之問的軌跡,不難看出,其學習的方向始終在向勝戰聚焦。
有人問戚繼光:“祖宗自設官軍,至今操練二百年矣。比子之操一二年者,孰為習士”?戚繼光回答道,比如一個學生平時學習學的都是詩詞歌賦,但考卷的題目卻是四書、五經,就算其手不釋卷,“一旦入場要作經義策論中選,所習非所用,如何可得?就是好學的,也徒然耳”。
人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要想在一個領域有所成就,無論智愚皆逃不出“一萬小時定律”。所以在戚繼光看來,如果軍士平時所學的不能與戰場所需無縫對接,就算操練一千年又有何用,到了戰場上仍然還是生的,況且“奈每見賊時,死生呼吸所系,面黃口干,手忙腳亂,平日所學射法、打法盡都忘了,只有互相亂打,已為好漢,如用得平時一分武藝出,無有不勝;用得二分出,一可敵五;用得五分出,則無敵亦”。
三、正心術為本
對勝戰之問的具體回答在戚繼光的《練兵實紀》與《紀效新書》中已分析與解答,一般人尋找勝戰之問的答案也多從跡上尋,而戚繼光卻是從心上求。在戚繼光看來,勝戰之問答案的根本在于將心,倘若能培養出將領的一顆 “一心從保安民社上起念”[19]之心,那么所有的勝戰之問都將迎刃而解。
《練兵實紀》與其余兵書與眾不同處就在于其明確提出了培養將領的途徑與方法,在一般人看來,培養將領的方法多重其兵法謀略,但在戚繼光練將的理論中,他認為最根本的是要培養將領的純臣之性,也就是其所提倡的“正心術而已矣” 。
正將領之心術不僅是戚繼光對勝戰之問的回答,也是成就戚繼光東南平倭,北方不戰而屈虜之兵不朽功勛,彪炳史冊的核心所在。
四、治心寇為要
為將者如何才算心術正?志在好人品,怎樣才算好人品?在戚繼光看來正心術與好人品需從治心寇中求,“人性之所有者,吾復之;人情之所欲者,吾反之”。
“世之為武夫者,積金帛、廣田宅、侈功名、報首領,與時遷移,今人謂之上智”,戚繼光則追求愚而又愚,“竭心力,治職事,盡其在我”,“疲有限之精力,必欲維持職守,於必不可為之中,陷阱在前,斧鉞不懼”。
世人多求長生之術,戚繼光認為為將之長生之術在于“身為大將,義在死綏”,“鞠躬盡瘁、夕死何憾?”。
在追求忠的過程中,戚繼光認為一時忠不算什么,要能從始至終的“忠”才算是真正的忠。“世祿之家,盡忠報國,分內事。一時有間則二三,則非忠矣”;世受國恩的同朝將領,“但壯年以來,為貨財、色欲、口體、勢利所奪,如是愛樂惡苦、貪生畏死,有所顧惜,則良知遂泯。忠矣且不能,況能一耶?”。
治心寇如仰面攻山,縱欲則入下坡推轂。瓊臺之花,灌溉而難茂,治心寇也;縱欲如路邊之草,踐踏而猶生,縱欲也。
在帶兵的具體實踐中,戚繼光認為練兵不僅是在于教場操練,那些都是具體的形式,即筌蹄(注釋:比喻達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之法,而兵靜處于閭閻,能蓄養其銳氣,講明法令,通之以情,結之以心,才算為真正的練兵之道。
在談到軍人的動與靜時,戚繼光并不認為形式上的靜就一定是靜,他更注重心中的靜,比如在其作戰時,“我要是雜念一動,就會張皇失措,就會不敗自亂”,“所以我和我的士兵都主張在戰場上要無所畏懼,要全神貫注,雖然行動如風,但卻心靜如恒,這樣才能無往而不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對將而言即是能保國泰民安,能保國泰民安即是明明德。
新時代呼喚下一個戚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