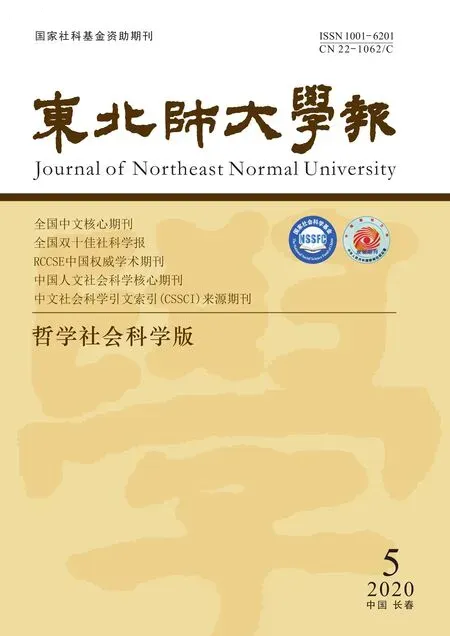“承”與“棄”——“陶隱士”形象海外“譯變”軌跡研究
謝紫薇,宮玉波,盧明玉
(1.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東方學(xué)院,河北 廊坊 065000; 2.北京交通大學(xué) 語言與傳播學(xué)院,北京 100044)
陶淵明(公元365~427年)是我國與李、杜齊名的詩人、文學(xué)家,也是中國最早被英語世界譯介的詩人之一。他的影響力突破了時(shí)間與地域的限制,他的思想感染著無數(shù)的讀者。直至今日,在中外學(xué)者的解讀下,陶詩依然煥發(fā)著生命力。陶淵明的藝術(shù)魅力在于他質(zhì)樸卻深邃的語言,在于他文字中透析出的哲思,更在于他詩歌中塑造的隱士形象。正因如此,中外讀者對(duì)陶詩進(jìn)行解讀的過程也是“陶隱士”這一藝術(shù)形象不斷豐富的過程。在中西方詩學(xué)傳統(tǒng)與意識(shí)形態(tài)的差異下,“陶隱士”的藝術(shù)形象在中外交流的過程中發(fā)生了變化。聚焦這一點(diǎn),本文探討該藝術(shù)形象隨陶詩英譯產(chǎn)生的變化并嘗試探索導(dǎo)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希望此研究可以作為中國古典詩歌與世界文化交流傳播過程中的一次嘗試。
一、“中學(xué)西漸”中的陶淵明
陶詩譯介在英語世界中已經(jīng)持續(xù)了120多年,其詩歌在英語世界讀者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屈原、李白與杜甫,影響深遠(yuǎn)。陶詩在西方世界的譯介已經(jīng)漸趨成熟,譯介模式也日漸多元化,從漢學(xué)家或譯入語母語譯者獨(dú)譯逐漸發(fā)展到譯入語母語譯者與漢學(xué)家合譯,且從個(gè)別詩歌的零散譯介到陶詩全集譯介,其既有針對(duì)大眾的一般譯介,也有面向?qū)W者的學(xué)術(shù)譯介,可謂異彩紛呈。海外譯者的不斷努力致使陶詩的魅力跨越山海逐漸被異國的讀者所接受。此外,自20世紀(jì)90年代起,美國陸續(xù)出版了幾部陶詩研究專著,更見陶詩在英語世界讀者中接受程度之高。
(一)海外陶詩英譯概述
陶詩譯介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出版的由翟理思(Herbert A.Giles,1845—1935)翻譯的《古今詩選》(ChinesePoetryinEnglishVerse)[1]3,自此陶詩正式進(jìn)入了西方世界。此后的100年來有將近9部作品整部或者零散譯介陶淵明的詩歌,統(tǒng)計(jì)結(jié)果如表1所示:
可以發(fā)現(xiàn),英語國家對(duì)陶淵明詩歌的接受過程大體可以分成三個(gè)階段:第一階段,英語國家對(duì)于陶淵明詩歌的譯介隨時(shí)間的變化由淺嘗輒止到漸成規(guī)模,由碎片化的零散翻譯逐漸變成全集譯介。陶詩英譯本數(shù)量上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陶詩在英語國家譯介的成功;第二階段,陶詩在英語世界讀者中接受程度的不斷提升導(dǎo)致了英語世界讀者對(duì)陶淵明全面譯介需求的增加,而這種現(xiàn)象促進(jìn)了陶詩研究的發(fā)展。研究內(nèi)容從單純的語言層面逐漸擴(kuò)展到作者研究、創(chuàng)作背景與創(chuàng)作意圖研究,目的是縮小譯者和詩人的心理距離,從而提高譯文質(zhì)量[2]22;第三階段,陶詩譯介的不斷深入引導(dǎo)西方社會(huì)逐漸搭建起陶淵明詩歌中的藝術(shù)形象,同時(shí)對(duì)于陶淵明的研究也逐漸從研究其詩歌的語言、意象等內(nèi)容演變到研究其詩歌的主題與挖掘詩文中的哲學(xué)思考。
(二)國內(nèi)陶詩英譯概述
相對(duì)于西方社會(huì)的陶詩譯介,國內(nèi)對(duì)于陶詩的譯介起步較晚,最早的譯本為方重先生于1984年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淵明詩文選譯》,此后譚時(shí)霖先生出版了《陶淵明詩文英譯》,最近出版的陶詩英譯集是2000年由汪榕培先生翻譯的《英譯陶詩》。以上三部是國內(nèi)陶詩比較主流的譯作,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翻譯家對(duì)陶詩進(jìn)行了零散譯介,譬如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以及許淵沖先生。
國內(nèi)對(duì)陶詩英譯關(guān)注度的逐漸提升,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了陶詩研究的維度。就研究領(lǐng)域而言,對(duì)于陶詩的研究不僅局限在中國文學(xué)領(lǐng)域,比較文學(xué)領(lǐng)域?qū)τ谔赵姷难芯繜崆橐伯惓5酶邼q,有許多學(xué)者將陶詩與相同時(shí)代或者相同主題的外文詩歌進(jìn)行對(duì)比研究,收獲頗豐。同時(shí),針對(duì)陶詩的譯者研究、譯文對(duì)比研究以及相關(guān)跨學(xué)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進(jìn)展。就研究內(nèi)容而言,陶詩也為翻譯學(xué)領(lǐng)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語料,許多學(xué)者撰寫論文分析陶詩英譯的策略,陶詩海外譯介的成功使得針對(duì)陶詩進(jìn)行的譯介模式研究也具有相當(dāng)?shù)睦碚撆c實(shí)踐意義。
綜上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陶詩在英語國家與本土的譯介發(fā)展存在不平衡的現(xiàn)象。在英語世界,陶詩譯介起步早,作品多;國內(nèi)譯介雖起步較晚,但發(fā)展迅速。國內(nèi)外譯者的不懈努力使得陶詩的譯介模式日趨成熟,這也為相關(guān)研究的發(fā)展提供了豐沛的例證;同時(shí)對(duì)于陶詩譯介的研究又可以進(jìn)一步指導(dǎo)陶詩翻譯實(shí)踐,形成一個(gè)良性的循環(huán)。
二、“陶隱士”形象的“承”與“棄”
戴維斯曾經(jīng)評(píng)價(jià)陶淵明:“作為一個(gè)詩人,陶淵明的一個(gè)重要特色是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自我形象。正是他在這方面的成就使他成為一位大詩人,并為后人所敬仰。”[1]53陶淵明的“隱士”形象無疑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最為成功的藝術(shù)形象之一。但通過對(duì)比閱讀與研究,筆者發(fā)現(xiàn)這一藝術(shù)形象在中西方讀者的印象中并非完全一致,其在譯介過程中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下面筆者將對(duì)“陶隱士”這一藝術(shù)形象在中西方交流過程中的譯變進(jìn)行分析。
此處,筆者采用了數(shù)據(jù)分析的方法確定研究對(duì)象。為了了解陶淵明的詩歌譯本在英語世界的接受狀況,筆者受到胡玲在《海外陶淵明詩文英譯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啟發(fā),采用WorldCat將陶詩的不同譯本輸入以獲得每部譯著的館藏情況,統(tǒng)計(jì)結(jié)果如表2所示:

表2 陶詩譯本海外館藏情況
由統(tǒng)計(jì)結(jié)果(截止到2020年1月7日)可知,海陶瑋、戴維斯、艾克爾和辛頓為譯集館藏?cái)?shù)量最多的四位譯者。我們將通過研究這四位譯者筆下的“陶隱士”形象粗略地構(gòu)建出英語世界讀者對(duì)該藝術(shù)形象的理解。
筆者已經(jīng)從館藏?cái)?shù)量上將現(xiàn)存的陶詩英譯本進(jìn)行了初步的篩選。館藏?cái)?shù)量某種程度上可以代表作品的流行程度,因此,這些作品對(duì)于探究“陶隱士”在英語國家傳播過程中的譯變具有一定的參考價(jià)值。此外,筆者在篩選文本的時(shí)候,通過建立數(shù)據(jù)庫進(jìn)行數(shù)據(jù)分析,篩選出相關(guān)研究引用度最高的幾篇詩文作為研究文本。文獻(xiàn)檢索選取三個(gè)國內(nèi)主流期刊檢索平臺(tái)CNKI(中國知網(wǎng)數(shù)據(jù)檢索平臺(tái))、維普數(shù)據(jù)庫和萬方數(shù)據(jù)庫。為保證研究對(duì)象全面覆蓋,采用主題檢索的方式,在搜索框內(nèi)輸入“陶淵明/隱士/陶淵明詩歌/陶淵明詩歌翻譯/陶淵明隱士/陶淵明藝術(shù)形象”為檢索項(xiàng),詞頻關(guān)系為“或”,隨即在已得的檢索結(jié)果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以“陶淵明/隱士”為關(guān)鍵詞進(jìn)行二次分類檢索,詞頻關(guān)系為“和”,共檢索出307篇論文。針對(duì)此307篇論文進(jìn)行分析,運(yùn)用Excel的排序、篩選等功能,對(duì)相似的關(guān)鍵詞進(jìn)行歸納整理,同時(shí)輔助以人工篩選,去掉了69篇與本研究相關(guān)度較低的論文,最終選定238篇有效文獻(xiàn)作為研究對(duì)象。將238篇文獻(xiàn)導(dǎo)入NoteExpress進(jìn)行全文下載創(chuàng)建一個(gè)簡單的文獻(xiàn)數(shù)據(jù)庫,并對(duì)該數(shù)據(jù)庫的內(nèi)容進(jìn)行詞頻統(tǒng)計(jì)與引用文獻(xiàn)統(tǒng)計(jì),篩選結(jié)果如圖1:

圖1 陶淵明“隱士”藝術(shù)形象研究引用詩文統(tǒng)計(jì)
筆者將兩個(gè)數(shù)據(jù)進(jìn)行合并,即通過分析館藏最多的四個(gè)譯本中引用率最高的詩句,可以得出一個(gè)相對(duì)科學(xué)的有關(guān)“陶隱士”形象譯變的結(jié)論。
(一)“陶隱士”形象的譯變
安德烈·勒菲弗爾認(rèn)為,翻譯即是改寫并且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種改寫,因?yàn)椤胺g能夠?yàn)樽髡吆妥髌吩谠次幕獾牡胤秸宫F(xiàn)形象”[3]。基于此種觀點(diǎn),在某一特定語言文化圈內(nèi)的文學(xué)形象譯介到另一個(gè)語言文化圈的過程中勢(shì)必會(huì)發(fā)生變化。因此,對(duì)于此種變化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譯入語國家讀者的接受情況,從而達(dá)到提升譯介效果的目的。陶淵明的隱士形象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一個(gè)經(jīng)典形象,在英語國家譯者對(duì)其作品的譯介過程中,這一形象與傳統(tǒng)陶學(xué)中的“隱士”形象在某種程度上發(fā)生了譯變。下文中,筆者選取的譯本均由不同背景和不同類型的譯者完成,每個(gè)譯本都有鮮明的特色。筆者將以譯文、譯集序言以及譯者注解為研究文本進(jìn)行分析。
1.何以“止酒”
“酒”是陶詩中的一個(gè)意象,陶詩中無一篇無酒[4]114。陶淵明更是以酒為題材寫出了非常多為后人稱嘆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飲酒》組詩、《止酒》與《述酒》。同時(shí)“酒”也成為了塑造陶淵明藝術(shù)形象的一個(gè)重要意象,許多學(xué)者都曾對(duì)其做過解讀。袁行霈曾評(píng)價(jià)陶淵明:“他對(duì)宇宙、人生和歷史的思考都是靠著酒的興奮與麻醉這種雙重刺激而得到的。”[4]113,可見在大多數(shù)中國評(píng)論家眼中,陶淵明的酒就是他進(jìn)行文學(xué)創(chuàng)造所不可或缺的因素,醉看世事也是其高潔性情的集中體現(xiàn)。但艾克爾對(duì)于“酒”的解讀卻獨(dú)樹一幟,甚至飽受爭議。
艾克爾對(duì)于陶淵明詩歌的翻譯觀深受中國古老詩學(xué)思想“詩言志”的影響,這使其專注于對(duì)詩歌本身的解讀,他企圖通過陶淵明的詩歌還原出一個(gè)“隱士”的藝術(shù)形象。從艾克爾所譯的一些陶詩及其為詩歌做的注解中,可以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還原一個(gè)艾克爾藝術(shù)世界中的“陶隱士”。通過對(duì)比《止酒》兩個(gè)譯本,可以窺探到艾克爾眼中“陶隱士”形象的與眾不同:
陶淵明《止酒》: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5]201
艾克爾譯:Since then from day to day/ I have never stopped wine./For if I stopped it/ My feelings knew no pleasure./Stopping at evening/ I could not get to sleep,/Stopping at dawn/ I could not even rise.[6]70
辛頓:I’d drunk nonstop my whole life through,/knowing it all felt wrong when I stopped./ I tried stopping at dusk,but couldn’t sleep,/and stopping at dawn,I couldn’t get up.[7]61
該詩句是《止酒》中最為傳神之處。張自烈直言“無往不止,所不止者獨(dú)酒爾”[5]202,以表示陶潛對(duì)酒的鐘愛。中國學(xué)者普遍將陶潛愛酒解讀成對(duì)于官場(chǎng)的失望,所以借酒澆愁,用酒精麻痹自己。胡仔評(píng)價(jià)《止酒》這首詩歌為:“淵明之用意非獨(dú)止酒。”[5]202然而,我們反觀艾克爾對(duì)于該句詩的譯文,可以發(fā)現(xiàn)艾克爾將“平生”翻譯成“Since then from day to day”即“自那以后”,很多學(xué)者將其定義為艾克爾在翻譯上的失誤。但筆者認(rèn)為,此處的處理符合艾克爾對(duì)于“陶隱士”這一藝術(shù)形象的理解。艾克爾在翻譯《止酒》的時(shí)候認(rèn)為酗酒正是陶潛仕途失敗歸隱田園的原因[1]17。他認(rèn)為此處正是集中體現(xiàn)了陶淵明的飲酒已經(jīng)到了“不能被意志和理性所控制”的程度[6]34。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艾克爾采用了許多程度副詞去表達(dá)戒酒而不能的焦灼情緒,譬如“never”“even”。而被歷代中國評(píng)論者所稱道的二十個(gè)“止”字也被艾克爾直接對(duì)應(yīng)成“stop”。對(duì)于中國學(xué)者而言,詩文中的二十個(gè)“止”字散布于詩歌的每一句之中,雖用同一個(gè)“止”字,但字字皆有深意,層層遞進(jìn),無論是針砭時(shí)弊還是表達(dá)一種醉意山水的心境,總之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反觀艾克爾的翻譯,采用相同的動(dòng)詞“stop”,一方面是為了突出“止”而不能,起到一種強(qiáng)調(diào)的作用;另一方面頻繁地出現(xiàn)“stop”也能讓讀者體會(huì)到陶淵明戒酒時(shí)焦慮的情緒。對(duì)比大衛(wèi)·辛頓的譯本,艾克爾的譯本明顯要更加富有情感。
與艾克爾不同,海陶瑋對(duì)于陶潛的“酒”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的翻譯基本上沿襲了歷代中國評(píng)論者對(duì)于陶淵明藝術(shù)形象的主流看法。在其翻譯《飲酒》詩的注釋中寫道:“醉酒之人,就仿佛嬰孩,無所顧忌,可以完全放松心神,放棄對(duì)周圍環(huán)境的抵抗,此種狀態(tài)恰似陶淵明。”[8]134海陶瑋對(duì)于《飲酒》(其七)的翻譯就體現(xiàn)出其對(duì)于“酒”的理解。
《飲酒》(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yuǎn)我遺世情。[5]175
海陶瑋譯:The fall chrysanthemums have lovely colors/I pluck the petals that are wet with dew./ And float them in this Care Dispelling Thing/ To strength my resolve to leave the world.[8]90
海陶瑋在翻譯這句詩的時(shí)候,盡可能地從形式到內(nèi)容上都保留了原文的韻味。整個(gè)翻譯在用詞上面給人以輕松愉快之感。“佳”字被譯成“l(fā)ovely”,這一處對(duì)應(yīng)不但實(shí)現(xiàn)了語義上的對(duì)等,更是體現(xiàn)出海陶瑋對(duì)于陶詩中“酒”這個(gè)意象的情感傾向。第二句中的“忘憂物”被譯者直譯成“Care Dispelling Thing”并加以注釋,一方面最大限度保留了原詩中在此處用典的精髓,另一方面“Care Dispelling”也與前文的“l(fā)ovely”在情感上形成了呼應(yīng)。該詩的前四句,為整首詩營造了一種悠閑雅致的情境,詩人將沾了晨露的菊花浮于酒杯之上,此情此景令其忘卻煩憂,靜靜地享受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因此在海陶瑋看來,飲酒幫助詩人達(dá)到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精神境界,酒是擺脫煩惱、孑然一身的精神慰藉。在對(duì)“酒”這一意象的解讀方面,海陶瑋的觀點(diǎn)同中國主流評(píng)介基本一致,這大概與海陶瑋漢學(xué)家的身份相關(guān)。
2.何以“修禪”
對(duì)于陶詩的思想研究,一直都是學(xué)界爭論不休的問題。但有一點(diǎn)是比較統(tǒng)一的,那就是陶淵明受到儒、道、佛的影響,但究竟誰占主導(dǎo),迄今為止也沒有明確定論。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陶淵明深受儒家學(xué)說的影響,其詩文用典許多都是出自儒家經(jīng)典;有學(xué)者認(rèn)為陶淵明屬于老莊思想,其詩歌中所倡導(dǎo)的避世歸耕、回歸自然與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契合;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陶淵明受佛教哲學(xué)的影響,因南北朝時(shí)期佛教盛行,且有學(xué)者考證陶淵明歸隱的住地正是佛教圣地;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陶淵明是受儒、道、佛三家影響的雜家,總之眾說紛紜,難有定論[9]。在西方世界,各個(gè)譯者對(duì)于陶淵明思想的解讀也是各成一派,但也大體如是。艾克爾認(rèn)為“陶潛的世界觀完全來自中國本土,并且以儒家思想為主導(dǎo)”[6]36。海陶瑋則對(duì)陶詩進(jìn)行了大量的考證研究,研究其詩歌中的意象與互文性,得出了一個(gè)結(jié)論,即陶潛詩歌創(chuàng)作受到儒家與道家思想的共同影響,并在其對(duì)于《形影神》的解讀中做出了具體的闡釋。而此處值得一提的是大衛(wèi)·辛頓對(duì)于陶詩思想的研究,他提出了陶詩與禪宗的關(guān)系。雖然禪宗盛行是在六朝之后,但辛頓認(rèn)為陶潛的思想與佛教的禪宗極端契合,并稱陶淵明為“禪宗中第一位不入沙門的弟子”[2]52。辛頓在分析陶詩的時(shí)候提出了一個(gè)重要概念——閑(idleness)。在《陶潛詩選》中,辛頓共翻譯了35首陶潛的詩歌(包括組詩),其中有12處都使用了idleness。以《歸園田居》(其一)為例:
《歸園田居》(其一):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yuǎn)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5]47
辛頓譯:home again.I’ve got nearly two acres here,/and four or five rooms in my thatch hut./Elms and willows shade the eaves out back,/and in front,peach and plum spread wide./Distant-village people lost in distant,/ haze,kitchen smoke hangs above wide-open/country.Here,dogs bark deep in back roads,/ and roosters crow from mulberry treetops.[7]18
陶潛通過《歸園田居》(其一)中的四句景色描寫,勾勒出了現(xiàn)實(shí)中的桃花源。對(duì)于此處的景物描寫,辛頓采用了自由詩的形式進(jìn)行翻譯。譯文看似模仿漢詩的形式,其實(shí)深入分析每句話,不難發(fā)現(xiàn),譯文常常從一個(gè)連續(xù)的詩句跨越到下一行詩句,例如“home again”“country”和“and”都是一些跨越到下一詩行的詩句;同時(shí),句子為了語義和語法完整,采用了許多連詞與標(biāo)點(diǎn),使得詩行中出現(xiàn)許多語義停頓,致使譯文難以傳達(dá)出原詩的韻律,但這種散文般自由的譯文風(fēng)格讀起來給人輕松自然之感,準(zhǔn)確地傳遞了原詩的內(nèi)容、主題和神韻。辛頓用西方現(xiàn)代詩的方式讓讀者從譯文的語言中就可以感受到一派閑情雅致的田園風(fēng)光。
《歸園田居》(其一):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5]47
辛頓譯:No confusion within the gate,no dust,/ my empty home harbors idleness to spare./Back again: after so long in that trap,/ I’ve returned to all that comes of itself.[7]18
《歸園田居》(其一)是學(xué)者們談?wù)撎諟Y明隱逸精神時(shí)引用率較高的一首詩,前面四行詩句體現(xiàn)出陶淵明在辭官之后歸隱田園的情境,最后一句畫龍點(diǎn)睛,使得前方所有的景色描寫霎那間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這種質(zhì)樸無華的鄉(xiāng)野生活為何被陶潛述說得這般恬淡美好?正是因?yàn)榫迷诠賵?chǎng)的“樊籠”之中,對(duì)自然心向往之,所以歸耕農(nóng)田之后才能感受到田園生活的美妙。辛頓在此處的翻譯傳達(dá)了他對(duì)塑造陶淵明“隱士”這一藝術(shù)形象的理解。在通常的解讀中“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是作者將“戶庭”與“虛室”比擬自己的內(nèi)心,用來表達(dá)擺脫官場(chǎng)回歸田園后詩人恬淡的心境,恰如莊子所言“瞻彼闋者,虛室生白”[10]。辛頓在翻譯該句詩的時(shí)候采用半虛擬半現(xiàn)實(shí)的描述,“戶庭”與“虛室”都被辛頓直接對(duì)應(yīng)成英文中的“the gate”與“my empty home”,而“陳雜”與“余閑”卻并未對(duì)應(yīng)成“dust”與“the sufficient leisure”,而是采用了意譯的手法,將“陳雜”譯成“confusion”,表現(xiàn)出作者歸耕田園時(shí)內(nèi)心的怡然;同樣“余閑”對(duì)應(yīng)成“idleness”。陶潛此處用“閑”類似一個(gè)雙關(guān)語,一方面表示“虛室”開闊,另一方面“虛室”又指陶潛的內(nèi)心世界,那么“閑”此時(shí)就是一種恬靜悠閑的心態(tài)。辛頓將“余閑”與“idleness”相對(duì)應(yīng),雖然損失了一些原詩的韻味,但也使得原詩更容易理解。此外,辛頓在處理“復(fù)得返自然”一句的譯文時(shí)充分體現(xiàn)了其對(duì)于“陶隱士”這一藝術(shù)形象的理解。中外許多評(píng)論家都曾對(duì)陶潛這句詩有過評(píng)論,其中大部分將其歸結(jié)為“回歸田園”,甚至有譯者將《歸園田居》直接譯成“Return to Nature”[10],但辛頓在翻譯該句詩的時(shí)候,并未用到諸如“nature”“countryside”等一些表達(dá)自然與田園的詞匯,而是直接使用了“I’ve returned to all that comes of itself”。辛頓對(duì)于陶潛“回歸自然”的主題有著更深層次的理解,他認(rèn)為陶潛的“回歸自然”實(shí)際上是“回歸自我”。陶潛的“閑”才是他創(chuàng)作的原動(dòng)力,這就是他的思想與佛教禪宗的契合之處,“隱士”的選擇根本是為了能夠達(dá)到一種精神上的“閑”。
3.何以還原“陶隱士”
A.R·戴維斯和海陶瑋一直致力于還原陶淵明在詩歌中的藝術(shù)形象。戴維斯曾言“個(gè)人抒情詩是對(duì)個(gè)人情感的描述,陶淵明就是這一傳統(tǒng)的偉大實(shí)踐者,他深受讀者的喜愛是因?yàn)樗髌分斜憩F(xiàn)出了一種個(gè)性,但是許多中國人似乎不愿在這一點(diǎn)上來欣賞陶淵明的成就,而是要從他的作品中發(fā)現(xiàn)其他的目的與價(jià)值”[11]15。此處戴維斯已經(jīng)對(duì)自己的研究對(duì)象進(jìn)行了定性,那就是研究陶淵明詩歌中所塑造的藝術(shù)形象,而并非真實(shí)世界中的陶淵明。由于歷史上陶淵明的傳記非常少,僅有的幾篇多出現(xiàn)在《隱逸傳》之中,因此大眾對(duì)于陶淵明形象的把握主要通過他的詩歌作品。假若用從詩歌作品中得出的關(guān)于陶淵明生平的推斷來分析他的詩歌,就會(huì)容易陷入邏輯上的循環(huán)論證,中西方詩學(xué)的差異在此處得以體現(xiàn)。傳統(tǒng)的東方詩學(xué)“詩言志”在此時(shí)并沒有影響到諸如戴維斯這樣的譯者,相反,他更渴望還原一個(gè)真實(shí)的文學(xué)世界中的“陶隱士”,而這一點(diǎn)可以從戴維斯對(duì)于陶淵明《飲酒》(其五)的翻譯中得到證實(shí):
原詩: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yuǎn)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5]153
戴維斯譯:I have built my hut within men’s borders,/But there is no noise of carriage or horses./ If you ask how this is possible: /When the heart is remote,the place becomes like it./ As I pluck chrysanthemums beneath the eastern fence,/I distant see the southern mountains.[11]96
《飲酒》(其五)是陶淵明廣為流傳的作品之一,尤其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句最為出名,該句被認(rèn)為集中體現(xiàn)了陶淵明歸隱時(shí)恬淡的心境。然而,該首詩在翻譯的過程中有一個(gè)難點(diǎn),那就是對(duì)句子主語的處理。從戴維斯譯本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對(duì)比原文譯文中增加了主語“I”。從語法層面上而言,增譯“I”可以使得英譯詩句更符合英文文法,有助于目標(biāo)語讀者了解詩句的含義;另一方面,譯者也想通過增加主語人稱“I”進(jìn)一步豐富陶淵明的藝術(shù)形象。但筆者認(rèn)為,此處是戴維斯忽略了對(duì)原文解釋的多種可能性,又或者是譯者根據(jù)自身的理解挑選了一種可能性闡釋給讀者。因?yàn)樵谠娜笔е髡Z的前提下,句子的主語可以是任何人,不一定就是詩人[12]。譬如詩句“問君何能爾,心遠(yuǎn)地自偏”這句話的主語可以是陶淵明,也可以是另外一個(gè)人。而譯者則采取與讀者互動(dòng)的方式對(duì)這句話進(jìn)行了處理,并且將“君”這個(gè)中文中的泛指人稱代詞對(duì)應(yīng)成了英文中的“You”,使得該句話變成了詩人的獨(dú)白,直觀地表達(dá)了詩人的想法。這種譯法雖然對(duì)于原文而言是一種損失,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加有助于讀者去理解陶詩的寓意。反觀中國的譯者,譬如方重就采用了更加忠實(shí)于原文的形式,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省去主語,以追求與原文形式上最大限度的切合。在戴維斯的眼中,陶淵明是一個(gè)汲汲于在讀者面前完善自我形象的藝術(shù)家,這又與中國歷代對(duì)陶淵明的認(rèn)識(shí)截然不同[1]53。
(二)“陶隱士”形象的傳承
無論在東方或者西方,對(duì)于大多數(shù)讀者而言,陶淵明都以一個(gè)“隱士”的形象出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之中。艾克爾更是直接將其譯本命名為《陶隱士:陶潛詩六十首》,足見其“隱士”形象的深入人心。雖然,上文中筆者已經(jīng)談及西方世界在陶詩譯介過程中“陶隱士”的形象在不同譯者的筆下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譯變,但是我們透過作品仍然能夠發(fā)現(xiàn),在針對(duì)陶淵明藝術(shù)形象的塑造上中西方仍然存在許多的共同之處。英語國家前期對(duì)于陶詩的譯介以及近期大衛(wèi)·辛頓對(duì)于陶詩的譯介都不夠全面,基本上都是沿襲傳統(tǒng)陶學(xué),并在此基礎(chǔ)上增加了個(gè)人的理解。海陶瑋和戴維斯是英語國家最早對(duì)陶淵明進(jìn)行全面譯介的兩位譯者,但漢學(xué)家的背景決定了他們雖然在個(gè)別之處對(duì)于陶淵明的形象進(jìn)行了探究,并提出了一些頗有見地的觀點(diǎn),但總體來說還是沿襲了中國傳統(tǒng)陶學(xué)的一些觀點(diǎn),并在此基礎(chǔ)上結(jié)合譯者自身的知識(shí)體系和研究方法,對(duì)“陶隱士”這一藝術(shù)形象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例如,“出仕”與“歸耕”是陶隱士這一藝術(shù)形象塑造的兩大主題。就其“出仕”的原因,中外學(xué)者的觀點(diǎn)大體都是政治動(dòng)蕩以及陶淵明的內(nèi)心意愿。海陶瑋直言“陶潛反映了他所處時(shí)代的沖突與矛盾,他的詩歌反映了中世紀(jì)中國文人墨客所處的兩難境地”[8]1。由此可以看出,海陶瑋對(duì)于陶淵明徘徊于“入仕”與“歸耕”持理解與贊賞的態(tài)度。這與國內(nèi)學(xué)者的理解如出一轍。袁行霈將陶淵明歸隱的方式進(jìn)行了不同層次的劃分:歸隱田園,回歸自然,離開人世,歸于空無[4]110。正是在“出仕為官”與“歸耕田園”之間的搖擺不定使得陶潛不斷去思考生活,這也是他詩歌的與眾不同之處。人們對(duì)于陶淵明的評(píng)價(jià),首先是將其作為一個(gè)“隱士”來對(duì)待。這種徘徊不定的生存模式,促成了陶淵明廣泛的詩歌主題,他被海陶瑋稱為“哲學(xué)詩人”,并且海陶瑋評(píng)價(jià)其詩歌“具有超越時(shí)空的非凡魅力”[8]1。“歸隱”與“田園”也成為陶詩最為人稱道的兩個(gè)主題,這些田園詩對(duì)于塑造陶淵明“隱士”這一藝術(shù)形象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王宏印在為《巴赫金詩學(xué)視野中的陶淵明詩歌英譯復(fù)調(diào)的翻譯現(xiàn)實(shí)》所做的序言中將陶淵明詩歌的主題分為十個(gè),即歸隱、飲酒、生死、田畝、詠史、讀經(jīng)、玄言、人倫、唱和以及烏托[13]。將陶詩主題串聯(lián)起來進(jìn)行研究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不同時(shí)期陶詩所反映出的詩人的心境與感悟。
而這種觀點(diǎn)也可以體現(xiàn)在中外譯者對(duì)于陶詩的翻譯方面。這一點(diǎn)我們可以對(duì)比中外譯者對(duì)于《雜詩十二首(其三)》的翻譯:
原文: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蕖,今做秋蓮房。嚴(yán)霜結(jié)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還復(fù)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shí),憶此斷人腸。[5]246
海陶瑋譯:The glorious blossoms are hard to keep,/Decline and growth cannot be foretold./ Yesterday’s springtime lotus flower,/Today has become the seedpod of autumn./ Stiff frost binds the grass in the meadow,/Decay and withering are never done./ Sun and moon will still resolve,/But we leave never to shine again./ With longing I look to time gone by—/Remembering it breaks a man’s heart.[8]88
汪榕培譯:As flowers cannot blossom all year around,/So fortune cannot always well abound./ In spring the lotus blossoms on the lake;/In autumn it bears seeds in summer’s wake./ When hoary frost hits plants that still survive,/The wild weeds wither but remain alive./ Whil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prolongs on earth,/I’ll die and never have a second birth./ At the thought of all those good old days,/I’m crushed by sad emotions the scene conveys.[14]
《雜詩十二首》是陶淵明歸隱田園偶感之作,詩人歸隱數(shù)年之后,感慨歲月流逝,回憶壯年入仕之時(shí)躊躇滿志,可憐壯志未成,禁不住傷春悲秋的深深悲苦。筆者通過對(duì)比海陶瑋與汪榕培的翻譯來分析勾勒陶隱士晚年的形象。整首詩通過意象的羅列與遞進(jìn)描繪出了今昔對(duì)比的榮衰景象。通過帶領(lǐng)讀者在時(shí)空穿梭中重溫同一個(gè)事物在不同時(shí)期的不同境遇,暗指詩人自己對(duì)于青春不再、時(shí)光蹉跎的感慨。通過對(duì)比分析,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海陶瑋的譯文與汪榕培的譯文在意象的描述上面用詞基本一致。但是通過對(duì)比表3可見汪譯版對(duì)某些意象做了相應(yīng)的改動(dòng),除了符合詩句傳遞的內(nèi)容之外更加注重詩歌的韻律。譬如秋蓮,汪譯版沒有直接譯成“autumn lotus”,而是貼合實(shí)際,譯成“seeds in summer’s wake”。“日月還復(fù)周,我去不再陽”也沒有像海陶瑋一樣直接處理成“Sun and moon will still resolve,But we leave never to shine again”。此處,汪譯版更加注重意義的傳遞,譯成“Whil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prolongs on earth,I’ll die and never have a second birth”,直接將“日月更迭,生命周而復(fù)始”的意思通過押韻的詩句表達(dá)出來。總體來說,海陶瑋的譯本更加力求在形式上與意象上都準(zhǔn)確地遵照原文,而且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風(fēng)格的一致。

表3 《雜詩十二首(其三)》海陶瑋譯版與汪譯版主要意象翻譯對(duì)比
當(dāng)讀者跟隨陶潛經(jīng)歷了時(shí)光穿梭、意象變遷之后,最后兩句詩畫龍點(diǎn)睛,點(diǎn)明了詩人內(nèi)心的矛盾。一方面,詩人選擇隱居山林,安貧樂道;另一方面,郁郁不得志也使得詩人內(nèi)心悲苦。詩句的最后一句才是全詩畫龍點(diǎn)睛之處,通過對(duì)最后一句的翻譯,可以體現(xiàn)出譯者對(duì)于全詩的理解,同時(shí)也將晚年的陶隱士這一形象勾勒得更加豐滿。海陶瑋的譯本與汪譯本在最后一句的處理上有一些不同。
海陶瑋譯:With longing I look to time gone by—/Remembering it breaks a man’s heart.
汪榕培譯:At the thought of all those good old days,/I’m crushed by sad emotions the scene conveys.
通過對(duì)比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兩個(gè)譯本在主題的表達(dá)方面是一致的,不同點(diǎn)主要集中在最后一句的處理上。海陶瑋在最后一句中引入了一個(gè)“他者”— “man”;而汪譯版則直譯為“I”。但從原文角度分析,我們很難確定“憶此斷人腸”中的“人”究竟是詩人自己還是指普羅大眾。或許此處正是陶潛為讀者埋下的一個(gè)伏筆,等待讀者在通讀全詩之后會(huì)有自己的感悟。但這并不影響整首詩歌傳遞出詩人對(duì)“時(shí)易事異”的慨嘆。
綜上分析,“陶隱士”這一藝術(shù)形象在譯介的過程中發(fā)生了譯變。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此種譯變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譯入語母語國家譯者對(duì)于所翻譯詩歌的理解。兩方面原因會(huì)導(dǎo)致理解上的不同:一是當(dāng)時(shí)的詩學(xué)發(fā)展;二是譯者自身的知識(shí)背景。但這種譯變也并非將“陶隱士”改造得面目全非,而是基于對(duì)這一藝術(shù)形象的普遍認(rèn)知。而這種譯變恰恰反映出中西方譯者在不同的詩學(xué)傳統(tǒng)與知識(shí)背景下對(duì)于翻譯能動(dòng)的創(chuàng)造。
三、“陶隱士”形象譯變之反思
通過研究陶詩中陶淵明“隱士”形象在譯介過程中的流變,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從譯者角度出發(fā),受到中西方詩學(xué)差異以及不同譯者所處年代經(jīng)濟(jì)文化與教育背景等方面差異的影響,西方譯者更注重從文本角度進(jìn)行解讀,并輔助其他背景資料。他們更加傾向于將陶淵明的隱士形象同詩人本人進(jìn)行分離,從譯者所處的年代特征角度出發(fā),挖掘陶淵明隱士形象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讀者的意義;從讀者角度出發(fā),“陶隱士”的藝術(shù)形象通過譯者的加工能夠更加符合當(dāng)時(shí)的主流詩學(xué)與讀者對(duì)該藝術(shù)形象的期待,在某種程度上更加有助于“陶隱士”這一藝術(shù)形象的傳播。總體而言,通過對(duì)陶詩英譯不同時(shí)期和不同背景的主流譯者進(jìn)行分析,大體可以勾勒出陶淵明在英語國家文化背景下的藝術(shù)形象,雖然在陶淵明原有“隱士”形象的基礎(chǔ)上或多或少發(fā)生了一些譯變,但這一形象的譯變一方面可以反映出譯著出版時(shí)譯入語國家讀者的接受程度;另一方面也能為構(gòu)建中國古詩詞海外譯介模式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