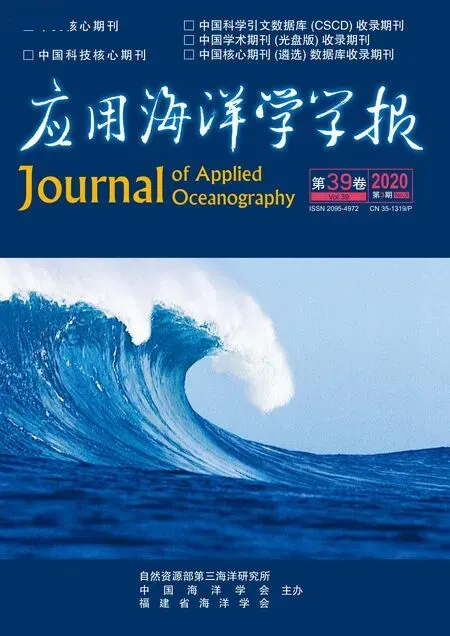渤海灣北岸海陸風及湍流強度特征分析
龍 強,王 鋒,王 暢,米欣悅
(1.唐山市曹妃甸區氣象局,河北 唐山 063200; 2.唐山市氣象局,河北 唐山 063000;3.河北省氣象與生態環境重點實驗室、海洋氣象探測試驗基地,河北 唐山 063200)
海陸交界的近地層是陸地與大氣、陸地與海洋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的重要場所,環境狀況復雜、區域特征明顯,自然資源豐富,其中海上風電資源以其清潔、高效的優勢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重視,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能源產業之一[1]。歐洲是全球海上風電發展最快的地區,我國起步相對較晚,2006年開始局地的海上測風,2008年我國第一座大型海上風電項目(上海東海大橋海上風電項目)的建設拉開了中國海上風電開發的帷幕[2]。2017年渤海灣北岸的唐山樂亭菩提島海上風電場300兆瓦示范工程啟動建設,成為我國北方地區第一個海上風電項目。
影響風電場選址和風機運行的客觀條件包括地形、風速、風功率密度等,其中又以湍流的影響最大,是導致風機齒輪損壞、葉片開裂、發電量不達標等的核心因素。近年來,多地風電場因強風湍流出現事故,2006—2014年浙江蒼南、福建漳浦、海南文昌等沿海地區風電場受臺風影響先后遭受倒塔、葉片破裂等嚴重損失,2010年8月甘肅瓜州一在建風機組因強風發生倒塔事故,2019年3月渤海灣北岸曹妃甸一機組葉片因強風整體折斷并引發另一支葉片斷裂,成為該風電場投入運行以來首個氣象條件導致的自然事故。為保障風機安全性和良好的發電性,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的風力發電機標準(IEC-61400)明確了風機設計湍流等級[3],湍流強度成為風機安全等級分級的重要參數之一。湍流具有隨機性、非線性,作為近海和海岸地區特有的地方性風,海陸風的周期性對湍流強度的變化也有一定的影響[4]。立足于降低事故風險、提升經濟效益,國內相關學者和專家對風湍流及其對構筑物的影響作了相關研究。陳飛等(2008)利用多種觀測資料評估了華東連云港沿海地區和近海風能資源,探討了風湍流強度對風力發電的影響[5];張雪芝等(2018)研究了湍流強度對風場發電量的影響,提出了利用實時湍流強度計算風電場發電量的方法[6];宋麗莉等(2004)對比分析了華南廣東沿海大風在近地層的陣性特征、演變規律,分析指出了結構工程抗風設計中我國相關規范存在的參數誤差,并提出了風參數取值的具體依據[7];顧明(2010)計算了北黃海、南海、相模灣等近海面層大氣湍流強度,指出其比近地層大氣湍流強度普遍低一個量級,且近海面層大氣湍流強度與風速呈負相關關系[8];黃林宏等(2016)利用全國風能資源專業觀測網數據評估了風機選型算法在我國的適用性,重點指出其在東南沿海和西北、華北平原地區的計算偏差[9]。著眼全國沿海,目前已有相關學者分析了我國華南、華東沿海地區的湍流特征,并結合實際應用需求提出了建議,但對于華北地區沿海,特別是地處內海的渤海灣卻鮮有相關研究。本研究以渤海灣北岸近海面層和近地層的湍流為研究對象,分析了當地海陸風及湍流強度的時空特征,并重點對不同天氣系統所致大風條件下的湍流強度特點作了剖析,以期為本地風電場建設和風力發電的氣象保障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海陸風分析資料源于唐山祥云島地面觀測站,地處渤海灣北岸,地理位置如圖1所示。根據站點所處位置,確定海-陸風(即海洋吹向陸地的風)風向為順時針E—SW,陸-海風(即陸地吹向海洋的風)風向為順時針WSW—ENE,晝夜以平均日出和日落時間劃分。本研究選取2017—2018年4個季節的觀測資料分析渤海灣北岸的海陸風特征。

圖1 渤海灣北岸相關站點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relevant stations on the north shore of Bohai Bay
湍流強度分析資料源于曹妃甸和嘴東兩座梯度測風塔,地理位置如圖1所示。曹妃甸風塔位于嘴東風塔SSE方向,地處吹沙造地而成、三面環海的曹妃甸海島,代表沿岸近海面層。嘴東風塔背依陸地,面向渤海灣,代表沿岸近地層。兩座風塔均隸屬于中國氣象局2008年牽頭組織實施的風能資源專業觀測網,設備型號、維保養護均一致,高度分別為100、70 m,垂直分層為10、30、50、70、100 m(嘴東站無100 m層),各層均有風要素監測。本研究選取2011—2013年觀測資料分析渤海灣北岸的近海面層和近地層湍流強度特征。
1.2 計算方法
根據IEC-61400標準定義,湍流強度是指10 min內風速隨機變化幅度大小,是10 min平均風速的標準偏差與同期平均風速的比率。計算公式如下。
(1)

2 結果與討論
2.1 海陸風特征
由圖2的風頻圖可知,全年、夏季和冬季白天由海-陸風向夜間陸-海風的轉變均明顯:全年白天海-陸風主導風向SSW頻率到夜間顯著降低,夜間陸-海風ENE風頻則顯著增大,海-陸風(E—SW)風頻到夜間降低6.5%,即陸-海風(WSW—ENE)風頻增大了6.5%;夏季白天以E、S和SSW風向為主導風向,均為海-陸風,三者的風頻達到了55.8%,夜間SSW風頻明顯降低、ENE風頻則顯著增大,海-陸風風頻到夜間降低達11.0%;雖然受冷空氣頻繁過境影響,冬季白天和夜間的主導風向均為W和ENE,風頻整體變化不大,但海-陸風風頻到夜間仍然降低了3.2%。

圖2 渤海灣北岸全年、夏季和冬季的晝夜風頻圖Fig.2 Day and night wind direction frequency rose diagrams of the whole year, summer and winter on the north shore of Bohai Bay
可見,渤海灣北岸的海陸風特征顯著,海洋在白天和夜間的熱源轉換帶來了沿岸風向的變化,這可能會給海面和沿岸湍流強度帶來一定的影響。
2.2 湍流特征
2.2.1 湍流垂直變化特征 利用兩座風塔的垂直監測數據計算湍流強度值,結果如圖3所示。可以看出,湍流強度隨高度增大而減小,且高度越高湍流強度減小的趨勢越平緩;平均風速隨高度的增大而增大,這與湍流強度的變化相反。由于海水熱容量高于陸地,近海面層溫度梯度小于同時間的陸上近地層,且海洋下墊面整體比陸地下墊面更簡單、平滑,因此曹妃甸風塔所代表的的近海面層湍流強度整體小于嘴東風塔所代表的的沿岸近地層湍流強度。

圖3 渤海灣北岸湍流強度和風速隨高度的變化特征Fig.3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urbulence intensity and wind speed with height on the north shore of Bohai Bay
由于所處位置下墊面的不同,近海面層和近地層湍流強度特征差異明顯。可見,在確定風電場選址時,應充分考慮項目所在地的精細化地形、地貌以及海洋氣候的影響,確保風電項目落地運行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2.2.2 湍流季節性變化特征 分別對近海面層和近地層湍流強度特征進行季節性分析(圖4)。由圖4(a)可知,無論近海面層還是近地層,各高度湍流強度的季節性特征較為一致,春季3個月(3—5月)的湍流強度整體變化不明顯或增大平緩,夏季(6—8月)湍流強度整體偏大,秋季(9—11月)為過渡性季節,湍流強度變化無明顯規律,冬季(12月至次年2月)湍流強度則相對偏小。由圖4(b)可知,相對于近地層,近海面層湍流強度季節性變化相對平緩,這可能是源于二者下墊面不同,海洋下墊面單一且曹妃甸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常年不淤不凍[10],環境的季節性變化不大,而陸地下墊面相對復雜,植被生長隨季節變化也較大,故近海面層和近地層湍流強度的季節性變化存在差異。
2.2.3 不同天氣系統下的湍流特征 渤海灣北岸向東直對渤海海峽,偏東大風在狹管效應的作用下在本地會得到顯著增強,成為本地大風的主導風向[11]。雷暴所致的下擊暴流往往會在本地形成極強風力,本地歷史極端風力(13級)即是一次強對流過程引發。對本地有直接影響的北上臺風平均每兩年1次,但2018年連續3個臺風過境,臺風對風電場的影響也應引起重視。因此,這里對偏東大風、雷暴大風和北上臺風條件下的湍流強度分別進行分析研究。
①偏東大風條件下的湍流強度特征。選取兩個冷空氣引起的偏東大風過程(2011年11月28日—29日和2013年3月18日—19日),研究大風期間近海面層和近地層湍流強度的變化特征(圖5)。強風條件下,近海面層和近地層風速隨高度增大而增大且增速減緩,湍流強度隨高度增大而減小且趨勢同樣減緩,但近海面層70 m及以下湍流強度整體比近地層湍流強度大,經初步分析,海面空氣動力學粗糙度可能是導致該情況的主因[12-13]。根據已有的研究結論,受海陸風和周邊環境變化影響,渤海灣北岸近地層空氣動力學粗糙度具有明顯的季節性變化特征[14],并非維持不變,且偏東大風在長風區、長風時的作用下,容易在渤海灣北岸形成大浪[15](該兩次過程最大浪高分別達到了5.2、5.1 m),海洋下墊面的粗糙元隨風速發生了變化,大浪的存在改變了近海面層的風場結構。綜上分析,偏東大風及其所致的大浪對近海面層湍流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

圖5 偏東大風期間10 m高度最大風速和最大湍流強度出現時各層的風速和湍流強度Fig.5 Wind speed and turbulence intensity of each layer when the maximum wind speed and maximum turbulence intensity at 10 m height appeared during easterly winds
②雷雨大風條件下的湍流強度特征。選取兩個雷雨大風過程(2011年7月30日和2011年9月1日),研究大風期間近海面層和近地層湍流強度的變化特征(圖6)。和冷空氣偏東大風環境相比,不穩定層結條件下各層風速、湍流強度的特征更特殊一些:近地面層風速有隨高度增大而減小的情況,近海面層和近地層湍流強度出現了隨高度增大而增大的情況,且該情況并非個例(圖略)。目前國內對此現象的研究或解釋比較少,除了海洋下墊面和沿岸下墊面的不同外,對流云團相對于風塔的移動路徑、結構的不規則性、云團的尺度等也可能是導致垂直方向上風速和湍流強度出現特殊情況的原因。

圖6 雷雨大風期間10 m高度最大風速和最大湍流強度出現時各層的風速和湍流強度Fig.6 Wind speed and turbulence intensity of each layer when the maximum wind speed and maximum turbulence intensity at 10 m height appeared during thunderstorms
③北上臺風影響下的湍流強度特征。在兩座風塔服役期間,僅有2012年8月3日—4日的臺風“達維”北上并從風塔位置經過(到達時已減弱為熱帶低壓),路徑如圖7所示。由于臺風期間嘴東風塔處于維修狀態,無數據記錄,因此這里僅作近海面層湍流強度和風速的特征分析。

圖7 臺風“達維”路徑圖Fig.7 Path map of the typhoon Damrey
“達維”過境期間各層風速、湍流強度隨高度增大分別增大和減小(圖8為10 m高度處風速最大時的湍流強度垂直變化,其他時次圖略),這和雷雨大風期間的情況不同,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系統尺度的可能性影響,“達維”系統尺度大于局地對流,在近海面層的影響不如強對流有更加個性化的特征。“達維”靠近時(相關要素變化如圖9所示),近海面層各高度風速逐漸增大,但湍流強度變化不明顯,當“達維”于8月4日02時中心經過風塔時(以氣壓變化為標識),各層湍流強度均達到最大,出現了明顯的波峰,各層風速顯著減小,但于1 h后達到最小,且隨著“達維”繼續移動離開,風速在波動中增大,但比之前風速偏小,湍流強度同時顯著減小。“達維”完全離開后,風速減小,湍流強度再次增大。

圖8 “達維”過境期間近海面層10 m高度最大風速出現時各層湍流強度Fig.8 Turbulence intensity of each layer when the maximum wind speed at 10 m height in the near-sea layer appeared during the typhoon Damrey

圖9 “達維”過境期間近海面各層的湍流強度變化Fig.9 Variation of the turbulence intensity at each near-sea layer during the typhoon Damrey
2.3 風機湍流強度特征值分析
根據IEC-61400標準,風機高度處設計最大抗湍流強度值為0.16。在曹妃甸風塔樣本中,70 m高度處湍流強度大于0.16占8.3%,最大湍流強度達到了0.49,且各季節均有出現。嘴東風塔相應的比例為9.4%,最大湍流強度0.43,各季節也均有出現。不同影響系統下,近海面層和近地層湍流強度有所不同,而“達維”過境期間的湍流強度反而相對偏小,最大僅為0.23,這與相關學者對華南、華東一帶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16-18],這可能是與北上臺風的能量耗散、強度減弱有關。
根據上述分析結論,對于華北渤海灣沿海地區抗湍流強度參數的確定,建議取值0.43~0.49,以區別于受臺風影響較小的歐洲和受臺風影響較大的華南地區,在確保設計安全可靠的基礎上降低建設成本和運營風險。
3 結論
利用相關岸基站、測風塔觀測資料分析了渤海灣北岸海陸風和湍流強度特征,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調整風力發電機抗湍流參數的建議,主要結論如下。
(1)渤海灣北岸晝夜風向由SSW的海-陸風向ENE的陸-海風轉變,這一變化在夏季更為顯著,海陸風特征明顯。
(2)整體而言,近海面層和近地層風速和湍流均隨高度增大分別呈增大、減小趨勢,受海水熱容和下墊面影響,近海面層湍流強度小于近地層湍流強度。
(3)湍流強度具有顯著的季節性特征,夏季大、冬季小、春秋季變化不明顯,且近海面層湍流強度相對于近地層湍流強度變化平緩。
(4)偏東大風條件下,受海面空氣動力學粗糙度變化影響,近海面層70 m及以下湍流強度反而比近地層湍流強度大;雷雨大風期間,近海面層和近地層的湍流強度、風速均有隨高度增大而分別增大、減小的特殊情況;臺風靠近風塔時,各層風速隨高度增大而增大,但湍流強度變化不明顯,臺風經過風塔時,湍流強度最大值和臺風中心到達時間一致,且比風速最小值出現時間提前約1 h。
(5)近海面層和近地層有8%~10%的湍流強度樣本超出了IEC-61400的風機設計標準,建議華北渤海灣北岸風力發電風機抗湍流參數調整至0.43~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