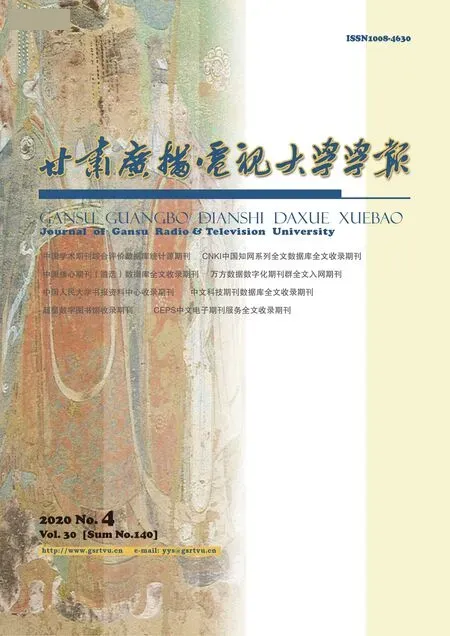貫休詩、書、畫創(chuàng)作內(nèi)在關(guān)系及其原因探微
盧勝志
(西北大學(xué) 文學(xué)院,陜西 西安 710127)
貫休是唐五代時期的著名僧人,他在詩、書、畫創(chuàng)作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歌有《禪月集》行世;書法成就可與懷素并稱,時人謂之“姜體”;羅漢畫在藝術(shù)界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唐朝著名詩人張格在《寄禪月大師》詩中稱道:“畫成羅漢驚三界,書似張顛直萬金。”[1]8630目前學(xué)界對于僧人貫休的研究大多各自為營,對于其詩、書、畫作品之間共同的價值內(nèi)涵一直沒有進(jìn)行較為全面地探索。本文著重以貫休詩、書、畫創(chuàng)作三者間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展開論述,試在創(chuàng)作理念與原因方面進(jìn)行深入探討,以使學(xué)界增強(qiáng)對貫休的全面了解。
一、貫休詩、書、畫創(chuàng)作之“筋力”論
在貫休創(chuàng)作的詩歌與書、畫作品中,潛藏著一種通貫一氣的精神魅力。我們借助貫休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自己的表述,即“筋力”。這里的“筋力”是指一種堅韌不拔的優(yōu)秀品質(zhì),一種超然獨立于世俗、又心系百姓的精神境界。這種精神特質(zhì),既是貫休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自我風(fēng)格的內(nèi)在體現(xiàn),更是其人格魅力與人生追求的外顯。并且在不同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中,貫休“筋力”品格的表現(xiàn)方式存在較大的差異。
貫休在《寄西山胡汾吳樵》一詩中寫道:“覓句句句好,慚予筋力衰”[2]90。在這里貫休既表達(dá)了對自己體力衰退無可奈何地哀嘆,更飽含著對自己命運(yùn)無法掌握地痛心疾首。公元842—846年的武宗滅佛事件,給寺院經(jīng)濟(jì)帶來了沉重地打擊,這使得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僧人群體的生活質(zhì)量斗轉(zhuǎn)直下。此外,安史之亂后,唐朝的中央政權(quán)就逐漸喪失了對地方節(jié)度使的實際控制權(quán)。各地方軍政大員,擁兵自重,為保證軍隊的數(shù)量,各地方官吏在朝廷征稅的基礎(chǔ)上,擅自增加賦稅的征收標(biāo)準(zhǔn),使得社會怨聲載道,民不聊生。
正是基于此種人生閱歷,貫休才對盛唐偉大詩人杜甫的詩歌有著極高的評價。他在《讀杜工部集二首》其一中寫道:“造化拾無遺,唯應(yīng)杜甫詩。豈非玄域槖,奪得古人旗。日月精華薄,山川氣概卑。古今吟不盡,惆悵不同時。”[2]54-55一句“古今吟不盡,惆悵不同時”,道出了跨越半個多世紀(jì)、跨越生死的兩個人的相濡以沫。對于廣大民眾的同情心理,對于社會的強(qiáng)烈譴責(zé),將兩個人的思想糾集到了一起。貫休對于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成就亦是認(rèn)同的,“日月精華薄,山川氣概卑”,寫出了他對于杜甫詩歌的認(rèn)同和仰慕。
此外,貫休對于以賈島為代表的“苦吟”一派的詩歌是持批評態(tài)度的。他在《讀劉得仁賈島集二首》中明確表達(dá)了自己的態(tài)度和觀點:“二公俱作者,其奈亦迂儒。”[2]55貫休除了在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表達(dá)對于“苦吟”這種作詩方法的批評之外,對于他們的詩歌內(nèi)容也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不滿。在《讀賈區(qū)賈島集》中,貫休寫道:“冷格俱無敵,貧根亦似愚。青云終嘆命,白閣久圍爐。今日成名者,還堪為爾吁。”[2]104
從貫休對于杜甫及以賈島為代表的“苦吟”一派詩歌作品的不同評價可以看出,貫休推崇詩歌創(chuàng)作要有利于時弊,要能夠反映當(dāng)時的時代。其現(xiàn)存的詩歌集《禪月集》共收貫休詩作716首,反映百姓生存艱苦以及揭露社會現(xiàn)實黑暗的作品共76首,占現(xiàn)存詩歌作品總數(shù)的10%多。除此之外,從貫休的詩歌作品中,也能看出其高尚的人格修養(yǎng)及做人的準(zhǔn)則。如其在《白雪曲》中所寫的“為人無貴賤,莫學(xué)雞狗肥”[2]22,在《塞上曲二首》其二中所寫的“男兒須展平生志,為國輸忠合天地”[2]33。其中尤能代表其做人原則的詩歌為《續(xù)姚梁公座右銘》[2]40-41,全詩從個人作為社會不同角色的多個角度展開論述:在面對得失方面的態(tài)度是“見人之得,如己之得,則美無不克。見人之失,如己之失,是享貞吉”;在對待兄弟朋友的時候,要“無輕賤微,上下相依”;在做事的時候要“勵志須至,樸滿必破”等。
《唐才子傳》卷十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唐昭宗年間,武肅錢镠因軍功被封為鎮(zhèn)東軍節(jié)度使,自稱吳越王。貫休當(dāng)時住在靈隱寺,往投詩賀,其中有一聯(lián)寫道:“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武肅大喜,但因為僭越之心過于膨脹,便令貫休將“十四州”改為“四十州”。“休性躁急,答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余孤云野鶴,何天不可飛!’即日裹衣缽,拂袖而去。”[3]433由此可見,貫休不懼強(qiáng)權(quán)、不阿媚權(quán)貴的精神特質(zhì)。
在貫休的書畫作品中,這種“筋力”特色也體現(xiàn)得十分鮮明。他在《觀懷素草書歌》中對懷素草書特色的描寫,既可以看作是其對懷素狂草藝術(shù)的贊頌,也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書法創(chuàng)作方法的一個總結(jié)。
乍如沙場大戰(zhàn)后,斷槍橛箭皆狼藉。又似深山朽石上,古病松枝掛鐵錫。月兔筆,天灶墨,斜鑿黃金側(cè)銼玉,珊瑚枝長大束束。天馬驕獰不可勒,東卻西,南又北,倒又起,斷復(fù)續(xù)。忽如鄂公喝住單雄信,秦王肩上搭著棗木槊。
一句“東卻西,南又北,倒又起,斷復(fù)續(xù)”,是貫休對草書書寫手法的高度概括。他并不斤斤計較于書法筆畫的精致,而是一種隨性的書寫。他的字表達(dá)的是一種內(nèi)在的不受世俗規(guī)則羈絆的精神氣質(zhì)。這種內(nèi)在精神的氣質(zhì)正與其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筋力”風(fēng)格相一致。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貫休反對苦吟,追求內(nèi)容要真切地反映社會現(xiàn)實、真實地反映自我內(nèi)心的想法,且不畏懼世俗權(quán)力的威脅。活出自我,敢說真話,不畏強(qiáng)權(quán)正是貫休一貫的風(fēng)格。
除《觀懷素草書歌》外,貫休在《龔光大師草書歌》中也用了一系列的比喻說明草書的無窮魅力所在:“雪壓千峰橫枕上,窮困雖多還激壯。看師逸跡兩相宜,高適歌行李白詩。海上驚驅(qū)山猛燒,吹斷狂煙著沙草。江樓曾見落星石,幾回試發(fā)將軍炮。別有寒雕掠絕壁,提上玄猿更生力。又見吳中磨角來,舞槊盤刀初觸擊。好文天子揮宸翰,御制本多推玉案。晨開水殿教題壁,題罷紫衣親寵錫。”[2]138“雪壓千峰橫枕上,窮困雖多還激壯”一句,更多的是形容自我生活的窘迫之境,進(jìn)而折射出生活在整個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的生存狀態(tài)。同時,他飄逸的書法風(fēng)格,正是其在藝術(shù)形式上彰顯自我傲然風(fēng)骨、不畏強(qiáng)權(quán)精神特質(zhì)的體現(xiàn)。貫休以“神”為主,以“意”為書的書法思想和縱放恣肆的草書,與其率真自然,豪放不羈的個性是相一致的[4]。這也是其草書被后世稱為“姜體”,在書林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所在。
貫休的繪畫作品以羅漢像最為著名。從繪畫題材上看,他的畫作接近老百姓生活,不是韓熙載這一類宮廷畫師所擅長的富麗堂皇的繪畫風(fēng)格。從貫休的羅漢畫中,我們能夠看到其畫作與詩歌、書法創(chuàng)作相一致的內(nèi)在精神特質(zhì)。《宣和畫譜》卷三中對貫休羅漢畫的特色有著較為詳細(xì)地描述:“然羅漢狀貌古野,殊不類世間所傳。”[5]82歐陽炯在《禪月大師應(yīng)夢羅漢畫歌》中也對貫休作畫時的狀態(tài)進(jìn)行了描述:“高握節(jié)腕當(dāng)空擲,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fèi)日。”[1]8638由此可見,貫休在作畫時,也和其書法創(chuàng)作時的方法相一致,不在細(xì)枝末節(jié)處下功夫。他在繪制作品時,更多的是將個人豪放不羈、任情灑脫的獨特氣質(zhì)融注其中。這種獨特的氣質(zhì)與貫休追求自我、不畏強(qiáng)權(quán)的內(nèi)在品格融為一體。在繪畫題材上,雖然他所畫的羅漢與自我僧人身份關(guān)系密切,但也接近民間大眾的內(nèi)在精神追求。他是始終站在民眾立場,替社會絕大多數(shù)人代言的,而不是虛飾、美化統(tǒng)治階級形象。
總之,在貫休的詩、書、畫作品中,其自我內(nèi)在的精神品格體現(xiàn)得十分鮮明。他的詩歌中體現(xiàn)的不攀附權(quán)貴、關(guān)心民瘼的精神以及書畫作品中彰顯的豪放、灑脫的風(fēng)格,都體現(xiàn)著貫休不受世俗拘束、不被強(qiáng)權(quán)左右的傲岸風(fēng)骨。其詩、書、畫創(chuàng)作的“筋力”所彰顯的內(nèi)在精神特質(zhì)是其詩歌以及書、畫藝術(shù)至今為人稱道的原因所在。
二、貫休詩、書、畫創(chuàng)作中的“野逸”之趣
與貫休灑脫的個性相一致,在其借助詩、書、畫的形式表達(dá)自我精神追求的同時,其作品內(nèi)容本身也帶給人一種“野逸”的審美情趣。這種“野逸”之感,在其詩歌中具體表現(xiàn)為句式的靈活自由、不受拘束,語言的粗糲以及情感的自由奔放。在貫休的詩歌作品中,詩句的靈活自由是最常見,也是最顯著可以表達(dá)作者“野逸”審美情趣的地方。如其詩作《胡無人》:
霍嫖姚,趙充國,天子將之平朔漠。肉胡之肉,燼胡帳幄,千里萬里,唯留胡之空殼。邊風(fēng)蕭蕭,榆葉初落,殺氣晝赤,枯骨夜哭。將軍既立殊勛,遂有胡無人曲。我聞之天子富有四海,德被無垠。但令一物得所,八表來賓,亦何必令彼胡無人。
在這首詩中,作者在句式上打破了對仗,而以三言、四言、六言、七言、八言等不同的句式表達(dá)自己渴望殺盡天下胡人的迫切心情,在情感上飽含著一種對國家、對民族的赤子之愛。與其他人的同題詩歌相比,貫休詩歌的句式更加靈活多變,其所表達(dá)的情感也更加奔放、熱烈。李白在同題詩作《胡無人》中寫道:“嚴(yán)風(fēng)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堅胡馬驕。漢家戰(zhàn)士三十萬,將軍兼領(lǐng)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guān),虜箭如沙射金甲。云龍風(fēng)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無人,漢道昌。”[6]該詩前十句全用七字對,后面幾句為了表達(dá)情感的自由,用了三言、五言、七言三種句式結(jié)構(gòu)。無論從句式的靈活性,還是情感表達(dá)的濃烈程度來看,李白之詩都要略遜一籌。南朝詩人吳筠創(chuàng)作的《胡無人》是五言律詩,南朝徐摛同題詩作是五言六句詩,其余同題詩作如聶夷中、徐言伯的作品均為五言詩,且表達(dá)的情感也都不如貫休詩作所表達(dá)的情感真摯、強(qiáng)烈。
此外,貫休的詩歌作品中,不受詩歌形式束縛的還有《讀離騷經(jīng)》《送盧舍人三首》《懷二三友人》《村行遇獵》《題成都玉局觀孫位畫龍》等。在語言的粗糲以及情感的表達(dá)方面,貫休在其詩《少年行》中,更是直接表達(dá)出對帝王顯貴的諷刺:“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2]24語言直率,情感直露。貫休的這類詩歌通過不加雕琢的語言以及奔放直露的情感抒發(fā),展現(xiàn)了作者的坦蕩襟懷。其詩作中的“野逸”情趣,除通過復(fù)雜的句式加以體現(xiàn)之外,更多地體現(xiàn)在奔放的情感表達(dá)方面。
在貫休的書法作品中,筆法的飄逸與縱橫恣肆本身就有“野逸”的特色。在《宣和書譜》中,他這樣寫道:“作字尤奇崛,至草書益勝。嶄峻之狀,可以想見其人。喜書《千文》,世多傳其本,雖不可以比跡智永,要自不凡。”[7]349-350在《宋高僧傳》卷三十亦有對貫休擅長書法的描述:“休能草圣。”[8]貫休的書法創(chuàng)作筆法奇崛,不同凡響,“乍如沙場大戰(zhàn)后,斷槍橛箭皆狼藉。又似深山朽石上,古病松枝掛鐵錫。”[2]51貫休草書書寫的是真性情,是胸懷坦蕩的自我。由于其書法難見,我們僅能從古人對其書法特色的描述中窺見一斑,實為遺憾。
貫休除了詩歌、書法作品成就很高外,其羅漢畫的創(chuàng)作在藝術(shù)界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宣和書譜》稱:“以至丹青之習(xí),皆怪古不媚,作十六大阿羅漢,筆法略無蹈襲世俗筆墨畦畛。中寫己狀,眉目亦非人間所有近似者。”[7]349貫休的羅漢圖像融入了自我的個性與理解,其奇崛野逸之處,正如《宣和畫譜》中記載的那樣:“然羅漢狀貌古野,殊不類世間所傳。豐頤蹙額,深目大鼻;或巨顙槁項,黝然若夷獠異類,見者莫不駭矚。自謂得之夢中,疑其脫是以神之,殆立意絕俗耳。”[5]82宋人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也道:“嘗睹所畫水墨羅漢,云是休公入定觀羅漢真容后寫之,故悉是梵相,形骨古怪。”[9]96古代書畫典籍中對貫休羅漢畫的記載多若此。其羅漢畫梵相、古怪的外貌是其畫作“野逸”特色的重點所在。研究者大多認(rèn)為貫休畫作中羅漢形象特點來自其夢中或入定時所見,但通過考察羅漢的由來以及貫休的詩歌作品,真相遠(yuǎn)非如此。貫休塑造的形骨古怪的羅漢形象有著深厚的現(xiàn)實基礎(chǔ)。段傳峰在《羅漢圖像發(fā)展史研究》一書中說:“羅漢的觀念雖然源于印度,可印度并無羅漢畫的繪制傳統(tǒng),所以我國畫家便在早期高僧畫和胡僧畫的傳統(tǒng)上創(chuàng)造出中國的羅漢形象。”[10]再者,有關(guān)十六大阿羅漢信仰的成熟是在唐朝,同時,羅漢又為外來宗教信仰,因此,貫休所畫羅漢具有梵相也不足為怪。
即使貫休塑造羅漢形象時,以西方僧人形象為描摹對象,但其所畫羅漢形象的形骨古怪,同樣令人費(fèi)解。不得不提的是,在貫休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也多有西方人面貌的刻畫、頭骨別致的吟詠。在《禪月集》中,就有幾首詩描寫了其日常交往中人物的非凡形象,如表1所示。

表1 貫休詩歌吟詠特殊面貌統(tǒng)計表
貫休和古印度僧人的交往,對其羅漢畫中羅漢形象的塑造具有深遠(yuǎn)地影響。除上面列舉的非漢裔僧人在李唐王朝的統(tǒng)治地域范圍內(nèi)活動外,貫休的詩作還描寫了其與周邊其他國家僧人的交往。在其詩歌《送僧歸日本》《送新羅僧歸本國》《送僧之安南》《送人之渤海》《送新羅衲僧》中都有體現(xiàn)。盡管有如此多的詩歌可以佐證,但域外梵僧具有古怪形狀頭骨的真實性也難以令人信服。相反,我國古代有關(guān)道家仙人形象的記載卻與貫休所畫羅漢形象有一致的地方。《神仙傳·彭祖》在論述仙人形象時說道:“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11]我國神話傳說中象征長壽的壽星老人即為頭骨前額突出。可見,貫休所畫的羅漢形象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國道家仙人形象的影響。在中國人的傳統(tǒng)觀念里,形骨變異是成佛、得道者作為修行成功者在外表上的變化,以此與普通人相區(qū)別。
貫休在羅漢畫中,除了對羅漢的面貌刻畫與眾不同之外,在繪畫筆法上,他擅長使用粗線條勾勒,很少使用工筆細(xì)描。這使得他畫出的羅漢畫整體上看起來剛健有力,有雄樸之風(fēng)。尤其是他畫的人物衣服,很少有精細(xì)的衣服紋理,更多的是通過繪制衣服上大的褶皺來凸顯衣服的存在。此外,貫休創(chuàng)作的羅漢個體,大多都瘦骨嶙峋,身上粗線條的骨頭勾勒,體現(xiàn)著繪畫者的奔放性格。
貫休為什么要用粗疏的線條勾勒瘦硬的梵相羅漢形象?這與貫休的僧人身份以及佛教的發(fā)源地有關(guān)。由于貫休是僧人,其繪畫創(chuàng)作時,以佛教人物為創(chuàng)作題材無可厚非。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來中國傳法的古印度僧人深目大鼻的特點,使得貫休在羅漢畫創(chuàng)作時,融入了他們的面部特征,使得他的羅漢畫看上去與眾不同。此外,由于貫休親眼目睹了社會底層百姓食不果腹的生存狀態(tài),所以在繪制羅漢畫時,人物形象瘦硬,而非天庭飽滿也就容易理解了。
總而言之,在貫休的詩、書、畫作品中,貫穿著一脈相承的精神氣質(zhì)。這種帶有“野逸”風(fēng)格的創(chuàng)作方式,是貫休個人文學(xué)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特色所在。這與其社會經(jīng)歷、教育背景、個人品格等都有著密切地聯(lián)系,而非單一因素所決定的。正是由于這種特有氣質(zhì)的存在,使得貫休的詩、書、畫作品跨越了千年的滄桑歲月,至今仍能引起人們的重視。
三、貫休詩、書、畫創(chuàng)作特色產(chǎn)生的原因分析
貫休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風(fēng)格,從總體上看無論是展現(xiàn)自我的傲骨、關(guān)心民瘼的“筋力”,還是其作品中的野逸之趣,都是其精神世界的真實寫照。貫休之所以有如此倔強(qiáng)、不畏強(qiáng)權(quán)的性格,與其獨特的人生經(jīng)歷和當(dāng)時動亂的社會分不開。
貫休自小在寺廟中長大,接受的是寺院教育。《宣和書譜》記載:“釋貫休字德隱,姓姜,婺州蘭溪人。七歲出家,日誦書每過千字,不復(fù)遺忘。”[7]349七歲出家到成年這一段時期,貫休從未離開過寺院。佛家樂善好施的教義,培養(yǎng)了他善良的性格。成年后,由于寺院經(jīng)濟(jì)遭到破壞,為生計所迫,貫休不得不四處晉謁高官顯宦。在晉謁、云游過程中,貫休接觸到了社會最底層的勞苦大眾,并且由于自我也屬于乞食一族,所以能深深地理解老百姓生存的艱難。貫休對于官僚群體的頌揚(yáng)之作,并非出于真心,而是為生計所迫。相反,那些反映社會苦難的詩作,卻是真正的肺腑之言。這從他對杜甫和以賈島為代表的“苦吟”一派的詩歌褒貶不同的態(tài)度中便可看出端倪。
唐朝到了后期,國家財政極其困難,龐大的官僚系統(tǒng),再加上邊疆兵患,統(tǒng)治階級的財政狀況已經(jīng)是入不敷出的狀態(tài)。845年武宗滅佛的部分原因是為了解決緊迫的財政問題[12]。作為僧侶的貫休,在國家這場經(jīng)濟(jì)危機(jī)面前首當(dāng)其沖地成為受害者。失去了靠固定土地維持生計的貫休,開始了四處游歷、尋找生存依托的生活。也正是由于此種遭遇,使得他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更多地表現(xiàn)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老百姓的艱辛。
由于經(jīng)濟(jì)危機(jī),朝廷開始千方百計地從百姓身上榨取錢財,導(dǎo)致農(nóng)民起義爆發(fā)。朝廷此時已經(jīng)無法掌控全國局勢。鎮(zhèn)守邊關(guān)的大將由于手握兵權(quán),有些甚至自立為王。這對于本就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老百姓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感同身受的僧人貫休,對此痛心疾首,但無能為力,他只能在文學(xué)藝術(shù)的領(lǐng)域宣泄自己的情緒。未曾有濟(jì)世之能,但有同情百姓之心,壓在胸中對社會的不滿情緒使他不宣不快。吳任臣在《十國春秋》中直接評價貫休道:“性落落不拘小節(jié),每于通衢徒步,行嚼果子。”[13]672貫休自七歲入寺廟,這正是其性格養(yǎng)成的關(guān)鍵時期,看不慣人世間的不平之事,不與世間的貪佞之人為伍,只在一心向善,為不平之事鳴冤,與其寺廟生活經(jīng)歷不無關(guān)系。因此他對世俗之間以利益為驅(qū)動的交際方式很是不屑,更是不愿。
貫休的交游極其廣泛,上至王公貴戚,下至平民百姓,無所不有。這使得他的文學(xué)作品展現(xiàn)的社會畫面非常廣闊:凡邊塞戰(zhàn)爭、進(jìn)士及第者、員外、科考落榜者、商客、平民百姓、僧人、義士、酷吏等,應(yīng)有盡有。由此使得貫休對生活在社會不同階層人的生活狀況了解得更加清楚,對人性看得也更加透徹。同時,作為佛門中人,他本身就不受朝廷法度的束縛,個人行動相對自由。因此,貫休性格中多了幾分真我,這使其在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時,能夠充分表達(dá)自我的真實感受。
綜上所述,貫休在詩歌、書法、繪畫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無論是其表現(xiàn)自我傲骨的“筋力”,還是其作品中體現(xiàn)出來的野逸之趣,都與其性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貫休灑脫不羈性格的形成,又與其所接受的教育、生活環(huán)境、社會身份以及個人接觸的社會群體密不可分。貫休詩、書、畫作品中共同特色的體現(xiàn),既是時代選擇的結(jié)果,也受其精神世界的影響。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成就了受后人敬仰的詩僧貫休。
- 甘肅開放大學(xué)學(xué)報的其它文章
- 融媒體時代甘肅紅色文化資源育人的路徑重構(gòu)
——以“習(xí)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課程教學(xué)為例 - 基于動力有限元分析壓縮機(jī)基礎(chǔ)
——地基動力相互作用 - 鄰域搜索策略人工蜂群算法的改進(jìn)
- 論微課建設(shè)與教學(xué)實踐應(yīng)用
——以甘肅廣播電視大學(xué)定西分校“計算機(jī)應(yīng)用基礎(chǔ)”課程為例 - 成人教育領(lǐng)域基于本體的課程學(xué)習(xí)分析技術(shù)研究
- 基于建構(gòu)主義學(xué)習(xí)理論的學(xué)生創(chuàng)新思維培養(yǎng)研究
——以“高等數(shù)學(xué)”課程中“導(dǎo)數(shù)的應(yīng)用”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