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仰觀聽 ????
張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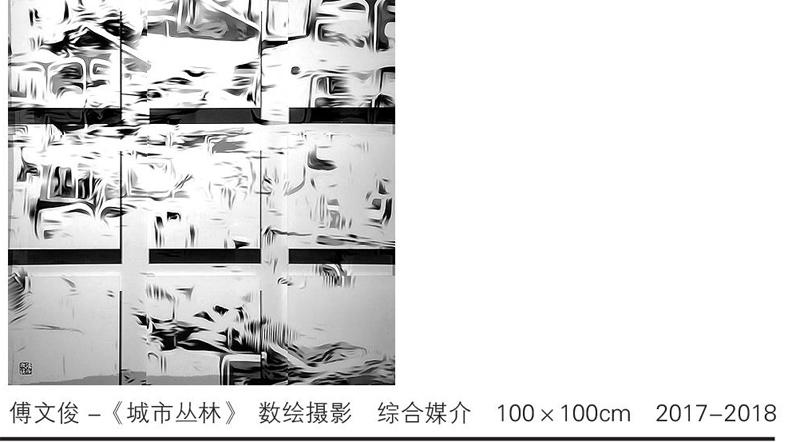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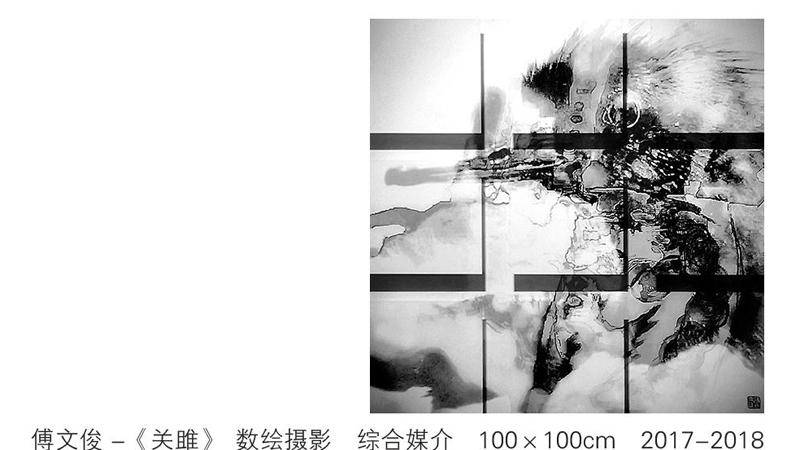
庭燎之光
庭? 燎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xiāng)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傳世一致認(rèn)為,《小雅·庭燎》寫的是周宣王。作者為誰不知道,可能是某位貴族,也不排除是鎬京的自由民。那時候沒有記者,《庭燎》卻極像一篇新聞特寫,抓住幾個鏡頭、不多一點(diǎn)對話,寫出了一個特殊時代特有的美感。
“夜怎么樣啦?”“還沒過半。”庭燎(樹枝纏成的大燭,放在庭院里照明,那時還沒有蠟燭這種東西)已經(jīng)點(diǎn)亮。公侯們來了,遠(yuǎn)處傳來車鈴鏘鏘。
“夜怎么樣啦?”“還沒過完。”庭燎燒得正旺。公侯們來了,車鈴聲陣陣悠揚(yáng)。
“夜怎么樣啦?”“天剛放亮。”庭燎映著晨光。公侯們來了,旌旗鮮明各色各樣。
這發(fā)問的人就是周宣王,他等著早朝,所以問時辰早晚。大臣有司就告訴他:才前半夜,再睡會兒吧。可他睡不穩(wěn),還是一再地問。就在一問一答里,時間從前半夜到后半夜,又從后半夜到東方欲曉、晨光熹微。
隨著時間推移,庭燎在變化:從剛剛點(diǎn)亮到熊熊燃燒,再從熊熊燃燒到煙光相雜。庭燎的變化其實(shí)是襯托夜色的變化:從前半夜到后半夜,夜越暗,庭燎越顯得亮;從后半夜到天破曉,襯著一抹魚白,庭燎冒出的黑煙漸漸看得見了。朱熹說,“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也”;王夫之說,“庭燎有輝,向晨之景,莫妙于此。晨色漸明,赤光雜煙而叆叇,但以‘有輝二字寫之”。
穿過這樣的長夜,諸侯公卿們趕來了:一片黑暗中,還看不見他們的車,就先聽見鸞鈴聲老遠(yuǎn)傳來,鏘鏘地跑得正急;長夜過半,車也近了,或許是望見了庭燎的亮光,公侯們放慢車速,雍容肅敬地前進(jìn),鸞鈴聲也跟著舒緩下來;終于,天光放亮,車子絡(luò)繹不絕地接近王庭,車上旌旗飄飄,繡著各個侯國、家族的徽號,晨光中,看得異常分明。
《庭燎》大概是我最早能讀出味道來的小雅:長夜不眠的天子、早早登程的諸侯、點(diǎn)起庭燎終夜等候的有司,不能忘了,還隱藏著一位被這一幕深深打動的作者。這些形象疊加在一起,就刻畫出一個國家的振作有為、蒸蒸日上。凡是經(jīng)歷患難而后上下同心、勵精圖治的時代,這樣風(fēng)格的詩都能喚起人們的團(tuán)結(jié)一心、努力奮斗。
只是多年之后,第一次讀到《毛序》的“《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時,心中不免小小意外。劉勰說:“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箴石”是用來治病的,這樣美的詩,莫非還有什么弦外之音?
鄭箋說:“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之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知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則所謂“箴之”者,是批評宣王不能備齊官員,徒有工作熱忱,卻沒抓住治國的重點(diǎn)。可是,若是如此具體明白的一個問題,何不明言進(jìn)諫?如此寓箴于美,未免過于晦澀。
《列女傳》的說法是:宣王中年怠政,早朝晏起,姜王后于是脫簪待罪,自我懲罰,宣王感動,納諫改過,“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此說又過于戲劇性了,寓言意味十足。《列女傳》的作者劉向家里世傳魯詩,魯詩說《關(guān)雎》也是為刺康王晏起而作,則宣王的故事,看起來頗像是康王故事的翻版。可見,這類故事都不過是為贊賞賢后、反對怠政的旨趣而設(shè),故事的真假、發(fā)生過幾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贊美勤政的背面,自有一層反對怠惰的意思在。
宣王小雅
《毛詩》中,從《六月》以下至于《無羊》共十四首,稱為“宣王小雅”,《庭燎》即是其一。
周厲王的暴虐,三千年后還很出名,他“專利”和“彌謗”的故事,我在始齔的年齡就聽說過。召穆公的勸諫沒被采納,只留下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名言。只是,那時年紀(jì)太小,尚不清楚他弄一個衛(wèi)巫來監(jiān)謗到底是什么意味。年長之后,看了韋昭的注釋,“衛(wèi)巫,衛(wèi)國之巫也;監(jiān),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這才明白,原來是利用巫者的專業(yè)技能來“高科技止謗”。再說明白些,巫者明面上的“有神靈”,其實(shí)是靠暗地里安插無數(shù)眼線來實(shí)現(xiàn)的(搜集情報的工作,德爾菲神廟的祭司們也擅長,古今中外巫者的共性),然則,竟是最早的特務(wù)統(tǒng)治,難怪會道路以目。兩千八百年前的人,心思到底簡單質(zhì)直,這樣大的心理恐怖實(shí)在承受不了太久,所以,僅僅三年就崩潰了——國人暴動,流王于彘。
國人暴動的時候,宣王還是小太子,年齡不會太大,也許和我聽故事時差不多吧,什么事都還似懂非懂。連這么小的孩子都要一起殺,可見國人真是恨透了。當(dāng)時,太子靖躲在召穆公家里,聽到外面人聲洶洶,看見大人們神色凝重,或許,還目睹了召公一面交出自己的兒子,一面暗地里傷心流淚。此后,他又隱姓埋名了十四年,才得以恢復(fù)身份,登上王位。這種見聞,在這樣的年紀(jì),會對一個人產(chǎn)生終身影響。因此,他不敢像父親那樣暴橫,也不像他的祖先周穆王那樣瀟灑而好奇,而是兢兢業(yè)業(yè)、小心翼翼,于是才有了《庭燎》中的一幕一幕。
從厲王流彘之后,到宣王即位以前,是長達(dá)十四年的“共和行政”,究竟是指“周召共和”,還是“共伯和干王位”,史學(xué)上雖然有爭議,但性質(zhì)其實(shí)相差不遠(yuǎn),都是貴族聯(lián)合攝政。這種半合法的治理沒有多大成效,周僅免于亡國而已。
所以,宣王即位的時候,“萬民離散”(《鴻雁序》)、“四夷交侵”(《六月序》),算得上內(nèi)憂外患。“宣王小雅”十四首,開頭四首全和軍事有關(guān),《毛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fù)古也。宣王能內(nèi)修政事,外攘夷狄,復(fù)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fù)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正是時世艱難的寫照。
《六月》北伐,是驅(qū)逐內(nèi)侵的獫狁;《采芑》南征,是討伐不服的蠻荊;《車攻》是巡守東都成周,鎮(zhèn)撫觀望的諸侯,《序》所謂“復(fù)文武之竟土”,可見此前早已境土不保;《吉日》田獵,是在西都本土閱兵講武、整頓朝綱。所幸北伐、南征、東巡、西狩均獲成功,這才奠下了中興的基石。緊接著便是《鴻雁》,《毛序》曰:“《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矜”同“鰥”)寡,無不得其所焉。”修筑城郭、安頓流民,真正惠及社會底層,如此,才算不僅有“中興”之名,且有“中興”之實(shí):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陳子展推斷,所謂“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是將流離失所的百姓組織起來修筑城郭,一方面增強(qiáng)了國防,一方面也以工代賑,救濟(jì)了饑民。想象當(dāng)時,雖曰“中興”,條件應(yīng)還是相當(dāng)艱苦的:個人的居所還來不及建起,救濟(jì)糧也僅能糊口,風(fēng)餐露宿,還是要勒緊褲腰帶,日夜趕工筑城。“哀鴻遍野”的成語,正從此詩而來。
生活艱困,便時常忍不住要“哀鳴嗷嗷”,詩言“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可見,當(dāng)時的社會上,也還有各色各樣的言論、觀點(diǎn),不能一致,甚至彼此指責(zé)。此情此境下,也只有徹夜不息的“庭燎之光”,能成為全體周民的精神食糧,讓大亂之余的無助百姓看到安居樂業(yè)的希望,從而認(rèn)為眼前的忍耐、付出是值得的——“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也讓社會上的爭論趨于平息,將全國上下的精神集中于重建家園的事業(yè)。《庭燎》之作,殆為此乎?宣王小雅十四首,《庭燎》剛好緊承《鴻雁》之后,其有意乎?其無意乎?
天子聽政
毛詩大、小雅的次第,都是先正后變:《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正大雅,《民勞》以下是變大雅,包含厲、宣、幽三王;《鹿鳴》至《菁菁者莪》十六篇是正小雅,《六月》以下是變小雅,包含宣、幽兩王。所不同者,變大雅始于厲王,變小雅始于宣王。
鄭康成見厲王無小雅,箋毛詩時便從“幽王小雅”分出《十月之交》《雨無政》《小旻》《小宛》,說這四首是毛公傳詩時擅改了順序的,本該屬之厲王。他提出此說,卻沒給出具體的依據(jù),只能由孔穎達(dá)雜引緯書替他證明,也是十分勉強(qiáng),后人大多不信。我猜鄭康成也未必有什么依據(jù),多半是讀書人的習(xí)性,偏愛結(jié)構(gòu)的均衡、體例的整飭,看不得大小雅在這里不對稱。后世的歷法知識也證明,“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的日食就發(fā)生在幽王六年,可見,至少《十月之交》這首,絕非是寫厲王的。
就情理而言,厲王無小雅也并不奇怪,恐怕恰是他殺人止謗的實(shí)績。召公諫厲王的話,只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流傳最廣,當(dāng)時卻是很長一大篇。當(dāng)初,厲王十分得意地告訴他:“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可見衛(wèi)巫倒是真的很能干。)召公立即講:這哪里是“弭謗”,不過是“障謗”而已: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弭”本是弓的末端,據(jù)說是因?yàn)橛屑忸^可以用來挑開紛亂的繩結(jié),引申為消除、止息。周厲王見沒人敢說話了,便自以為謗言已經(jīng)消除,其實(shí),“謗”并沒有被消除,而是被堵截了,存在心里不能表達(dá)。但不說不能等于沒有,堵截了就會壅積,積滿了就會爆發(fā),正如水之潰壩,一定會成災(zāi)。以上這些,都還不過是對眼前事態(tài)的判斷,接下來一篇關(guān)于治國的正論,才是得出此判斷的根據(jù)所在,也反映出召公深刻的學(xué)識:
“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dǎo),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xiàn)詩,瞽獻(xiàn)曲,史獻(xiàn)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guī),親戚補(bǔ)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cái)用于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cái)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這些話可能出自春秋時人的追憶,至于寫成《國語》一書,更要晚至戰(zhàn)國,過程中難免有后人的層層潤色,但即便如此,也依然可視為西周政治文化發(fā)達(dá)成熟的憑證。
“聽政”是個固定搭配,上可用之于天子治天下、諸侯治一國,下可用之于大夫、士治其家,都可以叫“聽政”,一直沿用到后世的皇帝和地方官身上,所有行政、治理活動都可用“聽政”賅而括之。但是,這詞的字面有其妙處,它意味著搞政治首先就是“聽”的問題,不是說、不是動,而是聽。“聽”是治理的重要方面,在召公看來,幾乎是主要的方面,因?yàn)椋宦牐蜎]有信息來源和判斷依據(jù)。
因此,自古以來,天子都不是生活在一片寂靜之中,他耳邊總交織、充斥著各種聲音。他讓上自公卿下到列士的全體貴族都獻(xiàn)詩,他們自己作的也行,從職務(wù)和采邑上聽來的也行,有美有刺、講好講歹,今天還能看到《詩經(jīng)》這部書,部分就得益于這個獻(xiàn)詩的制度。他也讓盲音樂家獻(xiàn)上樂曲,聽里面喜怒哀樂的感情;讓史官獻(xiàn)上史書,聽里面興衰成敗的教訓(xùn);讓太師、少師等音樂官來“箴”,這是一種勸誡性的韻語,專門指陳過失,“芒芒禹跡,畫為九州”就出自有名的《虞人之箴》;讓盲樂工來“賦”和“誦”,韋昭說賦是演唱公卿列士們獻(xiàn)的詩,誦是朗誦太師、少師作的箴;也讓各種行當(dāng)?shù)氖炙嚾颂嵋庖姡?dāng)時的手藝人多是國營作坊的職工,后來莊子筆下的庖丁、輪扁,還時不時有機(jī)會當(dāng)面教導(dǎo)君王,或許是此種制度的遺存。跟上述人等相比,庶人的教育程度大概最低,但也讓他們“傳語”,凡有所見,不拘格式、不拘體裁,口語傳達(dá)給王即可。天子的警衛(wèi)員、勤務(wù)員等近臣,可以詳細(xì)講他們的思考和計(jì)劃;天子的本家和親家,可以查缺補(bǔ)漏,隨時提醒;太師、太史等文化長官,可以給予天子教育;年高德劭的重臣,負(fù)責(zé)修正和完善。
這個樣子,從上到下,沒有不發(fā)聲、不說話的,形成密集的信息場。而天子居身其中,作用是“斟酌”。韋昭:“斟,取也;酌,行也。”好比從酒缸中舀酒吃,聽到的未必全采納,但要放開耳朵去聽,各個階層、各種人的聲音都聽一聽,天子的作用是聽完之后從里面舀上一瓢,即從海量信息中,經(jīng)過消化理解,取一部分合理的來實(shí)施。“這樣,決策就能順利推行,不發(fā)生悖謬”,那是因?yàn)椋@些決策是基于對大家心聲的理解“斟酌”出來的東西,因此,對各階層、群體都有所考慮、有所讓步,不會過于偏激。
上述對西周政治傳統(tǒng)的描述,難免有春秋、戰(zhàn)國人的想象摻雜其中,而且,即便是召公本人,為了說動厲王,也難免有所夸大。但是,就算擠掉大部分的“水分”,只留基本的觀點(diǎn)和框架,也還能看出:西周政治家有重“聽”的傳統(tǒng),他們對“言”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言”在他們眼中,也呈現(xiàn)出豐富的層次,而且,在國家層面也早有一套采集、分析言論的制度和方法。盡管召公說出來的可能只是這套制度的理想化版本,但終不至于憑空捏造,畢竟,完全沒有影兒的事,厲王聽了也不會信。
周厲王專山澤之利,本就是一意孤行的決策,才會導(dǎo)致民怨沸騰。他又令衛(wèi)巫監(jiān)謗,廢棄了西周固有的言論采集制度,使詩、曲、史、箴、百工之諫、庶人之語一時俱絕。等到“川壅而潰”,國人暴動,將經(jīng)營兩三百年的世界都會鎬京一掃而平;再經(jīng)過十四年風(fēng)雨飄搖、若存若亡的貴族共和,等到周宣王即位時,關(guān)于他父親在位時的聲音影響,想找得到一星半點(diǎn)兒都很難了。“厲王小雅”不傳于世,又豈是偶然?
關(guān)于厲王,從《毛序》看,只有五首大雅至今尚存:《民勞》《蕩》召穆公所作,《桑柔》芮良夫所作,《板》凡伯所作,《抑》衛(wèi)武公所作。除作《抑》的衛(wèi)武公年世較晚,他的詩有可能是詠懷歷史的“追刺”之作外,其他三人大抵是當(dāng)時的統(tǒng)治核心成員,進(jìn)諫厲王還不至有性命之虞(《國語》中今存芮良夫的議論和召穆公的進(jìn)諫,可見兩人屬于當(dāng)時僅存的少數(shù)尚能發(fā)言的上層人士)。最重要的,他們在國人暴動后充當(dāng)了周宣王的庇護(hù)人(召穆公自不必說,后人還懷疑凡伯就是傳說中的“共伯和”),他們的詩,想是因此才得以留存的。
中興之象
厲王的潰敗,成了宣王的教材。隨著宣王逐年長大,召公等人對厲王講過的道理,必然還會反復(fù)地、深入地講給宣王聽。
“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cái)用于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老百姓的一張嘴,是何等奇妙?好像抽象的“土地”要表現(xiàn)為山川衍沃等形形色色的功能形態(tài),“嘴”就是“老百姓”的具體化,“口”就代表了“人”,是人與世界交換物質(zhì)、信息的端口,因?yàn)椋煲浴⒆炷苷f。因?yàn)橐裕陀猩a(chǎn)的需求,推動出一切文明的成果;因?yàn)槟苷f,才能互相協(xié)作、進(jìn)行生產(chǎn),就發(fā)展出一切政治的現(xiàn)象。“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嘴不能不說話,不說話就無法生產(chǎn);而一旦說話,就會產(chǎn)生或好或壞的結(jié)果。“行善而備敗”就是統(tǒng)治者能做的:執(zhí)行好的、防備壞的,正確處理從嘴里說出的不同信息,這些信息才能正確反饋回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推動“財(cái)用”“衣食”的豐富,滿足嘴的需求,社會才能持續(xù)存在,物質(zhì)才能持續(xù)流動。而“行善備敗”的前提,就是要能聽得見嘴里說出的“善”“敗”,所以,治理百姓才必須“宣之使言”。
兩千多年后,隨著更多材料出土,人們獲知,周厲王的“專利”也不是無緣無故的,而是有著特定的歷史上下文:一方面是對淮夷和獫狁的戰(zhàn)爭消耗巨大,另一方面是原有的土地制度出現(xiàn)了危機(jī),提供不出戰(zhàn)爭所需的財(cái)富,這些都是有文獻(xiàn)可征的。據(jù)此,周厲王也開始被視為(某種程度的)改革失敗者,而非單純的“暴君”,甚至對他“專利”“止謗”的批評,也被認(rèn)為有可能是后世的某種刻意“抹黑”。然而,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本身并非道德批判,召公的諫言中仍然包含著顛撲不破的洞見。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自古哪有毫無困難的決策呢?而所謂正確的決策,總是在夾縫當(dāng)中作出的,是對各種階層、力量、目標(biāo)、困難、代價進(jìn)行權(quán)衡、妥協(xié)的結(jié)果。厲王毫無顧忌的“專利”和“止謗”,本身就是其失敗之源,底層邏輯則是對人性的嚴(yán)重?zé)o知。
“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老百姓心里想了,再從嘴里說出來,然后再去行動。這其實(shí)是一種可怕的力量,因?yàn)椋肓司蜁蔀檎Z言,說了就會成為行動。沖口而出的話,都曾在心里不知不覺地醞釀;突然流行的段子,反映的是人們不知道多少時間里的觀察和思索。而一個聲音一旦發(fā)出,輾轉(zhuǎn)傳播,多次迭代,重重暗示,又真的會變成口號、變成行動。問題是,成了行動,就來不及挽回;在心里的時候,又沒辦法發(fā)現(xiàn)和糾正。那么,唯一可觀察、可預(yù)測其發(fā)展、可作出干預(yù)的,恰是“宣之于口”的中間段。周厲王令衛(wèi)巫監(jiān)謗,正好掩蓋了這個可知可見的“中間段”,打斷了信息的正常流動。下情不能上達(dá),賢人不能開口,表面上太平無事,背地里暗潮涌動,外陽內(nèi)陰,上下離心,正是周易“否”之象——“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其結(jié)果必然是統(tǒng)治的崩潰。
及至宣王即位,“內(nèi)有撥亂之志”(《大雅·云漢》序),懲于厲王之?dāng)。匀灰雌涞蓝小.?dāng)時,宣王的手下,有《六月》的文武吉甫、孝友張仲,有《采芑》的方叔元老,有《烝民》的樊仲山甫,有《常武》皇父和南仲,還有一位程伯休父,是大史家司馬談、司馬遷的祖先,當(dāng)然,也少不了老臣召穆公虎。宣王大雅六首,“《云漢》,仍叔美宣王也”,《嵩高》《烝民》《韓奕》《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觀宣王大小雅,既有人才濟(jì)濟(jì)之感,又能看出君臣的和諧同心,或許這也正是召穆公等人苦心教導(dǎo)的結(jié)果。
此時,詩、曲、史、箴、百工之諫、庶人之語、近臣之規(guī)、瞽史之誨,想必已復(fù)行于王庭,故鴻雁的嗷嗷哀鳴,亦得以采入小雅,獻(xiàn)與王聽。盡管,《毛序》說《鴻雁》是“美宣王”勞來流民之詩,然而,“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雁于飛,哀鳴嗷嗷”,每每有凄苦之聲流露,未嘗不是召公等借由贊美使民情上達(dá)之意,以喚起宣王“哀此鰥寡”之心。詩言“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可見,這哀鳴也尚不為所有時人共同理解,有時也會受到指責(zé)。但公卿列士既然肯采,太師樂官既然肯獻(xiàn),便是隱隱地偏向在哀鳴的一邊,暗示“哲人”(《說文》:“哲,知也。”“哲人”謂智慧之人。)應(yīng)當(dāng)從這哀鳴中體察民生的艱困、民人的劬勞,而不應(yīng)怪罪于哀鳴之人。然則,宣王的勤勤懇懇、念茲在茲,背后或許也有《鴻雁》的一份敦促之功在。而《庭燎》之作,又似對鴻雁哀鳴之聲的應(yīng)答,將宣王君臣團(tuán)結(jié)奮發(fā)的形象譜成歌曲,傳唱于宮廷和民間,對下,固可以慰藉勞苦的周民、調(diào)停哲人愚人之爭;對上,亦不免寓戒于頌,時時勉勵宣王勤政愛民,則《毛序》所謂“箴之”者,意豈在斯乎?
孔子謂“詩可以觀”。宣王借《鴻雁》可以觀周民,周民借《庭燎》也可以觀宣王。千百年后,觀此二詩,尚可感受到君民上下的聲氣相通,縱然有哀鳴嗷嗷和哲人、愚人的爭論,終究好過厲王時代的寂靜無聲。評價一個時代、國家如何,不只要看有無富足、舒適的當(dāng)下,且要看到有無良好的預(yù)期。假如,《鴻雁》劬勞之情能夠上達(dá)無阻,而《庭燎》精進(jìn)之志能夠長行不輟,則雖有“萬民離散”“四夷交侵”之艱,也不妨反“否”為“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呈現(xiàn)出中興之象。宣王在位四十六年,是西周末最后一段和平歲月,這期間仍然有戰(zhàn)爭、旱災(zāi),觀宣王大小雅,所謂“宣王中興”的最動人之處,恰在《鴻雁》《庭燎》之間展露出的一絲振興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