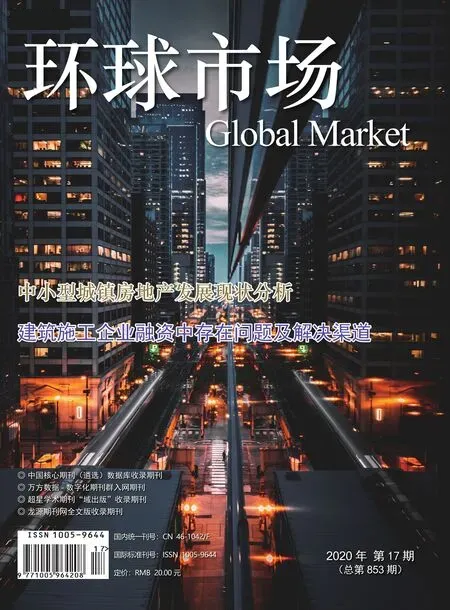基于激勵的碳減排政策工具實踐分析
李安勇 袁清瑞 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由溫室氣體積累造成的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經濟、社會和自然生態系統構成潛在的嚴重威脅,全球氣候變暖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1992 年里約熱內盧的地球峰會上,工業化國家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承諾防止對氣候系統危險的人為干擾,在200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控制在1990 年的水平。鑒于自愿簽署的承諾未能生效,1997年工業化國家共同簽署了《京都議定書》,承諾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到比1990 年低5%的水平,發展中國家因負擔不起清潔能源技術的發展而未包含在內。從那時起,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加了7650 億噸;2010年代平均溫度比1980 年代高了約0.5°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估計,現在地球溫度比工業化前的世界高1°C,每10年上升大約0.2°C。2015 年世界接近200 個國家通過為2020 年后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行動做出安排的?巴黎協定?,同意將全球平均氣溫的上升保持在比工業化前遠低于2°C的水平,并努力控制溫度增加不超過1.5°C。中國2016 年9 月成為完成批準《巴黎協定》的締約方,設立了碳排放2030 年達到峰值、單位GDP 碳排放比2005 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達到20%和森林蓄積量比2005 年增加45 億立方米等多項碳減排目標,并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十三五規劃。但2017 年6 月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
實現《巴黎協定》的氣候變化目標,需要經濟活動及其支持系統的大規模轉型。現在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還遠遠不夠,需要結構變革、學習、試驗和技術變革,而這些都充滿很大不確定性,意味著政策設計必須是動態的和適應性的,與增長、可持續發展和減少貧困相一致。政府可以采取很多可能的政策來控制碳排放量,這些政策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命令與控制型監管,第二類是基于激勵的監管,第三類是政府直接發展和推廣清潔技術。理論上,污染稅、總量控制與排放許可交易體系、政府鼓勵企業發展和推廣新的清潔技術這三種基于激勵的監管政策工具是實現碳減排的最好方式。現實中,各國對這些碳減排的政策工具開展了怎樣的實踐?面臨什么樣的挑戰和困難?有哪些可能的解決方案?本文主要對碳定價、全球工業脫碳化和負的碳排放等政策工具的實踐進行分析,以期對中國碳減排的努力提供借鑒。
一、碳定價
(一)設計良好的碳定價是有效碳減排策略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通過為企業產生的每單位碳排放設定一個價格來發揮污染控制作用,是利用市場激勵機制實現碳排放的負外部性內部化。第一,讓碳排放變成一項昂貴的活動,既會直接減少碳排放,也會促使企業尋求低碳排放的替代品,生產商會減少能源和工業生產的碳強度,消費者會選擇低碳強度的產品;第二,把如何減少碳排放的決策留給企業,將能降低碳減排的成本,通過碳減排創造增加利潤或節省成本的機會,碳定價還會促進創新和激勵新創意、新解決方案的產生。基于市場的激勵機制主要包括兩個政策工具:一個是征收碳排放稅,另一個是總量控制與碳排放許可證交易體系。這兩種監管方法都是依靠來自市場的激勵機制減少污染并最小化污染控制成本。
理論上,基于激勵的監管比命令與控制型監管更有效。第一,基于激勵的監管能在短期內推動更多具有成本效益的監管方式;第二,更重要的是,從長遠來看,基于激勵的監管能夠為企業提供激勵,促使它們尋求新技術以降低碳減排成本;第三,基于激勵的監管通過減少監管過程中做出明智決策所需要的信息,降低了借助對信息的控制而施加政治影響的可能性。當然,基于激勵的監管也有缺點:包括監測和執法方面的問題、污染熱點問題、市場交易清淡、價格波動及可能的對市場力量的操縱等[1]。雖然污染稅制度和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制度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但也存在重要區別。污染稅制度是一種“價格型工具”,政府設定污染的價格,然后與企業對污染權利的需求一起確定污染的數量;而污染許可證交易制度是一種“數量型工具”,政府設定污染的數量,然后與企業對污染權利的需求一起確定污染的價格。如何進行監管,取決于錯誤的相對成本。如果污染數量出現一點差錯后成本更高,那就應該利用總量控制和許可證交易制度固定住數量,允許價格自行決定。如果價格稍微弄錯一點會造成更大損害,那就應該利用稅收制度把價格固定在一個安全水平,由企業決定排污數量[2]。現在,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就在于克服這些障礙并進而發揮基于激勵的監管體系的潛力。
(二)世界絕大多數碳排放尚未定價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到2020 年4 月,全球共有61 項正在實施或計劃實施的碳定價計劃,這些碳定價計劃涉及46 個國家和32 個地方,將會覆蓋120 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相當于全球22.3%的溫室氣體排放[3](見圖1)。這表明,現在世界近80%的碳排放都沒有定價。而且碳價格在這些計劃中遠低于實現《巴黎協定》目標所需要的價格,碳定價計劃覆蓋的碳排放大約3/4 的價格都低于每噸二氧化碳10 美元[4]。根據斯特恩和斯蒂格利茨的估計,要利用碳定價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將需要現在對世界所有產業的碳定價在40-80 美元,到2030 年碳定價達到50-100 美元,而現存碳定價的中位數僅為15 美元,沒有任何地方的碳定價超過40 美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碳定價計劃覆蓋了該國超過一半的碳排放量[5]。
中國政府于2017 年12 月啟動國家ETS,并于2019 年3 月就ETS 法規草案開展公眾咨詢,這是正式國家ETS 發布的第一步。電力部門將是國家ETS 之下遵守碳減排義務的第一個部門,之后會逐步擴展到其他七個部門。在國家ETS 啟動的準備中,多數地方ETS 試點已經引入增強與國家ETS 設計細節相一致的衡量標準,包括減少免費限額的份額及免費限額從“祖父法則”向標桿轉換等。2018 年碳排放市場在多數ETS 試點繼續保持活躍,雖然不同試點的價格水平由于限額緊縮和市場信心不同而不同。多數ETS 試點的價格水平和交易量都比較低,主要是由于初始價格受拍賣最低限價等政府指引的影響而設定得較高,隨后隨著參與者對碳排放市場更好的認識和經濟放緩導致低于預期的碳排放而降低。一些ETS 試點已經把免費限額分配給最近活動水平較高的設施。2019 年3 月,中國公布了溫室氣體減排行動計劃,提議實行限額和交易計劃[6]。

圖1 區域、國家和地方碳定價計劃覆蓋的碳排放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比例
為什么絕大多數碳排放沒有定價?第一個原因是,當要求人們支付一種新稅收時,人們總體上會反對,即使最終他們將會在已有稅收上支付更少。例如,美國華盛頓州在2016 年曾提議對碳排放征稅并把新的稅收收入多數用于削減銷售稅,但遭到環保團體中想讓稅收收入用于清潔能源投資和再分配的左派反對;2018 年再次提議對碳排放征稅并將所獲取的收入都用于綠色投資和受氣候變化影響的社區,但又遭到了化石燃料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對碳排放征稅可能顯著提高化石燃料的價格,這種能源價格上漲可能造成嚴重經濟困難,特別是低收入家庭遭受更大困難。任何碳排放的大量減少都會引起能源消費方式急劇變化,且經濟成本很高。征收碳排放稅,或政府對碳排放許可證進行拍賣,都會產生大量收入,為抵消高能源消費成本帶來的問題,大部分這類收入都應直接通過折扣返還給納稅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的碳排放稅設立基金,降低稅收和把一些稅收轉移給家庭及受影響企業,受到公眾歡迎;雖然它有很大的化石燃料產業,但自2008 年啟動以來,碳排放價格持續上漲。如果碳排放稅有利于利益相關者,他們就不會反對,在政治上也是有效的。多數來自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TS)的收入被用于環保措施。美國氣候變化領導委員會(CLC)把碳排放稅直接以“費用和收益”形式返還給人們,雖然它缺乏效率和明確的目標,但即時和可見的收益對公眾提供了清晰的激勵,即使他們可能面對更高的能源價格。
第二個原因是,當企業依賴溫室氣體排放或它們的客戶依賴溫室氣體排放而運營時,限制碳排放會提高運營成本,降低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企業會反對限制碳排放。特別是如果其他地方的企業并不需要遵守同樣的規則時,尤其如此。
第三個原因是,有人認為,溫室氣體排污權貿易是不道德的。他們認為,將污染當作可以買賣的商品進行處理,不僅消除了與之相關的道德污名,而且對減排量進行交易還破壞了全球合作中所需要的責任共擔意識①。事實上,碳排放交易是自愿的,國家間的碳排放許可證交易對兩個國家都有利;而且,許多國家以更低成本獲得了更清潔的空氣;除少數例外,事實上所有污染監管都允許存在一定量的污染,因為零污染很少是有效率的或政治上可行的。
(三)碳定價有效的條件
盡管只取得有限的進展,碳定價的倡導者也在堅持這種思路。2019 年1 月開始,加拿大的碳定價最低20 加拿大元(14 美元),2022 年將會上升到最低50 加拿大元(37 美元)。2021 年,70%的全球航空碳排放預定會進入聯合國碳排放交易計劃,目標是把它們的碳排放量限定在2020 年的水平。中國在2020 年底預計會對高排放的電力行業啟動全國范圍的碳排放交易市場。歐盟的ETS在設立之初為能迅速啟動和運行,只對大量排放和容易檢測的發電廠、重工業領域進行碳定價;之后擴展到包括歐洲洲內的航空業,覆蓋歐盟近一半的排放;作為綠色協議的一部分,歐盟委員會宣布進一步把ETS擴展到包括交通、航運、建筑供熱等行業的排放,覆蓋增加到超過90%的碳排放。
碳定價要改變企業的碳排放行為,首先,要有可獲得的替代性能源。如果有容易獲得又廉價的替代性燃料,讓化石燃料變得昂貴,就可能迅速改變企業的碳排放行為。1990 年代美國二氧化硫排放許可證計劃成功減少發電廠的二氧化硫排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電力公司可以獲得低硫煤資源和從它們的煙囪中清洗二氧化硫的技術,這些公司可以把從政府那里獲得的二氧化硫許可證出售給很難獲得資源和技術的企業而獲利[7]。歐盟實行ETS 以來,特別是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碳價格都只有一位數,直到2018 年價格開始上漲到25 歐元(27 美元),開始有把高排放的煤炭趕出市場的效果,2019年歐洲的可再生能源首次生產了比煤炭更多的電力。如果只有極少的碳排放替代品,碳定價就很難改變人們的行為。2018 年OECD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所研究的42 個國家中的34 個,至少90%的道路交通工具排放的稅收相當于每噸碳排放超過60 歐元(69 美元)的定價,但在缺少便捷、可獲得的燃油替代品的情況下,人們還是支付了這些稅收,大量地駕駛。
第二,碳價格長期保持上升并足夠可信。碳定價將會激勵投資、生產和消費模式進行所需要的改變,激發降低未來的緩解成本的快速、大規模的技術進步。與碳定價相伴隨的不確定性意味著政策將涉及試驗,需要隨時監測,當碳價格下降或成本高到無法接受時要進行調整。碳價格信號在改變行為和驅動投資上的有效性取決于這些價格信號的長期可信度和可預測性。同時,保持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和調整碳定價使之與技術的最新進步或政策影響相一致是必要的。
第三,存在單一的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氣候變化是一種全球外部性,因此最好進行全球性的應對。碳定價政策將會從國際合作中獲益,反過來又會加強合作,而國際合作需要可信的相互承諾和穩定的激勵結構。在理想世界中,富裕國家對碳排放的評價更高,而貧窮國家的碳減排措施更便宜,這樣,不同國家之間碳排放許可交易的收益是最大的。而現存的碳排放市場,像歐盟的ETS,或美國東北部州的區域溫室氣體協議,傾向于同質化。單一的全球碳排放市場不僅效率更高,而且更少博弈的空間。沒有企業因為要與該計劃外的企業競爭而處于不利位置,沒有企業會試圖把工廠搬到該計劃覆蓋的范圍之外,即不會出現碳排放的“泄漏”,或不存在“污染天堂”。當缺少這種理想情境時,能源密集型企業和貿易導向型企業都會擔心競爭,而政府擔心工廠會搬遷到碳交易計劃覆蓋的范圍之外,因而尋求“邊境碳調整”(BCA)機制的保護。這種調整對于不是碳定價計劃成員國家的效果相當于關稅,通過這樣的調整,它允許計劃去覆蓋那些“嵌入”到進口產品中的隱藏的排放。
二、全球經濟脫碳化
(一)全球經濟脫碳化是艱巨的任務
根據IPCC 的估計,為把全球變暖控制在低于2°C,全球所有工業使用能源的總排放量到2050 年必須比現在低50-80%;如果要把氣溫上升控制在1.5°C,總排放量更要比現在低75-90%;甚至,在21 世紀中葉,數以億噸的二氧化碳需要從大氣中清除,即“負排放”。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從200 年前煤炭時代開始到1970 年,化石燃料的燃燒、照明和水泥制造產生了4200 億噸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從1970-2011 年,這一數字增加到3 倍,達1.3 萬億噸。化石燃料依然是全球電力系統的支柱,化石燃料發電量自2000 年已經增加到70%,到2018年達到17000 億千瓦時。煤炭是最大的化石來源,占全球發電量的38%;其次是天然氣,占20%。在中國和印度等主要新興經濟體,燃煤發電的份額超過60%。在許多發達經濟體,包括美國、德國和日本,煤炭和天然氣繼續提供大部分電力。由于對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賴,電力是能源領域最大的碳排放者,占全球能源相關排放的接近40%。電力領域的碳排放在2018 年達到138 億噸的新高。燃煤發電是能源領域最大的排放源,占2018 年能源相關碳排放的29%,它也占電力部門排放的近75%。
為緩解全球變暖的影響,當即的任務是鼓勵清潔(零碳)電力和電池存儲的推廣。電力供應在未來30 年需要增加4 倍,生產這些電力需要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大量增加,同時需要對化石燃料的碳捕獲和封存(CCS)的利用。可再生能源開始領先,2017 年可再生能源吸收了2 倍于煤炭、天然氣、石油和核電站加起來的投資,電動汽車(EVs)銷售也增長強勁。根據清潔能源咨詢公司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的數據,從2014-2016 年,全球電動汽車的銷量花了17 個月從100 萬輛增加到200 萬輛;而2018 年,其僅花了6 個月就從300 萬輛增加到400 萬輛。這些是全球經濟脫碳化最簡單的部分。
經濟中像重型運輸、加熱和工業等部門,很難輕易使用電力和鋰離子電池,其脫碳化將會困難得多。2017 年,這些難以脫碳的領域產生了大約150 億噸二氧化碳,或總排放量的41%,與之相比,整個電力行業的排放為136 億噸,最大的工業排放是水泥、鋼鐵和化工制造。而這些只是與能源相關的排放,還不包括農業、林業和其他土地利用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后者大約占總排放量的1/4(見圖2)。

圖2 不同部門的二氧化碳全球排放總量(2017 年,億噸)
(二)全球經濟脫碳化的努力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史蒂夫·戴維斯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利用“相當簡單和有限”的現有技術,繪制了凈零排放能源系統的技術路線圖,除了電力和電池,還包括氫氣和氨、生物燃料、合成燃料、CCS 及從大氣中直接清除碳。它們可以有不同的最終用途:氫氣可以在輕型運輸、重型運輸、加熱和煉鋼中發揮作用,合成燃料可以在噴氣式飛機中發揮作用,CCS 可用于加熱和水泥制造。每一種都有自己的缺點:大規模制造、運輸和使用氫氣有困難;乙醇等生物燃料已在燃料中與碳氫化合物混合,但能源作物與食品工業爭奪土地,而且它們的種植也會產生溫室氣體;無排放合成燃料依賴大量的氫氣和一氧化碳來生產代用碳氫化合物,因此它們的發展依賴于這兩種氣體的低成本供應;CCS 被認為是化石燃料的生存保障,但很難想象水泥等工業在不進行CCS 的情況下實現脫碳。
盡管如此,能源行業脫碳的障礙并非不可逾越。更重要的是,它們可以帶來經濟收益。IPCC 估計,從2016-2035 年,為把氣溫上升保持在1.5°C,每年需要花費大約2.4萬億美元,或全球GDP 的2.5%。2017 年的能源總投資是1.6 萬億美元,多數投資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到2050 年,經營凈零排放的“難以清除”工業的額外成本是1.2萬億美元。其中涉及的技術并沒有新的,而且,不像化石燃料,它們被使用的越多,成本就越低,這就為更多行業使用它們提供了激勵。氫氣可能是最有前途的,因為它是大規模電氣化的最佳互補,也可用于重型運輸、加熱和工業。要實現凈零碳排放,全球氫產量要從現在每年6000 萬噸增加到2050年的5 億-7 億噸。當然,為清潔地制造氫,多數氫將必須來自電解水,而目前電解水只占氫產量的5%(剩余的都來自化石燃料的“蒸汽重整”),這需要大量的低成本、零碳的電力[8]。
(三)全球經濟脫碳化的挑戰
整個工業部門幾乎一半的碳排放來自四個行業:水泥、鋼鐵、氨和乙烯。除非消費模式改變,否則所有這些行業都必須削減排放以滿足對汽車、建筑、塑料和基礎設施增加的需求。而且由于它們的產品多數都是商品化的,脫碳化帶來的高成本有“碳泄漏”的風險,即氣候政策更寬松的地方將會更便宜地生產這些商品的可能性。
減少工業排放的首要任務是鼓勵回收利用,但制造物品的方式也需要改變。鋼鐵行業的脫碳化是大的考驗。瑞典的鋼鐵公司SSAB、國有鐵礦石生產商LKAB 和國有電力企業Vattenfall 組成的零碳排放鋼鐵聯合風險投資Hybrit Development,正在啟動價值14 億瑞典克朗(1.5 億美元)的項目,將利用瑞典豐富的可再生能源,通過電解產生氫氣,并利用其生產“直接還原鐵(DRI)”,目標是通過控制焦炭的使用以消除幾乎所有的碳排放,使瑞典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生產無化石鋼鐵的國家。額外需要的電力將是驚人的,在滿負荷生產的情況下,Hybrit 每年將會使用大約150 億千瓦時電力,或瑞典目前全國電力供應的10%。假設電力價格保持在當前水平,這一過程可能會使粗鋼價格上漲20-30%。這樣重要的調整是緩慢的,因為規模化需要時間,Hybrit 希望2024 年完成試驗,并在到2035 年的10 年間進行全面試驗,最終達到商業化規模。
水泥行業的脫碳化則是更嚴峻的挑戰。水泥是世界上最廣泛使用的建筑材料,但水泥廠通常規模小、分散和資本不足,這使其更難脫碳。印度、非洲這樣的發展中地區對水泥的需求將會隨著經濟增長而大幅增加,這意味著會額外產生大量二氧化碳。水泥行業大約60%的廢氣來自生產熟料的煅燒過程。熟料被磨碎并與其他材料混合形成波特蘭水泥,用于研磨的動力通常也會釋放二氧化碳。幾乎所有剩余的碳排放都來自加熱窯的煤炭或焦炭,這些都可以用生物質或廢舊材料代替。隨著效率改善,這將是降低水泥的碳足跡最快的方式。CCS 對于從煅燒和加熱中捕獲二氧化碳是一種可能的替代選擇,但混合廢氣的二氧化碳 濃度較低,讓它們的捕獲過于昂貴。歐盟支持的比利時創新項目Leilac,目標是重新設計窯爐以使捕獲煅燒的廢氣更容易。更大的雄心是開發熟料的替代品,這將在減排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美國一家初創企業和大型水泥生產商LafargeHolcim 的合作公司Solidia 正在開發一種新型水泥,這種低熟料水泥將會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工業其他領域的脫碳也正在進行。Alcoa 和Rio Tinto 的合資企業Elysis 正在尋求對鋁冶煉進行革命性變革。目前鋁來自氧化鋁、電和碳三種成分的組合,電在由碳構成的正極與負極之間流動,正極與氧化鋁中的氧氣發生反應,產生二氧化碳和液態鋁,然后進行鑄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很大,比如在使用煤炭冶煉鋁的中國,每噸鋁會產生16 噸二氧化碳。Elysis 致力于用非碳材料做正極,產生氧氣而不是二氧化碳,以減少碳排放。其目標是到2024 年銷售成套技術軟件,用于世界各地改造現有冶煉廠或新建冶煉廠,使零碳鋁比現有技術便宜15%,生產效率提高15%,部分原因是正極的使用壽命比現有技術長30 倍。
工業脫碳化最終還是需要來自政府的壓力,以確保產業能夠采取轉型所需要的嚴厲的、長期的決策。首先,政府要確保有足夠的可再生電力和碳存儲場地,以實現更大規模的電氣化和CCS。其次,政府可以通過更嚴厲的碳定價、環境管制和金融支持,為氫氣生產和CCS 提供激勵。最后,政府可以鼓勵在公共基礎設施項目中使用環保水泥、環保鋼鐵和其他零碳材料,創造新的市場。這樣,工業就不必擔心客戶會轉移到別的地方,盡早擺脫高碳排放的老技術。
三、負的碳排放
(一)負的碳排放方法
目前,全球氣溫已經比工業化前高1°C,而且還在繼續攀升,主要是每年430 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巴黎協定》實現2°C 的目標,不僅需要排放大國更嚴格地削減排放,該協定也設想大大減少排放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即負的碳排放。IPCC 研究了2018 年的情景,如果要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到2100 年,需要從大氣中清除1000億噸到10000 億噸的二氧化碳,中值為7300億噸,超過全球10 年的碳排放量。
化石燃料仍然提供了世界大部分電力,而且發電廠在整個能源領域是最大的碳排放者。實現氣候和能源目標,需要全球電力系統有一個重大和加速的轉型。政策制定者在滿足由發展中國家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和終端領域電氣化驅動的電力需求強勁增長的同時,必須支持向低碳發電的迅速轉變。低碳的未來意味著解決化石燃料發電的碳排放問題,需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碳捕獲和封存(CCS)在這個轉型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9]。如果增加地球上的植被數量,可以從大氣中吸收一定數量多余的碳,種植森林或改善農田是不錯的方法,但并不特別可靠,森林可能被砍伐或燒毀;使用森林作為碳儲存庫最大的問題是,它們必須足夠大才能產生重要的不同,在IPCC 研究的情景下,森林覆蓋的面積相當于俄羅斯的面積,也只能吸收2000 億噸二氧化碳,比必要的要少得多。碳捕獲和封存(CCS)技術最初的用途是從燃煤發電廠的煙囪中吸收二氧化碳,并將其泵入地下地質深層,這樣發電廠接近碳中和。如果將同樣的技術用于生物燃料發電廠,泵入地下深處的二氧化碳 就不是來自遠古的化石燃料,而是來自最近生活的生物質。進行碳捕獲和封存(CCS)的生物能源(BECCS)發電站,將生物質作為可再生燃料,而不是簡單地作為碳儲存庫,不僅同樣數量的土地可以捕獲更多二氧化碳,而且光合作用儲存于植物葉子和樹木中的太陽能在生物質燃燒時轉化為電力(見表1)。曾經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燃煤發電廠,也是最后一個燃煤發電廠的DRAX,正在把自己改造成一個進行碳捕獲和封存的生物能源發電站。
BECCS 被認為是標準CCS 的變種,但由于技術和經濟原因,它尚未獲得真正的成功。世界上大約有2500 座燃煤發電廠,還有數千座天然氣發電廠、鋼鐵廠、水泥廠和其他產生工業量級二氧化碳的裝置。根據全球碳捕獲和封存研究所(GCCSI)的數據,其中只有19 座提供一定程度的碳捕獲和封存,每年有4000 萬噸二氧化碳被從工業源中捕獲,約占排放總量的0.1%。大規模捕獲和封存二氧化碳需要的重工業設備成本很高,如果碳排放者要為每噸100 美元的碳排放權利買單,人們才會對這樣的技術更感興趣,這將降低它的成本。但缺少這樣的高價格,就很少激勵進行這類投資。在某些情況下,政府甚至不需要補貼,碳排放定價就會讓碳捕獲和封存獲得收益。

表1 碳在大氣圈、生物圈和固體地球之間的流動
(二)負的碳排放的嘗試
半個世紀以來,石油公司一直在向它們的一些油井噴射二氧化碳,以將石油趕出巖石的凹角和裂縫,這是提高石油采收率(EOR)的過程,石油開采出來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留在地下。石油工業從自然資源中每年獲取2800 萬噸用于提高石油采收率的二氧化碳。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這些努力獲得的回報是一天50 萬桶原油,占全球產量的0.6%,這是一個CCS 可能進入的市場。美國得克薩斯的油田經常使用EOR,讓該州成為企業嘗試碳捕獲新方法的熱門地點。初創企業Net Power 在休斯頓建造新型燃氣發電廠,在純氧中碳燒天然氣以產生熱的二氧化碳流,直接驅動渦輪機發電,因為這些二氧化碳是純凈的,無須進一步過濾就可用于EOR。西方石油公司正在與致力于從空氣中直接捕獲二氧化碳(DAC)的加拿大碳工程公司開發一家電廠,目標是到2022 年把從空氣中捕獲的50萬噸二氧化碳泵入西方石油公司近乎廢棄的油井中。因為二氧化碳在空氣中的濃度很低(0.04%),DAC 是要求非常高的業務,但通過EOR 的石油開采使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可以在加利福利亞州低碳燃料標準的限額和交易計劃中獲得可觀的信用。
挪威石油公司Equinor 長期以來一直將二氧化碳泵入北海廢棄的油田中,以避免挪威對碳氫化合物工業排放所征收的嚴格的碳排放稅。作為在澳大利亞海岸租賃開發Gorgon 天然氣田的條件,雪佛龍公司被要求從天然氣中分離二氧化碳并存儲起來,項目的結果是每年400 萬噸二氧化碳,比其他任何不用于提高采收率的項目都要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能處理得克薩斯那種規模排放的碳捕獲和封存設施。在歐洲,運營像Gorgon 那樣大型的二氧化碳存儲庫的成本需要在許多碳源之間共享,這促使共享存儲基礎設施的集群趨勢。Equinor 和Shell、Total 等兩家石油公司提議將碳捕獲和封存轉變為挪威的服務業,他們將收取費用,從生產商那里收集二氧化碳,運到Bergen,然后通過管道運到海上注入點。
(三)負的碳排放的挑戰
我們對負的碳排放趨勢要謹慎對待。首先,全球碳捕獲仍然是以數千噸來衡量的,而不是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的數十億噸。如Gorgon 項目封存的二氧化碳,只是全球一小時的排放量。第二,該領域獲得的政府支持經常不確定或設計拙劣。例如,英國政府在2012 年承諾為CCS 提供10 億歐元的資金,但2015 年就停止了,競爭這筆資金的兩個項目——將二氧化碳封存在現存天然氣田的蘇格蘭項目和約克郡修建利用CCS 的燃煤發電廠項目因此而流產。美國在2008年頒布對通過CCS 封存的第一個7500 萬噸二氧化碳進行稅收減免的方案,即45Q,但企業無法確定項目最終會排放有利可圖的第7400 萬噸二氧化碳,還是多余的第7600 萬噸二氧化碳,投資熱情大大削弱。2018 年這一方案被修正,所有在2024 年1 月1 日前啟動并運行的項目都將獲得稅收抵免資格,激發了一系列投資活動[10]。最后,稅收減免、試驗性的碳捕獲工廠、發電的新方法已經激起投資者和企業的興趣,但能夠產生大量BECCS 工廠的CCS 產業及收集可持續來源的生物質用于這些工廠的基礎設施都有很長的路要走。直接空氣捕獲(DAC)在用非常昂貴的方法獲得純二氧化碳,它們需要發現新市場,通過學習更好的技巧和規模經濟來降低成本。
四、結論
應對氣候變化是一個緊迫且重大的挑戰,設計良好的碳定價是有效碳減排策略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實現《巴黎協定》的氣候變化目標需要所有國家實施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包括碳定價、技術路線圖、國家的緩解和發展路徑分析,以及把這些不同政策的優勢和局限性考慮在內的全球綜合評估模型。碳定價政策工具可以有效地減少碳排放,因為它們幫助克服一個關鍵的市場失靈:氣候外部性。碳定價本身可能并不能誘發實現?巴黎協定?目標所需要的改變的速度和規模,它需要與應對市場失靈的設計良好的不同政策互補。各國可能選擇不同的工具去實施氣候政策,這取決于國家和地方的特定環境及所獲得的支持。基于產業、政策經驗及理論研究,充分考慮到各種政策工具的長處和限制,與實現《巴黎協定》的氣候變化相一致的碳定價應該足夠高并且在長期保持確定性,才能夠為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提供支持性的政策環境。對于氣候政策尤其是碳定價的有效性非常重要的是,未來的路徑和政策必須是清晰的和可信的。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在能源系統推廣可再生能源和在工業領域推廣低碳制造技術的支持性政策來加速向低碳的轉型,包括資本支持、政府采購、稅收抵免、監管標準和運營補貼等。除非投資者確信在轉型市場中會獲得政府支持,否則它們不會在工業領域對低碳科技進行投資。碳捕獲和封存、進行碳捕獲和封存的生物能源及直接空氣捕獲都是富有前景但昂貴的負的碳排放技術,對其政策激勵的關鍵因素是政府對二氧化碳運輸和存儲基礎設施的建設。
注釋
① Michael J. Sandel. It's Immoral to Buy the Right to Pollut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7,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