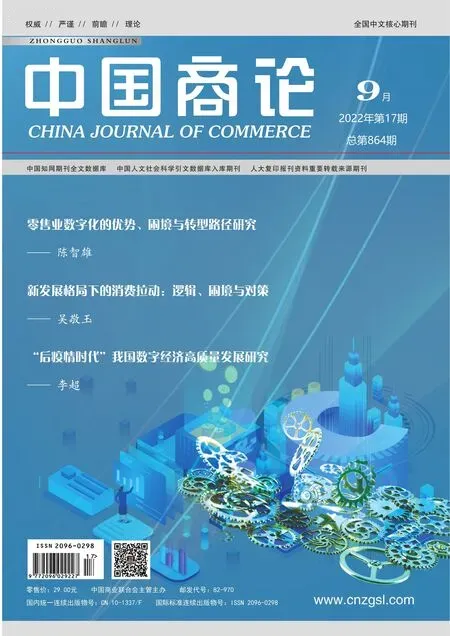網絡交易中標價錯誤合同的出路研究
袁浩然
摘 要:隨著網絡交易的愈發繁榮,網絡交易標價錯誤事件也屢屢發生,其中牽涉的法律問題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合同成立的問題,二是合同成立后能否撤銷的問題。針對前者,本文從售賣商品頁面信息的性質入手,認為對合同成立的判斷需基于商家的性質;而對于后者,本文則認為應取決于買賣雙方是否存在過失及過失的認定標準。
關鍵詞:網絡交易? 標價錯誤? 頁面性質撤銷
中圖分類號:F72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0)09(a)--02
網絡交易因具有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優勢在近些年得到了極大程度地發展,但相應的,紛繁復雜的交易糾紛也隨之而來,這其中最受社會矚目、消費者關心的,大概非網絡交易標價錯誤事件莫屬。為何大眾對此類事件特別敏感,究其原因,除網絡交易本身的特性之外,有相當程度的理由應是在如何處理這類案件上,社會通常觀念與司法實踐的沖突。其中涉及的主要爭議點包括:網絡購物錯價合同成立的標準是什么?若合同成立,賣家可否撤銷其意思表示?買賣雙方的權利如何得到維護?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將一一進行分析。
1 售賣商品頁面的性質
長期以來,學界對于電商平臺上商品信息頁面的性質一直存在著“要約說”“要約邀請說”和基于頁面信息的詳略程度個案判斷三種觀點。這種分歧看似止于2018年《電子商務法》的通過,因為該法第49條中有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不得以格式條款等方式約定消費者支付價款后合同不成立”。在如今網絡購物環境下,95%以上的商品買家需要在提交訂單的同時付款,即賣家出現標價錯誤的情況下,基本很難通過主張合同不成立來獲得救濟。贊成方的主要觀點為:買家未見實物便付款已承擔了較大的風險,若仍認為合同未成立,不僅與價金給付在契約成立之后的常理不符,也不利于買家權利的保護。但該法第20條又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應承擔商品運輸中的風險和責任。”即網絡交易與傳統的貨交第一承運人規則不同,必須貨交買家手中時其毀損滅失風險才能轉移,因此單純地認為買家承受較大風險似有與該條矛盾之嫌。更重要的是,合同的成立應取決于雙方是否達成合意而非價款支付,如若強行確認合同在此時已經成立的話,無異于在立法層面鼓勵社會大眾或屢見不鮮的職業撿漏群體利用他人的錯誤獲利。也有學者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發現,此種認可“撿便宜”的立法選擇會導致錯誤激勵,進一步放大社會交易損失,而認定“合同未成立”,允許賣家走出錯誤,則能實現社會損失的最小化。基于此,本文認為我國《電子商務法》第49條的規定不盡合理,尚有修改空間。
事實上,在一次完整的網絡購物中,消費者均需簽訂兩份合同,其一是消費者想要注冊賬戶而必須同意的“注冊協議”;其二是消費者下單購物的買賣合同。筆者在查閱各主流購物平臺的用戶協議后發現,其均規定有“本網站上銷售商展示的商品和價格等信息僅僅是要約邀請……只有在銷售商將商品從倉庫實際直接向您發出時,方視為……建立了合同關系”。可是在具體的判例中,法院都沒有引用用戶協議中的規定作為說理,僅分析消費者下單購物的合同。筆者認為此種架空用戶協議的做法并不妥當,用戶協議在性質上應屬于消費者此后一切購物行為的框架約定,那么消費者購物的買賣合同是否成立,原則上便應當先依據用戶協議中的條款判斷,將商品網頁信息定義為要約邀請。
另外,既然合同成立的前提是雙方當事人之間達成合意,那么在出現標價錯誤的情況時,雖然內容仍然明確、具體,可這并不能推出賣方有受該網頁上錯誤信息約束的意思表示。并且,考量誠信原則與交易習慣,企業經營者顯然未將契約是否成立之決定權交由網頁瀏覽者的意愿,經營者在承諾前取消訂單也通常不會給購買者造成實質經濟損失。
由此看來,似乎“要約邀請說”相較其他兩種學說更為合理,但是,筆者以為,將所有商品信息頁面都定義為要約邀請也是不妥當的。因為有一類經營者非常特殊,即以京東自營、天貓超市為代表的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電子商務法》第37條也明確規定,電商平臺需要以明顯的標記區分其自營業務與其他經營者的業務,并由平臺對其自營業務承擔完全責任。可以看出,這類經營者作為平臺的“親兒子”,不僅有著專屬的物流配送服務、極高的質量保證、較第三方更高的價格,還有著平臺信譽的背書。以京東自營為例,消費者下單并支付價款后,其并不會專門發送訂單確認信息,而是直接顯示在“我的訂單-待收貨”一欄,經系統自動確認后,便會更新物流信息為“您的訂單已經進入××倉庫準備出庫”,也因此消費者在付款后無需付出額外的確認或協商精力,僅需等待平臺自家物流配送即可。所以,筆者認為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的自營商品實際上與“貨物標定賣價陳列”的普通商品并無本質區別,即將這類商品信息網頁認定為要約較為合適。
相反,較為普遍的則是以天貓旗艦店、專營店、專賣店和個體經營戶為代表的平臺內第三方經營者。他們僅能算作平臺的“養子”,除去只能品牌方自己開設的旗艦店之外,各類專營店、專賣店與個體經營者質量參差不齊,甚至諸多商品展示頁面上還會有如“咨詢客服獲取優惠價”“加入店鋪會員領折扣券”之類的字樣,即商品頁面的價格并不完全是商家內心真意的反映。同時,消費者下單付款后大部分商家會發送一份確認函,內容多為表示已收到訂單。以淘寶為例,其確認函的內容包括商品信息及收貨人信息,并附有一個確認按鈕,而無論買家是否點擊確認,賣家均會發貨。由此可見,除明確說明接受訂單之外,此類確認函應屬提示性質而非部分學者主張的承諾。基于此,筆者認為對廣大的第三方經營者店鋪的商品信息網頁,應依照平臺用戶協議的規定認定為要約邀請。
2 合同成立之后的救濟
一旦雙方的意思表示被認定為具有拘束力,且符合要約承諾的規定,則合同即告成立,此時若賣家因標價錯誤而拒絕履行義務,合同便陷入了僵局。我國司法實踐對于標價錯誤的處理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就法院的判決來看,相當程度是利益衡量、公平合理分配合同風險的問題。而對于經要約承諾后成立的合同如何救濟,我國學界通常認為:當該錯誤屬于意思表達階段的錯誤,如工作人員誤輸入、系統程序出錯時,可依《合同法》54條規定的重大誤解或顯示公平撤銷。雖說有學者提出價金誤解并不在《民通意見》界定的重大誤解范圍之內,因此無法使標價錯誤涵蓋在《合同法》第54條的表示錯誤中,但《民通意見》未將價金列舉的原因是由于在實踐中,市場價不同而發生的矛盾大多不能認為是認識錯誤,而僅僅是可以有所周展的自由貿易行為,所以在立法上不宜將“價金”直接寫明而已,事實上,將“價金”與“品種、質量、規格和數量”并列在邏輯上并沒有問題。
但與此同時,如只因為價金達到了一個流于主觀的“重大”標準即可撤銷的話,無異于為賣家逃避責任大開方便之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借鑒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的規定,其要求表意人的撤銷權需以其無過失為前提,但就如何認定該過失,島內理論界與實務界也立論不一,難有交集。對此,筆者認為在判斷賣家是否有過失以決定其能否撤銷合同時,應從其內部入手,觀察是否有合理的內控機制,此內控機制的判斷也應是結合前述店鋪性質、當下信息技術水平與成本效益的客觀標準。例如,商品上架前、促銷開始前是否多次復核;是否設定商品底價;短時間大量訂單進入時,是否有自動警示或暫時下架機制等,若賣方并未作出此種安排,則推定其不具備合理內控機制。當賣方不具有合理的內控機制,或具有合理的內控機制但并未執行時,應認定具有過失,嚴格限制其撤銷權。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對消費者提供的保護并非沒有限度,賣家雖負有防止標價錯誤發生的注意義務,買家也同樣負有遵守誠信原則的義務。對買家來說,若網頁標示有“促銷”類字樣,即使價差巨大,其可能認為自己運氣好,剛好碰到價格低點,畢竟在各大限時或搶購活動中,諸多商品優惠至1元錢的情況也非鮮見;可若價差巨大,網頁又沒有標明“促銷”類字樣,貼吧微博等公眾平臺也有人大肆宣傳,或其一次下單超過正常生活需要的,便不能認為買家相信這種錯誤并無過失。此時買家下單后堅持要求賣家履行,則明顯已逾越權利行使的界限,對此,我們可以借鑒德國法院的做法,依照誠信原則或禁止權利濫用原則撤銷雙方的合同。
合同不成立或撤銷之后便涉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問題,雖然學界提出了以信賴責任規則作為消費者權益救濟的路徑,但這一責任不僅在我國沒有制度基礎,大陸法系的其他國家也較為少見,或許不宜在相關制度構建之前采用。筆者在查閱相關案例判決結果與各平臺賠償規則后,認為當當網的先行賠付規則無疑值得推廣,其具體規定為:因賣家標價錯誤未發貨使得買家投訴的,“當當有權按訂單金額的50%且最低10元最高500元賠付顧客,因此產生的不利后果及費用由商家承擔”。該規定一方面通過先行賠付規避了大量訴訟風險;另一方面,采用固定的標準賠償替代損失的具體計算,也防止了社會和司法資源的進一步浪費。同時,該規定也可以認為是雙方預先對因為錯價而可能導致的信賴損失如何計算與分擔的約定,一般來說,雙方自愿約定的事項是可以改善雙方利益且是有效率的。
3 結語
綜上所述,在我國錯誤制度一般規則規定不足的背景下,以規制合同成立為突破口,選擇與現實合同不同的要約承諾規則,平衡電商平臺、第三方經營者與消費者的利益無疑是最佳選擇。但在合同成立之后,若錯價屬經營者盡力而未能避免或消費者存在過失的情形下,也不吝賦予經營者撤銷權。最后,在我國信賴責任制度構建之前,采用當當網模式,用固定賠償標準替代損失的具體計算,應是科學與效率兼備的做法。
參考文獻
林麗真.網路交易標價錯誤之契約法律問題探討[J].東吳法律學報,2010(22).
吳瑾瑜.論網站標價錯誤之法律效力[J].月旦法學雜志,2010(187).
張偉強.網絡交易標價錯誤的經濟分析[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8,3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