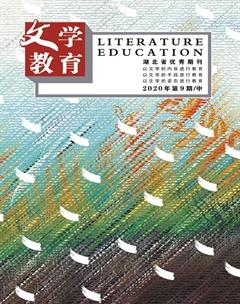曹七巧與悅子在女性主義視角下的對比研究
內容摘要:杰出女作家張愛玲的小說《金鎖記》與三島由紀夫《愛的饑渴》都鮮明地刻畫了具有悲劇性的女主人公形象。很多評論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分別對曹七巧和悅子兩位女主人公展開研究,但忽略了兩部作品在塑造女主人公的人生經歷、人物性格及作品悲劇結局上的共同點與差異性。本文首先介紹女性主義的理論內涵與發展概況,論證曹七巧與悅子在女性主義視角下的可比性;其次,從人生經歷出發,分別介紹曹七巧與悅子的生活,反思她們不同生活經歷對性格形成和差異性結局的影響;最后從社會背景等角度尋找曹七巧與悅子反抗的不徹底性和在不同社會歷史環境中面臨的相似困境,并由此體現出論文的現實意義和研究目的。
關鍵詞:曹七巧;悅子;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又稱作女權主義,它爭取的目標是兩性平等。十九世紀的法國催生了第一批大規模婦女解放運動。而作為一種文本批評或者話語批評的女性主義批評至遲出現在二十世紀末動蕩時期的西方。在男性為主導的話語體系中,文學似乎一直是男性作家在寫男人的故事,而女性主義的出現逐漸在文學作品中喚起女性的聲音。張愛玲的《金鎖記》與三島由紀夫的《愛的饑渴》都描寫了女性復雜的情感世界與悲哀的命運,他們在小說中圍繞女性主體進行建構,塑造了兩個性格各異的女性,她們在逼仄的大環境中所做出的選擇足以引起我們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和對社會價值的思考。
一.女性主義視角下的曹七巧和悅子
女性主義的概念原本是在政治領域中提出的,為了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男女不平等社會體制中替婦女爭取平等的社會權利。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和法國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為女性獲得經濟獨立和家庭的平等權利方面指明了道路。在二十世紀后半葉,女性主義不僅為女性爭取平等的政治權利,也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取得一定進展。在文學領域,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主張“關注婦女形象、女性創作及女性閱讀,建構女性特有的寫作方式、話語模式與文學經驗”①。因此,作家在作品中對女性精神世界的揭示和對女性悲劇命運的反思逐漸引起學界關注。
林幸謙在《女性主體的祭奠》中寫道“女性身體在總體壓抑中所匯聚到的力比多往往被闡述為焦慮、歇斯底里甚至瘋狂的狀態。”②文學作品中壓抑自身、隱匿潛意識中的情緒并逐漸扭曲或最終爆發的女性形象不勝枚舉。從女性主義文學的角度出發,反觀《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和《愛的饑渴》中的悅子,她們具有相似的人生經歷。曹七巧和悅子的父母都極早逝世,她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在別人的屋檐下生存,同時她們渴望被愛又極度缺愛。在男性為中心的大環境下,曹七巧和悅子常常處于被動、孤獨的境地中。曹七巧和悅子對于畸形的環境都有一定的反抗,她們將自己的不滿情緒體現在行動中。曹七巧面對“坐起來,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還沒有三歲孩子高”的丈夫,憧憬姜季澤帶給她精神和肉體上的滿足;而悅子面對對出軌行為毫不遮掩的丈夫憤而燒了臥室內情婦的照片并在丈夫去世后追求其他男性。
曹七巧與悅子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她們對抗環境的方式。同為反對僵化的社會規范,曹七巧在“長兄為大”的家庭中被做主嫁給患有軟骨癥的姜二爺,她用自己的尖酸刻薄為武器保護自己在姜公館中不受欺負,但在不信任的狀態下拒絕姜季澤的求愛,守護自己的家產孤獨終老。悅子不斷追求新的男性以填補丈夫缺失帶來的空虛,但她對愛的畸形渴望最終導致她用鐵鍬打死了心愛的三郎。她們在面對困境時既有傳統女性的隱忍包容又有反抗環境的試探之舉,但最終在墮落中走向自己的悲劇命運。
二.人生旅途中的曹七巧和悅子
曹七巧和悅子經歷著不同的人生,她們不幸的一生既有相似性也有差異性。她們不同又相似的人生給予了其精神內核中的反叛精神,但這股覺醒的女性意識并沒有支撐她們一往直前地去打破枷鎖、追求自己的幸福人生。在幾經抗爭之后,曹七巧和悅子都成為了不公正環境下的犧牲品。
曹七巧出生在一個開麻油店的家庭,由自己的兄長做主嫁到了當時的豪門望族——姜公館。但她出身卑微,在那樣一個傳統的封建舊家庭,就連服侍她的丫鬟都輕視她,認為“龍生龍,鳳生鳳,這話是有的。”曹七巧的丈夫患有軟骨癥,再加上周圍人對她的鄙夷,使她成為了別人口中“嘴這樣敞,脾氣這樣躁,人緣這樣壞”的“瘟神”。站在曹七巧的角度,她命不由己得被哥哥嫁給殘廢的丈夫,有了“你害得我好!你扔崩一走,我可走不了。你也不顧我的死活!”的委屈。自嫁入姜家她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要強的性格與潑辣尖銳的脾氣成了她在姜家生存的保護色。曹七巧的抗爭是一種帶有報復色彩的、任性賭氣似的反叛,她的敏感多疑、控制欲強、吝嗇保守的性格是她在缺愛、喪失信任的環境下逐漸形成的。在面對姜季澤對自己的示好,她分不清真假,只好一棒子打死,認為“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樣混賬”。本是對姜季澤有好感的曹七巧抑制自己的情感,守護自己的財產來保證自己小家的安寧。這種對愛的長久壓抑最終導致曹七巧心理的扭曲,度過了自己遭人憎恨、落寞的一生。
悅子出生于財主世家,是戰國時代名將的后裔,但當她父母雙亡、家庭敗落后并沒有得到丈夫的疼愛反而遭受丈夫出軌的刺激。傳統的日本價值體系更加推崇男性在社會、家庭分工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也導致悅子在丈夫出軌后喪失了自己追尋的生命意義,認為人生的信條是“不過分認真思考問題”。丈夫將情婦贈與的領帶帶回家,并將情婦的照片公然擺在家中,這一系列的行為都在不斷否定著悅子的存在價值。當丈夫生病后,她竟病態地期待著丈夫死去。在丈夫去世后,她認為“我不是去焚燒丈夫的尸體,而是去焚燒我的妒忌。”情感的缺失使悅子遁入虛空,她開始從公公彌吉、仆人三郎身上尋找情感補償。悅子的自我意識覺醒并沒有使她獲得理想的家庭關系,最終她親手用鐵鍬殺死了自己心愛的三郎,斬斷了自己的希冀以尋求最終地解脫。悅子的悲劇是一場追求美的毀滅,她對周遭環境的反抗是消極壓抑的。悅子將自己囿于父權社會下,將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不同的男性身上,沒有真正填補內心的空虛,沒有獲得真正的獨立與解脫。
曹七巧和悅子面對無路可走的現實都敢于尋求自救、打破生活困境。她們都處于喪失父母、囿于無愛家庭的窘境,面對相似的殘酷環境,她們都具備一定的反抗精神和追求愛情和幸福生活的意志。但曹七巧受到周圍人的鄙夷、輕視,變得敏感空虛、視財如命。她的性格受到世俗功利價值觀的影響,隨波逐流變成了自己原本最討厭的人。畸形的家庭環境造就了曹七巧畸形的內心,最終釀下人生的悲劇。悅子一直處于一種頹靡、抑郁的家庭環境之中,她消極抵抗著周遭的環境,在一次次失敗地追尋之后逐漸喪失了自我渴求重生的意識,她愛而不得便親手殺死了自己心愛的人,也親手扼殺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權利。重新審視父權制下的社會,審視矛盾的自我人格,曹七巧和悅子鮮活的生命、充裕的靈魂在異化的家庭中變得空白。令人窒息的人生際遇隔絕了不幸的曹七巧和悅子奮力掙扎所需的新鮮空氣,熄滅了她們追求幸福生活的火苗。
三.社會背景下的曹七巧和悅子
曹七巧和悅子生活的時代背景不同,但她們所處的社會都是以男性占據主導地位,女性附屬于其中的社會。她們受傳統社會文化的熏陶,受身邊環境的推動,即便自我意識覺醒,也只亦步亦趨,無力徹底打破不公的處境。魯迅在《吶喊》自序里曾談起,“叫醒鐵屋子里較為清醒的幾個人,而讓他們承受無可挽救的臨終苦楚”,這種做法是殘忍的。曹七巧和悅子察覺到自己身處“沉悶的鐵屋子”當中,但單靠自己的力量卻無法打開“鐵屋子的門”。她們在沉悶的時代和家庭中感到焦慮和無助,以服從為信條的一系列等級制度和僵化的父權制社會將兩個渺小女人的命運瓦解得支離破碎。
曹七巧面對丈夫“沒有生命的肉體”只能壓抑自己的天性,無法從家庭中獲取肉體和精神上的滿足。她身處傳統儒家道德標準規范下的社會,人們要求她按照社會默認的規則行事。但曹七巧從剛嫁進姜家的“雖是比以前暴躁些,但還有個分寸”變成了婚后別人口中“不似如今瘋瘋傻傻,說話有一句沒一句,就沒一點得人心的地方”討人嫌的模樣。曹七巧無法服從傳統女性“三從四德”的要求,又沒有能力沖破舊家庭的藩籬,為自己爭取現代女性所應有的獨立與自由。她曾希望從正常的男性姜季澤身上尋求愛情,但姜季澤并不是她值得托付的人。姜季澤的宗旨是“玩歸玩,但不惹自己家里人”,認為曹七巧是個累贅。卑微的曹七巧飽受宗法權威制社會強加到自己身上的苦楚,異化成了一個虛情假意、精神畸形的人。她將自己吃過的苦又轉嫁到兒女身上,成為了兒女思想上的獨裁者。曹七巧從肉體上禁錮長白和長安。她教會和引誘他們抽大煙,并給長安裹腳,將長安變成了外人笑話的老姑娘。另外,曹七巧從精神上毒害兒女,她攪和長白和芝壽的婚姻導致夫妻不和。她破壞長安和童世舫朦朧的愛情,用平扁尖利的喉嚨告訴童世舫自己的女兒吸大煙,撕碎了女兒的幸福。曹七巧從一個男權社會下的受害者轉而變成了封建禮教下“吃人”的禍害,她不僅沒有擺脫封建大家庭對她的束縛,也葬送了自己和兒女的幸福生活。
悅子身處在二戰結束后,日本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沖擊的矛盾的社會。她出身于一個戰國時代的名將后裔之家,本身受到了日本忠貞、順從、廉恥等傳統的儒家和武士道思想,但西方追尋自由獨立、利己主義等思想也影響著她。原本幼年喪母、青年喪父的她渴求從家庭中獲取溫暖,但丈夫的出軌引發她的強烈嫉妒之心并詛咒丈夫死去。待丈夫去世后,她迫于生計搬到了公公彌吉鄉下的家中。這第二個家不僅沒有彌補悅子內心的失落與空洞,更是將她推入憂郁痛苦的深淵。在丈夫服喪期間,悅子在公公的引誘下成為了他的情人。雖然悅子在生活和情感上依賴彌吉,但她從心底厭惡這種亂倫的關系。她偽善的記錄兩種截然不同的日記,一封寫著“只要擁有純潔的心、樸素的靈魂就夠了”,一封卻渴求“在沒有洞穴的金錢里鑿開一個洞穴,那就是自殺。”
悅子撕裂矛盾的精神讓她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她渴望健康青春的三郎帶給她新的生活,但兩人的社會階層教育程度存在巨大差異。三郎新鮮充實的肉體吸引著她,但倆人的巨大差距讓他們沒有思想上的共鳴。文化的沖突和斷層帶給悅子新的身份危機和焦慮虛無感,在沒有精神寄托的矛盾狀態下,悅子用鐵鍬砸死了心愛的三郎,毀掉了最后的希望。
曹七巧和悅子都身處男權社會下,沒有獨立堅實的經濟基礎,她們無法保證自己脫離舊家庭之后在經濟、思想上的獨立自主。在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中,曹七巧和悅子的反抗都是消極被動的。她們沒有徹底推翻封建舊家庭帶給自己的壓迫,將自己的命運寄托在他人身上。曹七巧即便在自立門戶后也固守著父權社會帶給她的舊思想,將金錢視為唯一信仰,扼殺了自己重獲新生的機會。“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曹七巧經歷了封建宗法家庭的改造,從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變成了吞噬別人的幽靈。悅子在丈夫去世后本可以重新生活,但她卻寄生在彌吉的家中成為她的情婦,喪失了獨立生活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悅子在殺掉三郎后瘋狂般說出“誰都不許折磨我,誰都不能折磨我。”但她不明白,折磨自己的罪魁禍首,不僅是戰后日本的現實社會,還有她自己空虛的心靈。曹七巧和悅子在僵化的封建社會中化身繭中的蠶蛹,限制著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受到世俗傳統思想的支配并在命運年輪的轉動下走向了悲劇人生。
四.結論
張愛玲的《金鎖記》和三島由紀夫的《愛的饑渴》在小說中對女性主體的塑造都對封建宗法制社會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曹七巧和悅子在女性意識覺醒之后并沒有和侵蝕她們的舊思想、舊文化徹底決裂,也沒有培養自己獨立的經濟能力來告別對男性主體的依賴。這既是她們自身思想、能力上的局限,也是整個時代和社會的局限。在面對社會現實的束縛時,曹七巧沒有將反叛進行到底,在傳統舊思想的影響下將自己與兒女的人生都毀于一旦。悅子的覺醒意識在丈夫出軌之后就已經萌發,但面對社會的不公并沒有猛烈反擊,而是在失敗的婚姻與人生面前繳械投降,走向靈魂的虛無。《紅樓夢》中說:“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這和曹七巧和悅子在時代洪流中掙扎過后落得一個可悲的結局也有些相似。但曹七巧和悅子的傳統女性形象在我們打破父權社會對女性沉重的枷鎖,重塑女性形象方面有重大借鑒意義。打破傳統社會價值標準對女性的束縛并改變大眾對女性的刻板印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希望更多反映女性意志的作品能改變傳統宗法道德影響下思維的局限,為我們帶來時代的曙光。
參考文獻
[1]三島由紀夫.愛的饑渴[M].唐月梅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2]張愛玲.張愛玲自選集[M].海南: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2005.
[3]閻嘉.文學理論基礎[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
[4]林幸謙.女性主體的祭奠[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5]孟娜.論張愛玲小說《金鎖記》中主人公的女性意識[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6,2.
[6]魏凱.迷茫與解脫——張愛玲小說女性主義分析[J].北方文學,2012,6.
[7]楊鋒.論《愛的饑渴》的悲劇根源[J].山西大同大學學報,2007,12.
[8]劉舸.試論三島由紀夫創作中的女性意識[J].四川外國語學院學報,2002,3.
[9]張真真,徐國琴,夏瀅.《呼嘯山莊》與《金鎖記》中女主人公女性意識之比較分析[J].才智,2017.
[10]田豐,李鵬.從女性主義視角看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形象[J].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11,1.
[11]姚亞美.論三島由紀夫小說中的女性形象[D].福建:福建師范大學,2009.
注釋
①閻嘉.文學理論基礎[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
②林幸謙.女性主體的祭奠[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作者介紹:王曉雪,寧夏大學人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中外文學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