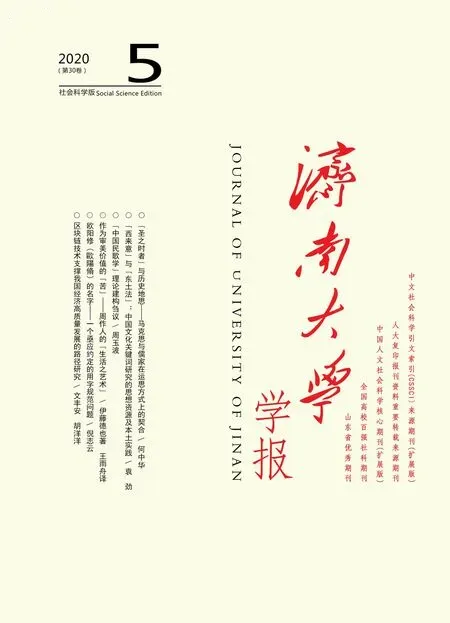中華文明史的玉器時代與王權起源
李秀強
(山東師范大學 齊魯文化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014)
一、問題的提出
侯外廬先生在《中國古代文明路徑與先王的起源》一文中曾指出:“中國古代史里有一個最特殊的問題,它的嚴重的程度是希臘羅馬所沒有的,這便是‘先王’問題。”(1)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頁。1936年,吳其昌先生作《金文名家疏證》,依據甲骨文、金文,通過對古文物、古文獻的考察,指出“王”字是由“斧”形逐漸演變而來。1965年,林沄先生發表《說“王”》一文,仍然從甲骨文與商周金文角度,進一步證明“王”字之本形像不納柲之斧鉞,而斧鉞最初是軍事民主制時期軍事酋長的權杖,后來逐漸演化成為王權的象征(2)林沄:《說“王”》,《考古》,1965年第6期。。此說超越了以往諸家舊說,在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然而,從考古年代學角度來講,甲骨文與金文是商周時期的文字,屬于中國歷史的青銅時代。青銅時代是中華文明的早期發展時期,但卻不是中華文明的起源時期。斧鉞之所以能與王權以及“王”字聯系起來,而備受部落最高軍事酋長的青睞,進而發展成為王權的象征,應該與中華文明的起源密切相關。故此,以斧鉞象征王權現象的最早歷史淵源,確乎不甚可能濫觴于文字已趨成熟發展的商周時期——青銅時代。
質言之,從甲骨文、金文角度證明商周時期的斧鉞是王權的象征,還只是注意到了中華文明史中以斧鉞象征王權現象的流,并未觸及以斧鉞象征王權現象的源。有鑒于此,我們試圖從中華文明起源和玉器時代斧鉞特殊功能的角度出發,追溯中華文明史中以斧鉞象征王權現象的源,從而進一步認識其演變的流。但這樣的探索需要考古學、文獻學、文字學等多領域的綜合交叉考察,并非易事。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西方考古學認為,西方古代社會的發展序列依次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然而,中國與西方不同,中國古代社會在石器時代之后還多產生了一個“玉器時代”,而中華文明就起源于“玉器時代”(3)有關中華文明起源于“玉器時代”的說法,詳參牟永抗、吳汝祚:《試談玉器時代: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國文物報》1990年11月1日;曲石:《中國玉器時代及社會學性質的考古觀察》,《江漢考古》,1992年第1期;吳汝祚、牟永抗:《玉器時代說》,《中華文化論壇》,1994年第3期;林華東:《“玉器時代”管窺》,《浙江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安志敏:《關于“玉器時代”說的溯源》,《東南文化》,2000年第9期;江林昌:《書寫中國自己的文明史——構建中國特色文史學科理論體系淺議之一》,《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江林昌:《書寫中國文明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這與西方文明起源于“銅器時代”相區別,在概念上正可以與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遠古文化史》稱西方古文明起源于“城市革命”相異(4)江林昌:《書寫中國自己的文明史——構建中國特色文史學科理論體系淺議之一》,《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17頁。。玉器時代孕育了中華民族所特有的崇玉文化,崇玉文化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的長河里奔流不息、盛而不衰,并貫穿于中國歷史中王權演進的始終。
具體而言,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順序,依次經歷了玉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三個階段。與此相對應,中華文明史中以斧鉞象征王權現象的起源與發展順序,也依次經歷了玉斧鉞時代、銅斧鉞時代、鐵斧鉞時代三個階段。也就是說,中華文明起源于玉器時代,而中華文明史中以斧鉞象征王權的現象也起源于玉器時代——也即玉斧鉞時代。林沄先生曾指出:
在新石器時代末期墓葬中出土的“玉斧”之類的器物,倒是頗值得我們考古工作者重視的,因為,我國古代國家形成的歷史,我們目前還是不夠清楚的,而這種歷史,一部分也許正隱藏在這些“玉斧”的背后呢。(5)林沄:《說“王”》,《考古》,1965年第6期,第312頁。
有鑒于此,茲不揣谫陋,試探討這些“玉斧”中所隱藏的中華文明起源時期的王權密碼。實際上,這樣的探索正當其時,因為古史重建已步入“黃金時代”(6)江林昌:《古史重建迎來了黃金時代——建構中國特色文史學科理論體系淺議之二》,《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且近一百年來,中國現代考古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發現,這其中包含大量遺跡與玉器遺物,為進一步探討此問題提供了新契機。
二、考古學所見“王權”與“玉鉞”之關系
在考古學上,一般認為斧、鉞、戚屬于同一類器物,來源于原始社會的石鏟、石錛等生產工具,具有劈砍的功能;在文獻學中,許慎《說文》云:“戉,大斧也。”《尚書·顧命》載“一人冕,執鉞” ,鄭玄釋鉞為“大斧”。由此可見,斧、鉞應屬同一類器物。而《說文》又云:“戚,戉也。”《詩·大雅·公劉》言“弓矢斯張,干戈戚揚”,毛傳:“戚,斧也。揚,鉞也。”《漢書》顏師古注:“鉞、戚皆斧屬。”總之,斧、鉞、戚屬同類器物,三者之間僅是尺寸大小有別而已。
玉鉞并不等同于石鉞。玉鉞成為王權的象征之前,先是經歷了石鉞的發展階段。石鉞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遺址中多有出土,且分布廣泛。在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大汶口早期文化等遺址中,石鉞有明顯的使用痕跡。而在崧澤文化、良渚文化、薛家崗文化、陶寺文化、齊家文化等遺址中,石鉞大多無明顯使用痕跡。這說明石鉞已經逐漸從生產工具中分離出來, 而可能已成為用于宗教禮儀或軍事的特殊器物。在中原仰韶文化等遺址中已出現大量的石鉞,這些石鉞與軍事統治權有關,且與原始巫術、原始宗教之間亦存在內在聯系。這說明斧鉞是神權、軍權相統一的器物。神權、軍權相統一的現象,也同樣存在于西方古代社會。在古希臘、羅馬的英雄時代,都存在一個權力顯赫的統治者,他不僅是專制的統治者,“同樣也是軍事首長、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審判長”(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頁。。這樣看來,中西方古代社會的統治者,都是集神權、軍權于一身的。
北陰陽營文化遺址是目前最早在墓葬中大量出土石鉞的考古學文化遺址。北陰陽營文化遺址中271座墓共出土142件“穿孔石斧”,這些“穿孔石斧”實際上均是石鉞(8)南京博物院:《北陰陽營——新石器時代及商周時期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北陰陽營遺址出土的石鉞,鉞身薄而輕巧,鉞刃鋒利,較有可能是軍事兵器。從墓葬等級以及隨葬品規格來看,北陰陽營文化遺址墓主人極有可能具有軍事身份,且社會地位也很高。也就是說,墓主人極有可能是軍事統帥。這說明北陰陽營文化石鉞是象征墓主人軍事身份的隨葬品,是墓主人軍權的象征。

北陰陽營石鉞

鸛魚石斧圖
又如,河南汝州閻村仰韶文化遺址曾出土一件大型陶缸,陶缸的外部繪有一幅“鸛魚石斧”圖。圖中石斧制作較為精美,明顯不是普通的勞動生產工具,而應是戰爭中的軍事武器。嚴文明先生認為:“它決不是一般人使用的普通勞動工具,而是同酋長身份相適應的、既可實用、又可作為權力標志的東西,是酋長生前所用實物的寫真。”(9)嚴文明:《“鸛魚石斧圖”跋》,《文物》,1981年第12期,第81頁。這就說明石斧是軍事酋長統帥權的標志物,也即軍權的象征。
玉鉞椎輪于石鉞。玉鉞是由石之美者——玉,精心制造而成,可謂石鉞中的最美者。《說文》云:“玉,石之美有五德。……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10)(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0頁。可見,玉乃“石之美”者,是美的象征。而且玉還有通神的功能,故有更為尊貴的地位。因此,玉鉞能夠超越石鉞,而更能成為神權、軍權的代表,也成為文明社會中王權的象征。

良渚文化反山玉鉞
良渚文化以玉器而聞名,而大量的高規格玉器多出土于貴族墓葬之中,這些墓葬多有玉鉞出土。這些玉鉞不僅制造精美,而且還置于墓主人手中,充分彰顯了墓主人對玉鉞的高度重視。從良渚反山發掘的十幾座古墓來看,每座墓葬只出土一件玉鉞,可見玉鉞是極為珍貴的。良渚文化玉鉞最為典型的例子是浙江余杭縣反山M12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大玉鉞,在玉鉞兩面刃上角各刻有一個“神人獸面”的神徽圖案,刃下角刻有一個神鳥圖案。巧合的是,這個“神人獸面”神徽圖案也見于一件大玉琮之上,而該玉琮與玉鉞同出一墓(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研究表明,該神徽圖案具有特殊的宗教意義。可見,該墓主人不僅是最高軍事統帥、部落酋長,同時還兼有巫師的身份。因此,該墓主人應是集軍權、神權以及王權于一身的領袖人物。良渚文化玉鉞僅發現于極少數較高等級的貴族墓葬之中,有些玉鉞柄還發現有象征良渚文化特點的神徽羽冠狀玉飾件,這些玉鉞直接體現了軍權、神權、王權相結合的特征。
此外,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燕遼地區最具特色的考古學文化——紅山文化,所發現的玉器也極其重要。紅山文化墓葬隨葬玉器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玉器多見于中心大墓,表明墓主人具有高貴的身份,且中心大墓多有祭壇相結合的布局,冢又圍繞神廟而建,這說明墓主人極有可能是部族酋長,同時也是通神的巫師;二是中心大墓只隨葬玉器而不見陶器,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一些低級別的墓葬卻專門隨葬陶器,這說明玉器具有特殊的意義;三是玉器的形制顯示出神秘色彩,玉器的擺放位置也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意蘊。紅山文化遺址共出土了6件玉、石鉞,這些玉、石鉞大多屬于紅山文化晚期,即距今5500~5000年左右。紅山文化晚期的玉、石鉞集中表現出軍權、王權以及神權相統一的色彩(12)劉國祥:《紅山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頁。。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完整的龍山時代考古學文化遺址。陶寺文化遺址發現了大型的城址、墓葬以及精美的隨葬品,根據墓葬的形制等判斷,陶寺文化遺址的墓葬可分為六個等級(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這些墓葬也出土玉、石鉞,且玉、石鉞只出土于第一至第三等級的高級墓葬中。從陶寺遺址墓葬出土玉鉞的情況來看,玉鉞是第一、二等級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和權力的標志器物,而這兩個等級的墓葬卻幾乎不見石鉞,這說明以玉鉞象征王權在陶寺文化中具有更為重要的地位。
至二里頭文化時代,玉鉞作為王權的象征仍然存在。學界一般認為,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鄒衡先生最早認定,二里頭文化第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14)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頁。。李伯謙先生亦指出:“二里頭文化的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15)李伯謙:《二里頭類型的文化性質與族屬問題》,《文物》,1986年第6期。經過不斷探索,二里頭文化主體部分為夏文化的觀點已成為學界主流認識。從目前的考古材料看,二里頭文化的墓葬可分為四個等級(1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9—101頁。。二里頭文化也出土玉鉞,而且這些玉鉞多出土于高等級的墓葬之中,這說明夏代的玉鉞仍然是王權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二里頭遺址還出土有青銅鉞。數十座一級乙類墓中,3座隨葬玉鉞,1座隨葬青銅鉞。玉鉞、青銅鉞同時存在于二里頭文化之中,這表明在青銅時代雖然青銅鉞已經開始成為王權的代表,但玉鉞仍然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依舊是王權的象征。而玉鉞與青銅鉞同時存在于夏文化之中,也是從玉器時代向青銅時代轉變時所帶有的過渡現象。
綜上所述,從良渚文化時期到二里頭文化時期,在中華文明史綿延發展的進程中,玉鉞作為王權的代表也具有連續發展的特征。換言之,從玉器時代到銅器時代,玉鉞作為王權的象征,具有不間斷發展演變的特點。而此后以玉鉞或其它高規格玉器象征王權的現象,也始終貫穿于中華文明史的發展進程之中。恰如侯外廬先生所稱,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是“新陳糾葛”的路徑,是“維新的模式”;而西方文明起源與發展是“新陳代謝”的路徑,是“革命的模式”(17)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頁。。亦如張光直先生所言,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模式是“連續性”的,而西方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則是“破裂性”的(18)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498—510頁。。
三、文獻學所見“王權”與“玉鉞”之關系
關于玉鉞代表王權,傳世文獻中多有記載。據東漢袁康《越絕書》所載,春秋時期風胡子與楚昭王論古史時講道:
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當此之時,作鐵兵,……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上述所論“以石為兵”“以玉為兵”“以銅為兵”“作鐵兵”,恰好對應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四個階段,即石器時代、玉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這里的“兵”,即是指“兵器”,而兵器必然包含斧、鉞。因此,將玉制作成斧斤之形以象征王權的玉鉞,作為軍事酋長的權杖,又是自然之事,此即所謂“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而“以玉為兵”的黃帝時代,即所謂“玉器時代”,正是中華文明起源的五帝時代,所以我們說中華文明史中以斧鉞象征王權的現象起源于“玉器時代”。
夏商時期,不僅玉鉞是王權的象征,甚至瑞玉本身作為“神物”也成為王權的象征。可以說,夏、商王朝的更替,實際上是以玉的轉移為標志的。《尚書·禹貢》載:“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史記·夏本紀》又載:“于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說文》曰:“圭,瑞玉也。”有學者指出廣義的圭應當包含玉斧,還有學者認為平首圭即源自玉鉞(19)錢耀鵬:《中國古代斧鉞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2009年第1期,第22頁。。若此說不誣,則玉圭與玉鉞、玉鉞同源,而應當都是王權的象征。因此,玉圭作為王權的代表,通過天帝傳給大禹,于是禹便得了天下,這便是夏王朝成于玉的明證。《史記·殷本紀》記載商湯滅夏,夏桀奔于鳴條時,講到這樣一個細節:
桀敗于有娀之虛,桀犇于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飐,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20)(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25頁。
商湯滅夏,取而代之建立新的中原王朝,首先取代的不是夏代所鑄以象征王權的“九鼎”,而是“俘厥寶玉”。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測,夏王朝的“寶玉”同“九鼎”的象征意義相似,都是王權的象征。掌握了“寶玉”神物即象征取代了王權,就可以號令天下,所以商湯滅夏之后,首要任務便是“俘厥寶玉”。商湯所俘取的夏王室的“寶玉”,可能都是玉禮器,其中可能也包含玉鉞。
在中國古代社會,關乎國家社稷命運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戰爭,故《左傳·成公十三年》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與戰爭都是國之大事,而最為重要的當屬祭祀。因為古人認為只有通過祭祀才能祈得神靈的佑助,才能保障國家的安寧。而且戰爭之前也要舉行祭祀,為的是祈求神明庇佑戰爭取得勝利。文獻資料表明,古人祭祀往往以樂舞的形式祭神。《禮記·祭統》云:
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21)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53頁。
《祭統》是專門講述祭祀禮儀之本的篇章,上述這則材料是講天子以樂舞祭祀神靈的儀式。值得注意的是,《祭統》言天子在以樂舞祭祀神靈時所秉持的是朱干玉戚,而玉戚即玉鉞。玉戚用作天子之舞,說明玉戚有著重要的地位,這也正反映出玉戚是王權至高無上的象征。
在《資治通鑒·后周紀五》中,也有玉鉞作為王權象征的記載,后周樞密使王樸卒,世宗親臨喪禮,并以玉鉞擊地,多次慟哭不能自已。后周世宗顯德六年載:
庚申,樞密使王樸卒。上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樸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上以是惜之。(22)(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9727頁。
由此可見,玉鉞即使到了五代時期,也不失為王權的禮儀權杖,仍然是王權的象征。總之,從文獻記載來看,玉鉞作為王權的象征之物,從五帝時代直至五代時期都受到了帝王統治者的高度重視。
毋庸諱言,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玉鉞象征王權的地位漸趨弱化,但以其它高規格玉器象征王權的現象卻始終貫穿于中華文明史的發展之中。譬如,秦始皇用以象征皇權的傳國玉璽,漢代的金縷玉衣,以及歷代帝王習用的玉璽,這些都是以高等級玉器來象征王權的至高無上。可以說,在整個中華文明史上,王權的發展始終伴隨著玉器的使用,高規格的玉器也始終是王權的代表。
四、文字學所見“王”與“玉”之關系
考古學、文獻學都表明,具有王權象征意義的玉鉞,影響了中華文明史上王權的起源與發展。而從文字學角度來看,斧鉞之形亦是“王”字的本象。圖畫的符號化是漢字的濫觴,以斧鉞之形探索“王”的字形起源,從而找尋出“王”字與斧鉞之間的歷史文化淵源,最終考證出斧鉞是王權的象征物,這在研究中華文明史上王權的發展方面,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實際上,“王”字與“玉”字也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兩字似乎在文字形成上有著相似且深刻的文字學淵源。不難發現,“王”與“玉”在字形、字義上都存在著同一性。
首先,從字義角度來看。《說文解字》釋“王”字曰:
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
許慎引董仲舒之語,認為能夠參通天、地、人三者,便可謂之王,并以孔子所說“一貫三為王”為證。其實,許慎的解釋并非符合王字的本義,現在已經很少有學者再相信古人“一貫三為王”的解釋了。不過,這卻代表了漢代人對“王”這個字的理解,深刻反映了漢代社會的思想狀況。《說文解字》又釋“玉”字云:
玉,石之美有五德。……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玉,石之美有五德者。者字新補。象三玉之連。謂三也。丨其貫也。”(23)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0頁。《說文解字》釋“三”云:“天、地、人之道也。”又“丨”與“一”相通,因此“象三玉之連。謂三也。丨其貫也。”即所謂“一貫三為王”。由此可見,“玉”字也蘊含著貫通天、地、人三者的含義,這與“王”字的意義是相暗合的。這看似是偶然的巧合,事實上絕非如此簡單,而是深刻展現出秦漢時期人們潛意識里就認為玉字含有王的意義。這也是秦漢時期以玉象征王權的文字學印證,究其根源,這正是受玉器時代以來崇玉文化的影響所致。
其次,從字形角度來看。現將《說文解字》中“王”與“玉”的古文字體和小篆字體分示如下:
“王”字:

(古文) (小篆)
“玉”字:

(古文) (小篆)
從字形結構上來看,不難發現“王”與“玉”的古文字體雖然存在著一些差異,但仍然有趨同的趨勢。時至秦代的小篆字體,其差異已經幾乎很小。唯一的差異是三橫之間的距離不同而已,若不仔細加以辨別,兩者就很容易混淆。而且從小篆字形來看,小篆的“玉”字更接近秦漢以后的“王”字。這說明秦漢時期人們似乎已經認為“王”與“玉”是同一字了,或者說“玉”字就代表著“王”字。關于此點,我們可以在后世文獻中找到證據。《廣韻·入聲·燭韻》載:“玉,《說文》本作王,隸加點以別王字。”《廣韻》似乎也已認為《說文》中的“王”與“玉”相似,隸定之后為了加以區別,才給王字加一個點以表示玉。需要指出的是,《說文解字》與《廣韻》對“王”與“玉”的解釋,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并非“王”與“玉”二字的本義。但這卻側面反映出,秦漢以后以玉象征王權之思想的根深蒂固,這種思想已影響了文字學上對“王”與“玉”的闡釋。
要之,我們雖然不能臆斷“玉”字就是“王”字,但從《說文解字》中關于“玉”與“王”字形、字義的同構性來看,可以肯定的是,“玉”本身就是王權的象征,或者含有“王”的意義。
五、結語
通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由此勾勒出中華文明史中以玉鉞象征王權現象的起源與發展的大致輪廓。從考古學上來講,中華文明起源于玉器時代,而中華文明史中以斧鉞象征王權的現象也濫觴于玉器時代。斧鉞是王權的象征,新石器時代雖然已經出現了石斧鉞,但彼時還只是生產工具,并未真正發展成為象征王權的器物。斧鉞真正演變成為王權的象征,應當肇始于玉器時代,而以玉鉞最為典型。玉器時代的玉鉞不僅是軍事酋長發號施令的權杖,也是最高巫師用以通神的法器,更是王者用以彰顯王權的圣物。所以,玉鉞是王權、軍權、神權三合一的象征。
從文獻學上來看,由五帝時代到夏商周三代再到秦漢時代,盡管王權的代表已逐步轉向青銅鉞和鐵鉞,但彼時玉鉞作為王權的代表,仍然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直至五代時期,玉鉞用作象征王權權杖的現象還時有閃現。不可否認,隨著歷史的不斷演進與發展,玉鉞逐漸退出王權的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以其它高規格玉器象征王權,但以玉象征王權的現象卻始終保留在中華文明史的發展進程之中。
從文字學上來說,《說文解字》中“玉”與“王”的古文字字形結構及字義存在同一性。雖不能以此臆斷“玉”字便是“王”字,但這似乎啟示我們,秦漢時期人們大概認為“玉”即“王”,或者說“玉”本身就帶有“王”的含義。準此,歷代帝王以玉彰顯王權的現象便不難理解了。
楊向奎先生曾指出:“研究中國古代史,有虞氏是不能忽略的一個歷史時代,應當在中國史上給他一個應有的地位。”(24)楊向奎:《應當給“有虞氏”一個應有的歷史地位》,《文史哲》,1956年第7期。有虞氏是五帝時代的部族,其歷史時代是中華文明起源的時代,也正是中華文明史上的“玉器時代”。那么,相應地來講,“玉器時代”也是中華文明史上不可忽略的一個歷史時代,也應當在中華文明史上給“玉器時代”一個應有的地位。以往,由于我們運用西方文明理論、考古學理論以及史學理論來研究中華文明,從而低估了中華文明獨立起源發展的特色,因而也低估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玉器時代”,這是十分遺憾的。而今,隨著考古資料的不斷豐富,“玉器時代”呼之欲出,當下已是時機彌補昔日之缺憾了。
附識:本文選題來源與主要思路,都源于導師江林昌教授的日常授課及已有論著,筆者在此基礎上所作的延伸和論證,有些還是導師尚未公開發表的成形觀點,特此說明。衷心感謝江林昌師的理解、支持與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