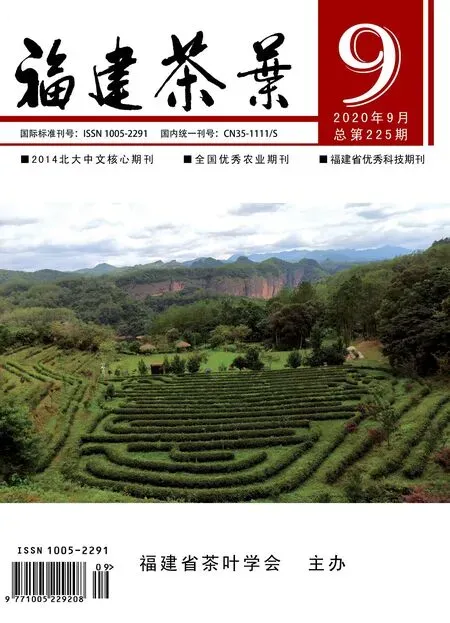關(guān)于陳元輔《枕山樓茶略》的幾個(gè)問題
曹建南
福州文人陳元輔的《枕山樓茶略》是散逸已久的清代茶書,朱自振教授從日本茶葉組合中央會(huì)議所獲得1805年版復(fù)印本,其文本分別被收入鄭培凱、朱自振編《中國(guó)歷代茶書匯編》和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編《中國(guó)古代茶書集成》(以下將此二書所收文本簡(jiǎn)稱“今本《茶略》”),為茶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貴的資料。本文擬根據(jù)古代日本茶書的相關(guān)資料,探討和陳元輔及其《枕山樓茶略》有關(guān)的幾個(gè)問題,就教于大方。
1 陳元輔其人
陳元輔,字昌其,福建福州人,史志無傳,生平不詳。2002年出版的《中國(guó)茶文大辭典》對(duì)《枕山樓茶略》的解釋是:“茶書。清代陳元輔撰。……作者未詳。”[1](P549)這里的“作者未詳”,顯然應(yīng)該是“作者生平未詳”的意思。章傳政等人2007年的論文也表示:“陳元輔,生平事跡不詳。”[2](P123)可見,茶文化學(xué)界對(duì)陳元輔的生平事跡是一無所知的。
但是,陳元輔是個(gè)能詩善文,工于書畫的民間文人,受到文學(xué)史、藝術(shù)史研究者的關(guān)注,他們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值得參考的信息。例如有人根據(jù)林潭《枕山樓詩集·序》:“自余庚戌,得交昌其,時(shí)方束發(fā)”的記載,推算出陳元輔應(yīng)該出生于順治十三年(1656)。[3](P47)陳元輔曾為程順則兒子搏萬的詩集《焚余稿》作序,落款為“康熙戊子蒲月既望閩中陳元輔昌其氏撰”。[4](P1)“康熙戊子”,即康熙四十七年(1708),可見康熙年間(1662-1723)是陳元輔活動(dòng)的主要時(shí)期。
陳元輔有《枕山樓詩集》、《枕山樓文集》、《枕山樓詩話》和《枕山樓課兒詩話》等在日本刊行。他的書畫在日本也有較高的評(píng)價(jià)。1855年,盤谷井暉在林潭《晚香園梅詩》安政版的刊刻后記中說:“余藏陳昌其書幅多矣。磊落不羈,筆法如神,而未審其為人,常以為憾。”[5]1876年的《青灣茗?圖志》所附《青灣茗?書畫展觀錄》也有:“陳元輔淡彩山水[絹本立幅]”的記載,[6](P290)可見,19世紀(jì)中期,陳元輔的書畫作品在日本收藏家之間頗有人氣,作為煎茶席茶掛還受到茶人的青睞。《妙蹟圖傳》(1909年)評(píng)陳元輔某草書作品曰:“此幅展之,只見雄豪之態(tài),諦觀之,則覺字與心應(yīng),腕與筆酬,縱橫跌宕,有顛素之趣。”[7](P253)認(rèn)為陳元輔草書有唐代書法家懷素狂草的韻味,陳元輔書法在日本評(píng)價(jià)之高由此可見。作為書畫家,陳元輔被收入日本思文閣出版的《美術(shù)人名辭典》。
陳元輔幾乎一生未仕,年輕時(shí)頗有懷才不遇的郁憤。例如他評(píng)注林潭《晚香園梅詩》中詩句“一從知遇羅浮后,幾度凄其鶴唳天”時(shí)說:“吾輩當(dāng)牢騷極不平之際每借一笑以代痛苦,所以古今來無限顛顛倒倒之事,蓋可付之一笑。……予當(dāng)夜深時(shí),半盞孤燈,一杯苦茗,回想此生,遭逢不遇幾為痛。知遇之難如此,今讀此,愈增太息矣。”[5](P3)又評(píng)注“枝南枝北不改芳,吾將為賦續(xù)江郎”句說:“‘不改芳’三字,只見梅之節(jié)操,……予憶試后無聊,忽曾子、子浴自潛園來,留之齋頭,命童子焚香煮茗,予與促膝談心。或仰天浩嘆,或搔首長(zhǎng)吁,甚至兩人互相泣下。”[5](P9)懷才不遇的陳元輔大概就是這樣在焚香煮茗、切磋詩文的歲月中度過了他的憤青時(shí)代的。
福州的不遇文人之所以能享譽(yù)日本,和他的學(xué)生程順則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琉球鴻儒程順則(1663-1735),閩人三十六姓后裔,字寵文,號(hào)雪堂,博學(xué)多才,官紫金上夫。曾五次到訪中國(guó),拜陳元輔為師,學(xué)習(xí)程朱理學(xué)和漢詩。他攜回《六諭衍義》等多種漢文典籍,為琉球王國(guó)的文教、典制建設(shè)作出了較大貢獻(xiàn),被譽(yù)為“琉球五偉人”之一。
陳元輔比程順則約年長(zhǎng)8歲,兩人之間是亦師亦友的關(guān)系,頗多宴飲酬唱。陳元輔的詩文集幾乎都是程順則資助刊刻的。例如《枕山樓詩集》,林潭在《序》中說:“程子寵文從余友昌其游,相得甚歡。一日袖昌其詩,問序于予曰:‘此師半生心血也,茲欲壽之梨棗。先生固知師之深者,愿乞一言弁其首。’”[8](P1270)對(duì)程的要求,林慨然應(yīng)允,并說:“世有如此之詩,藏之名山,以待傳人可也;即懸之國(guó)門,與眾共讀,亦無不可也。此寵文所以捐貲授梓,欲為其師傳不朽也。”[8](P1275)明確交代了程順則捐資刊刻陳元輔詩集的緣由。陳元輔《送程寵文歸中山·其九》:“枕山詩草委沙泥,獨(dú)檢焚余授棗梨”,自注曰:“程子捐貲,為予刻詩”,[8](P1358)可見程順則捐資為恩師刊刻詩集是確有其事的事實(shí)。而《枕山樓課兒詩話》則是由程順則發(fā)起,聯(lián)合了另外5人共同“捐資授梓”的。[9](P28)
至于《枕山樓茶略》是否和程順則有關(guān),根據(jù)現(xiàn)有的資料,我們無法給出判斷。
2 版本和書名
據(jù)管見所知,《枕山樓茶略》在日本現(xiàn)存兩個(gè)版本。一是文化2年(1805)9月的刊本,這是現(xiàn)在所知該書的最早版本,也就是萬國(guó)鼎《茶書總目提要》中提到的版本。萬國(guó)鼎的根據(jù)《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1930年),其中子部·譜錄類載:“《枕山樓茶略》一卷,清·陳元輔撰,文化刊”[10](P498),可見就是文化版。今本《茶略》就是根據(jù)這個(gè)版本排印的文本。另一版本是明治3年(1870)日本書肆布袋庵出版的田癡訓(xùn)點(diǎn)的插圖本,書名也是《枕山樓茶略》。“訓(xùn)點(diǎn)”是日本人閱讀古代漢文的輔助符號(hào),除了標(biāo)點(diǎn)斷句,還標(biāo)注漢字的日文讀音和調(diào)整語序的符號(hào),目的是幫助日本人正確理解中國(guó)的古代漢文。田癡,即田能村直入(1814-1907),日本著名的南畫家,煎茶文化的推行者。他訓(xùn)點(diǎn)的明治版的發(fā)行,擴(kuò)大了《枕山樓茶略》在日本的讀者層。
但是,在文化版問世之前,凡是涉及此書的文獻(xiàn),其書名均為《茶略》。記載琉球風(fēng)俗的戶部良熙《大島筆記》(1762年)提到:“有陳爺《茶略》之書,云乃委論茶事之書也。”[11](P374)意思是說,有一部叫做“陳爺《茶略》”的書,據(jù)說是一部詳細(xì)闡述了茶事的書。按照程順則在琉球文教界的地位,以及陳元輔和程順則的師生關(guān)系來說,18世紀(jì)中期琉球的讀書人把陳元輔稱為“陳爺”并非不可思議之事。雖然我們還無法確定在琉球流傳的這“陳爺《茶略》”究竟是刊本還是抄本。
大枝流芳《青灣茶話》(1756年)被稱為日本第一部煎茶書,其中設(shè)《采摭諸書》一節(jié),羅列了該書涉獵的和漢古籍共49部,《茶略》是其中之一,并標(biāo)明著者為“陳昌其,字廷耀”。[12](P77)雖然“字廷耀”有誤,但并不妨礙陳元輔所著茶書名為《茶略》的事實(shí)。《青灣茶話》有7處引用了《茶略》,其第一條說:
陳昌其《茶略》曰,物之得器,猶人之得地也。何獨(dú)于茶而疑之?蓋烹茶之器,不過瓦、錫、銅而已。瓦器屬土,能生萬物,有長(zhǎng)養(yǎng)之義焉。考之五行,土為火用生,母子想得自然有合,故煮水之器,唯此稱良。然薄脆不堪耐久。其次則錫器為宜,蓋錫軟而潤(rùn),軟則能化紅爐之焰,潤(rùn)則能殺烈焰之威,況登山臨水,野店江橋,取攜甚便,與瓦器動(dòng)輒破壞者不同。至于銅礶煎熬之久,不無腥味,法宜于礶底灑錫,久則復(fù)灑,以杜銅腥。若用鐵器以煮水,是猶用井水以烹茶,其悖謬似不待贅。[12](P89-90)
日本代表性煎茶書是上田秋成的《清風(fēng)瑣言》(1794年),書中引用了《茶略》5條,其中第一條(圖1)云:
陳元輔《茶略》云,茶之有性,猶人之有性。人性皆善,茶性皆清。[13](P483)
同樣是以《茶略》為書名的。文化2年6月,上田秋成在《答尾張人大館高門》中提到了刊刻“陳昌其《茶略》”的計(jì)劃[14](P47),可見直到文化版刊刻的三個(gè)月之前,日本人都是以《茶略》來稱呼陳元輔的這本茶書的。而且,陳元輔在《自序》也說:“茲特譜為二十則,曰《茶略》”,[15](P821)明確說明其書名是《茶略》。

圖1 《清風(fēng)瑣言》引陳元輔《茶略》書影
可見,陳元輔的茶書早先是以《茶略》之名在琉球、日本流傳的,大概是刊刻文化版時(shí),仿《枕山樓文集》《枕山樓詩集》《枕山樓詩話》之例,加上“枕山樓”三字,成為現(xiàn)在眾所周知的《枕山樓茶略》。
最早以《枕山樓茶略》這一書名加以引用的日本煎茶書是江戶后期的南畫家田能村竹田的《竹田莊茶說》(1829年)。田能村竹田(1777-1835)是代表日本文人煎茶頂峰的人物,善畫工詩,漢文造詣深厚,著述頗豐。所著茶書有《竹田莊泡茶訣》《竹田莊茶說》《石山齋茶具圖譜》,合稱《泡茶新書三種》,于天保2年(1831)刊行。作為文人畫家,竹田和陳元輔在飲茶情趣和生活價(jià)值觀方面是有某些共同之處的。
3 成書年代
《中國(guó)歷代茶書匯編》和《中國(guó)古代茶書集成》都把《枕山樓茶略》排在朱濂《茶譜》(1820年)之后,章傳政等人2006年的論文則將其成書年代定為“1908年前”[16](P67),這顯然是由于對(duì)陳元輔的生平一無所知而造成的錯(cuò)誤。如上所述,陳元輔是活動(dòng)于康熙時(shí)代的文士,因此,該書的撰寫不會(huì)晚于康熙年間。
事實(shí)上,我們發(fā)現(xiàn),有名為《茶略》的漢文茶書在刊刻于日本貞享3年(1686)的盤察《茶考》中被多次引用(圖2)。盤察,不知何許人也。根據(jù)《茶考·序》:“余掛錫于平安巽山下之寓”,以及落款“苾蒭盤察記之”[17]可知,盤察是一名禪僧,書后記有“貞享三年中秋日,書林”[17](P11)字樣,沒有標(biāo)明刊刻者或發(fā)行者。書中分《辨始》《辨名》《辨 色》《辨 味》《辨 德》《辨地》《辨 水》《辨 沸》《辨制》《辨器》十則,摘引中國(guó)茶書的相關(guān)內(nèi)容,摻雜一些日本的茶事和自己的意見,是一本內(nèi)容簡(jiǎn)要的漢文體煎茶書。書中共有5處提到《茶略》,摘錄如下:
1、《茶略》云,除煩去膩,人固不可一日無茶。然或有忌而不飲,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自清。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而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jiān)密,蠹毒自已矣。然率用中下茶云云[顧元慶《茶譜》亦引此語矣]。[17](P6)
2、《茶略》云,凡水泉不甘能損茶味之嚴(yán),故古人擇水最為切矣。《茶譜》同之。[17](P8)
3、《茶略》云,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dāng)使湯無妄沸,庶可養(yǎng)茶。始則魚目散布有聲,中則四邊泉涌累連,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云云。[17](P8)
4、《茶略》云,凡烹茶,先以熱湯洗茶葉,去其塵垢矣。[17](P9)
5、《茶略》所載凡有十六種:商象[古石鼎也];……。[17](P9-10)
上述5條引文均見于明代錢椿年撰、顧元慶刪校的《茶譜》,只有2、3、4這3條亦見于今本《茶略》,不知是盤察引用資料的錯(cuò)誤,還是后世刊刻《枕山樓茶略》時(shí)進(jìn)行了刪改。但根據(jù)第1條引文后“顧元慶《茶譜》亦引此語矣”、第2條引文末尾“《茶譜》同之”的夾注可知,在盤察撰寫《茶考》時(shí),《茶譜》和《茶略》是同時(shí)存在的。《茶考》中引用的中國(guó)茶書還有陸羽《茶經(jīng)》、蔡襄《茶錄》、毛文錫《茶譜》、審安老人《茶具圖譜》、胡文煥《茶集》以及喻政《茶集》,都是確有其書的實(shí)在資料,沒有虛妄杜撰。雖然明代還有顧元起的《茶略》,但內(nèi)容和體例都相去甚遠(yuǎn),與本文無關(guān)。因此,可以斷定,盤察《茶考》所引用《茶略》,就是陳元輔的《茶略》。

圖2 1686年刊行的《茶考》引《茶略》書影
前面說過,陳元輔大約生于1656年,那就是說,《茶略》是他30歲以前的著作。陳元輔的心路歷程顯示了這種可能性。和陳元輔有50多年交往經(jīng)歷的林潭在《枕山樓詩集·序》中說:“昌其癸丑以后詩,多感愴牢騷,猶之少陵在曲江夔府諸作,一字一淚者。無非以遇與心違,懷才莫展耳。”[18](P1274)癸丑為康熙十二年(1673),陳元輔約18歲,林潭對(duì)陳昌其18歲以后詩作的“多感愴牢騷”的評(píng)價(jià),和昌其戊午年(1678,23歲)評(píng)注《晚香園梅詩》詩句時(shí)表現(xiàn)出來的“憤青情緒”是完全一致的。而丙辰(1676)以后,“昌其或磨盾草檄,浪賦從戎;或匹馬孤舟,遠(yuǎn)尋知己。閱歷久而識(shí)膽深,識(shí)膽深而性情摯,向之怫悒無聊,忽啼忽笑者,今皆韜鋒斂穎。坐春風(fēng)中,讀其近作,顥顥噩噩,欎而善愁,婉而多風(fēng)。”[18](P1275)可見,陳元輔在 20歲以后,隨著閱歷增長(zhǎng),思想性格逐漸發(fā)生了變化,以至“向之怫悒無聊,忽啼忽笑者,今皆韜鋒斂穎”,憤青情緒大為收斂。大概就是這段思想性格發(fā)生轉(zhuǎn)變的時(shí)期,感悟到飲茶具有“能逐倦鬼,驅(qū)睡魔,招心胸智慧之神,滌臟腑煩惱之祟”[15](P821)的“才德”,陳元輔才參考前人茶書撰寫了《茶略》一書。
根據(jù)23歲評(píng)注《晚香園梅詩》時(shí)的憤青情緒來推測(cè),《茶略》應(yīng)是他26歲前后的著作,也就是1680年至1685年之間。
4 對(duì)日本煎茶文化的影響
《枕山樓茶略》“除自序和一部分內(nèi)容是屬于陳元輔自己撰寫者外,有部分內(nèi)容和明清輯集類茶書一樣,只是換換標(biāo)題,基本上也是抄自他書。”[15](P820)因此,從中國(guó)茶文化史的角度來說,《枕山樓茶略》也許并不是價(jià)值很高的文獻(xiàn),但此書對(duì)日本煎茶文化產(chǎn)生的影響卻是不可忽視的。
日本人所說的“煎茶”,就是“散茶”或“葉茶”的意思,是和“抹茶”相對(duì)的一個(gè)概念,因此,所謂“煎茶文化”就是圍繞散茶的茶文化現(xiàn)象。日本的散茶文化發(fā)軔于17世紀(jì)中葉的隱元東渡,在此之前,抹茶是日本飲茶的主流。和抹茶點(diǎn)飲法相比,散茶的飲用方法和使用器具有所不同,故《茶考》、《青灣茶話》和《清風(fēng)瑣言》等闡述散茶飲用法的早期煎茶書都大量引用明清茶書的有關(guān)敘述,《枕山樓茶略》是被引用次數(shù)較多的一種。
以藏茶器具為例。抹茶和散茶的貯藏方法不同,抹茶的原料未碾成粉末時(shí)用陶罐貯藏,使用前碾成粉末,然后裝入漆器小罐存放,因此,對(duì)于習(xí)慣于抹茶的日本茶人來說,如何選擇散茶的藏茶器具是一個(gè)新的問題。《枕山樓茶略》說:“故貯茶之器,唯有瓦錫二者。予嘗登石鼓游白云洞,其住僧為予云,瓦罐所貯之茶,經(jīng)年則漸有濕,若用錫罐貯之,雖十年而氣味不改。然則收貯佳茗,舍錫器之外,吾未見其可也。”[15](P822)強(qiáng)調(diào)的是錫器的藏茶效果。
為了宣傳錫罐優(yōu)于陶罐的觀點(diǎn),《清風(fēng)瑣言》引用了陳元輔《茶略》中石鼓山白云洞住僧的說法,田能村竹田更是以《枕山樓茶略》為依據(jù),圍繞藏茶器具展開了他作為文人煎茶家的生活價(jià)值觀論述。他在《竹田莊茶說》中說:
藏茶有高麗、三島、熊川,或古備前、古薩摩等壺,為人所賞珍,然其實(shí)功終無及于錫壺。可求購錫壺大小二(只),大者貯年中所用之茶,小者貯日用之茶。若聞司馬溫公之語,斯亦稍奢者也,然梅雨間等(季節(jié))終非此壺則難以堪(用)。是當(dāng)從《枕山樓茶略》之說。茶一旦濕而焙之,則氣味減一段,萬不可令濕。[18](P315)
在這段話里,竹田表達(dá)了完全贊同陳元輔對(duì)藏茶器具要求的見解。所謂“司馬溫公之語”,大概指的是司馬光《家范》:“人情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之類戒奢倡儉的論述。竹田認(rèn)為錫壺藏茶雖難免奢侈之譏,但梅雨季節(jié)卻非錫壺不可,應(yīng)當(dāng)遵照《枕山樓茶略》所說為宜。
竹田在司馬光的“戒奢論”和陳元輔的“挺錫論”之間做出了態(tài)度鮮明的選擇,表現(xiàn)了文人煎茶家的生活態(tài)度。節(jié)儉是美德,但不能一味強(qiáng)調(diào)節(jié)儉而損害了茶葉應(yīng)有的色香味,以致喪失了飲茶的清興雅趣。田能村竹田不避拾人牙慧之嫌,搬出《枕山樓茶略》作為自己觀點(diǎn)的背書,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文人的飲茶情趣和生活價(jià)值觀在日本文人煎茶界的權(quán)威性。
《枕山樓茶略》的《得趣》篇是《青灣茶話》和《清風(fēng)瑣言》共同摘引的內(nèi)容,精要地闡述了文人的飲茶情趣。田能村竹田在《竹田莊泡茶訣》中說:“陳昌其所論《得趣》一條,我所欲言一一說盡,無復(fù)余蘊(yùn)矣。余友阿縑洲喜之,錄掛齋壁。”[18](P313)認(rèn)為陳元輔的《得趣》是言簡(jiǎn)意賅、“無復(fù)余蘊(yùn)”的關(guān)于煎茶情趣的經(jīng)典論述。阿縑洲,即阿部縑洲,約生于寬政6年(1794),精通詩書篆刻,有《良山堂印譜》、《良山堂茶話》傳世,是煎茶道東阿部流的流祖。他抄錄了陳元輔的《得趣》篇掛在自己的書齋里,可見陳元輔的“煎茶情趣論”在日本文人煎茶家圈內(nèi)是很有影響力的。
從《青灣茶話》到《清風(fēng)瑣言》,再到《竹田莊泡茶訣》,日本的文人煎茶到達(dá)了巔峰期,但都把陳元輔的《得趣》作為“煎茶情趣論”的經(jīng)典加以推崇,可見《枕山樓茶略》在日本煎茶界的影響力之大。這和陳元輔的詩文、書畫在18-19世紀(jì)日本文人墨客之間的盛譽(yù)是相輔相成的。
綜上所述,本文認(rèn)為,陳元輔26歲前后撰寫的《茶略》17世紀(jì)末期就在琉球和日本流傳,被日本重要的煎茶書頻繁引用,19世紀(jì)初改名為《枕山樓茶略》刊行,對(duì)日本煎茶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