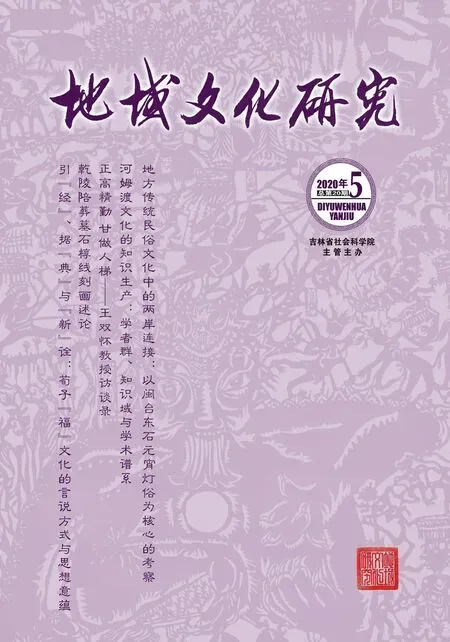地方民俗變遷之深描及其價值啟示
——評陳恩維著作《地方社會、城市記憶與非遺傳承——佛山“行通濟”民俗及其變遷》

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進程,文化變遷一直不可避免地持續(xù)進行著,這已成為人類學、民俗學長期探討的常態(tài)論題。國外學者直接或間接以文化習俗、社會風俗等為對象,依托理論架構(gòu)、民族志書寫、文化細描等方法,力求從文化變遷現(xiàn)象中尋索穩(wěn)態(tài)規(guī)律,產(chǎn)生了自成范式的古典進化論、傳播、新進化論、解釋人類學等學派。近百年來,在城鎮(zhèn)化以及全球化發(fā)展沖擊下,“鄉(xiāng)土中國”逐漸向“城鎮(zhèn)中國”轉(zhuǎn)型,地方文化發(fā)生了在傳承中變遷、盛衰交織分化的復雜過程。對此,前輩學者費孝通、林耀華等進行了諸多開創(chuàng)性探究,著眼于漢族地方社會變遷,寫出《江村經(jīng)濟》(1938年)、《金翼》(1944年)等經(jīng)典著作,呈現(xiàn)了農(nóng)耕時期傳統(tǒng)中國的社會結(jié)構(gòu)與文化變遷圖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城鎮(zhèn)建設(shè)、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及其帶來的文化變遷引起學界廣泛思考,學者們從引進、譯介國外文化變遷理論方法開始,逐步過渡到探究少數(shù)民族區(qū)域、農(nóng)村片區(qū)、具體村落的民俗變遷以及文化變遷與地方社會互動等論題,產(chǎn)生了豐富成果。其中,莊孔韶的《銀翅》(1996年)把社會史與文化人類學考察相結(jié)合,將文化變遷研究推向了新高度。除了這種綜合、全貌地研究村落文化變遷之外,不少學者還對單項民俗變遷進行考察,然而較多關(guān)注少數(shù)民族、偏遠村落的民俗變遷,對漢族人口密集區(qū)、區(qū)域城市社會的民俗變遷尚缺乏深入、立體的研究。201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陳恩維教授獨著的《地方社會、城市記憶與非遺傳承——佛山“行通濟”民俗及其變遷》(下文簡稱“陳著”)彌補了這個缺憾,是近年來我國地方民俗變遷研究的一部力作。陳著以廣東省第三大城市佛山的行通濟民俗為對象,依托豐富的史志文獻,并借助田野考察和理論觀照,將其置入地方社會、城市記憶和民俗變遷互聯(lián)的整體框架當中,在長時段和大空間視野下對行通濟民俗的源流、變遷進行了立體式深描,具有不可忽視的多維學術(shù)和現(xiàn)實價值。
一、在文獻、田野和理論融合中深描地方民俗變遷
任何民俗都有其淵源流變以及社會鏡鑒作用,如學者胡樸安所言:“蓋風俗乃歷史產(chǎn)物,鄉(xiāng)間習俗,皆有淵源,一事一物,俱關(guān)文化,故能知古今風俗,即為知中國一切。”①胡樸安:《插圖本中華全國風俗志》,上海: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1頁。陳著以對民俗的追根溯源為研究旨歸,有意識地將文獻考證、田野考察與理論分析相融合,立體、多維、精準地掘出以往學界慣性盲視或習焉不察的史志文獻和口述記憶,并以人類學眼光對各種文獻進行闡釋,從中清理出與行通濟民俗有關(guān)的證據(jù)鏈。文獻、田野和理論三方融合,顯示了方法論自覺和多方法組合意識,漸進式達到了深細、整體地研究行通濟民俗的目的——把握民俗傳統(tǒng)在地方社會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規(guī)律及其與城市記憶疊合的文化特質(zhì)。
民俗有著生成轉(zhuǎn)型、盛衰雜糅的“生命史”,但其漸趨模糊的軌跡往往沉隱于那些塵封的史志文獻之中。尤其是地方志蘊藏著大量的民俗記錄,研究民俗離不開地方志等文獻史料②汪玢玲、張徐:《方志與民俗》,《民俗研究》1989年第1期。。若不追索、考辨史料,僅以目之所察描述一項民俗,很難把握隱藏在歷史深處中的民俗本質(zhì)。如方李莉教授所提醒的,“不閱讀文獻,不查證歷史,僅以我們眼見的事實去描述,就很難把握這些隱含在歷史中的復雜事實。所以,在中國做民間藝術(shù)的研究,不僅要通過田野去對現(xiàn)實的生活情景進行‘深描’,還要通過文獻和出土的實物去‘深挖’背后的由歷史構(gòu)成的種種復雜因素。”③方李莉:《藝術(shù)人類學的中國化建構(gòu)》,《民族藝術(shù)》2017年第3期。陳著有效踐行了這一點,即從《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含東北卷、華北卷、西北卷、中南卷、西南卷、華東卷等共六卷)④該套《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多達五百余萬字,出版后被評價為具有“資料全”“資料翔實”“內(nèi)容豐富,類目較為齊全”等特點,“為研究者及廣大讀者提供了可靠的文獻基礎(chǔ)”,參見劉卓英:《中國民俗學研究的基礎(chǔ)文獻——〈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文獻》1992年第2期。陳著充分利用該資料,并進行了考證辨析。、《佛山忠義鄉(xiāng)志》(含乾隆、道光、民國版)、《廣東通志》(含明嘉靖、萬歷以及清康熙至嘉慶各版)、《南海縣志》(含明萬歷、崇禎以及清康熙至宣統(tǒng)各版)等數(shù)十種古近代方志以及1982年《佛山市風俗志》、1990年《佛山市城市建設(shè)志》、1990年《佛山水利志》、1991年《佛山市交通志》等十多種現(xiàn)代志書中“披沙瀝金”,挖掘了大量直接關(guān)涉“耗磨日”“過橋”“開燈”“放偷”“采青”等民俗事象的記錄;借此“順藤摸瓜”,又查到1939年《越華報》、1948年《電報》等民國時期直接記錄行通濟民俗但學界較少關(guān)注的系列短文;同時,擴展文獻查找范圍,以“搜羅必盡”為原則,搜查到了先秦兩漢至晚清民國期間與研究對象有間接關(guān)聯(lián)的數(shù)百種史志文獻,特別是梳理了宋元以來關(guān)涉“上元”、“走百病”等內(nèi)容的各類一手史料。“民間風俗是傳統(tǒng)的社會歷史文化,古今志書均有采擷民風民俗的傳統(tǒng)”①高天信:《舊志風俗與第二輪志書民俗雜談》,《中國地方志》2011年第3期。,依托這些史志文獻扎實鉤沉、追蹤通濟橋以及行通濟民俗事象的蛛絲馬跡,連綴、還原了行通濟民俗淵源流變的歷史脈絡和時空節(jié)點。比如,陳著第一章至第八章引用了大量史志、舊報刊等文獻記載,實證地考察了行通濟民俗淵源流變,內(nèi)容包括:第一章“行通濟”民俗的傳統(tǒng)儀式,第二章“行通濟”民俗與佛山地方空間,第三章通濟橋與佛山地方社會,第四章作為記憶之場的通濟橋,第五章“行通濟”民俗的文化淵源,第六章“行通濟”民俗的地方特色,第七章“行通濟”民俗的儀式流變,第八章“行通濟”民俗的內(nèi)涵變遷。扎實的考證助其考鏡源流,廓清了諸多懸而未解的行通濟民俗迷霧。比如,首次從實證層面厘清了通濟橋附近橋亭鋪街區(qū)的歷史發(fā)展邏輯以及佛山明代霍氏家族、明末清初細巷李家、清代僑寓人士與通濟橋的復雜互動關(guān)系;首次提出行通濟“這一民俗起源于南北朝時期,混合了多種民族習俗,經(jīng)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②陳恩維:《地方社會、城市記憶與非遺傳承——佛山“行通濟”民俗及其變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3頁。,從而洞悉了行通濟民俗之“北俗南傳”淵源及其累積沉淀、合流變型兼具的文化特色;首次系統(tǒng)考察了行通濟民俗的求子、求財、慈善內(nèi)涵及其功能變遷,等等。這些發(fā)前人之所未見的民俗考證尤見文獻功力,填補了行通濟民俗變遷史研究空白,是當前深化該非遺保護所亟須參照的學術(shù)資料。
作者在刻苦搜集史志文獻之外,還進行了頻繁往復、持續(xù)十多年的田野調(diào)查,每年全程“參與式觀察”行通濟民俗,獲得了豐富的訪談錄音、民俗錄像等田野資料。依王霄冰教授所論,“民俗資料,就其載體上可分為文字、圖像、實物、影音四大類。”③王霄冰:《民俗資料學的建立與意義》,《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陳著擴寬了“民俗資料”邊界,即圍繞史志文獻廣泛地援引其他多種形式的資料。這種在方志與田野、文體與主體、文化與生活之間搭建通路的努力收效甚顯,即著重在第九章“‘行通濟’民俗的當代傳承”等章節(jié)中借助高齡本地人訪談、實地考察、問卷調(diào)查、民俗儀式體驗等田野之法,還原民俗之“民”對于行通濟民俗生活的感受、經(jīng)歷以及多層次聲音,從民俗表象切入民俗深部,洞悉了地方民俗變遷背后的主體話語和生活規(guī)律。尤其糅合“文獻的田野”和“地理的田野”,調(diào)查分析標志性的空間(如通濟橋及周邊社區(qū)等景觀)、時間(如耗磨日、元宵節(jié)等節(jié)日)、人物(如本土大家巨族代表)、事件(如通濟橋修造史、行通濟記憶鏈等)、儀式(如放偷、走百病、偷青等)及其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或沖突,從而構(gòu)擬出地方社會和城市主體的生活相。陳著還適時引入法國歷史學家諾拉的“記憶之場”、美國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的“大傳統(tǒng)”和“小傳統(tǒng)”、德國學者揚阿斯曼夫婦的“文化記憶”、英國文化人類學家弗雷澤的“接觸律”等理論概念,借由質(zhì)性研究,闡明了行通濟民俗真實存在、或隱或顯的存續(xù)邏輯、傳承動力與發(fā)展機制。
二、以長時段與整體化并舉的視野觀照地方民俗生態(tài)
正因基于文獻、田野與理論融合的方法深描地方民俗變遷,陳著緊緊立足于地方及其單項民俗,但又沒有僅就地方談地方、就民俗論民俗,而是將“地方社會”“城市記憶”“民俗變遷”這三個關(guān)鍵詞貫穿于全書十章。這種在佛山地方社會的歷史(時間維度)和城市(空間維度)結(jié)合及其動態(tài)格局中觀照行通濟民俗的研究理路,形成長時段與大空間耦合的開放視野,突破了以往較多截時段、文本式、分割化地研究地方民俗的局限。這得益于作者長期沉潛關(guān)注佛山的文獻資料、歷史人物和民俗事象,以及對地方的自覺融入和對民俗的主動認同。對于這片提供衣食供給、文化滋養(yǎng)的珠三角核心腹地,十多年來作者從陌生臻于熟悉,從地理上的“異鄉(xiāng)人”成長為文化上的“本地人”。這使作者不僅了解佛山地方社會自古至今的發(fā)展史,而且諳熟各類包蘊著嶺南“地方性知識”的史志文獻。作者運用文獻知識和民俗方法,對這個表面上看似資料缺乏、儀式簡單的行通濟民俗進行了長時段與整體化并舉的深入研究,進而積十多年之力(2006年-2018年)撰成此書。
一是體現(xiàn)了長時段視野。西漢司馬遷提出“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以撰史實踐強調(diào)了在長時間內(nèi)“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重要性。法國年鑒學派代表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認為,只有在長時段中才能看清社會、文化的深層結(jié)構(gòu)變動。作者沒有把行通濟民俗研究變?yōu)榧兇獾臍v史研究和現(xiàn)象描述,而是按照顧頡剛“將民俗材料與治史目的相結(jié)合的做法……把清代以來盛行的源流考鏡方法引入民俗研究之中”①施愛東:《顧頡剛故事學范式回顧與檢討》,《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08年第2期。,敏銳把握民俗變遷的長期、緩慢、持續(xù)性特征。細言之將行通濟民俗置入千年以上的長時段內(nèi),把唐宋以來所涉及的時點、人物、景觀、事件等納入實證考察范圍,以志、圖、史互證方式研究行通濟民俗變遷的結(jié)構(gòu)性機理。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如第三章力圖“闡釋佛山人如何通過通濟橋來表達他們內(nèi)心的某些訴求,特別是他們對家族、村落、地方以及國家的認同,從而解開本地人和外來客都熱衷于‘行通濟’之謎”②陳恩維:《地方社會、城市記憶與非遺傳承——佛山“行通濟”民俗及其變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3頁。。這就既呈現(xiàn)了行通濟民俗“是什么”和“如何是”,又揭示了背后的“為什么”,在規(guī)避淺表化、浮泛化取向之時把握到了深層的地方民俗變遷規(guī)律,具有一種洞悉民俗變遷邏輯的縱深感,
其次彰顯了整體性視野。陳著由通濟橋到行通濟民俗,隨后入乎民俗之內(nèi)且出乎民俗之外,將這一因橋而興的民俗現(xiàn)象置于自然、社會、歷史、文化之中進行整體考察,呈現(xiàn)了通濟橋與佛山水系變化、城市空間格局、社會記憶功能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橋之建造、維修與佛山本土大家巨族之間、本土鄉(xiāng)紳和僑寓商紳之間、民間社會和官方政府之間的隱秘關(guān)聯(lián)。不僅如此,還進一步深刻提出:“通濟橋歷代的毀與修,既反映了佛山社會關(guān)系和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更迭演變,也折射了家族—社區(qū)—地方—國家的復雜互動關(guān)系。”③陳恩維:《地方公共建筑營造中的家國互動——以佛山通濟橋為例》,《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4期。可以說,陳著通過對通濟橋場所重建、記憶框架、文學敘事和記憶功能的敘述,闡明了行通濟民俗生生不息背后的內(nèi)在動因。以此為基礎(chǔ)再向橋俗漫溯,從空間、時間兩個維度整體性地追溯、考索行通濟民俗的文化淵源、生成過程、儀式流變、內(nèi)涵衍化和功能變遷。這種將民俗和歷史、儀式與社會聯(lián)動考察的思路,貫穿了研究“語境中的民俗”的人類學整體性視野。因此,不僅探清民俗本體,也透察了民俗主體及其城市語境和日常生活世界,甚至呈現(xiàn)了各種話語、權(quán)力交織的社會文化語境,及其對民眾主體、民俗本體的復雜影響和交互關(guān)系。進而揭示出,在現(xiàn)代化、城市化進程中,地方民俗可以自我調(diào)整、運作、創(chuàng)造的方式進行傳承發(fā)展。
三、依托深度描述和理性判斷的互動觀照非遺保護實踐
民俗研究的基礎(chǔ)功夫在于依托田野考察進行“細描”,即細致地描述一項民俗本體的形式面貌、儀式細節(jié)。“細描”源自20世紀前期英國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倡導的參與觀察式研究,其核心旨意是采用俯視視角對事象進行客觀記錄、零度寫作,從而科學、客觀地書寫民族志,在此過程中研究者隱而不彰,價值立場“中立”。20世紀60年代以后,科學、客觀的民族志書寫范式受到質(zhì)疑,研究者個體的主體感、在場感以及情感觀念得到注視,民族志逐漸被視為一種敘事行為與文化解釋。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以“深描”等核心概念構(gòu)建了“邁向文化的解釋理論”,對看似客觀的民族志“細描”構(gòu)成反撥,其要義在于,主張在文化個案中概括意義、對個案進行擴展性解釋。陳著吸納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在縱、橫向兩個方面做到了對民俗事象、儀式及其變遷過程的細描,但未止步于細描,而是將行通濟民俗置于國家與地方、歷史與現(xiàn)代、事像與主體聯(lián)動的視野中進行“深描”,追根溯源地剖清了行通濟民俗的長時段、立體化變遷過程,從中尋索出民俗傳入及其本土化、民俗變遷與地方社會互動等帶有普遍性意義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陳著在地方社會和城市記憶語境中“深描”行通濟民俗,接通了從現(xiàn)代轉(zhuǎn)向后現(xiàn)代的民俗學前沿理念,與那些著力于描述民俗史實、事實的民俗志文本相錯位,在研究深度上有鮮明拓進。
當然,“深描”民俗還不是陳著的最終目標,“身入”且“心入”,由表及里地融合深度描述和智性判斷,才體現(xiàn)了一個民俗研究者抬頭觀天、低頭望地的文化初心和現(xiàn)實情懷。作為一名早已熟悉佛山民俗的“文化本地人”,作者對行通濟民俗及其相關(guān)的非遺保護投入了深厚情感,因此在“細描”乃至“深描”行通濟民俗變遷之外,還融入糅合了學術(shù)眼光和理性思考的價值判斷,即從民俗本體中跳脫出來,批判性地審視分析非遺保護語境中的行通濟民俗復興行為,并對處于不斷重構(gòu)過程中的民俗修復提出諸多有價值的意見建議。比如第十章“‘行通濟’民俗的文化修復”提出:2002年重建的通濟橋與古橋形制不符,安全作用不明顯,未達到對核心文化空間的修復;把現(xiàn)代巡游當作行通濟民俗主體,排擠遮蔽了傳統(tǒng)儀式;政府打造行通濟慈善文化品牌,還只停留于形式聯(lián)合階段,等等。在分析、反思現(xiàn)行保護傳承措施得失成敗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從空間修復到文化修復”“從社區(qū)傳承到公共參與”“記憶再現(xiàn)與傳統(tǒng)重構(gòu)”等具有針對性的修復策略。求真與尚善的旨歸相交織,批判性立場與建設(shè)性意見并重,使得陳著在凸顯學術(shù)意義之時,也彰顯了關(guān)懷地方、照亮現(xiàn)實的公共精神。
結(jié) 語
在民俗整體趨于潰散的全球化時代,這部盡力發(fā)掘史志文獻并融合田野、理論的地方民俗變遷研究著作,兼具資料之學、闡釋之學、致用之學等多維學術(shù)和現(xiàn)實價值。尤其是陳著發(fā)掘了大量前人未曾關(guān)注過的但又關(guān)涉行通濟民俗淵源流變的各類記載,抵近由“紙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口述史料”構(gòu)成的三重證據(jù)法①余悅:《從二重證據(jù)到多重文化的民俗學研究——〈民俗研究的多重文化審視〉緒論》,《學術(shù)評論》2018年第1期。,其文獻考辨之功與資料學價值不容忽視。進而言之,這種研究理路有助于深化認知文獻與民俗的關(guān)系,即文獻不只是記錄民俗的載體,還對民俗研究具有反哺作用。具體而言,文獻深掘與民俗深描是互動的,深掘文獻可促進民俗的深度化描述,而深描民俗又能發(fā)揮文獻的最大化價值。20世紀90年代中國民俗學之父鐘敬文曾指出:“民俗是一種民眾文化事象,對它的研究,不僅僅是理論考察,它的資料本身也是有價值的。”②鐘敬文:《建立中國民俗學派》,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5頁。以史志文獻為主要依托的民俗資料之學是民俗闡釋之學、致用之學的基礎(chǔ),在民俗研究中不可或缺,否則很難發(fā)揮其闡釋和致用功能。在這一點,陳著可謂有突破性的探索和貢獻。
除了建立關(guān)于行通濟民俗的資料之學,陳著的創(chuàng)新之處還在于:在地方社會生態(tài)視野下深描行通濟民俗儀式的生成和流變,在城市記憶衍變中闡釋行通濟民俗的文化認同功能及其衍化,在非遺保護語境里總結(jié)反思當代行通民俗的保護傳承實踐。這種整體、融通的研究進路,體現(xiàn)了視野創(chuàng)新、方法創(chuàng)新和價值創(chuàng)新,對優(yōu)化“碎片化”“條目化”的民俗變遷研究具有多重參考價值。尤其具有鮮明的現(xiàn)實意義和鏡鑒意味,有助于地方政府、社會各界審視、反思那些流于浮躁、表面的地方非遺保護實踐,進而改進新型城鎮(zhèn)化背景下的非遺可持續(xù)保護方法。當然,這部散發(fā)著實證色彩的著作以民俗個案為研究對象,在人類學意義上的“主位”描述方面或許還有推進空間,但總體上對于地方民俗研究、非遺保護實踐具有鮮明的示范意義,值得政府官員、非遺保護工作者、民俗研究者深讀細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