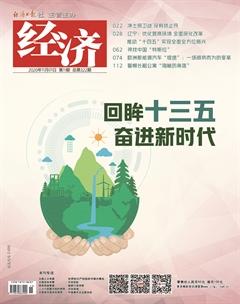新格局下筑牢金融風險防火墻
許亞嵐
我國對外開放的步伐堅定且迅速,中國金融業也在不斷追求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比如取消對銀行領域的外資持股限制、金融業準入負面清單正式清零等。與此同時,金融風險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開放條件下國際游資是主要風險
金融全面對外開放下,我國金融穩定將面臨新挑戰。
“我國對外開放的力度加大也是為了應對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逆全球化的做法。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這種策略顯示了我們的胸懷和態度。”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研究所所長黃震對《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表示,過去40多年,我國的對外開放一直有管理、條件、步驟和風控,如今這些經驗在金融領域依舊適用。“越開放,風險越高,對安全的要求也越高。我們應該看到當前整個國際環境其實并不友好,甚至一些對中國有敵意的國家可能會蓄意破壞中國的對外開放。因此,我國對外開放的政策是否會受到干擾和影響,也會影響到我們的金融穩定。政策能夠持續,金融就更加穩定。”
也有很多國家和機構愿意加入并支持中國的經濟建設,但也不排除有一些帶有投機成分的資金會進入中國并潛伏下來,等到關鍵時刻再“發力”從而影響中國經濟。另外,一些西方投資者有“剪羊毛”的習慣和經驗,因此,我國對外開放的同時也要警惕這些投資者。
中國機構有能力與外資機構同臺共舞,甚至能變得更強,而這需要國內機構與外資機構享受同等待遇、公平競爭。“令人擔心的是,我們的一些措施給與了外資機構超國民待遇,為他們提供了太多優惠、優待,而內資機構甚至可能沒機會參與其中。”黃震如是說。
開放會帶來更多的風險挑戰。面對風險,我們現在選擇加大開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濤看來,這表明現階段我們對管理風險、防控風險、防止外部沖擊具備足夠信心,“在此情況下,我們需要更好地發展資本市場,實現對外開放”。

聚焦風險,尹振濤對《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稱,第一,一個更開放的市場更容易受到外部的沖擊,外部沖擊可能會挑戰我國現有的金融體系和監管體系;第二,國內外資企業的經營活動有一部分受所屬國管理,同時也受駐地國管理,因此必然會面臨一些監管沖突;第三,外資進入國內后也可能對我國傳統的、本土的金融機構產生一定影響和沖擊,我國企業的業務份額可能會受影響,這也是一個新挑戰。
“目前,主要金融風險來自國際市場。”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告訴《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風險主要來自滬港通、深港通,因為這些管道的資金來去自由,撤退速度比較快,其中游資比較多,“不過目前,由于我國資本管制尚未取消,因此國內市場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大”。
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目前看主要可能來自國際游資。董登新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正加速推進,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力度也較大,資本管制最終必然會放松。“因此,我們可能面臨兩方面風險,一是跨境監管合作問題,二是國際游資的沖擊或國外資本的大規模策略。目前,介入資本市場的外資主要風險點是從滬港通、深港通進來的,但其總體規模不大,因此風險仍然可控。”
要做好輸入性風險防范
全面對外開放條件下,我國可能會面臨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
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教授陶士貴對《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表示,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2007年-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中,由于我國資本項目實行了嚴格管制,沒有受到太大沖擊。但隨著我國金融業全面開放,外資金融機構可以控股甚至獨資運營,QFIIR和QFII額度去年就取消了,資本管理越來越難。“今年以來,美聯儲實行無限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利率趨近零,不排除其未來實行負利率的可能性,而我國仍實行較穩健的貨幣政策,沒有跟隨貨幣‘放水,中美銀行間利差可能在2%-3%,若投向房地產或股市,則收益更大。在此情況下,可能形成大量外資進入我國進行無風險套匯套利活動,從而獲得暴利。”
陶士貴還表示,金融全面開放后,第一,美元在沒有大幅貶值前可能會投資我國的優質資產或投資我國金融市場,從而獲得更高回報,將風險外移;第二,可能會引起國際資本的大進大出,進而影響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這將考驗我國金融監管當局的決策能力和對政策的把握能力;第三,人民幣國際化是一把雙刃劍,“金融的全面開放會促使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但很可能會帶來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的難以協調、統一,即在條件沒成熟的情況下,急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會帶來新的風險和挑戰”。
在越來越多的外資和外資金融機構進入我國金融市場的背景下,我們要做好輸入性風險防范。
對此,陶士貴提出了四點建議。一是講求金融對等開放原則,要求進入我國的金融機構的國家也要對我國開放其金融市場。二是采取區別對待原則,可以對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村鎮銀行等地方金融機構加速外資并購,但對國有控股金融機構則要把持好控股權,防止控股權落入外國投資者手中。三是制定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機制和制裁名單制,對不遵守我國金融相關法律法規的外資金融機構,可將其列入失信名單并進行相應制裁,在存款、貸款、支付結算等方面進行限制,對問題嚴重的外資甚至可以督促其退出金融市場,依法行事,加大處罰力度,保證金融市場的安全和穩定。四是在支付清算、金融數據獲取等敏感信息領域,限制外資機構準入。
此外,“還需壯大國內金融機構,對其提供與外資機構同等的資源和條件,使其有足夠的競爭力”。黃震稱,近年我國一直在做風險防控整治的工作,而在加強企業創新和加強企業競爭力的培育方面力度還不夠。因此,必須加大力度,提高競爭力,提高內資的國民待遇,實現對外、對內統一待遇。

無論是新的風險挑戰還是風險防范,在尹振濤看來,最重要的還是制度框架。過去我國沒有完全開放的時候,制度框架是適應當時市場的,而新的市場制度框架肯定需要相應調整。我們需要與更多的國際規則接軌,需要一個國際通行的、與國際相適應的監管政策體系,而不是哪里有風險就去堵哪里。這個挑戰和要求是最大的,也是一個正常、合理運轉的市場所需要具備的條件。
我們還要加強風險防范的應急能力,不能等風險龐大了、出問題了再去管理,提前、實時預警,做好輸入性風險防范,重要的一點是能夠及時發現風險。
提前預警加強科技能力和防控演練
開放趨勢下,金融風險隱患不斷疊加,風險點不斷增多,最終有可能點連成面,出現金融危機。因此,要通過提高監管水平,防控局部性金融風險的發生。
董登新認為,一方面要嚴查、嚴打金融與證券違法犯罪,這是基礎性工作;另一方面,穩健的貨幣政策也是我國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一環。我國貨幣政策不能大水漫灌,不能讓流動性過于泛濫。“外匯體制改革、資本項目管制的放松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要把握一個度,在經濟和金融的承受范圍內去開放。國際化是一個大方向、大趨勢,要根據監管能力,尤其是央行駕馭貨幣的政策能力,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逐步放松資本管制。隨著調控能力的增強、監管水平的提高,我們可以化解一些金融風險,也可以防范金融危機。”在這方面我國一直走得比較穩健,改革布局堅定有力,尤其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方面,做得比較好。
董登新還表示,一方面,我國金融風險的承受能力正在增強;另一方面,隨著調控水平、監管水平的不斷提升,我國在打擊證券違法犯罪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另外,金融創新方面也把控得當,沒有出現失控局面。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對于金融風險的監測預警,可量化、可視化程度已經非常高。黃震認為,我們還需繼續加大對金融科技創新的投入。監管也需要科技化的能力,“要做到及時預警和發現,現階段重要的一點就是加強科技能力,通過科技手段實現預警。”尹振濤稱。
在做好風險預警方面,陶士貴建議,建立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和預警機制;動態分析人民幣跨境資金的流出與流入的流向和數額,主動進行大數據分析,發現異常情況,及時采取對策,防范國際投資資本的攻擊;加強對我國金融不同行業和領域的動態分析,了解和監測外資機構的異常情況,及時預警和應對;加強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和各地地方政府金融監督管理機構的協調配合,加強信息溝通和機制協調,防止出現監管真空和監管漏洞。
同時,也要加強對風險防控的演練和壓力測試。黃震表示,針對金融機構和監管如何防控風險,我國不妨多做一些演練,適當公開一些風險事件,加強風險處置能力,做到有能力預防風險也有能力應對風險。“另外,要加大歷史研究和國際研究,了解歷史上一些國家在金融風險面前的成功做法和失敗教訓,通過總結歷史經驗來服務我國當前的對外開放和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