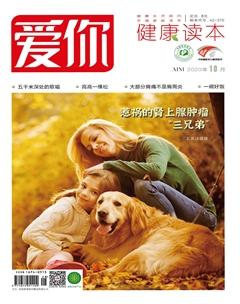界線
半文
我的大學導師后來去了美國搞研究,在佛羅里達有個房子,房子不大,地很大,約三畝。旁邊是一家美國人,也有個不大的房子,也有塊很大的地。兩家房子之間,只有大片的草地,沒有圍墻,也沒有籬笆。導師的老母親過去住,不習慣。
鄰居說英語,不說漢語,不習慣。種大片的草,不種莊稼,不習慣。兩家之間,沒墻沒籬笆沒條界線,不習慣。不說英語,遠遠地看見了,點個頭致個意,不算大問題。除草也不算大問題,美國人推著割草機一圈一圈走下來,兩家之間,一塊地的草高,一塊地的草低,有了一條隱約可見的界線。
導師的老母親也割草,不用割草機,用花刀,把草一棵一棵挖起,敲去粘在根上的泥,再一棵一棵放在太陽下,曬干。反正孩子在上學,導師又飛來飛去講課,她有的是時間。每一棵草,都要斬草除根。斬完草除完根,兩家之間的界線,就更明顯了。不過,老母親還是不習慣。按照她的習慣,兩塊地中間,最好要修一條圍墻,起碼是用竹木編一道籬笆。這樣,鄰居就不會越界,看著就安心。
除完草,她讓導師從國內帶些種子,種幾壟屬于家鄉的蔬菜,青菜、茄子、西紅柿、馬鈴薯。為了界線更明顯,她又在最邊上種瓜,種的是家鄉的甜瓜。又用細竹斜斜地搭個瓜架,瓜蔓順著往上爬,一直爬,爬成一道綠墻。幾乎密不透風。她感覺可以了。這界線,不只隔離了人,還好看,葉綠、藤柔、花黃,滿滿地開了一架黃花,像一道風景。
瓜不懂人意,長著長著,瓜蔓越過界,爬到對面草地上去。她把越界的藤蔓扯回,讓它朝著自家方向爬。過兩天,又有藤蔓過了界。有時去扯瓜藤,看見對面草地的主人,她尷尬地笑笑。對面那人也微笑,好像面對一面鏡子。于是,她更尷尬。人家不在意,可她在意。天漸熱,藤蔓瘋長,她扯了又扯,總扯不完,內心快被這些藤蔓扯瘋了。
過幾日,結了瓜。結了瓜就不能扯藤,容易掉落。即便不落,藤碎了,瓜會變苦。看著自家的甜瓜在別人家的草地上膨脹,成熟,她內心糾結,越了界,這瓜是給別人長了。還讓人嫌棄,誰知道人家喜不喜歡。
有一陣,導師一家去邁阿密度假,一去十余日。老母親到了邁阿密,一邊度假,一邊想著,瓜熟了,會落在鄰家地界,那地的主人會有意見。或者鄰家把越界的瓜摘了,吃了。把不越界的也摘了,吃了。自己也有意見,種這一架甜瓜,沒吃到甜,倒先嘗到許多的苦惱來。
從邁阿密回來,老母親不進家,先去看那一架瓜。過界的瓜果然沒掛在藤上,也沒落在地上,被摘走了,剩下寥寥幾個小瓜和幾朵黃花。不過,長在自己家地界的都在。
她搖搖頭,朝自己的房子走,到門口,突然捂住了嘴:門口堆著一排甜瓜,整整齊齊,像列隊歡迎他們一家人歸來。導師對老母親說,界線不在地上,而是畫在人心里。
梁衍軍? 摘自《揚子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