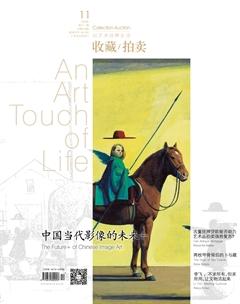張大千的晚年目疾與畫風之變
施之昊



大千先生1976年1月(七十八歲)定居臺北。之前行蹤漂泊,于中國香港、日本、美國、南美諸地生活交友。眾所周知的是,其晚年由于目疾而變法,創造了“潑墨潑彩”的藝術表現方式,驚艷全球。但是具體而論,其目疾發作之確切年齡與病情發展程度卻需進一步證實。
筆者所見的關于大千先生的藝術傳記有三:謝家孝:《張大千的世界》(1982)、李永翹:《張大千全傳》(1998)、黃天才:《張大千的后半生》(2013),其中皆提及大千先生目疾之情況。
目疾后的非議
《張大千的世界》一書為大千先生健在時口述。作者提到,大千先生目疾后惹來非議,實則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由于大千先生素來出手闊綽,“是職業畫家中最不吝惜筆墨,最大方的一位”。但是隨著年紀的增長,加之目疾所累,這樣的饋贈少了。于是就有人認為大千先生的目疾是一種“高明的借口”,作為婉拒索畫之托詞。看了這副眼鏡的照片,這樣的猜測不攻自破,也不得不令人感嘆“人心不古”。
大千先生的目疾肇始于1957年夏,這一年他五十九歲。他在巴西八德園內,布置自己的園林。經常指揮工匠挪移大石,有一次竟親自出力,與工匠一起搬動巨石,導致雙目發黑,種下病根。后經美國、日本以及香港地區名醫診斷,只能治標,難以治本。加之大千先生素有糖尿病史,使得目疾雪上加霜,難以回春。
是年冬,大千先生有詩云“吾今真老矣,腰痛兩眸昏。藥物從人乞,方書強目翻。逕思焚筆硯,長此息丘園。異域甘流落,鄉心未忍言。丁酉十二月,目疾半年后作”。
書中提到大千先生1967年定居臺北后,“一位同鄉謝運璠醫師,為他詳細檢查了視力,分別為他配了各種情況下使用的不同光度、不同距離的四副眼鏡,看書的、作畫的、一公尺以內的、三公尺以外的等四種不同的眼鏡,雖難免換鏡的麻煩,但看起來能清楚,就達到了輔助他視力不足的要求了。”上文提到的一副眼鏡就可能是其中一副。
《張大千全傳》一書是大陸最權威、最翔實的記錄張大千先生生平的著作,采用編年寫法。其中涉及大千先生目疾的內容時提到,大千先生1958年1月于東京作《冬菇圖》,后題“齋房芝良,常山中生,食之,七孔皆光明。予以目疾,于丁酉十一月就醫東京,平生酷嗜冬菇,日人所稱茸者,時上市方盛,鮮美而廉,逐日食之,頗覺雙目漸療,試為此畫,時不拈弄者半年矣,因書冬心(金農)句其上,以記一時樂事”。
又有是年7月,先生在八德園作《松間高士圖》并題“南朝宣紙女兒膚,在北宋時已稱難得。此紙水墨相發,何多讓耶?惜目障未能白描耳”。
1959年5月下旬從巴西飛赴日本,為友人作《仕女圖》并題“大千居士目障二年矣,何由傳神寫照耶?死罪死罪”。
目疾導致晚年的畫風突變
《張大千的后半生》一書作者為大千先生生前好友,臺北“中央日報”社長,長期于日本安排大千先生生活與事業。其中提到大千先生目疾之事如下:
“大千眼疾自五十九歲發病,一直纏擾著他的后半輩子,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右眼完全失明,左眼并需戴配玻璃片極厚的特制眼鏡。”其中提到的眼鏡,應該就是上圖所示的樣子。
大千先生繪畫風格多,表現力強。借助上述三則敘述,我們或可從其目疾上來分析畫風書風之變化。20世紀60年代后大千先生的畫風有一個由細筆向粗筆變化之趨勢,有的山水作品亂頭粗服,不修邊幅,令人難定真贗。大千先生作品會由于目疾而變得粗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目疾會嚴重影響其對色彩的判斷,所以有一階段之作品用色乖張甚至邋遢。發展到后來,其采用潑墨潑彩之技法,設色濃重或用于金箋,使得畫面出現現代感,顏色層次明顯,也是目疾所致。同理,其書風也有從細致向粗率之發展,晚年書風奇絕開張,猛利雄強。結合畫風之特色而相得益彰。
最后,諸君可參考《中國鑒藏家印鑒》(江西美術出版社)一書中的大千用印,或可佐證其目疾之事。
筆者幾年前在臺北張大千故居摩耶精舍,看到那里的落地玻璃窗的中間部位,有一塊特制的玻璃鏡片,講解員介紹這是讓張大千看窗外景色的鏡片,也類似于一種“眼鏡”。此物更加可以佐證目疾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