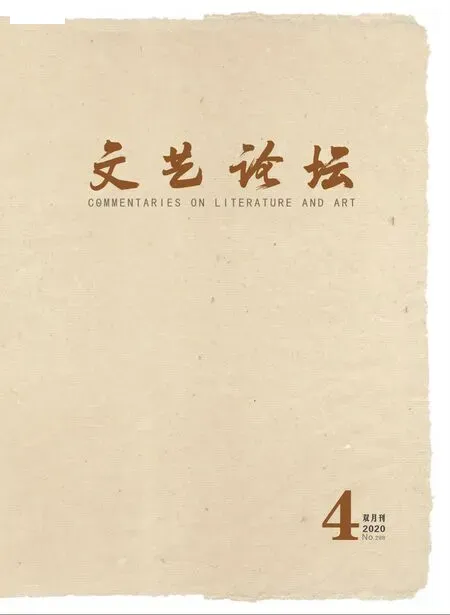“青年寫(xiě)作”的再分化
——從“斷裂”到“后浪”
韓松剛
“青年寫(xiě)作”的問(wèn)題,并不是一個(gè)新話(huà)題。但是,隨著這些年來(lái)文學(xué)界對(duì)“青年寫(xiě)作”的過(guò)度關(guān)注,則似乎真的成了一個(gè)大問(wèn)題。其中,《中華文學(xué)選刊》2019 年針對(duì)117 位當(dāng)代青年作家的問(wèn)卷調(diào)查,以及隨后的“當(dāng)代青年作家問(wèn)卷調(diào)查”筆談;后浪、文景、譯林、理想國(guó)、上海文藝等眾多出版機(jī)構(gòu)對(duì)于青年作家原創(chuàng)文學(xué)的支持;2020 年由中國(guó)作協(xié)青年工作委員會(huì)與《南方文壇》雜志、廣西民族大學(xué)文學(xué)院聯(lián)合主辦的“新時(shí)代青年寫(xiě)作的可能性”研討會(huì),等等,都顯示了“青年寫(xiě)作”在當(dāng)下的熱鬧、重要和迫切。
關(guān)于“青年寫(xiě)作”話(huà)題的源起,我無(wú)意去考證。這是一個(gè)具有進(jìn)化論意味的概念,就像我們可以很輕易地把一個(gè)關(guān)于“80 后”的“青年寫(xiě)作”問(wèn)題,談成了令人瞠目結(jié)舌的“中年危機(jī)”。因此,“青年寫(xiě)作”的問(wèn)題,不僅僅是“寫(xiě)作”的問(wèn)題,還是“青年”的問(wèn)題。關(guān)于這些問(wèn)題,很多文章都談到了,比如何平的《青年的思想、行動(dòng)和寫(xiě)作》、楊慶祥的《21 世紀(jì)青年寫(xiě)作的坐標(biāo)系、歷史覺(jué)醒與內(nèi)在維度》、何同彬的《關(guān)于青年寫(xiě)作“同質(zhì)化”:作為真問(wèn)題的“偽命題”》、李壯的《呼喚常識(shí)中的犄角:青年寫(xiě)作關(guān)鍵詞》、顏煉軍的《“阿多尼斯的死與生”——青年寫(xiě)作芻議》、行超的《探索文學(xué)寫(xiě)作的邊界——當(dāng)下青年創(chuàng)作的幾個(gè)面向》等等,都極具思辨性和啟發(fā)性,他們的深入討論延伸了關(guān)于“青年寫(xiě)作”的思考路徑,同時(shí)引發(fā)了更多的相關(guān)問(wèn)題。
在一個(gè)人人都可以寫(xiě)作,也都可以談?wù)搶?xiě)作的時(shí)代,青年作家和“青年寫(xiě)作”一樣,正在經(jīng)受更為復(fù)雜、更為細(xì)致,也更為嚴(yán)峻的現(xiàn)實(shí)考量和思想檢驗(yàn)。青年作家正在不可阻擋地成為文學(xué)期刊、文學(xué)出版、政府機(jī)構(gòu)、高等院校等眾多部門(mén)爭(zhēng)相搶奪的“人才”砝碼,似乎有得“青年作家”得文學(xué)天下之勢(shì)。而與此同時(shí),青年作家本應(yīng)肩負(fù)的文學(xué)抱負(fù)和藝術(shù)理想?yún)s在無(wú)意和無(wú)形中被忽略、消解,逐漸淪為速朽的消費(fèi)時(shí)代和名利場(chǎng)域中缺少精神附加的衍生品。似乎沒(méi)有哪一個(gè)時(shí)代的青年寫(xiě)作正面臨著如此巨大的分裂和分化。而我打算談的,就是“青年寫(xiě)作”的再分化。
之所以說(shuō)“再分化”,當(dāng)然是針對(duì)在此之前已經(jīng)發(fā)生過(guò)的分化而言。那就是20 世紀(jì)末轟動(dòng)中國(guó)文壇的“突發(fā)”事故——斷裂。“斷裂”事件源起于1998 年的《斷裂:一份問(wèn)卷》,主要發(fā)起人是韓東和朱文,這份列有13 個(gè)問(wèn)題的問(wèn)卷,以朱文的名義發(fā)表在《街道》《文友》和《嶺南文化時(shí)報(bào)》上,《嶺南文化時(shí)報(bào)》還特辟了專(zhuān)欄進(jìn)行討論。問(wèn)卷一經(jīng)發(fā)出,便得到了不少作家的回應(yīng)和文壇的熱議。此后,關(guān)于“斷裂”的討論不絕如縷。之后的1999 年,海天出版社還出版了由韓東主編的“斷裂叢書(shū)”,推出了6 位作家的小說(shuō)集。
今天,當(dāng)我們以奇異而凝重的目光回眸這段歷史時(shí),依然能夠感受到那一代青年作家的現(xiàn)實(shí)處境、精神姿態(tài)和價(jià)值追求。其時(shí),韓東37 歲,魯羊35 歲,朱文31 歲,朱朱29 歲,魏微27 歲,一個(gè)個(gè)青春飛揚(yáng)的面龐,昭示著一個(gè)名副其實(shí)的青年寫(xiě)作群體。他們旗幟鮮明地展現(xiàn)了自己的寫(xiě)作姿態(tài)——斷裂——這是屬于他們的精神宣言。如果我們?cè)侔褧r(shí)間的指針往前撥弄20 年,回到新時(shí)期文學(xué)的發(fā)生現(xiàn)場(chǎng),那可能是更早先一步的“青年寫(xiě)作”分化,傷痕文學(xué)、現(xiàn)代文學(xué)、先鋒小說(shuō)、尋根小說(shuō)、新寫(xiě)實(shí)小說(shuō)等各類(lèi)寫(xiě)作噴涌而出,其中尤以先鋒小說(shuō)與傳統(tǒng)文學(xué)的分化最讓人稱(chēng)贊。只不過(guò),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學(xué)技法,壓抑已久的內(nèi)在激情的快意釋放,并沒(méi)有讓這一時(shí)期“青年寫(xiě)作”在各種文學(xué)思潮的奔涌中,獲得一種強(qiáng)有力的價(jià)值支撐和精神突圍。而這一分化持續(xù)的時(shí)間,不過(guò)是短短的幾年。但毫無(wú)疑問(wèn)的是,這次分化,為1998 年的“斷裂”事件在歷史的脈絡(luò)里埋下了寂寞的種子。相較于新時(shí)期停留在文學(xué)層面上的分化,由“斷裂”開(kāi)啟的分化,更為民間化、精神化,也更徹底。正如韓東所言:“斷裂,不僅是時(shí)間延續(xù)上的,更重要的在于空間,我們必須從現(xiàn)有的文學(xué)秩序上斷裂開(kāi)。”
斷裂,是最為徹底的分化。他們要和腐朽的文學(xué)秩序斷裂,他們要在這一秩序之外創(chuàng)造新的文學(xué)和藝術(shù)。因此,他們有自身文學(xué)觀念的認(rèn)同和不認(rèn)同:“和我們的寫(xiě)作實(shí)踐有比照關(guān)系的是早期的‘今天’‘他們’的民間立場(chǎng),是真實(shí)的王小波,不為人知的胡寬、于小韋,不幸的食指,以及天才的馬原,而絕不是王蒙、劉心武、賈平凹、韓少功、張煒、莫言、王朔、劉震云、余華、舒婷以及所謂的傷痕文學(xué)、尋根文學(xué)和先鋒文學(xué)。”在這種不無(wú)偏激卻不失偏頗的激烈態(tài)度中,隱含的是那一代“青年寫(xiě)作”的理智、激情和理想。“我們的目的在于明確某種重要分野,使之更加清晰和突出,我們反對(duì)抹平以及混淆視聽(tīng),反對(duì)曖昧圓滑的世故態(tài)度。”
讓我們?cè)侔涯抗廪D(zhuǎn)到2020 年。2020 年5 月3 日(“五四”青年節(jié)前一天),嗶哩嗶哩獻(xiàn)給新一代的青年宣言片《后浪》 在央視一套播出,并登陸《新聞聯(lián)播》前的黃金時(shí)段。在此段視頻中,國(guó)家一級(jí)演員何冰登臺(tái)演講,認(rèn)可、贊美并寄語(yǔ)年輕一代。何冰堅(jiān)定而深情的聲音,極具感染力的表演,讓不少青年看得熱淚盈眶。隨后,這段演講在朋友圈刷屏,甚至被網(wǎng)友稱(chēng)之為現(xiàn)代版的“少年中國(guó)說(shuō)”,而“后浪”一詞更是一夜之間成為了年輕人的代名詞。但視頻同樣引發(fā)了爭(zhēng)論,不少網(wǎng)友表示出不認(rèn)可和不贊同。5 月4 日,《后浪》主要的策劃人之一楊亮表示,“這個(gè)片子主要是希望讓看到的人能夠被視頻所傳達(dá)的積極向上的內(nèi)容和精神所鼓舞,通過(guò)這段視頻讓公眾重新認(rèn)識(shí)大多數(shù)年輕人并引起共鳴”。而對(duì)于視頻刷屏所出現(xiàn)的一些不同的理解,他援引了視頻中的一句話(huà)作為解釋?zhuān)骸熬雍投煌贻p人應(yīng)該容得下更多元的審美和觀念。”
與“斷裂”這個(gè)劇烈而有沖擊力的“文學(xué)事件”不同,“后浪”的走紅,更像是一個(gè)群體自我眷戀的“文化事件”。“前浪”主動(dòng)走向“后浪”,開(kāi)始表現(xiàn)出對(duì)年輕一代的關(guān)心和祝福,并主動(dòng)認(rèn)可他們多元的“年輕”價(jià)值觀,似乎值得歡呼雀躍,但我們同樣要反省的是,在巨變的時(shí)代和復(fù)雜的現(xiàn)實(shí)面前,這些所謂的“贊美”和“鼓勵(lì)”是否僅僅就是一碗對(duì)于精神病入膏肓的年輕人無(wú)用的心靈雞湯呢?我們不會(huì)否認(rèn)和拒絕青年人參與一個(gè)時(shí)代公共事務(wù)的重要性,但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一種理性而切實(shí)的反思,尤其必要而可貴。
對(duì)于青年作家來(lái)說(shuō),沒(méi)有反思的寫(xiě)作,就是平庸的寫(xiě)作,沒(méi)有思想的生活,就是頹廢的墮落。我們不會(huì)拒絕生活的幸福,就像我們不會(huì)拒絕正當(dāng)?shù)奈膶W(xué)利益,但我們同樣不能拒絕思想的危機(jī),就像我們不能拒絕文學(xué)的抱負(fù)。當(dāng)下的青年寫(xiě)作,正在名利的喧囂和利益的蠱惑中,走向新的分化。這種分化的面貌是多種多樣的,有作家的分化、文體的分化,以及文學(xué)分化之下的內(nèi)容的分化、風(fēng)格的分化,等等。與上個(gè)世紀(jì)末相比,新時(shí)代的青年作家面臨著不可同日而語(yǔ)的時(shí)代境遇,經(jīng)濟(jì)的飛速發(fā)展,社會(huì)的日新月異,媒介的無(wú)處不在,以及與此相伴隨的生存困境、價(jià)值混亂、精神弱化,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青年作家”。在這種復(fù)雜的現(xiàn)實(shí)氛圍中,青年作家如何自處、如何抉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許多決定本身很多時(shí)候可能無(wú)關(guān)乎文學(xué)。因此,有的青年作家,選擇投入體制的懷抱,在體制的保障和溫暖中,在各種文學(xué)獎(jiǎng)項(xiàng)的簇?fù)硐拢鲋篮玫奈膶W(xué)夢(mèng);有的青年作家,選擇游離于主流的文學(xué)圈,要么在新的媒體空間中揮灑自我、享受新文藝的歡呼,要么在艱難的文學(xué)環(huán)境中,堅(jiān)持標(biāo)榜自由身份,尋覓關(guān)于寫(xiě)作的新曙光。其實(shí)不論是體制內(nèi),還是體制外,身份之外的“寫(xiě)作”所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內(nèi)容”才更能證明一個(gè)青年的價(jià)值觀。對(duì)于大部分青年作家來(lái)說(shuō),他們既不與時(shí)代親密相擁,也不與體制直接對(duì)抗,與各種精神的捆綁保持一種若即若離、貌合神離的姿態(tài),也不介意去做一個(gè)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眼花繚亂的利益驅(qū)使中,青年作家似乎很難拒絕現(xiàn)實(shí)的誘惑,而且很容易在自我安慰中將文學(xué)的精神抱負(fù)偷換成平庸的成敗得失。當(dāng)然,我承認(rèn),青年作家對(duì)體制的態(tài)度會(huì)影響到寫(xiě)作本身,但我也不會(huì)固執(zhí)地認(rèn)為,體制會(huì)最終決定一個(gè)青年作家寫(xiě)作的上限。寫(xiě)作,說(shuō)到底還是關(guān)系才華和能力的事情。
如果說(shuō)“斷裂”是一次精神層面的文學(xué)分化,那么當(dāng)下青年作家的分化,則是一次由技術(shù)、資本、市場(chǎng)和名利等多種因素共同催生的生存分化,這種分化是具體的,也是庸俗的。如果說(shuō)“斷裂”代表了一代作家的寫(xiě)作姿態(tài),是一次帶有創(chuàng)造性、反叛性精神目標(biāo)的文學(xué)實(shí)踐,那么“后浪”作為一個(gè)時(shí)代不可回避的“文化現(xiàn)象”,則呈現(xiàn)了這個(gè)娛樂(lè)時(shí)代光怪陸離的“思想貧瘠”,這個(gè)現(xiàn)象背后是已經(jīng)躺下的中國(guó)當(dāng)代青年的精神。我們應(yīng)該在什么樣的層面上去確立當(dāng)代“青年寫(xiě)作”的未來(lái),這個(gè)問(wèn)題讓人困惑。而以當(dāng)下的文學(xué)態(tài)勢(shì)來(lái)看,殺死“青年寫(xiě)作”的不是時(shí)間的消逝和隨消逝而來(lái)的生命敵意,而有可能是來(lái)自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各個(gè)角落里自以為是的“扶持”和“溺愛(ài)”。“青年寫(xiě)作”的未來(lái),只需要“青年”自己踏出一條路,“扶著走”是不會(huì)有任何前途的。
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寫(xiě)道:“現(xiàn)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zhì),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這未可知的青年精神,其實(shí)是一眼便能看得出來(lái)的,作者只是沒(méi)有直接道出罷了。一百年過(guò)去了,在告別了那個(gè)物質(zhì)貧乏時(shí)代的同時(shí),當(dāng)代青年的精神并沒(méi)有在這個(gè)物質(zhì)豐盈的時(shí)代隨著體魄的健壯而強(qiáng)勁起來(lái),相反,從《斷裂:世紀(jì)末的文學(xué)事故——自由作家訪(fǎng)談錄》,到《野生作家訪(fǎng)談錄:我們?cè)趯?xiě)作現(xiàn)場(chǎng)》 (中信出版集團(tuán)2019 年版,該書(shū)以訪(fǎng)談、人物報(bào)道的形式集中介紹了袁凌、康赫、楊典、朱岳、孫智正、盛文強(qiáng)等14 位非職業(yè)寫(xiě)作者的文學(xué)之路),再到《中華文學(xué)選刊·青年作家問(wèn)卷調(diào)查》,及至嗶哩嗶哩彈幕網(wǎng)帶來(lái)的青年宣言片《后浪》,也就是從60 后、70 后,到80 后、90 后、00 后,我們明顯地感覺(jué)到一種精神的多元分化,以及這多元之下不可遏止的思想衰退。在這個(gè)衰退中,一切都顯得無(wú)能為力。但是,好好地睜眼看世界,不對(duì)復(fù)雜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困境、生命的迷惘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也仍然很重要。
與作家的分化相伴而生的,還有文體的分化。“斷裂”時(shí)代的分化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反抗和獨(dú)立,而“后浪”時(shí)代的寫(xiě)作分化,精神上的“斷裂”已經(jīng)不是十分明顯,一切的寫(xiě)作都被死死焊接在秩序的接口上。這種“分化”主要表現(xiàn)在文體的多元和豐富上。與傳統(tǒng)的詩(shī)歌、小說(shuō)、散文寫(xiě)作不同,這個(gè)時(shí)期的文體在新媒體、市場(chǎng)、資本以及相應(yīng)的消費(fèi)刺激下,顯得琳瑯滿(mǎn)目。科幻文學(xué)、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非虛構(gòu)文學(xué)等類(lèi)型寫(xiě)作,已經(jīng)具備了十分強(qiáng)大的文體力量,徹底改變了在傳統(tǒng)文體的夾縫中艱難生存的尷尬處境。我們可以對(duì)孱弱的“青年作家”表達(dá)不滿(mǎn),但我們要理性而客觀地承認(rèn)他們?cè)谖捏w分化中的文學(xué)實(shí)踐。這確實(shí)是不可忽視,也是十分重要的存在。
文體的分化,意味著表達(dá)路徑和方法的多元,意味著對(duì)于繽紛現(xiàn)實(shí)的接納和融匯,意味著各種寫(xiě)作手法的肆意和可能。這相對(duì)于傳統(tǒng)的寫(xiě)作文體來(lái)說(shuō),無(wú)疑是巨大的豐富和進(jìn)步。文體的變化,體現(xiàn)了“文學(xué)觀”的變化。這個(gè)時(shí)代的文學(xué),已經(jīng)不是傳統(tǒng)文學(xué)的舊有面貌。我們不能四處揮舞著傳統(tǒng)的“文學(xué)”棍棒唯我獨(dú)尊。但同樣不能忽視的是,文體的多元,并不代表著取消和混淆“文學(xué)”的邊界。“文學(xué)”是有限度的,就像伊格爾頓在《文學(xué)事件》一書(shū)中所言:“‘文學(xué)’這個(gè)詞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用法,但這并不等于說(shuō)它的使用方式完全是隨意的。即便是那些持最慷慨的多元論觀點(diǎn)的后現(xiàn)代主義者也不可能把火腿三明治稱(chēng)為文學(xué)。”但是,很多時(shí)候,我們卻漠視或者放任這種“限度”,比如關(guān)于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爭(zhēng)論、比如關(guān)于非虛構(gòu)文學(xué)的非議等,都源于這一“限度”。
文體分化的背后,還涉及各種各樣的操縱,就像生活的背后永遠(yuǎn)有一只看不見(jiàn)的手。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gè)“虛無(wú)的時(shí)代”,但卻已經(jīng)實(shí)實(shí)在在地技術(shù)化和資本化。就像我們必須要承認(rèn),網(wǎng)絡(luò)寫(xiě)作正在通過(guò)市場(chǎng)和資本的運(yùn)轉(zhuǎn),依靠點(diǎn)擊率和瀏覽量,戲謔化地侵占我們最后的精神堡壘,“而這堡壘本可以用來(lái)保存一種道德、一種倫理、一系列超越性?xún)r(jià)值或者保住可以在蒙昧當(dāng)?shù)赖哪甏樟辽鐣?huì)的火種:詩(shī)歌、文學(xué)、藝術(shù)”。
對(duì)于“青年寫(xiě)作”,過(guò)度悲觀和盲目樂(lè)觀都不合時(shí)宜。我們終究要正視那些已然存在且一直存在的問(wèn)題,尤其是在這個(gè)寫(xiě)作趨于容易和簡(jiǎn)單的時(shí)代,一切認(rèn)真的思考都變得越發(fā)艱難和膚淺。“青年寫(xiě)作”似乎正在成為“平庸的寫(xiě)作”的代名詞,他們更樂(lè)于享受秩序的安逸和榮譽(yù)的快感,從而取消了文學(xué)本有的理想和目的。“這是一個(gè)普遍缺乏勇氣的時(shí)代,也許還是一個(gè)不再需要勇氣的時(shí)代。”可是,與“斷裂”時(shí)代相比,這個(gè)時(shí)代的青年寫(xiě)作不僅僅缺少勇氣,還缺少智慧和能力,是不是這是一個(gè)不再需要智慧和能力的“后浪”時(shí)代呢?
“斷裂”時(shí)代的青年作家們,對(duì)既定的寫(xiě)作秩序表現(xiàn)出了滿(mǎn)滿(mǎn)的敵意。“我們不是現(xiàn)存文學(xué)秩序的受益者,而是這個(gè)秩序在利用我們的年輕、才華。它想與我們做交易,只要我們俯首稱(chēng)臣就將給我們以極大的利益補(bǔ)償。的確,我們的寫(xiě)作已經(jīng)到了這樣一個(gè)關(guān)口,整個(gè)文壇正虛席以待,只要你向在座的敬酒致意,便能坐下來(lái)與他們共享名利的盛宴。”當(dāng)下的青年作家們,大部分顯然已經(jīng)闖過(guò)了這個(gè)關(guān)口,參與并制造著一個(gè)時(shí)代的文學(xué)繁榮和精神狂歡,其樂(lè)融融。當(dāng)然,總有一些“落伍者”,被卡在了關(guān)口之外,他們或落寞、或慶幸,但是否會(huì)成為未來(lái)寫(xiě)作的另一道景觀呢?
當(dāng)下的青年寫(xiě)作,有著強(qiáng)烈的個(gè)體意味,也因此呈現(xiàn)出固執(zhí)己見(jiàn)的審美趣味,這都無(wú)可厚非。但是,“為了個(gè)人立場(chǎng)而個(gè)人立場(chǎng)乃是為了提高自我重要性的努力,因?yàn)榫芙^承擔(dān)責(zé)任實(shí)際上是個(gè)人立場(chǎng)的喪失”。作家的成長(zhǎng)需要時(shí)間和空間,但是留給青年作家的時(shí)間和空間確實(shí)不多了,那些虛擬而多維的網(wǎng)絡(luò)世界,并沒(méi)有給文學(xué)留下充足的精神余地。
從“斷裂”時(shí)代到“后浪”時(shí)代,我們一直在目睹“青年寫(xiě)作”的發(fā)生,但“青年寫(xiě)作”“發(fā)聲”的機(jī)會(huì)并不多,即便是有機(jī)會(huì),發(fā)出的聲音也是微弱而無(wú)力的。今天,青年的日常生活與自身的理想寫(xiě)作,正在發(fā)生或者已然發(fā)生真正的“斷裂”,一種難以回應(yīng)自身所處的時(shí)代氛圍、所承擔(dān)的社會(huì)角色以及所面對(duì)的生活難題的“世界性欲望”已經(jīng)幻滅。
寫(xiě)作說(shuō)到底是關(guān)乎“個(gè)人”的事情,但這個(gè)“個(gè)人”已經(jīng)無(wú)法擺脫時(shí)代與社會(huì)的總體性景觀,因此,一切寫(xiě)作包括青年寫(xiě)作,雖然都是從文學(xué)開(kāi)始的,但從來(lái)都不應(yīng)該是一個(gè)純粹的文學(xué)問(wèn)題,而是一個(gè)具有現(xiàn)實(shí)性和歷史性意味的精神命題。“斷裂”之后,精神何為?“后浪”來(lái)了,文學(xué)何為?關(guān)于這個(gè)命題,還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討的話(huà)題,限于篇幅,留待將來(lái)。
注釋?zhuān)?/p>
①②③⑦⑧⑨汪繼芳:《斷裂:世紀(jì)末的文學(xué)事故——自由作家訪(fǎng)談錄》,江蘇文藝出版社2000 年版,第308 頁(yè)、第309 頁(yè)、第315—316 頁(yè)、第333 頁(yè)、第315 頁(yè)、第321 頁(yè)。
④魯迅:《論睜了眼看》,《魯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1 頁(yè)。
⑤[英]特里·伊格爾頓著,陰志科譯:《文學(xué)事件》,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7 年版,第30 頁(yè)。
⑥[墨西哥]奧克塔維奧·帕斯著,趙振江等譯:《批評(píng)的激情》,燕山出版社2015 年版,第385 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