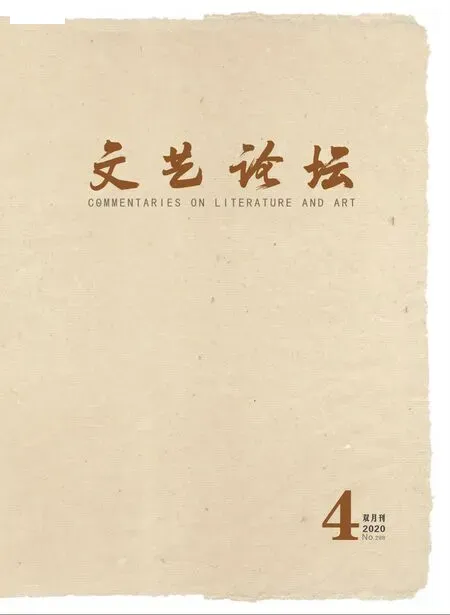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電影《芳華》的空間景觀與身體政治
原雪輝 于莉莉
電影《芳華》以一代人鮮明而獨特的青春記憶在當時刮起了影院內外一股懷舊風,文工團作為影片的第一現場通過導演與觀眾內在的集體記憶以及外在的時空綿延引發了一陣追憶“芳華”的熱潮。文工團的存在、發展與時代條件下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在這個由各個階層的獨立細胞構成的單位組織結合體中,用個體的生命體驗回溯文工團空間的意義建構,并以身體為連結點串聯起了創傷與修復的集體空間實踐。
一、文工團空間與意識形態的再生產
作為軍隊文藝團體,文工團是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時是基層戰士身處艱苦的軍營生活和殘忍的戰場中唯一的色彩,繼承革命宣傳隊的政治和文化傳統,以部隊官兵為服務對象,一切文藝活動都圍繞部隊的文化需求展開,因此其管理機制上有一定的規范。
文工團作為特殊年代誕生的文藝團體在嚴歌苓的劇本和馮小剛的鏡頭下有別于普通大眾對文工團的刻板印象,以一個“時代傳聲筒”的角色呈現了作為軍隊重要組成部分的物理空間和以政治文藝服務為主要內容的文化空間。最初以中國工農紅軍宣傳隊為雛形而誕生的文工團承載了為軍隊服務的使命,它的誕生以及命運流變都與戰爭息息相關。《芳華》中的文工團在那場戰爭中通過文藝演出鼓舞士氣、宣傳意識形態和野外戰地救護成為那個時代記憶里芳華與創傷同在的歷史場域。
馮小剛導演鏡頭下文工團的空間魅力基于自身的記憶回溯與電影空間本質所攜帶的奇妙的景觀特色,他將文工團塑造成了一個富于詩意的動態空間以及在這個空間中一群風華正茂的青春胴體,片中大量文化符號的呈現諸如歌舞排練和表演、大鍋飯、稀缺的零食、軍裝,不只在影片空間中以青春昂揚的激情鼓舞著浴血沙場的戰士,更以云淡風輕的姿態重塑著屏幕前的觀眾的記憶。在進行文藝表演的功能展現時,文工團以極富專業性的藝術精神充當了那個年代青春舞臺、藝術追求的空間形象,以一種獨特的戲劇張力將藝術精神和政治使命結合在戰地舞臺上進行空間實踐,這使得革命理念能夠借助表演性的藝術滲透進每一個人心里。馬克思主義空間哲學理論家列斐伏爾指出:“具象的空間包含著復雜的符號意義,與隱蔽的社會生產相聯系,同時也與藝術相聯系。”空間是一種社會的產物,它受到社會生產和社會關系的影響,在這里文工團作為革命性文藝的空間形象,在充當歌舞戲劇等表演能指的同時,其革命宣傳功能使其將文藝性外核與革命性內核碰撞連接,其獨特的空間張力成為特殊時期政治意識形態的承載和藝術發展的高地。
影片自前期宣傳到上映期間,“銀發一族”被其中所呈現的文藝典范一度喚起了他們的記憶認知和藝術認同,即使作為新時代的年輕人也多數被影片中展現的歌舞典范深深折服。那一代人尤其是專門從事文藝創作和宣傳的文工團成員參與了文藝典范的再生產,他們被召喚為革命的主體,在個體經驗的基礎上一起形塑著那個時代的集體生命體驗。影片將極富時代特征的藝術表演形式進行藝術再造,《草原女民兵》《沂蒙頌》《紅色娘子軍》等歌舞表演貫穿全片,為觀眾營造了浪漫的青春懷舊氛圍,在藝術上力圖呈現文藝兵們自我理想化的追求,同時將革命精神幻化為美妙的肢體動作和音樂,將戲內戲外的革命記憶得到政治升華。文工團建立初期就擔負著為普通老百姓做革命理念宣傳的作用。影片開始在街頭刷寫革命標語的視覺鏡頭,畫外音蕭穗子對劉峰的介紹也以歌頌默默無聞的英雄這種革命奉獻精神為引領,進而為我們引出了影片的第一現場——文工團,在影片中文工團與前線部隊一起擔負著革命斗爭的作用,不僅在戰場上以革命文藝的表演形式,更在文工團大院內部以斗爭的方式宣揚革命精神。法蘭克福學派提到的“工具化”理論指出:“活動的價值對它來說是內在的,同時對另一目的或價值的定性區分與人類工作或游戲的其他形式相聯系。”文工團承載了政治宣傳和革命鼓勵的內在價值,通過革命舞曲等形式將宣傳和鼓舞的目的與軍隊戰士們的革命精神和戰斗士氣相聯系,在當時物質匱乏和技術落后的條件下,文工團成為提升軍隊戰斗力的重要一環,作為意識形態輸出與再生產的重要工具,文工團起到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作用。阿爾都塞指出,“一種意識形態總是存在于一種機器及其實踐或常規之中,這種存在即是一種常規的存在”,阿爾都塞在這里強調了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物質的存在,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來傳達統治階級的意志。文工團作為一種空間場所不僅具有了物質存在的特性,更作為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傳達主流階層的思想,成為軍隊和文藝兵們精神力量的象征和塑造者。
文工團所承載的雙重價值產生了包括馮小剛在內的所有那個特殊的歷史場域中的人記憶中美好而荒誕的生存圖景。社會由自身邏輯和必然性形成的空間所組成,這和自然空間與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密切相關,這些空間形構了不同的“場域”,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指出:個體“就被拋入這個空間之中,如同力量場中的粒子,他們的軌跡將由‘場’的力量和他們自身的慣性來決定”。在當時崇尚集體主義,摒棄甚至消除個人主體性的時代環境中,文工團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場域,或者說一個由國家意識形態所建構的“組織”單位,在進行意識形態宣傳過程中無形地消解了作為個體的理想。這個革命的文化場域集結了像郝淑雯和陳燦一樣具有等級優越感的革命后代、從上海優越家庭來的大小姐林丁丁以及擁有各種能歌善舞且成分清白的青年男女,而出身平凡但自身被動處于超我境界的劉峰以及家庭出身悲慘的何小萍在這個“組織”里就成為了集體意識形態斗爭的對象。在文工團內部這個顯性空間中,不同個體之間因青春年少以及胴體的吸引編織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在集體主義的氛圍中他們為了共同的目標進行著文藝性的空間實踐。但在文工團之外,個體與其家庭緊密相連,在社會這一外部空間,個體所代表的家庭形成了不同環境、不同階級的隱性的家庭空間,而從破碎再生又被驅逐的家庭中邁入人生希望。文工團的何小萍依然難以融入這個由等級秩序組成的“大家庭”,因而在顯性空間和隱性空間的轉移中與社會相勾連,并在個體命運的流轉中建構社會變動給人們帶來的創傷性記憶。
二、作為烏托邦的文工團解體
編劇嚴歌苓在對文工團的描述中與馮小剛一道將個人經歷與時代相結合,依附于時代對他們記憶中的集體即文工團進行了一個從認同到懷疑最終走向逃離的過程。在空間功能上,受意識形態的規訓,文工團承擔著政治宣傳的作用,是紅色文藝綻放的舞臺,隨著戰爭結束和革命形式的轉變,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傳播者的角色自然也會被功能性消解。
《芳華》是一段被意識形態定型書寫的歷史,作為隱喻性象征的意識形態被消解在影像結構的裂縫之下,憑借馮小剛和嚴歌苓的創傷性集體記憶為觀眾展示了一個烏托邦的綻放時代的影像空間。在中國影視文化研究的語境之下,以意識形態作為“元話語”來探討存在于影像空間中的獨特內涵和敘述方式。中國歷史發展的時代環境使不同的階層群體形成了一種認知社會的機制,在對意識形態進行界定的過程中,借鑒特里·伊格爾頓的概念:“社會生活中觀念、信仰、價值的普遍的物質生產過程”和“特定階級或集團的生存狀況和體驗。”伊格爾頓將意識形態跳脫于單純的個體經驗而將其放置于社會層面上來理解,這能夠很好地幫助我們來理解意識形態屬性下影片中不同個體在文工團這個小社會空間里的命運走向以及對集體主義的反叛。阿爾都塞指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以‘意識形態方式’發揮其功能作用。”文工團在這里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勢必擔負著彰顯國家意志,尤其是時代精神和革命精神的作用,它將樸素的生活觀念和舍己為人的價值觀集中體現在劉峰這個人物符號上,劉峰被置于道德的最高點甚至信仰的高地,超脫于普世價值觀的神壇地位,在文工團這一特定空間中嚴格按照政治和軍事紀律來層層管理,個人的生命欲望體驗被裹挾在了不可見之處。由于意識形態和生產關系密切相關,不同時代下的生產關系要求通過國家機器的權力作用來保證,阿爾都塞認為:“勞動力再生產不僅要求一種勞動力技能的再生產,同時,也要求一種對現存秩序的規則以人身屈從的再生產,即工人們對統治意識形態的歸順心理的再生產,以及一種剝削和壓迫的代理人們恰如其分地操縱統治意識形態的能力的再生產。”文工團作為軍隊文藝生產和意識形態的傳聲筒,在積年累月地進行文藝生產活動的同時,嚴格地按照軍隊秩序進行空間實踐并接受意識形態的規訓。在國家意識形態規訓機制之下,文工團符合一種規訓藝術的“嚴格紀律”,在文工團空間里起規訓權力最主要的功能是“訓練”,這也是影片開始直至影片結束馮小剛芳華記憶中最耀眼燦爛的空間景觀呈現,“訓練”是獨屬于文工團空間的規訓功能,區別于規訓前的挑選和戰地表演的征用,在這里是為了更好的挑選和征用而在規訓機制下嚴格的對操練對象的訓練。通過意識形態的規訓和技術訓練,文工團將散布在各個階層各個環境中的盲目的肉體和獨立細胞有秩序地排列組合成一個組織結合體,“訓練”造就個人,同時又泯滅個人,作為一種把獨特個體既視作操練對象又視作操練工具的權力的技術,謙恭而多疑的形成了一種令這些獨立細胞相互凝結又集體排斥的持久的運作機制。而被推上神壇的劉峰和受尊崇意識形態的規訓卻又被排斥在外的何小萍被無上推崇的集體主義拋擲在了時代禁忌的位置,無法與時代和這些規訓權力合謀。“觸摸事件”中劉峰被嚴刑逼問,這種審訊方式并不是為了獲取真相,也不經過嚴刑拷打,而是在被規定的程序內以不被認可的受害者的身份在受制約的形勢下被迫公認罪行的合法運作。受意識形態規訓的文工團是通過何種方式來體現其權力的?與文工團的功能性質類似,表演是一種儀式,一種宣揚意識形態的儀式,通過嚴格的規定形式實現政治儀式的作用,具體表現在影片中幾組大事件發生之后文工團按規定停演或修改演出節目。在意識形態的規訓之下,集體成為不自覺的執行者甚至是恐懼者,造就了集體惡的空間景觀:“觸摸事件”中林丁丁將劉峰的愛意表達認為是對神圣的褻瀆和辜負,以及集體對“犯錯”的“雷又鋒”的冷漠態度和對何小萍的排斥,何小萍像一個“囚禁者”被窺視,“胸罩事件”令獨自在舞蹈房練功的她被放置于中心瞭望塔(在這里指文藝兵們居住的紅樓宿舍)的窺視之下,與其說那些好奇海綿胸罩歸屬于誰的文藝兵們在樓上窺視著泳池旁飄搖在風雨中的“臟物”,毋寧說是在窺視著已被集體定性的“撒謊精”并等待她將其“臟物”拿走后“人贓并獲”,但終究還是被代表意識形態的、試圖替天行道的偽道義者呵斥和規訓。
嚴歌苓筆下的文工團“紅樓”前身是軍閥姨太太們居住的空間,是一座外表破敗遺存著舊社會痕跡的老式宅院,但在嚴歌苓與讀者的心里是有著獨特價值記憶的“神圣空間”。與此相類似,馮小剛鏡頭下的文工團也是一處超脫世外的“烏托邦”,但在這里“烏托邦”的概念與當時的社會革命相聯系被賦予了階級色彩。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爾庫塞對烏托邦思想的態度用來理解文工團在這里的烏托邦色彩再好不過,“馬爾庫塞非常贊賞超越既存社會的‘烏托邦精神’,試圖用‘烏托邦(的)’來修飾那些被既存社會擋住去路的沖動(impulse)、熱望(aspiration)和幻想(fantasy)”。馬爾庫塞的烏托邦思想,不同于空想社會主義中對烏托邦“無此地方”的解釋,而是集一切美好愿景的可能實現的地方,類似于福柯提出的“異托邦”思想,但在《芳華》這部影片中一切超越既存現實的熱切和幻想的青春記憶被馮小剛濃縮在了文工團空間里,我們無法確知那個時代文工團真正的模樣,但他給我們呈現了一個布洛赫意義的“烏托邦的”文工團,一種普遍存在于一代人記憶中的精神現象,在布洛赫這里,“烏托邦的”通常和精神意識相勾連,指代對美好的期盼,或許正是深刻的傷痕記憶令嚴歌苓和馮小剛更傾向于為觀眾展現一個充滿熱望和沖動的文工團,尤其在時代文化、服裝樣式、歌舞表演的展現中用極富浪漫化的詩意表現手法天真地映現出那個令我們無限遐想的烏托邦空間,某種程度上,影片中文工團空間與創作者和“銀發一族”的關系是一種“人與實際生存狀況之間的想象性關系”。文工團在革命和戰爭中烏托邦的象征地位,與劉峰的神性地位,在超我中偏離了人性和自由的正常軌道,在時代癥候形成的集體無意識傷害中我們瞥見了劉峰在自我觀照中對人的本能欲望和像正常青年戀愛的渴望。在這種渴望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對社會情感結構和社會關系以及其生產關系的獨特理解,帶有意識形態的性質。劉峰命運的大起大落受惠于意識形態的規訓卻又損毀于階級斗爭的漩渦,在對文化霸權的反抗中重塑著意識形態的烏托邦想象。
作為時代傳聲筒和意識形態宣傳工具的文工團在時代的裹挾中與戰爭一起走向了形式的消亡和精神的永恒,對全知視角的蕭穗子和諸多情感代入的觀眾來講,文工團的解散無異于烏托邦的消逝。至于空間裂隙產生的原因,首先基于劉峰與何小萍對等級化的懷疑,充當“活雷鋒”的劉峰在這個由不同家庭背景和階級人群構成的組織群體內憑借一切符合英雄主義的特質獲得了從上至下的尊崇和愛戴,“以名譽、光榮和愛國主義作為號召,最有可能影響到組成群體的個人,而且經常可以達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這就是為人所稱道的雷又鋒,抗洪救災、舍己為人的英雄品質,在那個弘揚集體主義和犧牲精神的時代,價值評判標準不允許任何異質形態的存在,被推上神壇的英雄一旦回歸自身便違背了價值標準而被打入萬劫不復的境地,這是因為他并沒有因為所有的英雄事跡而成為等級秩序的接班人。而像郝淑雯從出生就處在社會固化的等級秩序高處的人。其自身優越感是劉峰與何小萍無法企及的。何小萍的自我救贖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被徹底擊潰,“軍裝事件”是社會身份轉換的一次表演,在一種“當解放軍就沒人欺負了吧”的權力話語中,多次被欺辱的自身經歷尤其是被拋下神壇的最善良的劉峰的悲慘遭遇讓她重新回到自身,不再渴望集體認同,甚至起身反抗以示對等級化的懷疑和集體主義的背棄。然而影片在文工團解散之際的告別酒宴,以極富感染力的表現形式復現深厚的戰友情誼,用酒精麻痹和集體合唱來彌合存在于文工團的階級差異和人際沖突,只是這樣的場景缺失了劉峰與何小萍,一種想象性的階級彌合與不舍情誼更具諷刺的悲情意味。在內部情感的裂隙之外,外部環境是造成文工團解散的客觀直接性原因。戰爭結束之后,擔當革命精神文藝宣傳工作的文工團影響力勢弱,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工團的表演形式和政治形態脫離了大眾的審美趣味,從牛仔褲和鄧麗君歌曲的傳入可見一斑,政治功能的消退以及新興事物的沖擊令文工團不再具備存在的意義,在軍隊和國家政策的調整下文工團勢必要隨著它為之服務的戰地一起消失在時代的洪流中。當現代文化思潮和社會改革的步調加快,每個人都在為自己謀出路,即使不被政策解散,文工團的分崩離析已是必然。
三、身體作為文工團內外空間的“連結點”
源于嚴歌苓創傷性記憶的文本寫作在與馮小剛視覺化合謀過程中通過時代形塑了個體的生命體驗,而這些集體記憶與生命體驗嵌入了社會空間的影響。福柯強調:“身體是來源的處所,歷史時間紛紛展示在身體上,它們的沖突和對抗都銘寫在身體上,可以在身體上面發現過去事件的烙印。”《芳華》用身體話語再現青春懷舊的同時將身體作為重要的連結點串聯起了文工團的內部與外部空間網絡,以浪漫化的語法揭示了創傷與修復的政治空間實踐。
文工團作為特殊年代意識形態傳聲筒的集體空間存在,其形成和運作不單是政治文藝要求,還包括不同個體之間的微妙關系,由于身份背景和階級的差異,文工團里不同個體的關系不是有序的平均分配,相反,是一種無序的牽制,文工團的目的在于塑造集體的形象,因此作為集體異質性存在的劉峰與何小萍在這種無序的牽制中成為時代斗爭精神的犧牲品。“人之所以為人,就是他有著令人憎恨也令人熱愛,令人發笑也令人悲憐的人性。并且人性的不可預期,不可靠,以及它的變幻無窮,不乏罪惡,葷腥肉欲,正是人性魅力之所在。”在這里,身體美學體現了人道主義的身體關切,文工團的“活雷鋒”劉峰因著由人性散發的良善被冠之以集體英雄主義的地位,從集體主義視角對劉峰的肯定將劉峰推上無欲的神壇,在被林丁丁的個體否定之后,一度光芒萬丈眾星捧月的豐碑又被集體主義摔得粉碎,劉峰與文工團除何小萍以外的戰友們之間相對平衡的關系見諸于他拋開人性之外的道德牽制,而劉峰與眾人再次回歸到相對平衡的無序牽制關系當中時,是他被聯防辦的土匪行徑欺辱之時郝淑雯的出手相助,如果說劉峰被處分之時文藝兵友們的冷漠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無視,那郝淑雯這時的相助則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憐憫,一種對“同一陣營”戰友被外人欺辱的反抗。也正是這種無序牽制關系的不穩定性,讓劉峰在“觸摸事件”之后甘愿奔赴戰場試圖完成自我救贖,曾經作為罪魁禍首的手臂在戰場中被炸穿動脈,以舍身取義的姿態即使放棄生命也要完成英雄的使命,以手臂或者說劉峰身體作為連結點將空間從文工團轉向戰場完成了空間轉換的藝術和歷史邏輯,又通過假肢在一場階級欺辱事件中將空間轉向開放后的現代空間。
影片浪漫化的視覺展演通過女文藝兵們美好的胴體來展現。馮小剛鏡頭下的文工團處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卻有一種超然性,不僅表現在影片的拍攝手法,更在于馮小剛以一種凝視的目光對女文藝兵胴體的完美呈現,然而這又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文工團像童話城堡一般鑲嵌在冷酷的時代現實中。她們的青春胴體與文工團一樣充當了功能性的身體表演,并通過各種身體訓練來提高個體的身體意識,與時代精神和文藝表演形式一起遮蔽了作為其本體的獨立意義,階級意識形態借助于身體的自然性,從身體到外部服裝再到身份等級,刻畫著不同身體的生命體驗。當身體遭遇指責與嘲笑時,舒斯特曼的身體美學觀指導我們要尊重身體在生命中的本質地位。何小萍因體臭初入文工團便被郝淑雯嫌棄,軍裝事件以及之后的“托舉”事件和“胸罩”事件在不同身份階層的自我認知中完成了社會身份的展演,這不僅是文工團這個小集體空間的關系矛盾,更延伸了社會空間的等級沖突,在身體與環境的互動關系中,身體美學的社會作用發生異化,劉峰與何小萍始終都沒有完成身份的轉換,由林丁丁、郝淑雯、陳燦和政委等人組成的隱形金字塔空間始終都無法容納劉峰與何小萍的介入,正是這樣的身份裂隙造成的空間裂隙,使劉峰殘缺的身體與何小萍異態的身體具有了空間指向性且遠超于其身體本身的意義,而劉峰與何小萍身體的流放成為不健康社會身體的隱喻。
“身體是事件被銘寫的表面,是自我被拆解的處所,是一個永遠在風化瓦解的器具。”不同的時代背景下身體被意識形態規訓,但身體的自然天性卻又總能進行逾越,呈現在身體上的一種抗爭形式就成為一種特殊的身體政治景觀。作為典型的空間實踐,表演式抗爭存在于底層群體的抗爭譜系之上,意識形態下人道的眷顧讓失去權利的犧牲人的命運轉折跌宕,“你永遠不知道它投下的是炸彈還是食物包裹”。在文工團和戰地醫院見過了太多的殘酷、遭遇了太多冰冷對待的何小萍,在救死扶傷之后成了英雄,突然的殊榮卻讓她變得精神失常,而被眾人奉為道德模范的劉峰獲得的太多的榮譽與獎章在被下放的那一刻也只不過是一堆印著榮光的廢品,而他卻想要在尸橫遍野的戰場借生命實現自己的價值,通過犧牲身體來洗刷“恥辱”。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何小萍的兩段獨舞:被減掉的高原獨舞與重點呈現的草地獨舞,何小萍獨自刻苦地練習舞蹈,試圖通過身體資本的提升實現自我價值并獲得集體尊重甚至身份轉變,這種自我保護終究沒有得償所愿。高原獨舞雖然被剪掉了,但何小萍裝病卻是她的身體表演式抗爭的首次出場,在這過程中伴隨著特定的空間實踐,尤其是在惡劣條件下戰地慰問演出的一種身體政治實踐,何小萍的個體權力訴求失敗,但這一身體抗爭形式卻表達了一種人性的智慧。何小萍的草地獨舞作為一種身體實踐,讓過去的事件以持久性身體記憶的方式沉淀在她的身體里,當她起舞的瞬間,影片將此刻的舞臺空間與文工團空間尤其是托舉事件中的練功房和高原舞臺空間相連結,這不僅是對自我記憶的激活,更是在無意識中對創傷性記憶的修復和消解。
文工團的經歷對馮小剛一代人的意義非凡,與嚴歌苓的一拍即合不僅是對集體記憶的追認,也是對時代空間的重新認知和反思。在這個富于詩意的動態空間里,我們看到了意識形態傳聲筒的獨特效用以及革命精神的有效傳承,同樣也看到了集體主義對個體戕害的貶斥,而作為異質個體的身體實踐,拋開了不穩定的無序牽制關系,在連結不同空間關系的過程中不僅實現了自我的救贖,更完成了創傷性集體記憶的消解和對空間記憶的縫合。
注釋:
①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London:Blackwell Ltd,1991.
②[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王逢振譯:《快感:文化與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238 頁。
③⑥⑦⑨[法]阿爾都塞著,李迅譯:《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當代電影》1987 年第3 期。
④[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著,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年版,第15頁。
⑤Terry Eagleton,Ideology: an introduction,London:Verso 1991,p28-30.
⑧鄧光輝:《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當代影視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13頁。
⑩[法]古斯塔夫·勒龐著,馮克利譯:《烏合之眾》,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年版,第39 頁。
?汪民安:《身體的文化政治學》,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4 頁。
?嚴歌苓:《芳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55 頁。
?Michel Foucault,Language,Counter Memory,Practice,Bouchard,1981,P148.
?[斯洛文尼亞]齊澤克著,邱瑾譯:《我們卷入戰爭了嗎?我們有敵人嗎?》,《生產》第一輯第7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