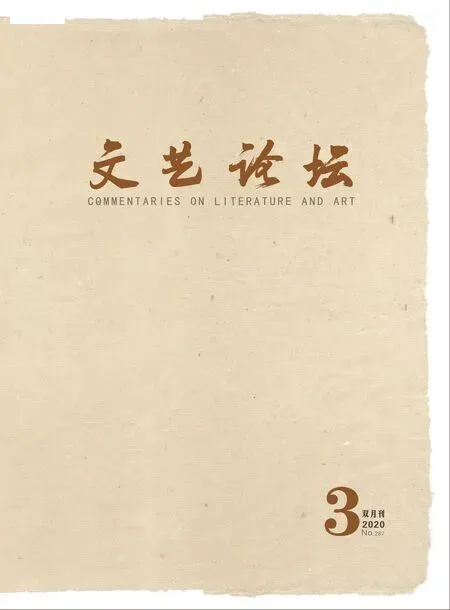一種歷史理性精神的建構
——評馮驥才《單筒望遠鏡》
◎ 房 偉
馮驥才的長篇歷史小說《單筒望遠鏡》(人民文學出版社),一經發表出版,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1977 年,馮驥才就曾創作出版了長篇小說《義和拳》。多年來,馮驥才對晚清津門歷史、義和團運動,一直保持著關注。馮驥才之后創作的《神鞭》《三寸金蓮》 等歷史小說,可以歸為“市井歷史傳奇”小說,既有著尋根文學的影響,也與1980 年代世俗日常敘事凸顯有著內在聯系。1990 年代之后,馮驥才轉向民俗學研究領域,但文學一直是他關注的藝術門類。這部《單筒望遠鏡》無疑是馮先生不忘初心,多年來對津門歷史獨特思考的結晶,也是多年來藝術沉淀之后的一次爆發。與此同時,這部歷史小說,也對當下歷史小說創作,起到積極指導作用。
歷史與文學的關系非常復雜,好的歷史文學應該是歷史理性與歷史想像力的融合與再造。亞里士多德說,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文學則是可能發生的事,就鮮明地點出文學對想象力、情感判斷的追求。中國傳統之中,文學與歷史的糾葛更復雜。《史記》 被稱為“無韻之離騷”。很多文人的創作,也都以能入史為極大榮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卻偏不取文人,認為“文學對資治無益”。金圣嘆也曾說,歷史乃以文運事,文學則為因文生事。文采對于歷史而言,不過是幫助其更好敘述的工具,而對文學而言,想像力與情感的因素,則是文學的根本,事件不過由此而生已,真假莫辯。佛學思想的引入,更讓中國的古典小說,甚少追求理性的真實,而更多注重相對論、循環論性的非理性史觀。因此,中國古代歷史小說,有傳奇和演義兩類,說到底,還是虛構大于真實,追求“好玩的歷史”。讓人擔憂的是,意識形態的權威性,又迫使歷史與道德結盟,遮蔽了人本身的豐富性與復雜性。這種道德化的意識形態企圖共存的,還有借助民族國家敘事,將歷史“鐵血化”的傾向。這種做法,始于晚清小說,大盛于網絡小說之中。
進入新時期,歷史小說也有一個大爆發期,《少年天子》 《皖南事變》 《白門柳》 《曾國藩》等一系列優秀作品,都在追求歷史真實性與歷史理性上有了長足進步。但這種傾向,因為新歷史主義的出現,遭到了顛覆。不可否認,新歷史主義在破除意識形態偏見,追求人性解放之中的意義不可忽視,但它的重要缺陷在于,它毀掉和顛覆的,不僅是階級對抗的說教灌輸,而且是中國人來之不易的歷史理性意識。在它的狂歡化的敘述背后,其實又回到了中國古代“傳奇”傳統。這種情況,因為消費時代介入,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在對新歷史主義的贊揚聲中,不是沒有清醒的反思,但都被一概指責為“階級化的僵化歷史思維”,跟不上后現代歷史潮流。而某些海外華人作家,也深受后殖民思維的影響,刻意迎合西方視角,重新打量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的近現代史,這無疑造成了中國歷史在文學書寫中的變形扭曲,乃至主體性的喪失,淪為西方后殖民化的奇觀想象。
如果分析中國當下歷史文學創作,我們會發現,一方面過于嚴肅,一方面過于輕佻,兩種做派導致歷史敘事,欠缺理性的歷史精神,也缺乏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真正的愛國精神。我們太想在歷史中包裹意識形態企圖,從而導致概念壓倒了性格,意識壓倒了存在。歷史對人類的作用,除了教化裨益,也許還在于它給我們展現出不同生存形態、行為動機和文明發展的可能性。同時,我們的歷史敘事,還有“戲說”的臉譜化做法,這些都與我們對歷史的道德主義態度有關。
由此而言,《單筒望遠鏡》則是中國歷史小說對新時期以來歷史小說的反思和發展。首先,馮驥才對于歷史真實的關注,有一種理性精神的積極意義。格蘭特將所謂真實分為“應合的真實”與“內聚的真實”,所謂“應合的真實”,以逼真與精確表達現實,追求客觀真實,是對現實的有效捕獲;“內聚的真實”,則以心靈的主體真實為基準,是對現實的某種釋放。我們曾經有過左拉式的寫實主義,我們也有過以幻象與想象激活現實的“魔幻現實主義”、強調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們對現實主義的訴求,往往在這兩種美學傾向之間搖擺。真正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應兼具這兩種特點。我們以此考察馮驥才的《單筒望遠鏡》就會發現,他對歷史的觀照和書寫,既不同于傳統的現實主義筆法,也與新歷史主義和先鋒寫作大異其趣。這部小說甚至與他早期的《神鞭》等“津門歷史傳奇”系列作品也有很大變化。馮驥才注重歷史的真實語境,同時也強調了創作主體的重要性,和歷史小說創作的當下意義:“當代人寫歷史小說,無非是先還原一個歷史軀殼,再裝進昔時真實的血肉,現在的視角,以及寫作人的靈魂。”可以說,他將歷史的客觀真實與歷史的“心靈真實”,進行了有效的融合。我們既對當時的歷史氛圍情境有了很深的了解,也能通過歐陽覺的悲歡離合,更好地反思我們當下的歷史意識,更好地樹立理性的愛國主義觀念和多種文明交流發展的文化觀。
其次,正是由于對歷史真實的關注,《單筒望遠鏡》之中,我們隨處可見,馮驥才先生的民俗學研究,對他的小說創作的影響。這也是這部小說的獨特之處。這讓他的歷史小說,比一般的小說家,多了一層學術功力,也多了一層“細部真實”的爐火純青的歷史還原的功力。而這種以民俗學介入歷史敘事,高度還原歷史真實的思維方式,我們可以在現代文學之中李劼人的《死水微瀾》 《大波》等作品中看到其風采。1990 年代以來,在新歷史主義小說的沖擊之下,這種歷史寫作方法,在文壇變得甚為沉寂。而馮驥才的《單筒望遠鏡》無疑為中國的歷史小說,恢復歷史理性思維,提供了很好的借鑒。這本《單筒望遠鏡》,無疑是一張晚清津門庚子事變的“工筆畫卷”,為我們原生態地復活了那場慘烈的歷史事件。晚清天津人日常生活的逼真再現,過節的講究,建筑的特點,衣食住行的風俗,紙店的種種生意門道,紙張類型特點,大到義和團的典章制度,后勤軍需,服裝設置,切口慣用語,真假團民軼事,八國聯軍的裝備,人員組成等等事宜。馮驥才將這種種歷史的細節,全都細細密密地縫織入了津門紙店二少爺歐陽覺的愛情悲劇之中,雖然線頭很多,但不蔓不枝,全都緊湊地依附于歐陽覺的視角之下,讀來清晰準確,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歷史敘事的情節有效性,同時又有著強大的歷史還原感。這種對于晚清津門歷史的民俗學式的還原,不僅有利于增強小說的敘事魅力,也有利于讓我們深入地理解,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晚清津門”,在中國近現代上獨特的歷史意義,進而更好地思考中國的近現代發展史。
再次,這部小說充滿了象征與隱喻意味。正是這種象征性的存在,讓這部歷史小說,變成了對歷史精神與歷史心靈的把握。“單筒望遠鏡”的意義,有批評家指出,世界是單向的,文化是被放大的,現實似乎遙不可及。這里提出了一個文化交流的“焦慮”問題。我們總在被放大的現實之中,無所適從。然而,在我看來,這架單筒望遠鏡,既是歐陽覺與莎娜的愛情悲歡的見證,也是一種“文化主體距離”的象征。距離產生美,也產生隔閡與沖突。關鍵是如何看待與處理這種距離。同時,“單筒望遠鏡”既是不同文明交流之間距離的隱喻,也更像是真實逼近歷史的“理性精神”的象征。在這架望遠鏡之中,一切發生的殘酷的歷史事件,都被馮驥才忠實地記錄下來。而那棵“大槐樹”,則既象征著中國傳統的家庭文化,也象征著以“家國”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明。有“大槐樹”的“材”,歐陽家才能聚財發家,才能協調團結家庭。而大槐樹更象征著傳統文明賦予晚清中國的文化根底。大槐樹的毀滅,是歷史的悲劇,更孕育著歷史重新出發,重塑中華現代文明的契機。
最后,馮驥才對“文明沖突”的思考,有著積極的建設意義。該小說積極探索了東西方兩種不同文明碰撞產生的融合、罪行、抵抗和想象。馮驥才對“歷史之惡”抱有清醒的認識。文明的碰撞之中,“歷史之惡”在主體與客體之間是雙向的。愛德華·吉本曾言,人類的歷史,乃是由血、火、眼淚與人類的愚蠢寫成。歐陽覺與莎娜的愛情,起于不同文明的相互吸引,最終了結于文明的隔閡與沖突。歐陽覺對莎娜的藍眼睛和白皮膚著迷,而莎娜則喜歡這位二少爺的東方式的優雅。盡管倆人語言不通,但這并不妨礙愛情的火焰熊熊燃燒。那張寫有“明天”的紙片,仿佛是一個巨大符號,充滿了血淚的質問。這既是對那些以歷史的名義,殘忍地剝奪個體的生命和財產,踐踏他人尊嚴的所謂“歷史主體”的質問,也是對人類歷史本身的強有力的反思。歐陽覺的家人死于那些以“懲罰暴支”為口號的八國聯軍,莎娜也被以“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虐待至死。莎娜的父親,到死時手中還拿著那只單筒望遠鏡。人性深處的黑暗,仿佛是潘多拉的盒子,在人類面對戰爭的威脅時,人類的貪婪和暴行,在戰爭行為之中,被無情地釋放出來,而在大歷史的“惡”之中,其實不分種族、國家和文明。
對于歷史之惡,馮驥才更注重反思精神。馮驥才在前言中說:“中國人眼中的西方人,不是西方人眼中的西方人,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人,也不是中國人眼中的中國人。”我們的歷史小說創作,有很多借助西方視角看待中國歷史的文本,也有也不少純粹從中國人視角出發,丑化西方人,漫畫化西方人的文本,而真正表現中國與西方兩個文明之間相互了解、交流的文本,能同時尊重“他者”與“自我”的歷史小說文本,則非常匱乏。這無疑需要柯林伍德所說的“歷史反思”精神:“歷史哲學關懷的并非思想本身,而是思想對客體的關系,它既關懷著客體,又關懷著思想。”小說批判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入侵,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義和團運動的愚昧無知和殘忍。2019 年,歐洲爆發了好幾起恐怖襲擊。那些投擲向穆斯林的炸彈,讓人觸目驚心。犯罪分子甚至以新十字軍東征的“白人基督教衛道士”的身份自詡。這一切似乎重新在驗證著亨廷頓有關“文明沖突”的論斷,也在一個多元與全球化的時代提醒我們,種族、文明之間的沖突,也許并非像我們想的那么樂觀,因此,這也更需要我們反思歷史,在寬容、理性與人性化的基礎上,追求不同文明之間的理解,讓歐陽覺和莎娜的悲劇不再重現。
但是,馮驥才既沒有刻意書寫后殖民視角下的東方奇觀,也沒有以戲謔的歷史狂歡,以價值的消解歸于歷史的虛無,而依然在文明的沖突與人性的沖突之中,堅持了“正義”的倫理原則和人性的救贖。這無疑是這本小說更深刻的價值意義和敘事魅力之所在。小說結尾,寫到歐陽覺向著侵略者勇敢地沖去,“他繼續向前走著,在對面的喝令中,又一片密集的子彈呼嘯而來。”雖然,這只是無望的自殺式報復,但馮驥才無疑也為小說抹上了一筆亮色,即所有的文明融合與交流,必須建立在平等自愿與互存共榮的基礎上,而無論侵略者如何美化自己的行為,都不能改變侵略的非正義本質。這種歷史的道德態度,讓馮驥才對歷史復雜性的探索,并沒有陷入虛無主義的陷阱。
歷史學家卡爾說:“不能因為一座山橫看成嶺側成峰。就說該山實際上根本無外形可言,或者說,它有無窮的外形。”這無疑提醒我們,歷史文學的探索,不能脫離歷史的相對真實。中國歷史文學如果要發展,必需在反思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基礎上,進行更勇敢的民族文化主體性探索,這也是中國文化真正講述“中國故事”,塑造理性歷史心靈主體的必要方法。正如艾文斯所說:“當一個后現代作者提出聲明——歷史的線性時間乃是過去的東西,她似乎沒有意識到在這個描述之中存在的反諷,因為聲稱某個東西是過去的產物,其自身就是在利用時間的歷史概念。”西方希望通過后現代再次解放歷史動能,但代價是,后現代再次毀滅了中國的現代——我們淪為后現代的“邊緣”。我們必須在現代和后現代之中,尋找出屬于自己的建構歷史的力量。周立民指出,馮驥才的這部小說,“通過人物命運的安排,體現作者超越狹隘的道德、民族要求的人類意識,實現小說文字之上的精神超越。”這種“精神超越”,其實也正體現了更為寬廣的文化主體意識,這也正是《單筒望遠鏡》給我們帶來的啟示。
注釋:
①這兩種真實詳見[英]達米安·格蘭特著,周發祥譯:《現實主義》,昆侖出版社1989 年版,第3 頁。
②④馮驥才:《單筒望遠鏡》,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1 頁、第248 頁。
③[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譯:《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1997 年版,第28 頁。
⑤[英]卡爾著,陳恒譯:《歷史是什么》,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93 頁。
⑥[英]理查德·艾文斯著,張仲民等譯:《捍衛歷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235 頁。
⑦周立民:《一樹槐香飄過歷史——評馮驥才長篇小說<單筒望遠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