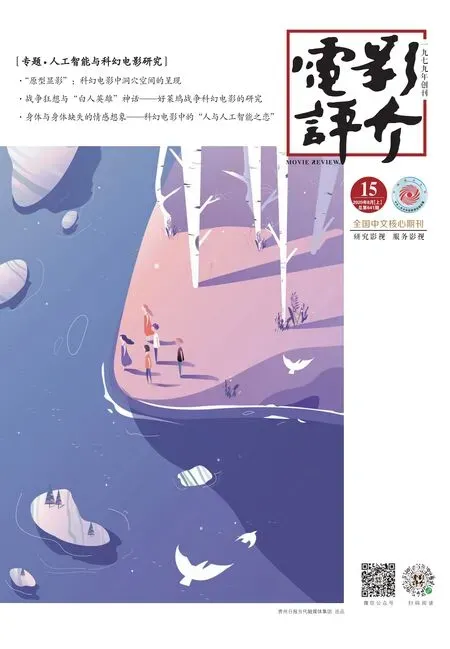消費文化與娛樂政治:中國電影市場的多方博弈(1945-1949年)
林吉安
抗戰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人們熱切期望重建起一個強大的“新中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電影也深深地被卷入各種社會力量的博弈當中。這種博弈既體現在商業層面的利益爭奪,也觸及文化和政治層面,成為管窺1945-1949年中國社會的一扇窗口。鑒于此,本文將從電影檢查、電影稅收和票價管理三個方面入手,分析1945-1949年中國電影是如何在官方與民間、政治與商業、媒體與觀眾等多方力量相互博弈下生存和發展的,從而管窺當時中國社會的某些切面。
一、存廢之爭:被抗議的電影檢查制度
抗戰勝利后,隨著全國電影業的重組,國民黨政府迅速恢復了對收復區電影業的管理。盡管為了適應當時的社會環境,國民黨政府自1945年10月1日起就廢止了《戰時出版品審查辦法》,但要求“電影戲劇檢查仍繼續辦理”。在這一規定下,國民黨中央戲劇電影審查所很快就在上海設立了辦事處,并于同年10月15日宣布從次日起對收復區電影進行審查,從而正式恢復全國統一的電影檢查制度。
正如有學者指出:“1945-1949年的電影檢查,在制度、組織體系和檢查標準方面,大體沿襲了戰前和戰時的一套組織系統和若干條文規定。”其中,道德風化問題是檢查的重點。據資料顯示,截至1947年,被禁映的影片有17部,其中國產片8部,外國片9部,“全屬神奇怪誕或誨淫傷雅之舊片”。然而,隨著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白熱化,1947年5月內政部要求電影檢查處對“過分諷刺政府”的影片“依法予以嚴格檢查”。由此,電影檢查力度明顯加強,且尤為注重思想意識方面。即便是古裝歷史題材影片,“只要其情節和對白被檢查當局認為有涉時局或引人聯想而不利于國民黨統治,亦被嚴格檢查與刪剪”。對于現實題材影片,檢查則更為嚴厲。據統計,在1945年10月到1948年9月這3年間送審的162部國產影片中,遭到刪剪的就多達48部,約占三分之一。
這種嚴厲的檢查遭到電影界人士的激烈抨擊。在1948年上海《大公報》主辦的時事問題座談會上,陽翰笙便提出中國電影面臨的“主要困難是檢查制度”,并控訴電影人“在剪刀下生活”的創作窘境:“我們往往有好作品,怕通不過檢查,自己先就忍心剪掉。有時一個電影,什么都好……卻只有一樣不好,就是通不過檢查官的剪刀”。為此,他強烈呼吁“檢查制度要放寬”。另外,也有評論建議改革電影檢查制度,放寬檢查尺度,“除了有傷風化的猥褻鏡頭要被檢去,思想上都可以比較自由”。甚至當時還有廢除電影檢查制度的呼聲。1945年12月31日,應云衛、馬彥祥、宋之的、潘孑農、沈浮、陽翰笙等戲劇電影界人士在重慶西南實業大廈舉行座談會時,就提出取消審查、演出自由等意見,并推舉應云衛、馬彥祥等五人起草意見書,以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討論。
其實,人們對電影檢查并非從一開始就持抵制態度。事實上,在電影勃興之初,由于市場亂象頻生,一些有識之士有感于電影的巨大社會影響力,要求政府對市場上流通的影片“嚴加選擇,去劣留良”,并呼吁“迅訂檢閱取締之章程,頒行全國,以挽薄俗”。甚至有評論指出,要想發展民族電影業,“第一急務,是設立電影審查會!”盡管當時電影人對審查也不無意見,但大多只是對審查的方式和方法不滿,而并不反對審查本身。譬如,孫師毅就曾撰文指出,盡管江蘇省教育會“在組織的方法上,不能令人無言;在審查的方法與態度上,則殆屬刺謬百出”,但“省教育會之發起審查,在原則上,我予以同意”。可見,對電影進行必要的審查是當時社會各界的基本共識。到了20世紀30年代,電影人也大多只是“要求它本身健全的合理的組織和運用”,而并沒有從根本上質疑審查的合法性。戰爭期間,出于抗戰宣傳的需要,電影審查更成為時代的必需,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
那么,為何到了1945-1949年電影人對檢查制度這么不滿,甚至要求從根本上廢除電影檢查制度呢?筆者認為,這與當時知識分子普遍追求自由、民主的時代氛圍分不開。在抗戰勝利前后,中國新聞界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拒檢運動”。經過兩個月的抗爭,1945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第十次常會最終通過了廢止出版檢查制度的決定。這極大地鼓舞了當時的文化界。由此,廣大電影人也應聲效仿。1946年1月,當國共兩黨及各民主黨派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時,重慶電影戲劇界發表了《致政治協商會議各委員意見書》,要求政府“廢除對話劇、電影、舊劇、新劇的一切審查制度”“保障戲劇電影業的營業自由”。這種主張被寫進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所提出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隨著政治協商會議談判的破裂,以及國民黨政府對和平建國綱領的撕毀,這種“廢檢”抗爭以失敗告終。
二、稅率之辯:高額稅賦下的影院抗爭
抗戰勝利后,盡管國民黨政府曾試圖進行經濟恢復與重建,但成效并不理想。加之蔣介石挑起內戰,軍費開支巨增,導致國民黨政府的財政赤字愈加嚴重。為增加財政收入,國民黨政府決定大幅征稅。由此,包括電影在內的各行各業被迫承受沉重的稅賦,使得當時社會民怨四起。
1946年1月4日,上海市政會議通過《上海市筵席稅娛樂稅征收規則》,規定娛樂業中除有特殊規定者外,一律按價征收30%的娛樂稅,其征收范圍涵蓋戲劇院、電影院、音樂場、說書場、歌場、舞場、賽馬場、溜冰場等一切“以營利為目的”的娛樂場所。但兩周后,上海市政府為了加強保衛力量,又于1月18日開會決定在娛樂稅中加征20%作為保衛團經費,使稅率提高至50%。同樣,成都市政府為籌集自來水公司第二期經費,也決定自1946年8月起將電影娛樂稅從30%提高至40%。這種稅率的大幅提升,無疑會大大增加影院的經濟負擔。況且,影院還需繳納其他多種稅賦,如印花稅、營業稅、特種營業牌照稅、所得稅、利得稅等。在這重重稅賦下,當時已漲為800元的票價,除去所交稅額后,最后只剩下不到一半的錢(300多元)由影院方和制片方平分。除法定稅賦外,政府還經常以攤派、募捐等名目向影院臨時征收額外的稅捐。如重慶市政府為了征召青年軍就曾要求影院攤派二千萬元,在七七紀念時又募捐一百萬元。這無疑進一步加大了影院的負擔。
這種高額稅賦和苛捐雜稅,不僅遠超戰前的征收標準,甚至比抗戰時期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1935年北平市頒布的《娛樂捐征收章程》,“娛樂捐按票價或入場費價百分之十征收。”1937年廣州市電影院所需繳納的所有稅捐也才20%。即便是抗戰時期,娛樂稅也僅提高到30%。然而,到了和平時期,國民黨政府不但沒有減稅以休養生息,反而大幅增加稅率,這無疑會招致電影從業人員的強烈反對。
面對沉重的稅收負擔,各地影業紛紛發聲抗議,甚至以停業示威。例如,成都市影劇業公會就對政府增加娛樂稅的政策“深感不滿”,甚至連“輿論界人士(也)甚望市府能體恤商艱,收回成命”。重慶市各大影院更于1946年元旦全面停業,以示抗議。然而,經過協商后,最終結果卻并非降低稅率,而是提高票價,將原來的350元漲至600元。這種做法實質上是將經濟負擔轉嫁給觀眾,而這無疑會抑制觀眾的消費,進而影響到影院的營業。當時有報道指出:“看電影已成為高貴的享受,而經營電影業的人,也叫苦連天,在重稅和生意冷淡下,紛紛虧累與停業。”如重慶的“升平”“一園”和“國泰”三家影院在1946年就虧損了三千多萬元。其“虧累停業的原因雖是有兩種:稅重、生意淡,其實根源只有一個:因為稅重,院方收入少,也因為稅重,票價訂得高,票價高,看的人就少,生意自然冷淡了。”可見,過重的稅賦已給影院造成了極大負擔。
在上海,這種抗議之聲更是此起彼伏。1946年初,上海市政府決定加征20%的娛樂稅時,廣大戲劇電影界人士便發出強烈抗議,批評上海市政府違反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中有關“分別減輕電影、戲劇、音樂之娛樂捐與印花稅”的規定,提出“除要求將新增的百分之廿撤銷外,并呼吁百分之卅依舊太高,要遵從決議,再加減輕”。同時,上海《電影周報》也發文批評這是一種“挖肉補瘡的方法”“對于觀眾也是過重的負擔”。然而,面對電影界和社會輿論的批評,上海市政府并未理會,仍舊強制執行。
在娛樂稅的重壓下,上海各大影院于1946年7月1日起全體罷市,以示抗議,同時向社會各界公告,要求減低稅捐。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上海市政府被迫決定于同年8月1日起將娛樂稅降為40%。但不久后,上海市參議會又決定從同年11月1日起恢復50%的娛樂稅率。對此,娛樂界代表以“營業情形不佳”為由,數度前往參議會請求撤銷原案。在據理力爭下,經市府財政局和參議會財政組商議后最終決定暫時維持40%的娛樂稅率。然而,即便如此,立法院在討論修正娛樂稅法時,多數立法委員仍認為40%的稅率“未免過高”。最終,在同年12月4日公布的修正版娛樂稅法中,明確規定“稅率不得超過原價百分之廿五”,且政府“不得以其他任何名目增加附加稅捐”。然而,上海市政府并未執行該項政策,仍以40%的標準征收。對此,上海市電影院業同業公會于1947年1月6日和7日在《申報》上并排刊登兩則啟事,提出“中央法令不容不遵,市民權利不容忽視”,并聲稱“減低稅率事關全市民眾福利”,從而試圖借助中央法令的權威和社會民意的力量給上海市政府施壓。最終,在電影界的抗爭下,上海市政府決定從1947年2月1日起將娛樂稅減低為25%。可見,在此斗爭過程中,作為電影行業組織的上海電影院業同業公會發揮了積極作用,顯示了當時中國社會民間力量的頑強抗爭。
三、票價之戰:通貨膨脹下的政府管控
由于內戰等原因,國民黨政府陷入了嚴重的財政赤字。盡管國民黨政府采取了諸如提高稅賦等財政手段,但仍無法填補軍費這個“無底洞”,于是只好增發法幣,而這又引發了通貨膨脹的嚴重后果。面對日益惡化的經濟情勢,國民黨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強制推行金圓券改革。然而,這一政策并未扭轉局面,反而使形勢急轉直下,社會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在日益嚴峻的通貨膨脹形勢下,電影票價也隨之不斷上漲。以南京的四家首輪影院為例,其票價在1946年1月初時分為200元、300元和350元三個等級,僅半個月后就分別漲至300元、375元和450元;3月11日起又漲為420元、560元和700元;4月4日起漲到800元、1000元和1200元;7月1日起又進一步漲到1200元、1400元和1800元;11月1日起更漲為1500元、1800元和2500元。也就是說,僅在1946年,南京首輪影院的票價就漲了七八倍。而隨著通貨膨脹愈演愈烈,電影票價更是飛速上漲。即便是后來政府強制實施限價政策,也無濟于事。1948年6月18日,政府將上海市首輪影院的限價座票價定為6萬元,其余70%座位的票價分別為15萬元、20萬元和30萬元三種。然而由于物價上漲過快,電影票價幾乎每隔一兩周就要上調一次,且漲幅不斷加大。就在限價政策實施僅一周后,限價座票便從6萬元漲至10萬元。隨后又從7月2日起再次上調,將限價座票漲為20萬元,其余座位則分別漲至30萬、40萬、50萬和60萬元。僅半個月后,上海電影院業同業公會又決定自7月17日起將各級票價一律增加九成,最低限價票也從20萬元漲至40萬元。像“大光明”“國泰”“大華”“美琪”等首輪影院,則將最低限價票提高至45萬元,其他座位則按時段和影片質量進行單獨定價,其中日場分70萬元、100萬元和120萬元三種,夜場分90萬元、120萬元和160萬元三種。如果是質量較好的新片,票價則高達200萬元。可見,此時電影票價已基本處于失控狀態。
一般而言,電影票價理應按照市場規律,由影院根據市場的供需情況進行自主定價,但當時的情況并非如此,而是受到來自政府、影院、片商乃至觀眾等各種社會力量的共同影響和制約。其中,從片商的角度來說,中西片商當然“希望票價最好能節節提高”,因此他們“對于票價的調整尤其積極主張”。但從觀眾的角度來說,他們則希望票價越便宜越好,因而普遍反對漲價。對于影院而言,他們一方面當然希望適當提高票價,以保證影院經營,但另一方面又不愿因票價過高而抑制觀眾消費,因而傾向于在片商和觀眾之間尋求平衡。例如1948年8月17日,當片商要求將票價提高90%時,影院因“顧慮觀眾購買力”,最后決定西片影院上漲70%,國片影院上漲20%。
除了市場因素外,這一時期政府在電影票價的制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電影“實負宣揚文化,普及教育的兩重任務”,因此為了滿足人們的觀影需求,國民黨政府對電影票價實施嚴格管控。然而,在通貨膨脹愈演愈烈的情況下,無論是影院還是片商均有強烈的漲價訴求,因此它們往往聯手向政府施壓。譬如1948年5月,電影院業同業公會以職工薪金、電費、廣告費、外匯等各項費用激增為由,要求將電影票價提高55%,但社會局最終只準許增加20%。西片片商則在多次要求上調票價而未果后,最終決定停止供給新片,以示抗議。同時還與影院公會共同派出10余名代表向上海市社會局請愿,要求將限價座的數量從30%降為15%,或者是提高限價票價格。但這一訴求遭到時任社會局局長吳開先的拒絕,其理由是“設限價座之目的,在使經濟能力稍差者,亦有看電影之機會,如將限價座減少或將限價票價格提高,則失去設限價座之本意。”為保障這種限價政策的實行,上海市社會局、警察局和電影院業同業公會還共同派員到各大影院核查座位數目,劃定限價座位區域,繪圖呈報并將限價座位表張貼在各影院門前。同時,為了打擊黃牛黨搶買限價票,或是與影院賣票人員勾結等不良現象,政府還規定“限價席票不準預售,購票后即須入座”,并對擅自減少限價座位或提高票價的行為予以懲罰。然而,僅僅半年后,由于金融改革失敗,物價徹底失控,這種限價政策于1948年12月底正式取消。
由此可見,當時的電影票價是在市場力量(影院、片商和觀眾)與政府力量(社會局、警察局)相互博弈下的結果。正是在這種多方博弈尤其是政府的強力管控下,電影票價變得相對便宜。盡管從面值上看數目很大,“但較之戰前增加之倍數,則遠不如其他物價之高也”。與其他文化娛樂消費相比,看電影已是相當的經濟實惠。如1947年,電影票價僅是京劇票價的15.6%,舞場票價的42%。而到了1948年,電影票價變得更便宜,甚至“幾支紙煙,也足抵得上四流電影院中的票價了”。這種相對低廉的票價對擴大觀影群體無疑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也推動了1945-1949年電影市場的蓬勃發展。
結語
電影從來就不只是純粹的藝術,也不僅僅關乎商業和娛樂,而是與社會各個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作為“電影場域”的核心力量之一,電影放映既要受到制片和發行的影響,也要受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制約,如社會環境、政府、觀眾和媒體等。這些力量背后均有著不同的話語和訴求。大體而言,影響電影放映的話語主要有商業話語、大眾話語、精英話語和意識形態話語。
對于1945-1949年的中國電影而言,電影被深深地卷入到官方與民間、政治與商業、媒體與觀眾等多方力量的相互博弈當中。盡管電影人的力量微薄,無法與強大的國家機器相抗衡,但他們依舊為自己的合法權益不懈抗爭,從而在多方力量相互博弈的夾縫中求得生存與發展。雖然當時中國社會整體呈現出“國家權力上升,民間社會和公共空間式微”的發展趨勢,但電影作為一種影響廣泛的大眾文化依然展示出蓬勃的生機,并為抗戰勝利后的中國社會開拓了一片重要的公共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