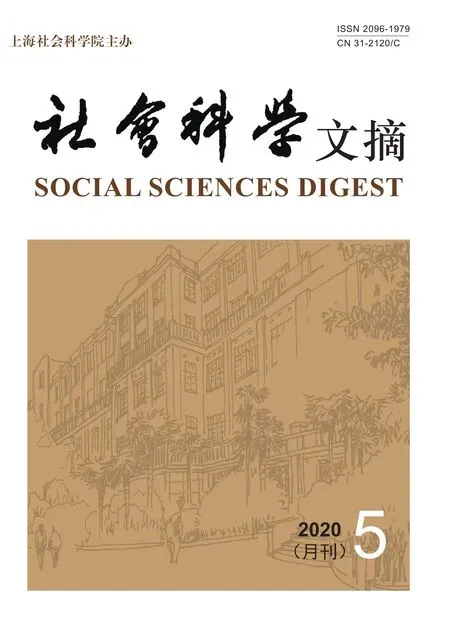儒家如何認可同性婚姻?
——兼與張祥龍教授商榷
文/白彤東
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微弱多數做出了同性婚姻合法的裁決。最高法院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其執筆的多數意見(即支持同性婚姻合法的意見)中引用了孔子的說法,而在大陸一些儒者中引發強烈反響。肯尼迪引用的孔子的話,應該是來自《禮記·哀公問》。原文是:“禮其政之本與。”而肯尼迪將其表述成“Confucius taught that marriage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也就是“孔子教誨說,婚姻是政府/治理的基礎”。在本文,我會展示張祥龍是如何回應這一問題的,然后試圖對他的回應做出一些批評和修正,以期給出一個對同性婚姻問題既不背離儒家所認可的社會責任,但又更加照顧個體自由的立場。
張祥龍論證的儒家立場:包容同性戀,反對同性婚姻
在大陸儒家學者因為肯尼迪大法官引用孔子而掀起的一片對同性婚姻的反對聲中,張祥龍給出了既基于儒家原則、但又非常溫和的、并且是基于學術討論的意見。站在儒家立場上,張祥龍對同性戀甚至同性民事結合都表達了包容的態度。這部分是因為他對陰陽的解釋沒有采取一種本質化的、把陰陽等同于男女的立場,雖然最終反對同性婚姻,但是他回應了一些可能的反對意見(比如通過收養來保證儒家看重的生生)。其他回應此問題的儒家,基本上對陰陽采取了本質化的解釋,從而對同性戀采取了根本抵制的立場,更沒有對同性戀、同性婚姻的任何同情理解以及對其辯護的任何回應,而是基于一些對同性婚姻問題的想當然的“丑化”。我最終要辯護的是比張祥龍更溫和的立場,這也是我會以他的回應為主要對象的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對同性婚姻爭論的焦點是,在接受同性戀甚至同性的民事結合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接受同性婚姻。大陸儒家的其他回應基本上是連同性戀都拒絕的。因此,本文的討論就不會以這些儒家的回應為主,而是以張祥龍的文章為主。
張祥龍文章整個立論的根據,來自他所認為的作為中國哲理思想淵源的“《易》的古遠傳統”,他認為,《周易》里的乾坤兩卦可以解釋為陰陽,而陰陽可以進一步解釋為雌雄。通過對陰陽觀念在不同早期文本中重要性的展示,他得出結論:“中國古代哲理思想主流的中樞處是有性別可言的。”儒家視男女與夫婦、親子之間有內在關聯,他/她們都是構成世界的原生結構的體系,不是偶然的或只由社會及文化建構出來的。因此,儒家總體上不會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就是不會將它與異性男女構成的夫婦或家庭等同。孔子心目中的婚禮,是將男女變為夫婦的結合,是要不斷地生養后嗣。因此,張祥龍認為,這種對婚姻的理解與肯尼迪最終對同性婚姻的意見有重大的差別。
但是,儒家并不認為同性戀本身是邪惡的,而是會認為這種現象只是陰陽相交不充分而產生的某種偏離,如果數量不多,也屬尋常現象。根據張祥龍的理解,儒家的立場既區別于基督教的極端保守派所持的對同性戀絕對拒絕的立場,也區別于那種認為性別與性取向是人可以隨意建構的立場。張祥龍認為,儒家可以接受同性戀甚至民事結合,但不能接受同性婚姻。對此,他給出了如下理由:
第一,同性婚姻會導向群婚制。其原因是從現行的一夫一妻的異性婚姻擴展到同性婚姻的跨度,明顯地大于從一夫一妻婚姻擴展到(比如)一夫多妻,后者畢竟在相當一些民族的婚姻史上出現過,甚至現在還在某些族群中存留。張祥龍進一步認為,這離濫交乃至人獸婚姻也就不遠了,從而也意味著婚姻制度的解體。
第二,同性婚姻違背了儒家的孝道,即“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孟子·離婁上》)。即使同性家庭收養孩子,也不能滿足父母有親生后代的期望。
第三,同性婚姻家庭對其撫養的孩子有傷害。張祥龍指出,同性戀養育孩子是在一個儒家認為的非真實的家庭里進行的。張祥龍指出,與生身父母在一起對孩子的撫養最好,而同性家庭的撫養會傷害到孩子。這是因為同性家庭會影響到孩子的性取向,而后者會妨礙孩子將來融入主流(異性戀)社會。
第四,允許同性婚姻,實際上是對其的鼓勵與宣傳,從而不能保證這種婚姻保持一種少數、例外的狀態。
堅持儒家立場,包容同性婚姻
張祥龍在兩篇相關文章中,把上面提到的諸多儒家立場更進一步泛化為中國哲理思想的一般特征,并且與西方的哲學特征相對。他認為,以兩希文明(希臘和希伯來)為起源的西方文明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二元分叉的思想方式(a dichotomous way of thinking)”。而中國的思維不是這樣的。這種對中西不同的描述也是學界乃至通俗評論界常見的說法。這里的一個明顯問題是:這種中西相對立的區分本身難道不也是一種二元分叉的思維嗎?撇開這個邏輯上的辯難不說,我們知道,中西都有超過兩千年的復雜傳統,其內部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流派。把這么多流派總結出一兩條共同特征,這似乎很可疑,有大而無當之嫌。不如就事論事,根據我們理解的一些儒家原則來給出對同性婚姻問題的處理,然后將其與根據不同的一套原則的處理進行比較,而不用非要說這是中西的差別。
張祥龍的論證建立在一套以陰陽概念為基礎的形而上學之上。即使是采取儒家立場的人,也不一定接受或看重這一套陰陽形而上學。在這里,我們不如回歸一些儒家內部不同流派都共同接受的基本價值,這樣就更具有包容性。
那么,與同性婚姻問題相關的儒家的重疊共識有哪些呢?這里最關鍵的就是家庭在儒家倫理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張祥龍也承認這是儒家的根本特征之一。
具體來講,家庭的一個重要職能是生生,而生生的重要含義就是傳宗接代。通過祖先與子孫,這種生生也讓我們可以超越狹隘的個體為道德提供基礎。儒家雖然可能容忍同性關系,但是它不能占據主流,我們也不能鼓勵其成為多數,否則就打亂了個體家族乃至人類的生生不息。反過來講,如果不能生生的只是少數,那么儒家可以對其寬容。
與生生相關,家庭的另外一個重要職能是對子女進行道德培養。家庭不但要將子女養大,還要讓子女有一個推己及人的起點,在父母的關愛中學會對父母的愛,進而去關愛別人的父母與子女,此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在生生和道德培養上,父母與子女都要有關聯,但是這種關聯是不是必須通過基因的連接實現,是可爭議的。
與道德培養相關的還有家庭內部的倫常。與我們的話題相關的,就是要“夫婦有別”(《孟子·滕文公上》)。比如,父母在孩子的培養上會擔當不同的角色。
還有其他幾條儒家原則也與我們的討論相關。第一,雖然儒家反對對個體道德培養的暴力干預,但也強調個體的社會(包括家庭)責任。第二,儒家不會罔顧人類的自然條件,但也不會將這種條件絕對化。第三,作為一個與時俱進從而流傳了幾千年的傳統,儒家接受對其經典和原則的新的解釋,即所謂舊邦新命的原則。這種解釋的空間要比《圣經》的解釋空間大得多。在這些原則的前提下,讓我們來看看張祥龍反對同性婚姻的幾條理由能否成立。
張祥龍的第三條理由中的一點,就是親生父母的撫養對孩子最有利。但是,如果儒家是希望家庭關愛作為道德培養的起點的話,應該關注的是保證家里面父慈子孝等價值的實現,而不是孩子的父母是否為親生父母。可能親生父母對子女的關愛,從統計上講更強些,但是這不足以否定養父母對子女可以有著同樣或者更深的關愛。否則,儒家應該徹底反對收養,但這與儒家歷史上的立場相背。畢竟,收養也是生生的一種方式,也展示了對收養對象的仁愛。如果只有親生父母家庭才可以接受,那么,在歷史和當今的環境下,儒家也要反對離婚后重組的家庭,甚至父母一方不幸早逝后重組的家庭。所以,雖然根據我們的常識,親生父母對待孩子可能會更好,儒家會支持孩子盡量在親生父母家庭長大,但是儒家不會徹底反對非親生父母的家庭,這里可以包括收養、夫妻一方去世后或夫妻離婚后重組的家庭以及同性婚姻家庭。
同性戀夫婦的一方也還是可以有親生的孩子的。對此,張祥龍的第三條理由的另外一點是同性戀家庭可能會鼓勵孩子的同性戀傾向。這與他的第四條反對理由相關,即允許同性婚姻會鼓勵更多的同性婚姻。為什么不能鼓勵同性婚姻?這里有一個張祥龍沒有說到的原因,即同性婚姻可能會違反夫婦有別的儒家倫常。但是,如張祥龍自己所言,陰陽不一定對應于男女。在家庭里面,如果作為父母的男女雙方沒有承擔起不同的角色,也是有問題的。相反,在同性婚姻家庭中,往往同性雙方中的一方會表現出不同于其天生性別的性別傾向,這就沒有違反儒家的夫婦有別的基本倫常。
張祥龍給出的不能鼓勵同性婚姻的理由還是儒家根本的生生原則。即使我們不接受儒家的這條基本原則,也會接受人類的一個基本事實:人類要通過生生來延續,而迄今為止,生生是要靠男女的某種結合來實現的。如果同性婚姻成為主流,這對人類的延續會造成根本的影響,或者讓人類無法延續,或者讓這種延續的代價太高。因此,無論是從儒家原則出發,還是從人類生生延續的基本需要出發,還是從社會公平的角度,我們可能都不希望同性婚姻成為多數。但是,張祥龍自己也承認,同性家庭并不一定會讓孩子更有同性戀傾向,即使有的話,如果同性家庭占少數,那么這種改變也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我們允許同性婚姻,但同時表達對主流婚姻應該為異性婚姻的期望和政策支持,這樣的兩手結合的政策,也不會鼓勵更多的同性戀和同性婚姻的出現。
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如果儒家反對同性婚姻的立場是基于生生,那么,儒家應該同樣反對那些所謂的異性婚姻下的丁克家庭,即那些有能力但是拒絕生育后代的異性婚姻家庭。換句話說,就儒家的生生原則來講,同性婚姻的危害要小于不生孩子的家庭的危害。但是,如果我們回到前一段的論證,就會發現,儒家要堅持的是同性婚姻家庭、丁克家庭在社會上不成為主流。在家庭內部,儒家會堅決反對子女們因為不同原因自主走向不生孩子、也不收養被認作是家庭后代的孩子的道路。
其實,在同性婚姻和現代丁克家庭問題出現之前,儒家已經面臨類似的挑戰,這就是來自佛教以及后來的天主教的挑戰。佛教的和尚、尼姑,天主教的牧師、修女,都是拒絕結婚、生育乃至家族內部的收養的。如果一個家庭的子女都走上這條道路,或者一個社會里這種選擇成為主流,也同樣背離了生生原則。但是,儒家并沒有因此而排佛,尤其是佛教的不婚不育的社會實踐。
這里,我試圖給出的更溫和的儒家立場,依然要反對同性婚姻變成婚姻主流,也依然要通過社會輿論和公共政策鼓勵異性婚姻。也就是說,儒家的立場還是要用社會和家庭責任對個人選擇加以限制。在依照個人主義支持同性婚姻的人看來,這個立場可能還是對同性婚姻有軟性的壓制。我想,這是最自由的儒家立場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立場的一個根本差別。
張祥龍所給出的反對同性婚姻的第二條理由即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包括違背了父母對有后代的期望。對此,主動選擇下的丁克家庭、出家人、選擇去做天主教牧師和修女的人,更是對這個原則的公然違背。而同性婚姻可以通過雙方各自生育或者收養來回應這個問題。對此,張祥龍的一個反對意見是,收養的孩子并非親生,而父母是期望子女有親生的后代。但是,如果儒家歷史上可以接受,或者說希望父母能接受因為生理原因無法生育后代的子女去收養下一代,那么,儒家為什么會反對同樣因為生理原因(天生或很早期形成的、無法改變的同性戀傾向)而無法生育后代的同性婚姻的收養呢?
那么,現在張祥龍的反對理由就還只剩下第一條。在這一條中,他指出,如果允許同性婚姻,那就離人獸戀和人獸婚姻不遠了。但這種指控至少對某些出于自由主義而為同性婚姻辯護的人來講,是不成立的。在婚姻上,他們所強調的是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相關各方成人之間的同意(consenting adults),而不是某一方自己出于情感或者欲望就可以了。根據這個原則,兩個成人,如果是同性,如果同意結婚,當然就應該允許他們。在我們通常對“同意”的理解上,這是人所特有的能力。這里,人獸戀和人獸婚姻就無法成立,因為獸是無法在人類的意義上表達同意的。
如果我們持前文所述的儒家立場(保證主流的后代延續和生生),則一個簡單的回應就是堅持人獸之別,堅持人倫的根本性。這種人倫背后也是要假設雙方的人類意義上的互動。這與自由主義要求雙方的同意是類似的,因此也就自然拒絕了人獸戀乃至人獸婚姻。
因此,張祥龍反對同性婚姻的第一條理由的關鍵是,對同性婚姻的辯護完全可以用來辯護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乃至更泛泛的群婚制。從自由主義或者個人主義的立場來看,確實,如果兩個同性成人通過雙方同意可以結成同性伴侶,那么,為什么不可以讓三個或者更多的成人通過同意進入某種婚姻關系?但是,很多自由主義者對群婚制尤其是一夫多妻制,可能都是排斥的。
對此,儒家應該如何回應呢?我的態度是,這本來就是對自由主義者及他們既有的信條(比如“同性婚姻當然要支持,但是一夫多妻是封建殘余”)的挑戰,儒家為什么非要回應呢?眾所周知,一夫一妻制是人類的特例,只是通過基督教西方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強勢,這種制度才成為世界的主流。嚴格來講,傳統中國確實也不存在一夫多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多妾的制度。儒家雖然承認一夫一妻可能更有利于實現儒家認同的價值,但可以在以穩定和關愛為首要善的條件下,允許一些非一夫一妻的婚姻形式存在。
當然,從自由主義的立場來說,這里有一個平等的問題,即如果允許一夫多妻,就應該允許一妻多夫。傳統的儒家如同張祥龍所指出的,有對女性地位的抑制,因此可能會反對一妻多夫。并且,從生物學上來講,一夫多妻有利于男人保持其基因延續,但一妻多夫并不利于女子的基因延續。對后者來講,更重要的是(同性或者異性)“夫婦”中的另一方在養育上的幫助。雖然如此,如果我們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或者不把男女角色絕對化,那么我們就應該把有多名伴侶的權利同樣賦予男人和女人。畢竟按照上面的說法,我們也可以論證,在傳播自己的基因上,離婚對男性的利益大于對女性的利益,但是,我們很難想象哪怕是一個當代溫和的儒家會因此支持限制女性離婚的權利。權利所要保護的對象恰恰是權力或利益有可能不同的人,否則,權利就沒有意義了,我們就都應該留給生物傾向和人的權力去決定這個世界應該怎樣了。權利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于給予強者和弱者以同樣的保護,讓我們脫離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或者儒家所說的禽獸狀態。因此,如果接受了基本的權利觀念,儒家就必須在允許一夫多妻的同時也允許一妻多夫。這確實要求儒家修正一些傳統信條。但是,我們看到,對同性婚姻帶來的后果,即對一夫一妻制的挑戰,可能更是對自由主義者或者個人主義者的挑戰。我們更要問接受同性婚姻的自由主義者,你們準備好了擁抱同性婚姻會帶來的其他“自由”嗎?也就是說,自由主義者是否準備好了真的做一個自由主義者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