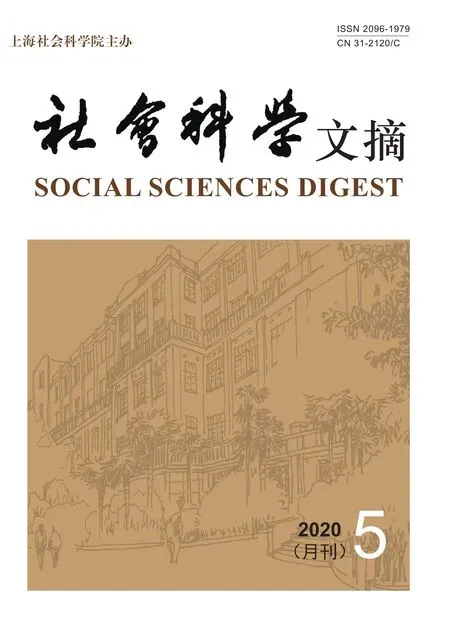四部之學的轉換與近代文章流別論的生成
文/常方舟
在近代西學東漸思潮的影響之下,西學的分科觀念對傳統學術和知識的分類方式產生了新的沖擊和挑戰,經、史、子、集四部之學悄然發生轉換。舊有的詞章之學因應西學知識分類體系的沖擊而發生異變,成為近代文章學理論轉型的重要前提。在清末學制設計中,文章流別課程的設置與本土文學史的誕生息息相關。近代文章流別論的生成汲取了傳統文章學體用兼論的要素,并在向現代文學學科轉型的過程中逐步實現了與西學知識型的對接,形塑了本土早期文學史的書寫范式。
四部之學與四部之文的分合升降:從《昭明文選》到《文史通義》
漢魏六朝漸啟有韻為文、無韻為筆之分,展現出文體學的自覺意識。劉勰《文心雕龍·諸子》雖得出“經子異流”的結論,但其暢論諸子、史傳,仍未脫離“論文敘筆”的基本框架。任昉《文章緣起》以文章源出六經之論為本。《顏氏家訓》謂:“夫文章者,源出五經。”文本于經的思想深入人心,早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成型以前,經傳在傳統文論中的導源性地位業已確立,且鮮有動搖。
而史、子、集部與歷代文章學理論交互的情況以及三者之間的升降排序則更為錯綜復雜。“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于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于晉代。”劉歆作《七略》,子部始自樹立,且其序位僅次于經部。阮孝緒《七錄》折衷眾錄,將《經典志》《諸子志》《文翰志》更名為《經典錄》《子兵錄》《文集錄》,新增《紀傳錄》,僅次于《經典錄》,大致對應后世經、史、子、集的內容秩序也基本落定。相較于類目名稱得以沿襲的經典、諸子二編而言,其改《文翰志》為《文集錄》的理由是“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至此,作為文詞之總名的集部也呼之欲出。《隋書·經籍志》最終成為經、史、子、集四部典籍目錄分類確立的濫觴,該序次也沿用終始。
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昭明文選》將選文標準限定為“事出于深思,義歸乎翰藻”,這一取法原則顯示出“去筆化”的鮮明傾向,凸顯了藻繪文章的純粹價值,在尊經崇史的時代語境之中實屬特出之論,為經、史、子部文本能否被視為文章的合理性質疑埋下了意義深遠的伏筆。而鐘嶸《詩品》對“羌無故實”“詎出經史”的詩歌批評也頗有微詞,對詩文未分階段詩歌自是一家的獨立地位有所回護。
盡管經、史、子部與文論的交互屬性長時間處于眾說紛紜的狀態,此三者作為文章體制取法的根柢之學始終有理論脈絡可循,并在從學術流別向文章流別騰挪的過程中,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差序化格局。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明確將經、史、子、集在詞章之學中的序列問題推到時代的前臺。《文史通義》在尊經的前提下拋出了“六經皆史”的論斷,雖非首創顯豁之論,卻也為從歷史角度辨析文章學的學術源流奠定了方法論范式:
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菹也。后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辨。后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余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于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
另據張之洞《書目答問》集部別集類條下注,其于清朝文人別集“除詩文最著數家外”,僅取“其說理紀事考證經史者”,其《輶軒語》也明確闡發讀集不能工文的觀點:“近代文集,鄙者無論,即佳者少看數部亦無妨。多讀經、子、史,乃能工文;但讀集,不能工文也。”張之洞是晚清癸卯學制的制定者,推定這一表述與《奏定大學堂章程》中的“文章出于經傳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間存在直接聯系,似未為過。而早在清末新式學堂大量興起之前,李端棻《請推廣學校折》曾提出在各省設立面向二十五歲以下人士的學堂,規擬課程內容之一為“誦經史子及國朝掌故諸書”,也恰好將集部摒于所學之外。
由于清代向慕實學的治學風氣使然,章學誠《文史通義》從史本位出發爬梳歷代文章流別,其“子史衰而文集盛”的觀念成為近代文章流別論的重要理論淵源,而癸卯學制的綱領性意見也在清末民初詞章之學的學科建制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為經、史、子、集四部之學進入近代文章流別論并發揮作用的歷史語境和理論傳統。
近代文章流別論的生成:經、史、子、集之體與情、事、理之用
清末《奏定大學堂章程》設有歷代文章流別一科,明告此科教員可仿照日人文學史著述撰成講義,為文章流別與文學史的合流開啟了方便法門。諸如“若六經之文,非可以文論者”這般,將儒家經典看作文章是對經部典籍和尊經傳統“輕瀆”的傳統觀念不再壁壘森嚴,經、史、子、集四部文本盡皆被納入文章的范疇。其中,章學誠的文章流別論及其對四部之文分化遷轉的敘述邏輯,成為清季民國四部之文“辨體”的理論起點。
如馬絅章《效學樓述文內篇》“論古來文章流別”一節所云:“經、史、子、集四部,質言之,經,載道者也,史,記事者也,子以談理為宗,集以摛詞制勝者也……子家各有宗門,而其典章制度之屬,多與經史出入;惟文集之名,出現稍晚,其體最裂。”這與章氏之論相近。近代湖北羅田學人王葆心所撰《古文辭通義》書名即步趨章學誠《文史通義》,書中全篇引證了章學誠有關經、史、子、集四部文章的流別敘事,作為撰述宗旨和取法對象。來裕恂《漢文典》把文章體裁分為“撰著之文”與“集錄之文”,前者指“君師道判,政教權分”以后諸子百家的著述,后者則是道裂學散之后的產物,這一論述邏輯也和章學誠對經、子、集三者演化關系的看法完全一致。
歷代傳統文章學不乏關于文章體用關系的表述。王世貞曾以理、事、詞三者隱括歷朝文學。魏禧提出文章之用不外乎明理、適事。陽湖派惲敬欲以子部救正文集之失,并用言事、言理、言情區分文詞的效用。桐城派劉大櫆《論文偶記》也隱約將明理、寓情之文與具體的子、史文章進行勾連。
盡管傳統文章體用論對文章表情、言事、明理的作用有所認識,近代文章學著述卻首次且集中地出現了大量以經、史、子、集四部的分體學說來對應情、事、理三種文章作用的表述。王葆心《古文辭通義》提出:“經義分自經類,在著述門,為說理;記載分自史類,在記載門,為記事;論辨分自子,其類亦統在著述之說理。告語一門亦言經,左史之遺,推合其類應并出自經史。三者之外統歸詞章,詞章則抒情一類之匯。而情、事、理三者之流別明矣。”桐城殿軍姚永樸《國文學》云:“古今著作,不外經、史、子、集四類,約而言之,其體裁惟子與史而已。蓋子有二派,老、莊、孟、荀、管、墨諸家,皆說理者也,屈、宋則述情者也,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以下諸史,則敘事者也。”這一觀點在其之后所撰《文學研究法》中得到了悉數保留。高步瀛《文章源流》同樣也以理、事、情三者分別對接子、史、集三部。劉咸炘《文學述林》將文章歸為事、理、情三者,并將其與史、子、集部文字作大體對應,惟經部文字未涉其中:“事則敘述(描述在內),理則論辨(解釋并入),情則抒寫,方法異而性殊,是為定體。表之以名:敘事者謂之傳或記等,史部所容也;論理者謂之論或辨等,子部所容也;抒情者謂之詩或賦等,古之集部所容也。”他闡明事、理、情是文章撰寫的目的所在,為文之用,敘述(描寫)、論辯(解釋)、抒寫則是文章撰寫的具體方法,為文之體,傳記、論辯、詩賦等文類名稱,為文之名。
近代文章流別論將經、史、子、集和情、事、理三者進行對接的做法及對后者闡發的深入程度皆為過去所不及,這與近代域外文章學思想的傳入有關。20世紀初刊載于《新民叢報》上的馬君武《法蘭西文學說例》,提出散文分為五種,分別是記事、辯論、學說、戲劇和書牘。這一觀點正為王葆心《古文辭通義》所化用,后者遂以記事、辯論和書牘分別對應記載門、著述門和告語門。又比如,來裕恂《漢文典》將文體分為敘記篇、議論篇、辭令篇,敘記篇和議論篇的篇頭小序分別采納了日人兒島獻吉郎《續漢文典》“敘記之文”和“議論之文”的提法,而辭令篇則包括詔令、奏議等文類,與《續漢文典》文章辨體觀一致。而集中出現以情、事、理三種統系統攝四部文章的現象,還隱約延伸到了日后經過東洋改造而間接傳入國內的“知、情、意”三分法,體現了近代文章學豐富多元的理論空間。
四部余論:純雜文學觀念的引介與近代文章學的駢散異趣
清代以前,經部文字亦鮮少被選入詩文總集,而史部和子部文本被納入文章選輯范圍內卻并不少見。姚鼐《古文辭類纂》未將史、子文字選入集中,但據《經史百家雜鈔序例》可知,曾國藩明確表示將姚氏不錄的六經、史傳也采入古文辭的選本之中,且冠以“經史百家雜鈔”之名。對此,朱東潤先生指出,曾國藩對古文辭內涵的界定最為寬泛:“曾氏之言古文,既包經史百家言之,而旁通之于駢文,故古文之領地,至是遂最為龐大。”這大大拓展了古文的范圍。經、史、子不僅是文章取法的源頭,其本身也可被視作文章之一部。對經、史、子、集四部文本所具有的“文學合法性”產生分歧的理論出發點,既與外來文學觀念的引介和滲透有關,也與駢散異趣的近代文章學派分理念有關。
清末西方文學進化論和純文學觀念的引入,帶來了文學批評方法的更新和文學史書寫范式的演進,對經、史、子、集四部之文的再認識產生了偌大的影響。朱自清曾指出,新興的語體現代文學“大部分是受了外國的影響,就是依據著種種外國的標準”,但在文學傳統里也能找到它的因子:“‘純文學’‘雜文學’是日本的名詞,大約從De Quincey的‘力的文學’與‘知的文學’而來,前者的作用在‘感’,后者的作用在‘教’。”在破除雜文學體系、建立純文學觀念的進程中,經、史、子、集部文本的“文學性”也迎來了新的驗示。
劉咸炘曾指出:“最近,人又不取章說(按:指章太炎),而專用西說,以抒情感人、有藝術者為主,詩歌、劇曲、小說為純文學,史傳、論文為雜文學。”根據他的觀點,純文學將文章格調設為闌入文本的標準,“正與《七略》以后齊梁以前之見相同”。可以見出,由于純文學設立了以作品美學價值為轉移的準入標準,集部反而成為優先同時也是最易被認定為具有純文學性質的文本,而隸屬于經、史、子部的文本卻往往被劃入雜文學的范疇。這樣的處置既延續了清代中后期文筆之分的理論重提,也暗含了近代選學和古文兩大陣營文章學思想的對峙。
阮元以《文選》錄文原則為準繩,主張辭章理應區別于經、子、史:“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后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也。”阮元也指出,古文家的陣地往往天然地集中在經、史、子三部,與《文選》的路數截然不同:“昭明選例以沈思翰藻為主,經、史、子三者皆所不選。唐宋古文以、經、史子三者為本,然則韓昌黎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選,其例已明著于《文選》序者也。”梁章鉅《退庵隨筆》援引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后》,力排眾議,揚駢抑散:“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以為煩,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他對真德秀《文章正宗》等歷代詩文選本闌入經史文字也頗有微詞。
另一方面,姑且不論古文先驅韓柳自述為文旁搜遠紹,于經史子無所不取,僅就清代桐城派而言,桐城派先驅之一方以智曾論取材次第云:“昔人謂胸中先有六經、《語》《孟》,然后讀前史。史既治,則讀諸子,是古人治心積學之方,往往有敘有要。”他明確將經史子三者視為文章薪火之要素。方苞奉敕選編《欽定四書文》有云:“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對采擷經史入文予以表彰。吳德旋直接將史書視作文章之一部:“《史記》、兩《漢》《三國》《五代史》皆事與文并美者;其余諸史,備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觀也。”
清代駢文和古文之間本就存在駢散異趣的分歧,但兩者的矛盾在清末民初的文章學語境中顯得愈加突出,并鮮明地體現在四部文章與純雜文學觀的呼應關系之中。劉師培凸顯選學的文學性:“誠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經、諸子之中,非六經、諸子而外,別有古文一體也。”經、史、子被歸入古文的界域,集部的特殊性得到彰顯,駢文地位亦得以抬升。郭象升《五朝古文類案敘例》認為選輯一法為集部所獨有,進而提出駢文方是承載集部獨立價值的唯一載體:“所謂駢文者,義固絕遠于經史諸子,而亦以此故,有獨立一部之精神,而散不盡然。”
清末的文章流別論逐漸為文學史的書寫所替代,其側重點也從四部文章流變和體用改換到了具有文藝美學價值的經典作品賞析:“《奏定大學堂章程》與《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的巨大差別,不只在于突出文學課程的設置,更在于以西式的‘文學史’取代傳統的‘文章流別’。”在文學史的演進之中,文學觀念自身的演進無疑發揮了極大的催化作用:“近代作家在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下,對文學本體的認同、文學審美特性的論述,都有助于純文學觀念的確立。”純文學、純文藝觀念的確立,充分肯定了集部的獨立價值和地位,也為古代文學史的去取標準設置了新的難題。
結語
經、史、子、集所代表的傳統知識型在西學東漸的語境中不斷遭遇祛魅,勢必為新的現代知識體系和學科分類所代替。四部之學在近代文章流別論中的演化和新變,折射出過渡時代文章觀念和文學概念的變動不居。與此同時,當前本土文學史的書寫困境仍未得抒解,與“文學性”更強的詩詞歌賦相比,體量龐大的古代文章作品應以何種標準、何種方式、何種比重采入文學史中,始終是困擾文史研究者的難題。郭豫衡《中國散文史》主張回歸《文選》傳統,將作品有無“沉思翰藻”作為選入散文文學史的基準:“從漢語文章的實際出發,這部散文史的文體范圍,也就不限于那些抒情寫景的所謂‘文學散文’,而是要將政論、史論、傳記、墓志以及各體論說雜文統統包羅在內。因為,在中國古代,許多作家寫這類文章,其‘沉思’‘翰藻’,是不減于抒情寫景的。”回歸近代文章學的歷史語境,抉發四部之學與近代文章流別論生成的關系,或許能夠對這一議題的深入討論有所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