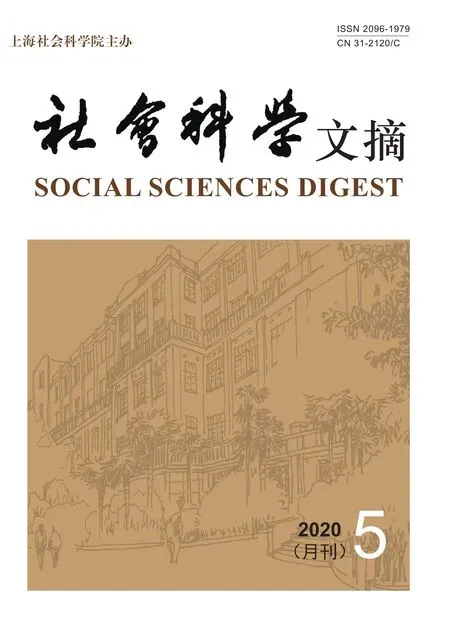美國智庫全球輿論生產與公共外交缺陷
文/彭偉步
美國智庫歷史悠久、數量眾多、影響巨大,自其誕生伊始,便對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思想生產、觀點供給、決策參與和學術研究,是美國智庫的生存價值基礎,并成為美國政治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是美國軟實力的重要架構,不僅對美國政治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為更加深入了解美國智庫的發展情況及其在全球的輿論生產,筆者于2019年10月15日至11月1日奔赴美國考察,通過與數個美國著名智庫的對話和觀察,了解美國智庫如何形成和發揮影響力,怎樣通過多種渠道和平臺傳播研究結論,牽引世界政治的走向等相關情況,以便為中國智庫的學術研究、思想生產,以及開展公共外交,增強我國軟實力和智庫影響力提供一些借鑒。
國際政治變化推動美國智庫發展
美國智庫的發展與美國政治制度、國際形勢以及國內的稅收制度有密切關系。20世紀初,美國智庫出現第一次較大規模的繁榮。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開始在這一時期誕生,并幫助美國政府制定政策。第二次繁榮是在二戰后至20世紀60年代。戰后美國政府急需發展經濟,需要學者和研究機構為政府獻計獻策,提供決策依據,因而非常重視民間研究機構的意見。一大批為政府提供咨詢意見的智庫因此得到迅速發展,并因此獲得社會與政府的大量資助,成為影響美國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重要力量。
此后,60年代、80年代、90年代,美國智庫因為世界冷戰與國際政治的急劇變化又實現了三次大發展,從而奠定了今天美國智庫的繁榮與運作基礎。因為美國智庫建立在政治制度的基礎上,故“旋轉門現象”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智庫研究人員與政府官員的角色不斷輪換。政府與智庫之間互動密切,一方面總統邀請智庫研究人員擔任高官,推行符合自己意愿的治國理念;另一方面研究人員任職于政府,實踐學術理論。因此,智庫的“政治化”或者“半官方”的色彩非常濃郁。
在20世紀世界兩大陣營冷戰期間,為及時掌握世界各地發生的政治動態,預判國際局勢的變化,美國政府通過多種手段鼓勵民間成立智庫并開展相關研究,以便為美國政府應對國際政治變化提供智力支持。
在政府的鼓勵下,美國智庫規模龐大,研究人員數量驚人,例如布魯金斯學會有400多名從事研究的專職人員,其發表的研究報告對社會和政府產生重大影響。2019年10月,筆者在布魯金斯學會、彼得森經濟研究院等智庫的訪問期間,了解到美國法律規定美國國會在做出一些重大國際決策前須召開有智庫與學者參與的聽證會,以便在出臺相關政策時能夠傾聽到公眾的呼聲,使政策更符合民意,更加科學和合理,能夠平衡社會各階層利益,權衡政策出臺后美國利益的得失,避免出現重大政策失誤。雖然政府在施政時可以依托行政團隊,根據自己的決策意志出臺治理社會的政策,但是過去的美國政府均形成了決策之前傾聽智庫聲音,并根據智庫的研究觀點衡量決策得失的傳統,因此,美國的社會制度以及聽證會為智庫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環境。
國際政治變化是推動美國智庫發展的外部因素,在這個因素的強力作用下,美國智庫從小到大,發展成今天影響美國政治和世界國際政治的重要力量,甚至成為美國政府的“代理人”。研究報告的預判性與精準性顯示了美國智庫較高的研究水平,以及對時局的精準判斷。智庫幫助政府制定合理的應對策略,保持政策的延續性,這就不難理解美國智庫為歷屆政府所重視。
巨額資金為智庫運作提供充足經費
國際形勢的變化與國內建設的需要,為美國智庫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但是美國稅收制度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更大,它保證了美國智庫能夠從外界獲得源源不斷的資金。美國的遺產稅和個人所得稅很高,但是如果富人把遺產捐贈給學術研究機構,按照美國《國內稅收法典》501(C)3條款,捐贈款項可以抵銷部分甚至全部應繳稅費,捐贈者不僅可以減少納稅,而且提高了社會美譽度。稅收減免制度促使富人紛紛向智庫捐款。因此美國智庫每年都能得到外界的大量資金捐助,這些資金支撐了美國智庫的研究,推動了智庫的發展。
美國智庫的資金來源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美國大財團、大家族或者富有人士的資助,例如美國著名財團洛克菲勒對許多美國智庫提供資助,要求智庫就其關心的課題開展研究,并提交較為客觀、獨立的研究報告;二是社會普通人士的捐助,例如彼爾森經濟研究院的資金來自大量社會普通人士的資助;三是政府項目資金的資助,政府通過委托或者公開競標的方式,向社會公布一批亟待開展研究的項目,由各個智庫通過競標來承擔研究工作。
在美國富有人士或家族的資助下,智庫快速成長。截至2018年,美國智庫數量有1872家,蘭德公司(Rand Corp)、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遺產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城市研究院(The Urban Institution)無論是影響力,還是資金捐贈額度,都在美國排名前四。例如2018年蘭德公司募集到3.27億美元,布魯金斯學會募集到1.05億美元的資金。除了美國社會向智庫提供資助外,許多外國政府也向美國智庫捐贈資金,亞特蘭大顧問委員會(Atlantic Council)、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中東研究院(Middle East Institution)、斯廷森中心(Stimson Center)等均獲得了外國政府的大量資金支持并從事相關研究。這些智庫的研究報告對美國政府在國內外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了顯著的影響,甚至直接左右美國政府的決策。
美國智庫的全球輿論生產
美國總統實施四年一次的競選機制,這為許多從事智庫研究的學者提供了從政的機會。許多著名的智庫研究人員因為多年從事美國政治和經濟研究,對不同時期的美國公眾的思想發展與政治訴求非常了解,能夠觸摸到美國公眾的脈搏,了解不同時期美國社會存在的問題,并根據研究提出許多治理決策意見,而為許多參選總統的政治人士所吸納,也因此影響到美國政府的決策。如果研究報告得不到政府的采納,智庫就會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政治游說,傳播思想,一方面為美國公眾提供不同于政府的觀點,向政府施壓;另一方面營造輿論,對某一研究對象進行攻擊,以顯示研究報告的價值,增強智庫的影響力。例如布魯金斯學會通過官方網站、自辦電視臺和電臺、社交媒體、周刊、季報、年度報告、書籍等,委派專家接受主流媒體采訪,主動接觸政府官方,從而產生立體化的輿論攻勢,達到營銷其觀點的目的。由于其多年來已在國際上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又背靠美國強大的軍事、美元、媒體霸權,因此其研究報告很容易引起國際輿論的注意并得到西方媒體的大篇幅報道,全球化輿論因此得以形成,對被研究的對象要么產生強大威懾力,要么創造改善其與美國政府關系的氛圍。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在全球化時代,美國利益建立在對國際政治、經濟進行控制的基礎上。美國智庫為政府提供了眾多研究報告,以維護美國在全球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利益,左右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時,美國智庫研究人員為了擴大其影響力,經常接受美國電視臺、報紙、廣播的采訪,利用美國媒體強大的傳播力與影響力,影響全球輿論,或借助官網、社交媒體、學術研討會、邀請政府官員演講等方式發表其觀點,實現其影響政府外交決策的目的。
例如1948年11月誕生的蘭德公司利用其與美國軍方的緊密關系,多次組織研究人員對世界各國進行軍事刺探和分析,準確預測許多重大事件的發生。蘭德公司對中美建交、古巴導彈危機、美國經濟大蕭條和德國統一等重大事件均有非常高的預測水準。這些成功的預測使蘭德公司聲譽達到頂峰,一舉奠定了其在美國政界與軍界的地位,成為美國政府和軍方的首席智囊機構。華盛頓智庫彼得森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迪(Nicholas Lardy)在2018年底出版的《國家的反擊:中國經濟改革終止》(The State Strikes Back-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對中國經濟發展走勢提出了許多觀點,質疑中國“國進民退”的經濟發展策略。這種觀點引起許多美國政界人士的關注,進一步加深了他們對中國崛起的憂慮,以及對中國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的不滿,因此紛紛支持政府要求中國改變經濟結構、開放市場等政策,甚至施壓中國改變政治制度。
在訪問的過程中,筆者詢問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米切爾·漢森(Michael Hansen)“美國精英是否弱化了對中國的支持?”他證實,越來越多的美國社會精英降低了對中國的熱情與支持,而轉向支持特朗普遏制中國的政策。如果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有可能構成對中美關系的持續性傷害,這值得我國相關部門重視。
與美國智庫的研究報告在世界上形成強大的輿論相比,我國智庫發表的研究報告,卻鮮有西方媒體進行大幅報道。這雖然與西方國家的報道視角與偏見有關系,但也顯示中國智庫無論是研究水平,還是客觀性和中立性均有待提升。此外,我國媒體在國際缺乏話語權,雖然對影響中美關系的中國智庫報告進行大篇幅報道,但是由于影響力遠不及西方媒體,因此也就無法在全球范圍內制造強大的輿論,從而幫助我國政府闡述外交政策、維護我國的利益。
美國智庫的知識生產傾向與職業操守缺失
美國智庫的運作離不開外界大量資金的支持,因此其學術與政策研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研究基調、領域與課題多少存在一定的傾向性。這就導致美國智庫在知識生產、學術研究以及公共外交等方面存在缺陷。
據筆者了解,幾乎所有的智庫都在官方網站上列明經費的使用情況以及捐贈者的名單,再三強調其研究工作的獨立性與客觀性。言下之意,他們的研究工作不受捐助人的意志所影響,即使資金來自政府或特定的基金會,也會基于客觀和獨立判斷的智庫研究工作原則,向外界提交客觀的研究報告,為政府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決策參考意見。
然而,筆者發現,美國智庫雖然努力保證研究的客觀性與獨立性,但是仍然受到多方面的制約,而使智庫的客觀性與獨立性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影響,使智庫的公共外交偏好受到公眾的質疑。例如中東財團和政府對美國智庫的資助最多,他們是美國智庫的金主,也是支撐美國智庫運作的主要資金來源。2018年10月2日,卡舒吉進入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領事館,辦理結婚相關手續,卻從此失蹤。沙特涉嫌謀殺卡舒吉的行為在國際上受到強烈關注,但是美國智庫鮮有對此事的激烈反應和批評性研究報告,而特朗普政府也對此事大事化小,淡化其負面影響。這就說明雖然美國智庫再三向外界強調其運作的獨立性,但是從此事來看,仍然無法避免公眾對其獨立性與客觀性的疑問、對智庫職業操守的懷疑。這背后反映了中東特別是沙特阿拉伯的資金明顯影響了智庫的研究。
美國媒體、美元、軍隊是維護美國利益的三大支柱。美國媒體獨霸天下,再加上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是一個能夠在國際政治舞臺發揮顯著影響力的國家。因此,超級實力使美國的任何舉動都可能引發世界政治海嘯,造成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動和重組。當美國政府官員與智庫高級研究員的觀點相契合時,政府便會引用智庫的報告結論,制定外交政策,對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國家進行施壓,甚至顛覆其政權。美國智庫由此實現研究價值的最大化,擴大了其在全球的影響力,使受到研究報告影響的國家不得不調整政策。一些國家不得不給予智庫更多的資金支持,希望智庫的研究報告淡化其對美國的威脅,形成的結論對自身更有利。例如,除了中東是美國智庫最大的資金來源外,以色列也給予一些親猶太人的智庫巨額的資助,以幫助其獲得美國政府更多的經濟和軍事支持,以及促使美國政府出臺更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
美國智庫除了發表研究報告影響美國政府政策外,還通過智庫的游說活動,幫助資金資助者獲得更大的政治利益。有時,為了向特定的對象索取捐贈資金,一些智庫還故意出臺不利該國的研究報告,以此要挾該國向其投資。這種做法顯然違背了智庫當初設立的初衷和中立原則,因此受到公眾的強烈質疑。
美國智庫是美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影響國際政治的重要力量。美國智庫通過社交媒體、傳統媒體等發布消息,出版研究報告,邀請政府官員宣講相關政策等方式,加強與公眾的互動,在全世界制造輿論,達到影響政府決策與國際政治的目的,進而擴大智庫的影響與聲望,維護美國利益,但也因為美國智庫具有利用媒體制造全球輿論的能力,一些智庫為制造轟動效應,夸大研究結論,欺壓其他國家,嚴重誤導公眾,對被批評的個人、組織與國家極不公平。
結論
特朗普上臺后,改變了美國智庫的游戲規則,即其在重大決策時減少對美國智庫的智力依賴,也不積極吸納智庫的研究結論,并減少了政府對美國智庫的資助,甚至限制游說集團的活動,導致一些美國智庫缺乏資金來源,也導致“旋轉門現象”面臨失效的困境,但總體來說,美國智庫仍然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國際政治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美國智庫已經深入美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對社會運作和國際關系產生顯著影響,已與美國政治融為一體,不可能因為特朗普的個人意愿而消失。
智庫是公共研究機構,其價值就在于其研究報告的科學性、客觀性與預判性。美國智庫之所以能夠左右美國和世界政治的發展,除了其具備較高的研究水準外,還與美國媒體、美國政府影響力有密切關系。當前,我國面臨美國政府的強力打壓,如何更好地促進美國公眾對中國走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避免誤判,增進了解,攜手合作,一方面,我國政府和企業要適當向美國智庫提供研究經費,幫助我們更加全面地瞭望中美關系的發展,通過智庫直接或間接的游說工作,改善與美國政府與工商界的關系;另一方面,我國智庫要加強與美國智庫的合作,成立中美聯合智庫,幫助兩國政府和公眾相互了解,促進合作,化解分歧。我國學者要積極加入美國智庫,幫助美國智庫研究者增進對中國的了解與認識,使其研究報告更加科學、客觀,規劃中美關系的發展,實現中美之間的良性互動。
智庫是集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參與的機構,能夠提供政策導向、分析和咨詢服務,使決策者和公眾可以就公共政策問題作出明智決定。加快發展我國智庫,提升智庫研究的影響力,是促進我國社會全方位發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強在全球的輿論影響力,提升智庫在全球地位的主要渠道。我國目前面臨許多國內外亟須解決的問題,更需要智庫的參與,以幫助政府前瞻性地規劃和制定國際政治政策,增強我國應對國際政治變化的能力,謀劃可持續的國際政治發展戰略,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