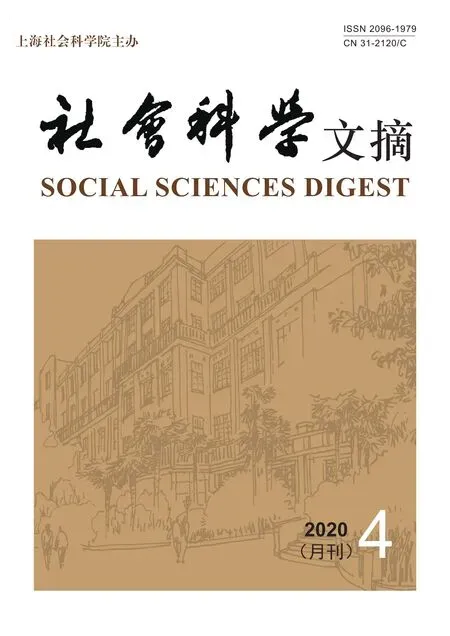論中國民法的法學實證主義道路
文/湯文平
晚近40年,我國民法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當前卻又面臨著成長的煩惱,有諸多問題紛至沓來。例如在萬眾矚目的民法典立法方面,究竟是“能不動就不動”還是銳意創新,是將既有單行法基本原樣搬入還是大動干戈?這個襁褓中的民法典與民法學及判例是何關系,解釋適用的方法規則如何?在呼聲日高的民法評注領域,究竟是緩行還是斷行,是多關注本土資源,對法史、比較法例簡之又簡,還是繼續與法史、比較法例的傳統大幅并軌?在基礎法學界也摩拳擦掌的民事案例指導(判例)制度領域,民法學人感嘆歆羨異域判例反哺活法的成績,卻對于本土仍處于一盤散沙階段的案例實踐基本無力,那么,究竟要不要立即轉向,使民法發展唯本土判例馬首是瞻?
對它們的回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難以奏效的,而應站到道路選擇的高度,探索大本大源,方能大徹大悟,而后于擇定的道路上“在發展中解決問題”。是故下文即先從我國民法發展的現實形勢及長遠目標入手,探索道路的大致圖景,然后從法史維度、法哲學維度及法學方法論維度予以深描。
選擇法學實證主義道路的必要性
1.立法謙抑(逃逸)。我國民事立法工作有新舊兩條“心法”,舊的叫“宜粗不宜細”,新的叫“能不動則不動”。首先必須承認,這兩大“心法”還是有一定正當性的。因為在任何時代,立法和司法都不能超越法學的水平。法學自己提供的支持是有限的,立法有時候粗一點確實比細一點要好;能不動就不動也總比瞎動要好。有了這兩條“心法”,還可以確保民法典編纂工作按時間紅線如期完成。而且,法典化的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即便是法學已經掌握的東西,也不必全部納入法典,而應在一開始就將法典的交給法典,法學的留給法學,如此則二者相得益彰,更有利于未來民法典的健康運行。在謙抑因素之外,兩條“心法”有更多的立法逃逸嫌疑。因為就許多問題民法學可能已有足夠準備,且也應當入典,卻因此“心法”而被拒之門外。“宜粗不宜細”頗具反智主義意味——此前民法(學)已牛毛繭絲無不辨析的研究成果,現在宜粗不宜細了,又把它擰成一股繩,結果太過粗糙的立法便放棄了對司法的約束和指導。而所謂“能不動就不動”,也往往并非真“能不動”,只是怕動了惹麻煩,所以仍自我安慰說“能不動”。想到未來民法學將在上述似是而非、若有若無的“小傳統”里虛擲光陰,混著“法之蛀蟲”(基爾希曼語)的日子,足可令學人不寒而栗。
2.本土學說準備不足仍須比較法支援之處甚多。即便打破“能不動就不動”和“宜粗不宜細”的桎梏,積極作為,在一定階段的立法中都仍會有不少問題難下定論。可是很多時候,在比較法上又有成熟穩定的方案可以直接“拿來”。此際應允許后法典時代的民法學能以比較研究為先鋒繼續成長。在這些大的資源移植契機面前,如果因為立法時間紅線加上法條主義道路自我設限,而將民法典編纂前沒有完成的借鑒任務干脆打入冷宮,裝作根本沒有這回事一樣,那如何對得起法典編纂的“初心”。
3.民法繼續成長及擔當原創使命的必需。有些問題是可作定論、立法也作出了正確的定論,但隨著時間推移,又有繼續發展、革新的要求,故須在法典化之后交由法學、判例繼續自由地探索和建構,這是不言自明的。在更廣闊的背景之中,更要看到,世界民法都面臨著大變局,西方先哲留下的民法體系已不敷應對,需要中國這樣的復興大國擔當原創使命。所有相關例子都有一個共性,即民法大傳統也為之撓頭,甚至可能帶來范式的重整。中國民法應賡續先賢遺風,直面難題,充當新時期世界民法創新的發動機,這也是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民法學人共同體所應有的擔當。所以在民法典編纂的任務面前固然可以將這些重大疑難“多聞闕疑”,但是在未來法典解釋適用中決不可畫地為牢,徹底避開創新使命。
4.沿“一帶一路”催生新共同法的必需。民法作為交易基本法,堪稱“一帶一路”的制度先鋒,在沿線各國之間統合民法規范,將有力地促進經貿發展與人民福祉。統合思路不外乎二,其一是目前比較流行的國際、區際統一私法模式,其二是歐洲近代法典化浪潮之前的共同法模式。前述第一種模式仰賴強有力的政治推動,這往往是可望不可及的,所以《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CISG)這種成功例子鳳毛麟角,幾成絕響。在“一帶一路”的愿景下,同樣是第二條路子(即法學主導的新共同法)更具可操作性。若能遵循正確的發展道路,我國民法甚至可以在催生新共同法方面比歐洲私法一體化呈現出更多的后發優勢。法典化往往只是制度充分發展、基本固化時的終結之舉,而不是制度蓬勃創新、急劇上升時的開辟之舉。然而我國當下民法發展正處在蓬勃創新、急劇上升階段,所有上述現實問題,都在提醒我們,民法典編纂不應成為中國民法發展的一個障礙,甚至都不應成為打亂既有發展隊形的所謂“新起點”,而應只是活法河流當中泛起的“浪花”(溫德沙伊德語),不僅延續了此前民法的傳統,而且在法典化之后仍能不捐細流,百川歸海。這是法學實證主義的發展道路。
道路選擇不能純依所謂“理性選擇”。認識現實局限及形勢,認識發展目標,然后作出一個“合目的”的理性判斷,對于選擇民法發展道路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就像選擇以“理性”的自然法為現行法依據一樣,這種對理性的自信往往被證明是盲目的。道路選擇還須放入到法史、法哲學、法學方法論的既有智識系統中,去審視、去建構、去查明走這樣一條道路究竟有什么根據,又將帶來怎樣的觸動。
法學實證主義之法史維度
法學實證主義主義肇源于先法典時代。回顧歐洲私法在法典化浪潮之前的歷史,一些特征會自然地凸顯出來。其一就是取法乎上。歷史之所以選擇羅馬法,應該主要是因為它的優質體系順應了新時期的制度需求,所以歷史法學強調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但是不重日耳曼法而偏重羅馬法。第二個特征是往還于文本與現實之間。自11世紀羅馬法復興以后,先有注釋法學派,主要依歸于羅馬法源文本。后又繼之以評注法學派,更重視將羅馬法當代化、本土化,從而將古代的規范與當下的生活“聯結”起來。第三個特征是兼顧本土化和國際化,成功催生了跨法域的共同法。歷史法學派強調“民族精神”,但取法的羅馬法其實最有國際趨同性。而在近代法典化浪潮之后,由于各國民法學在法源論及方法論上紛紛轉向,徹底偏于內省各自的民法典,共同法遂成絕響。第四個特征是法學向現行法的“實證化”。這個“實證化”在傳統上的淵源多元而久遠,并深刻地影響了法學的發展。一方面,正是因為可以向現行法轉化,所以法學有動力廣泛搜求古代文獻,尋找制度靈感。另一方面,因為“歷史法學”研究“歷史”是為了“實證化”為現行法規范,所以法學家可能一邊到處找新材料支持自己的觀點,一邊又擔心貪多嚼不爛,提防法的神秘化,對羅馬法材料掐頭去尾,更對日耳曼法、教會法材料閉目塞聽。第三方面,“歷史法學”對待“歷史”的手段是比較“粗暴”的。在一定范圍內其正當性大約可以從兩個角度來找。其一,不少妥當的規范或許存在于理性之中,或許存在于習慣之內,的確要超越已經建立起權威的法源材料去尋找。其二,基于論證的說服力需要,前者(妥當的規范)又不能不與后者(權威材料)關聯起來。所以在法史上,我們除了看到前述溫德沙伊德和耶林從理性中“流淌出來”的規范納入之外,還可以看到大量商事規則在體系化時不住地拿捏羅馬法這個“變形金剛”。這個“變形金剛”作為一個隱喻,也可以為當今常用的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等法學方法在先法典時代的法學實證主義找到淵源。第五個特征是法的自治化、專業化。羅馬私法之自治化特征在近代羅馬法復興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習慣法及法學家法的優越地位即其彰顯。甚至到了法典化之后仍有體現,例如民法典里據優越地位的任意法對當事人意思的揣測和描摹,例如判例法、習慣法、學理的自然生長,均為適例。在(市)民法這個崇尚自治的領域,與口含天憲的干預型人定規則相比,更被信賴的是找來法史、比較法例、習慣、學說、判例等素材,讓它們在“事理”和生活的規范需求面前“物競天擇”。規范自治行為的私法也由此而自治化。“不依賴于倫理、政治、國民經濟等外物”目的則大概有二,一是減負,二是專業化。在人類社會日益自詡理性覺醒以后,法的專業化便越來越重要。所以在程序上搞一系列一條龍式的形式安排,在實體法上,則強調概念建構、涵攝,對倫理、政治、國民經濟等“外物”當然也就既無暇顧及,也不敢多談。于是法學實證主義又在后來的德國民法典編纂中常常遭受逃避社會使命的指責。
先法典時代法學實證主義的上述特征很大一部分因法典化浪潮而湮沒法學的確更像基爾希曼說的,只是法條病變接駁處的蛀蟲,或者如耶林所云,就像法律機器上面一個個小零件。法學實證主義精力彌滿的作品——民法典簡直就是“歷史的終結”,法律實證主義應運而生。
法學實證主義之法哲學維度
法學實證主義與法律實證主義經常被混為一談,這是法哲學上的一本糊涂賬。法哲學奢談法律實證主義,提出各色“命題”,但在實踐層面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法律實證主義的命運在兩大法系完全不同。依個人所見,法律實證主義在兩大法系的命運如此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兩大法系的法源論出發點不同。成文法國家談法律實證主義,無論怎么談法,實際上都免不了過于糾結法條文義,而束縛了學說、判例的必要自由。甚至在納粹時代,可能會因為被要求無原則地追隨“被法律化的元首的意志”或“民族精神”,或者“惡法亦法”,而在法律人共同體“盲目的飛行”中使法治國的良法善治遭受絕大損失。再來看判例法國家,由于普通法的優位法源為判例,其法律實證主義道路先天地就比較安全。判例在類型上可以區分為一次性判例、確定性判例、持續性判例、習慣法,法律人在判例運用時基本的思維定勢是,自己所舉的判例立場最好是成串的判例鏈條。而特別要留意的是,這些一串串的判例之所以能成串,以及成串后提煉出怎樣的判例立場,其實都是德沃金式“說故事”(或曰“建構”)的結果,并且這個說故事的找法過程,都是面對待決案件事實而展開的。稍稍有一些法律實踐經驗,應可理解,這種說故事的找法過程,最容易在先前判例群及當下待決案件事實間“穿梭往還”,量身打造出“個案規范”來。所以,在判例法系,法源論的出發點也就預先抵銷了法律實證主義的弊病,甚至為了使得其上下其手的找法方式不過于離譜,法律實證主義剛好還是對癥下藥。無論是“英美法系之法律實證主義更接近法學實證主義”,還是“大陸法系法學的‘實證化’優勢”,其實在法哲學上都意味著,法學實證主義(或曰理想中的法學實證主義)乃是法律實證主義和自然法之間的中庸之道。法律實證主義和自然法在法哲學上相對而出,都跟正義一樣長著一張普洛透斯之臉,善變而難以把握。但是應該不會有疑問的是,法學實證主義的如下優點主要淵源于法實證主義:自治化、專業化,與倫理系統、政治系統、經濟系統之間有屏障,而又有耦合機制;注重規范的有效性,通過將各色材料中發現的規范適用于裁判,而同時獲得規范與裁判的有效性。而以下優點則主要淵源于自然法:在法的成長及學說、判例的演變過程中,執著地謀求凸顯來龍去脈,使習慣法的機制一般化,希望通過法例、學說、判例、慣習之中傳承的“慣性”基因自然地植入正義和正當性;超越立法者劃定的法條粗跡,追問法史、比較法及其他淵源,敢于承擔起價值評判的責任,使各個案裁判都沖破實在法的“天花板”上升到正義的考量;法學通過法史、比較法研究引介規范時,一搞懂文獻,即觀照與生活事實的聯結,甚至不惜像對待“變形金剛”一樣拿捏前述規范淵源,其背后是對事理(或曰事物的本質)的自然流露的尊重。
要求超越法律實證主義選擇法學實證主義道路,實際上也是在順應自然法復興的潮流。此時的法學實證主義將是對法律實證主義的揚棄。故而一方面,也像法律實證主義在法律論證中言必征實,不像自由法學那么天馬行空;另一方面,又不死摳法條,而是納入了更多的資源,包括古老的自然法原則、近代理性法、當下以各種判例或習慣為外衣的“事理”等廣泛意義上的自然法,并在法教義學體系中建構活法河流。在潮流上,與大陸法系的法律實證主義相比,英美法的法律實證主義更貼近法學實證主義,但是大陸法系背景中的法學實證主義卻將因法學與判例雙重通說互競互濟機制而更加合理、有效。因為以大陸法系為背景的法學實證主義到底還有一個獨特的優勢,即賡續“學者法”的傳統,重視現行法之法學研究,以學者代言并融會立法、判例等資源的法教義學體系為集大成者。英美法研究教義的學者及學說影響力要小得多,司法與學術“各行其是”。在法學實證主義之下,學說為立法和司法提供智力支持,同時又與判例互競互濟。由于學者有更豐富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具體問題的深入挖掘,而且作為教義學、法史及比較法文獻的“保管人”,他們比飽受時效之苦的立法者和法官,有更多的理由成為權威體系的建構者和代言人。總之,脫離了法學的“實證化”,揚棄法律實證主義,也不過是贏得一個半截子的法學實證主義。
法學實證主義之方法論維度
方法論維度可以為法學實證主義提供依據,并因選擇這條道路而帶來許多方法論的觸動。法學方法論所要應對的任務大概包括:從各類素材中提取規范;加工及編纂規范;面對個案時發現并適用規范。基此則法史研究文獻的方法、比較法的功能等同法或共振峰理論、商事習慣采風、法社會學的田野考察法之類,都是“從各類素材中提取規范”,這可以說是法學及法最初的原始積累。拉倫茨等人方法論體系中的規范理論、體系理論、法典編纂理論,則主要是在“加工及編纂規范”。至于各類法律解釋方法、涵攝、權衡、類比,則是“面對個案時發現并適用規范”。這三項任務之下的具體方法在一定歷史階段曾有繼起關系。但是在近代法典化之后,核心任務應該已明確為面對個案的法律適用,并且隨著法律論證的思路不斷復雜化、精細化,原本歸屬于其他任務下的方法也互相雜糅著歸入其中。先法典時代的法學實證主義由個案決疑走向建構、實證,后法典時代法學實證主義從污名化的法律實證主義中涅槃,則是由建構轉向以問題為中心的論題目錄。這是方法論維度的“螺旋式上升”,需要細致觀察。
當代法學方法論一條主要的路線斗爭是法論題學與法學建構方法之間的斗爭。近代之前被繼受的羅馬法主要是判例法,有濃厚的論題學色彩。概念法學借助法學建構方法將其“九蒸九曬”,打造為概念金字塔,找法方法也配備為涵攝。雖有耶林等氏入室操戈,指陳其弊,但也不能不承認這種體系化方法簡約了法律適用過程,利于法律運行的穩定性。而法學實證主義在原初的意涵上也與此概念法學的特征緊密關聯。自目的法學、利益法學、評價法學相繼勃興,概念被不完全概念、原則所淹沒,涵攝被類比、權衡所擠兌,基本的特點是順應針對個案正義的現實需求,故須打開缺口,增添論題,但又眷顧建構及涵攝所傳遞的法之安定性價值。法律論證理論的登場,意味著論題從內部證成和外部證成角度愈益豐富,而安定性價值進一步爭取溝通行為規范的背書。這個“背書”的實質就是借助類似于阿列克西那種成套的“法律論辯規則”,盡可能“理性地探討非理性的東西”,將思維“黑箱”內的部分盡可能縮到最小,并就最終保留在“黑箱”里的部分仍在論辯規則上給予安定性、平等性的確保。動態系統論同樣是增添論題,雖自認為是在法學建構與論題學之間的中庸之道,但若考慮到論題學也追求一個“論題目錄”,動態系統論與之在本質上應該是一致的。即都有志于論題的拓展及條理化,但是在條理化方面實際上也都不得門而入。若以法學實證主義的眼光來看待論題學與法學建構進路的分歧,則基本規律是首先依論題學進路凸顯主題,其次是篩選主題,再次是以篩選所得的主題為材料建構規范。
選擇法學實證主義道路首先意味著在制定法概念之外納入更多的論題,借重二元通說互競互濟機制等就待決個案尋得穩妥而又滿足個案正義要求的個案規范。這些個案規范在類案中實踐驗證,成為穩定的存在之后,又可以通過法學建構融入于體系之中,未來找法又在一定范圍內變得涵攝即可,縮短法律發現的過程。這樣法律發現的論題學化和法學建構分成了兩個互相影響的過程,實現法學實證主義法教義學體系的“盈科而后進”,或曰“螺旋式上升”。
法源擴展帶來了一個關鍵性問題,或者說選擇法學實證主義道路帶來一個兼跨法哲學和法學方法論的問題,即如何對待制定法。個人主張,應綜合借鑒并發展薩維尼、薩科等人的建議方案,對制定法立場區分技術因素、政策因素,并進一步細分政策因素。首先,技術因素應該屬于法學的“用武之地”,即便制定法已經給出了一個立場,也不應被當作“終極方案”而在民法發展進程里畫地為牢。其次,對政策因素還要進一步區分為涉及政治層面的政策因素和涉及一般價值判斷的政策因素。就前者應旗幟鮮明地遵循制定法給定的立場,就算制定法未給立場,也不宜由法學擅自填補漏洞或續造。例如建設用地使用權到期之后是否自動續期,自動續期的話是否不必續費的問題。對于一般價值判斷性質的政策因素,法學卻并非如星野英一等人所言,同樣“不比普通人更有優勢”,而是完全可能像技術因素一樣,在斟酌制定法的得失之后,再做整體熔裁。評價法學最大的問題,是在某些疑難問題上,從制定法尋得幾個節點,將之作為論證的參照基準,然后就其余在制定法里沒有明確安頓的節點一一參照基準“妥當”安排,自成體系。接著像小電網向大電網并網一樣,將前述工作獲取的“小電網”并入民法體系的“大電網”。這樣初看起來,似乎很成功、很可靠,而且符合法律論證學的原理——通過盡可能多的節點之關聯檢驗融貫體系。可是假如制定法派給的那個作為參照基準的節點有誤,其實已滿盤皆錯。基爾希曼描述的那個慘淡前景——立法修改一個字,汗牛充棟的法學文獻即告作廢——其實就是一在立法層面糾正個別節點,“小電網”即如圍棋盤上一大片棋子一次性歸零。法學實證主義要求一開始即審視作為參照基準的那個制定法節點,只有當這個節點不是技術因素,也不是一般價值判斷性政策因素,而是政治層面的政策因素時,才接受此前評價法學的“盲從”做法。
結語
法學實證主義的根本追求是打開法律實證主義及法典帶給的枷鎖,確保現行法能自由地進化,確保個案正義,同時卻又確保可依托體系建構、法律論辯規則乃至匯聚法律人共同體和人民群眾法律智慧的系統性著作等,提升現行法的穩定力。近代以來后法典時代的民法發展為此要走很長彎路,才最終有意無意間重返先賢的定見。依照本文提示的思路,在法史、法哲學及方法論三大維度的觀照之下,將從“有意無意”的行動轉為自覺的道路選擇,并借法學實證主義理路反向作用于前述三大維度的認知和實踐。在這種循環往復中,不僅法學實證主義道路將更為清晰、更可遵循,法史、法哲學、方法論之相關領域也將別有洞天。而就本文開篇所及我國民法當前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民法學人共同體將有定見:
民法典立法的理想模式是先有充分理性商談出來的學術通說代言體系,然后經由條文重述直至法典化。但是在時間紅線的壓力下,就立法謙抑(逃逸)現象也不必過于困擾,而應風物長宜放眼量,只要能以法學實證主義理念保持民法發展的主動性,立法的不足可以在活法河流中被蕩滌一空。故未來民法典的運行中,應賦予學說及判例更大的自由,應區分立法當中的技術因素、一般價值判斷性政策因素、政治性政策因素,僅最后一種因素才能要求對制定法較高規格的遵循。為了確保民法發展繼續保持開放胸懷,取法乎上,應延緩對本土立法、判例的內向化,故在當前呼聲日高的民法評注領域,不宜邯鄲學步,一上手就師法經典法域的經典評注(如目前正被我國學人集體模仿的德民慕尼黑評注),而應下更多功夫在歷史評注、比較法評注上。特別要強調的是,前述“歷史”評注應該是接續世界民法“大傳統”者,而非“為賦新詞強說愁”地一頭栽進我國立法的“小傳統”,在此前各單行法陳陳因襲中繞圈圈。取法乎上,并以絕大魄力自我保障取法乎上的自由,是法學實證主義永恒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