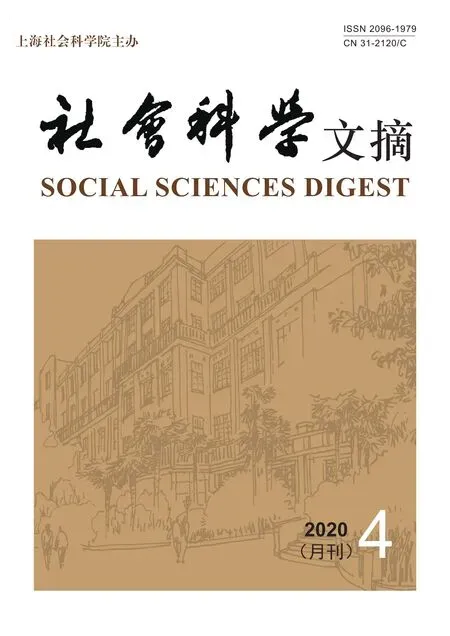論緊急狀態下限權原則的建構思路與價值基礎
——以我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為分析對象
文/張帆
問題的提出與限定
在我國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中,憲法的三個條款同時寫入“緊急狀態”這一概念。另外,原本被人們寄予更多期待的《緊急狀態法》也中途夭折,被《突發事件應對法》(以下簡稱《應對法》)所取代。《應對法》存在如下不足。首先,《應對法》缺乏對公民權利的足夠重視。其次,作為一部調整和規范突發事件應對關系的法律文件,《應對法》僅僅將突發事件視為一種客觀的事實,忽略了其可能蘊含的規范性意義。最后,從更深層次看來,《應對法》其實在立法精神上忽視了(規范的)突發事件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內在關聯。如果以上分析可以被接受,那么,就我國《應對法》而言,以下問題便不是突兀的或毫無意義的:在這部法律中,是否有必要設置與權利有關的法律原則?如果有必要,又該怎樣建構這些原則?立法者又會遇到哪些難題呢?
有關緊急狀態的不同立法模式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緊急狀態的理解都遵循了一種基于目標的極端的理論方案,即一種以利維坦式的主權者為絕對本位的方案。由于緊急狀態關乎主權者的生存,在他們那里,重要的不是民眾的權利,而是他們自己的(或以自己為中心的小部分群體的)利益或特權是否受損。如果選擇這種視角,緊急狀態與權利之間的關系就十分簡單了:根據主權者的判斷,緊急狀態只要有可能(哪怕可能性很小)危及權力甚至生命,那么緊急狀態就屬于一種強勢的取消條件。
除了前述傳統進路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方案來規范緊急狀態呢?布魯斯·阿克曼的“緊急狀態憲法理論”為此提供了一種智慧和有益的知識資源。首先,阿克曼更新了緊急狀態的規范基礎。他敏銳地指出,傳統成文憲法所規定的緊急狀態是以“生存理性”作為憲法的基本理念,但是鑒于時代背景的轉換以及問題自身的復雜性,對緊急狀態的界定與規范應當讓位于“重新保證理性”,也即向普通民眾保證,緊急狀態僅僅是一個例外事件,無需過度擔心與極端恐懼。
其次,為了保證緊急權力不被濫用,阿克曼主張將論證負擔置于政府之上。阿克曼承認,一種“超級多數的投票機制”并不會自動發生作用,而是必須依賴于行政機關的積極作為,即持續不斷地向國會提供真實的信息,尤其是讓少數派得到信息。因此,他建議在國會中成立一個監督委員會,迫使行政機關持續提供各種信息來為自己行為的合法性提供理由。
如果對緊急狀態的規范必須要考慮到普通民眾的訴求,那么,權利就不再是可有可無的,或者不再是一個可以被隨意取消的對象。在這種立法模式中,權利的位階至少被提高了,或者說,權利可以與權力一起正式地平等對抗了。如果沿著這個思路走下去,一方面,人們可以繼續設計具體的法律制度來實現這二者(權力與權利)的平衡;另一方面,人們也有可能進而討論一個(元)理論問題:在(如此規范的)緊急狀態之下,政府應當如何在原則上對待公民的權利。
設置限權原則的必要性:基于體系融貫性的論證
(一)設置限權原則之必要性的論證
如果承認《應對法》是憲法的下位法和對憲法的具體化,它就必須同我國《憲法》保持一種體系上的融貫性。然而,《應對法》并沒有滿足這種立法上的原則一貫性。首先,該法的第一條明確提出了“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這一總體性要求。然而,即便不考慮該條的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也并不能全面涵攝公民的基本權利。其次,該法第十二條要求“財產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毀損、滅失的,應當給予補償”,但這種方案也僅是事后的補救措施,即便有效,也并不充分。最后,該法第十一條其實是比例原則的重述。然而,這種方案過于簡單了:一方面是因為它忽略了比例原則自身所隱藏的缺陷,并想當然地將其視為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是因為它放棄了一種努力,即放棄了探尋其他或許是更為精致與有效的法律原則的智慧征程。
(二)命名問題:“限權原則”還是“權利保護原則”
我國憲法并沒有將權利保護置于一個絕對的排他性地位,而是體現了某種限權的思想。如果這一論斷可以被接受,《應對法》中的有關公民權利的原則性規范最好被表述為“限權原則”。如此建議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基于筆者于本文中提出的體系性融貫的要求;二是更加符合該法的立法用意和語詞表述。這里對第二點稍加論述。《應對法》的第一條其實已經明確宣示了自己的立法精神和價值取向:在“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前,立法者強調了三項更為重要的實踐目的,即“預防和減少突發事件的發生,控制、減輕和消除突發事件引起的嚴重社會危害,規范突發事件應對活動”。或許有人不同意這種語言序列所表達的重要性位階,但即便拋開這一爭議,無論是第一條的原則性規定,還是后文諸多具體的規則性表述,不可否認的是,它們共同預設了政府在應對突發事件中的主導地位和推動作用。換言之,“預防”“減少”“控制”“減輕”“消除”等諸多行動和措施的施行者都是政府和公權力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如果承認這一點,那么“限”字似乎更好地體現了政府的主體地位與基于政府主導的視角。尤其是在緊急狀態下,政府必須對公民的某些權利給予某種必要的限制。
也許有人會質疑道:“即便承認政府的主導性,‘護權’也未嘗不可呀?政府難道不可以護權嗎?‘限權’的思想會不會在實踐中造成權利的損害呢?”對此,我們將作出以下兩點回應(這兩點回應也可以視為對“限權原則”之名的進一步證成):
首先,盡管古人強調“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且上文也花了一定的篇幅來討論命名問題,但在本文看來,名稱所實際體現的價值追求比名稱本身更為重要。其一,任何正式的法典中都不會在每個法條之前添注一個括號以標明該條款的名稱,因此無論是叫“限權原則”還是“護權原則”,其實僅為人們的使用和稱呼便利,并不涉及任何實質的行為評價和合法性判斷。其二,無論選擇何種稱謂,《應對法》都不應也不會削弱一個基本的價值追求,即對公民權利的始終保護。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政府行為的最終著眼點和行動“紅線”不是民眾的權利,那么任何“限權”原則的建構則是毫無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上,限權和護權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已。其三,更為重要的一點,人們之所以會對“限權”之名感到擔憂,主要是受限于一種傳統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或許是因為思維的便利,人們通常僅會關注緊急狀態(及其所引發的行政舉措)和公民權利這兩個極點之間的互動和沖突:要么是緊急狀態威脅公民權利,要么是公民權利碰撞緊急狀態。因此“限”字似乎必然預設了一種沖突和對立的狀態。實際上,后文將會指出,如果不把緊急狀態視為一種單純的事實,而是將它和權利都視為一種解釋性的概念,那么,通過一種創造性的解釋,人們就可以在一個更大的價值之網中實現這兩個概念的融合。
其次,如果選擇“限權”之名,實踐中可能會產生一種超范圍的涵蓋效果:限權(利)的同時也意味著限權(力)。公法調整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重在規范公權力之授予行使。如果任意擴大公權力的范圍和法律依據(法源),將使公權流于恣意。由此,作為公法的一員,如果《應對法》中規定了限權原則,那么其所“限”之權實際上不僅包括權利,還應包括權力。換言之,雖然從政府視角出發,緊急狀態需要對公民的權利有所限制,但如果將該法置于更大的法治語境之中,同時再考慮公法本身的功能性限制,《應對法》對公權力的限制也應屬于必有之意。在這個意義上,限權與護權在此處同樣一致,并無厚此薄彼的意味。
動態的限權模式及其價值基礎
(一)《應對法》應選擇動態的權利限制模式而非靜態的權利清單
既然不是所有的權利都需要被限制,那么,在緊急狀態下,哪些權利應當入選而哪些不必列入呢?通常的思路是制作一個清單,然后將必須予以限制或不能限制的權利分門別類地放進去。但這種思路的缺陷也十分明顯。如果考慮到人類的理性有限,制成一個令人滿意的清單就成為一個極有難度的工作。為了避免上述難題,立法者可以選擇一種動態的限權思路。
例如,當第一次恐怖襲擊發生后,為了防止再次發生類似襲擊,同時也為了防止民眾的恐慌,行政權力可以采取一種“一攬子”的限制措施,將盡可能多的權利納入限制清單之中,例如言論自由權、私有財產權,以及上文提到的在無需遵守合理懷疑的標準的情況下限制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權。之所以可以采用這種大范圍的“一攬子”模式,主要有兩點考慮。第一,因為緊急狀態的突發性與復雜性,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難以在短時間內作出準確的判斷,因此較之于仔細甄別所帶來的不便(例如高昂的時間成本),不如采取一種類似于一體授權的權利限制模式。第二,緊急狀態是暫時的,而且對實體權利的限制必須同時輔之以程序性的限制,例如“類似于自動扶梯那樣”的有關宣告和解除緊急狀態的程序。如果特定的程序決定終止緊急狀態,那么在極為有限的時間內對權利進行廣泛限制的消極影響也是可控的。當然,如果決定延續緊急狀態,則權利清單的范圍必須予以限縮。一方面,政府已經對特定緊急狀態的具體情況有所了解,從而可以有針對性地采取行政措施;另一方面,社會和普通民眾也會根據緊急狀態的特殊性采取適當的調整和自我保護方案。如果突發狀況的沖擊性已經減弱,也就需要適時調整入選的權利清單。簡言之,在緊急狀態的第一階段,所限權利的范圍可以大一些,但隨著緊急狀態的延續,需要被限制的權利類型將會逐漸減少,這個過程應當從恢復某些最不能限制的極少數權利開始。
(二)動態的權利限制必須輔之以一種動態的雙重論辯思維
上述動態的權利限制必須同時輔之以一種動態的雙重論證/論辯思維。例如,面對國民甲的反戰言論,為了避免可能引發的動亂,處于戰爭狀態的該國政府能否限制其言論自由權呢?除了在立法上必須作出一種暫時性的保證及相關的程序設計之外,政府還必須做好以下準備:考慮到行動成本,政府通常會在采取措施前提出一種在最大程度上有利于自己的解釋。如果沒有反對意見,具體措施便可以直接貫徹執行。不過,政府必須明白,一旦開始執行,它的解釋并不處于絕對的、不可撼動的地位。甲完全可能作出相反的回應。
如果感覺最初的解釋太過薄弱,政府可以作出一個新解釋,但這種做法將會顯得之前的舉措有些隨意。它也可以繼續增添理由來強化論證,但考慮到原始起點較低,后續的證明負擔可能會太重。它還可以選擇第三種方案,一種更為具象化、更為直觀或更為形象的論辯方案,即求助于其他“同樣重要的”權利。在很多清楚的案例中,通過這種較為形象的“權利對抗權利”策略,政府的論證負擔通常可以大為減輕。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引入對立的權利,論證結構就可能因此而改變,尤其是在出現權利分歧的時候。例如,人們可能質疑,那些對立的權利是否真的存在。如果的確存在,又如何證明它們之間是“同等重要的”呢?為了回應這些疑問,政府可以選擇那種基于目標的方案,或者也可以求助于更為抽象的基于價值的論證。如果選擇后者,政府方面至少要承擔兩項論證責任:其一,它必須建構一個獨特的價值來為那些對立的權利背書;其二,它還必須在兩種價值之間進行比較,從而證明這些權利之間是“同等重要的”。當然,較之于原初的具體化策略,政府的論證負擔被大大加重了。但與此同時,原則論證的范圍也在無形中被進一步拓展了。由于至少涉及兩種價值,無論最后比較的結果如何,更多的道德價值被統合進一個論證結構之中。
盡管論證已經高度抽象,但相反的論辯依然可能出現,因為不同的立場會把不同的價值視為“最基本的”。不過,爭論的存在不意味著論辯會一直持續下去。通常,政治過程會選擇一種弱的(消極的)論辯,即允許一方首先采取行動,并同時為該行動提供辯護;而另一方則負責監督,隨時準備啟動反駁程序展開論辯。就緊急狀態而言,消極論辯擁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具體來說,為了有效應對突發情況,以及其他不可預知的危險,政府在采取最初的行動時僅需承擔較弱的論證負擔,尤其是要首先保證不會實質性地否定或長期限制相關權利。作為其結果,政府的迅速行動會有效安撫民眾,而它的初步論證則會讓民眾相信,民主的憲政結構并沒有因此而終結。
(三)政府對權利的限制并不必然與權利或自由相沖突
如果政府對權利的限制始終或必然意味著對普通民眾之權利的侵害,那么,無論選擇動態的限制方案,還是靜態的權利清單,其實都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區別。不過,如果可以將諸多政治和法律概念視為解釋性的,而且承認它們都是人為建構的概念,它們之間便會有相互融合的可能。當然,這里必然會涉及最基本的解釋策略問題。為了更形象地說明這一點,可以以大家都熟悉的交通規則為例。在通常情況下,每位司機都有權利自由行駛,而且諸多私權利的不同設置其實也可以等同于劃定了各自正常行駛的邊界。但是,如果遇到突發情況,個體的自由行駛就必須要受制于外在的限制,例如政府的限行措施或交警的現場指揮。即使那些外在的限制會使人感到不便,但沒有一個理性的主體會因此而抱怨,因為大家都會承認,政府對某些權利的限制其實是為了那些真正珍貴的權利——例如生命權——不受到損害。換言之,政府的限制行為可以獲得道德辯護。
當然,哪些權利是最核心的,其本身也是一個解釋的問題。究竟選擇哪些權利被列入絕對不可限制的清單,哪些權利屬于一般性的限制性權利,這些問題最終都屬于政治與立法實踐問題,且不同國家的政治和歷史傳統也會影響到最終清單的制定。不過,這些實踐差異的存在并不會掩蓋以上討論的理論價值。無論是否還有人堅持那種必然沖突的主張,也不論他們是否提出各種精致的論證方案,但始終不可否認的是,在理論上,人們的確可以找到一種權利限制與權利之間可以相容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就是動態的權利限制模式的價值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