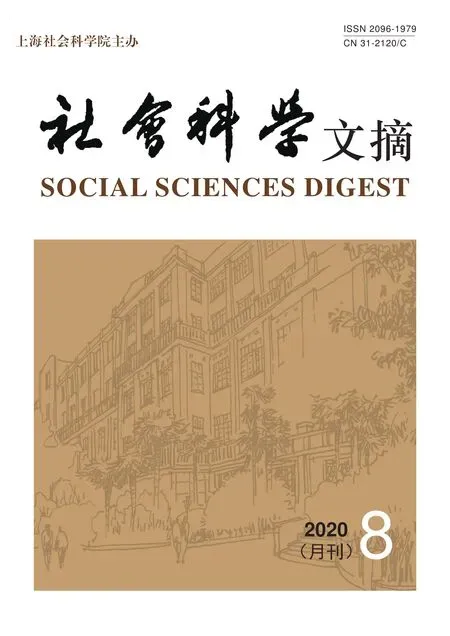當(dāng)代中國新史學(xué)發(fā)展趨向問題芻論
——立足于近代社會史研究的討論
文/王先明
新時期以來的史學(xué)發(fā)展所取得的成果,世所共見。在深刻的內(nèi)在反省和高度對外開放交流的促動下,歷史學(xué)發(fā)展在開拓創(chuàng)新中形成了最具鮮明的時代特色:新領(lǐng)域、新視角、新理論、新方法甚至新話語等,實際上提示著中國史學(xué)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無論是宏觀性研究,還是微觀性探討,史學(xué)研究的新成果林林總總,令人目眩。總體來看,新時期以來的歷史學(xué)取得的成就更突出地體現(xiàn)在新領(lǐng)域的開拓與新體系的建構(gòu)方面。
如何確切地定義“新史學(xué)”,是頗多爭議的一個問題。從20世紀初梁啟超高舉這一旗幟之始,百年來學(xué)人多所論議,旨義所在并不相同,其內(nèi)涵、外延頗多差異。就本文而言,不擬糾結(jié)于概念本身之爭,只是從問題的學(xué)術(shù)聚焦和學(xué)術(shù)討論的可操作性出發(fā),以兩個視角來限定這一學(xué)術(shù)用語的基本義涵:即新時期以來史學(xué)演進的新走向或新態(tài)勢。如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繼出現(xiàn)的社會史、文化史、環(huán)境史、醫(yī)療社會史、區(qū)域史以及新社會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等等,均可一概將之視為“新史學(xué)”之范圍。
一
20世紀80年代,當(dāng)思想領(lǐng)域改革開放的春天已經(jīng)出現(xiàn)后,史學(xué)界的理論思考也進入了極為活躍的時期。學(xué)界對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的歷史命運、中國社會形態(tài)問題、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基本問題等也進行了深入討論。學(xué)術(shù)思想的活躍與相對寬松開放的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共同創(chuàng)造了一種“多元化”理論與方法并存的學(xué)術(shù)生態(tài)環(huán)境。
“歷史發(fā)展動力論”和“歷史創(chuàng)造者”的大討論,成為中國史學(xué)界思想、理論轉(zhuǎn)向的一個重要風(fēng)向標(biāo)。在對“文革史學(xué)”批判的同時,人們也對以階級斗爭為主線、以“革命運動”為主導(dǎo)內(nèi)容的史學(xué)理念提出了強烈質(zhì)疑和深刻反省。同時,面對“以經(jīng)濟建設(shè)為中心”的時代任務(wù)的提出,面對人們社會生活的新變動,中國歷史學(xué)如何確立自己在新時期應(yīng)有的地位和實現(xiàn)自身的學(xué)術(shù)價值等問題,就成為人們必須關(guān)注卻又并非能夠即刻解決的課題。正是在這種特定歷史條件下,人們感受到了“史學(xué)危機”的存在和由此而生成的壓力。
在1983—1985這5年間,“史學(xué)危機”成了史學(xué)界的一個主題詞,起先,是由大學(xué)生和青年學(xué)者提出,繼而,整個史學(xué)界都卷入了“是否存在史學(xué)危機,史學(xué)危機癥結(jié)何在”的討論中。事實上,學(xué)界雖然爭議熱烈,在基本問題上卻沒有獲得多少學(xué)術(shù)意義上的認同,但是,人們卻不能不承認史學(xué)本身面臨著不容回避的時代挑戰(zhàn)和尋求新突破的巨大壓力的問題。各種試圖沖破陳規(guī)舊矩的創(chuàng)新和努力,就在“史學(xué)危機”深沉的壓力下開始萌動了。在這個大背景下檢視新史學(xué)發(fā)展走向,我們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以下兩點:
第一,“史學(xué)危機”無疑是“新時期”史學(xué)轉(zhuǎn)向的歷史前提。“于是,有關(guān)‘史學(xué)危機’的討論成為史學(xué)的自我反省和重新定位,成為對史學(xué)發(fā)展道路的探討和預(yù)見。”“與‘史學(xué)危機’討論同時興起的,是‘三論’熱、歷史發(fā)展合力論和‘歷史創(chuàng)造者’的爭鳴”,是“‘文化史’與‘社會史’的倡導(dǎo)”。社會史不過是當(dāng)時眾多尋求突破的努力之一而已。
第二,從整個20世紀發(fā)展的長程來看,而不僅僅局限于新時期的短程視野,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興起不能定位于新興學(xué)科,也不是新開拓。準(zhǔn)確地說是“復(fù)興”。早在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與文化史就已經(jīng)興起并一時蔚為風(fēng)尚,中國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研究曾經(jīng)達到一個新的高度。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復(fù)興的社會史和文化史來擺脫史學(xué)危機,借以重新建構(gòu)新時期歷史學(xué)的學(xué)術(shù)追求,既不僅僅是基于現(xiàn)實的考量,也不僅僅源于西方學(xué)術(shù)理論的沖擊,更根本性的原因恐怕還是中國歷史學(xué)學(xué)科內(nèi)在發(fā)展的必然走向所導(dǎo)致的。
進入21世紀以來,社會史又以區(qū)域史、鄉(xiāng)村史的拓展和社會生態(tài)史或環(huán)境社會史的建構(gòu),刷新了自己的學(xué)科風(fēng)貌。這些論題的問題意識十分強烈,學(xué)術(shù)研究空間和學(xué)理建構(gòu)內(nèi)涵極其豐富,它們的存在和發(fā)展預(yù)示著近代史乃至整個歷史學(xué)方向和學(xué)科的生成。
二
新時期以來新史學(xué)研究實踐表明,不同學(xué)科間的交叉滲透或跨學(xué)科研究似已成為一種慣性態(tài)勢。雖然人們關(guān)注的歷史理論的學(xué)科來源并不一致,但是,在跨學(xué)科研究取向中所造成的“社會學(xué)化”問題卻未能從根本上引起我們的重視。
“歷史學(xué)的社會學(xué)化”問題,究其根本而言,不在于社會學(xué)概念、理論、范疇引入的多與少的問題,其特指的是“社會學(xué)理論模式”(或社會學(xué)知識結(jié)構(gòu))先行的取向原則:即以先驗的社會學(xué)知識模式來填充特定時段的史料,借以建構(gòu)出社會史的體系;而并不是在對其“社會”歷史運行本身做符合歷史學(xué)學(xué)科規(guī)范的研究基礎(chǔ)上,進而與社會學(xué)理論、范疇進行雙向?qū)W科整合而形成的社會史體系。
正是基于學(xué)科理論建構(gòu)的必要性,我認為這樣一種取向存在著比較明顯的缺憾:比如,社會史的復(fù)興及其學(xué)科建構(gòu)伊始,實質(zhì)上包含著對既有的“革命史”、“階級斗爭史”為主線的中國近代史模式的反思,或者說是一種研究取向的否定。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一個學(xué)科的存在與否或者一個學(xué)科發(fā)展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建構(gòu)起“合理說明與解釋模式”。顯然,作為一個具有學(xué)科或?qū)W科方向的中國近代社會史,無法回避的帶有學(xué)科根本性的問題就是:
第一,中國近代社會史劃分的標(biāo)志是什么?任何歷史研究都無法回避歷史分期問題,它是從根本上影響和制約歷史學(xué)學(xué)科建構(gòu)的基礎(chǔ)性問題。1840年作為中國古代史與近代史的歷史分期,體現(xiàn)著自己的學(xué)科質(zhì)性,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時間標(biāo)志,而是關(guān)系到整個“中國社會史”理論認識和體系建構(gòu)的重要關(guān)節(jié)點,亦即作為歷史界標(biāo)的劃分中國古代社會與近代社會的事件和時間是什么?它體現(xiàn)著社會史之不同于政治史、通史的理論內(nèi)核。而事實上,這一問題在中國近代社會史學(xué)科建構(gòu)和發(fā)展中完全被忽略了。這自然為社會史學(xué)理體系建構(gòu)設(shè)置了內(nèi)在的困境:一方面,社會史的形成原本就具有對“革命史”范式的認知否定,其主旨是建構(gòu)“有血有肉”的“全面”的歷史,以此超越內(nèi)容過于干癟的“革命史”。另一方面,作為近代社會史研究起點卻又沿襲“革命史”的歷史分期。這種學(xué)科理論上的矛盾和沖突,無疑構(gòu)成社會史學(xué)科發(fā)展的困境。既然社會史是不同于“革命史”的另一種新史學(xué)體系,那么古代社會與近代社會的歷史分期為什么等同于革命史的分期?
第二,無論社會史有多少種不同認識和理解,但在學(xué)科定位上屬于歷史學(xué)則并無太多爭議。因此,如何在歷史發(fā)展的長程中揭示和展現(xiàn)“社會”本身的歷史進程和趨向,并以此與經(jīng)濟、文化、政治的歷史演進有所區(qū)分,是其學(xué)科建構(gòu)和學(xué)理認知的前提,如果這個前提被忽略或被模糊,社會之為史則無以為據(jù)。問題是,社會史理論建構(gòu)中的“社會學(xué)化”能夠呈現(xiàn)的內(nèi)容則只是一個“歷史上的社會”的知識體系,即將社會結(jié)構(gòu)、社會生活、社會功能歸置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段之內(nèi)分別加以描述,卻無法真正建構(gòu)或說明社會本身演變的歷史趨向、時代特征以及各社會要素的內(nèi)在關(guān)系。人們所能真正看到的其實是“社會問題”史研究,而非社會史研究。社會史研究的“社會學(xué)化”取向莫甚于此。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關(guān)于區(qū)域史與區(qū)域化取向問題。區(qū)域史并不僅僅是時空結(jié)構(gòu)下的歷史。在此可引述國際區(qū)域史研究的經(jīng)典以為參證。
其一是布羅代爾。他的《地中海與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是區(qū)域史的經(jīng)典之作。從學(xué)科理論的規(guī)范性和準(zhǔn)確度看,布羅代爾提出歷史時段理論,有助于我們對區(qū)域史學(xué)科規(guī)范建構(gòu)的思考。他將歷史時間分為三個層次,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個體時間,分別賦之于歷史學(xué)特質(zhì)的概念: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這是一個蘊含全面的時間空間和經(jīng)濟、文化、制度與人事的歷史學(xué)范疇,具有學(xué)科建構(gòu)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其二是濱下武志。他提出的“亞洲經(jīng)濟圈”理論對我們正確地認知區(qū)域史規(guī)范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他的研究視角是以“地域性”到“區(qū)域性”再到“全球性”的線索展開的,進而對“亞洲經(jīng)濟圈”理論和“全球化與東亞區(qū)域歷史”相關(guān)問題進行探討和研究。這種視野,就是以探求歷史學(xué)規(guī)律的“總體史”為目標(biāo)。這一模式建立的基點恰恰提示我們:區(qū)域史并不僅僅是相對于民族國家史的地方性的歷史模式,它是一個新的整體史的研究視野和方法。
在近年來的“區(qū)域化”研究取向中,學(xué)術(shù)界的盲目跟風(fēng)和隨波逐流的非理性傾向是十分明顯。對此問題,有學(xué)者提出進行“跨區(qū)域研究”或“區(qū)域比較研究”作為彌補。然而,這仍然未能切中要領(lǐng)。因為,跨區(qū)域的區(qū)域史研究和區(qū)域史比較研究并不具有操作性。在已經(jīng)失范的學(xué)術(shù)狀態(tài)下,“區(qū)域”并無限定,完全是研究者個人隨意設(shè)定的范圍,何謂跨區(qū)域當(dāng)然也就無從說起。
如何在學(xué)術(shù)規(guī)范意義上建構(gòu)整體史意義上的區(qū)域史?由于區(qū)域范圍的界定本身即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區(qū)域史的實踐也就難以在規(guī)范的學(xué)理層面獲得一致認同。區(qū)域史是現(xiàn)代歷史學(xué)發(fā)展進程中的學(xué)術(shù)建構(gòu),它不是歷史本體存在(如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典章制度等)。正因為如此,學(xué)術(shù)規(guī)范的建構(gòu)尤其關(guān)鍵,否則無法進入真正的學(xué)術(shù)話語體系,致使所有的研究內(nèi)容都可標(biāo)舉為區(qū)域史,而實際上又在消解著真正的區(qū)域史。
三
新時期以來的歷史學(xué)一定意義上就是伴隨著新理論、新方法的不斷涌現(xiàn)和植入而興盛成長起來的。1980年代之后,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長期被封禁的各種理論、學(xué)說和思想,一時大幅度地涌入,為史學(xué)研究的取向、史學(xué)體系的重構(gòu)、史學(xué)觀念的更易等等,提供了充足的條件。稍加追記則不難發(fā)現(xiàn),新時期以來在史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中,對于理論與方法的熱衷和努力已經(jīng)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可問題是,新時期以來歷史學(xué)理論的基本態(tài)勢在于:一味忙于求新與引進,而來不及消化與思考;除了在史學(xué)理論界留下了思想的足跡之外,并沒有引導(dǎo)中國史學(xué)產(chǎn)生一個實質(zhì)性的改變。更為突出的問題是,現(xiàn)在歷史學(xué)的學(xué)位論文、學(xué)術(shù)論文和專著,動輒引用西方學(xué)者(哪怕是二三流學(xué)者)的論點展開自己的論述,而不再引用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的論點,這幾乎成為新的教條主義。
新時期的史學(xué)發(fā)展進程中形成多種面相,其理論基點和研究方法已經(jīng)日趨多元。這一發(fā)展態(tài)勢其實蘊含著一個一個相對主導(dǎo)的訴求,即對以往史學(xué)體系詮釋框架的解構(gòu)——當(dāng)然,有些是“無意”的解構(gòu)。過去30多年,學(xué)者在理論方法的追求上做足了功夫,新的研究方法層出不窮,但其在學(xué)術(shù)建樹或?qū)W科建構(gòu)的實效方面,卻未能獲得學(xué)界的認同。對于走向新時代的歷史學(xué)的學(xué)術(shù)使命而言,系統(tǒng)性的學(xué)理詮釋體系的建構(gòu),遠比以往體系的“解構(gòu)”更為重要。
特別值得關(guān)注的是,新世紀以來新XX史的相繼推出劃出了一條刻意“求新”的當(dāng)代史學(xué)演進軌跡;逐新風(fēng)尚一路猛進,雖然其論證內(nèi)容或有不同,但其思維方式和立論模式卻基本一致。某種意義上說,它構(gòu)成了新世紀以來史學(xué)演進的總體趨勢。其中,的確也有務(wù)實求真的創(chuàng)新性成果的推出,為新時期史學(xué)的開拓建構(gòu)助力頗多;但也出現(xiàn)了一些逐新求異的流風(fēng),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論框架中添加中國史料,結(jié)構(gòu)出所謂新的成果。流風(fēng)所向影響頗大,值得我們認真反思。
從許多研究成果看,他們論定的“新”是基于研究理念、方法、視角方面,甚至有些研究只是換了一套話語模式:新詞、新語、新概念、新樣式,而這些并不構(gòu)成新學(xué)科、新領(lǐng)域、新方向的要件。就學(xué)術(shù)研究而言,新方法、新理論、新視角等是可以運用在幾乎所有學(xué)科研究中的,它們同樣適用于政治史、經(jīng)濟史,乃至事件史研究。研究理論和方法的趨新意味著工具性或研究手段的變化,卻并不能由此形成或建構(gòu)一個新學(xué)科或新領(lǐng)域。
無論什么新方法、新視角、新理論,它們既從不屬于,也不可能專屬于新XX史的特殊領(lǐng)域。學(xué)術(shù)概念和學(xué)術(shù)范疇?wèi)?yīng)該在嚴謹、準(zhǔn)確、規(guī)范和科學(xué)的前提下精確凝練。倘若從更為嚴謹?shù)膶W(xué)理層面上推敲,這些問題是否值得三思呢?
四
檢點歷史學(xué)的行程,我們當(dāng)深刻感悟,在一味追逐求新的風(fēng)向引導(dǎo)下,新史學(xué)的發(fā)展似乎正在疏離史學(xué)求真的學(xué)科特質(zhì)。從科學(xué)的觀點來看,學(xué)者只應(yīng)問一學(xué)之真?zhèn)味粏査男屡f。求真乃史學(xué)之所以為史學(xué)的根本宗旨。要而言之,史學(xué)之求真可分四個方面:
其一是考訂史料之真實。史料是史學(xué)研究的基石,是人們認識、解釋和重構(gòu)歷史所必須的材料。所有史料都是人的活動的遺存,與人本身密切相關(guān),而人始終受到利益的制約和影響,因此史料本身也當(dāng)然地受限于各種利害關(guān)系——即使不是刻意偽造史料。歷史資料的形成非常復(fù)雜,撇開歷史資料所反映的歷史真實性不談,就資料本身而言,要看清它的真實面目顯得非常不易。因而,歷史研究要求得歷史之真,首先得辨析史料之真。
其二是揭示史實之真相。史料學(xué)只是歷史科學(xué)中的一門學(xué)科,史料學(xué)不等于歷史學(xué)。只搞史料的考訂、編排,最多能把一個個的個別史實弄清楚,而不能找出各種史實之間的互相聯(lián)系,真正呈現(xiàn)歷史真相。“闡明歷史真相”是歷史學(xué)家的責(zé)任,這既是歷史學(xué)的學(xué)科準(zhǔn)則,也是中國史學(xué)秉筆直書的傳統(tǒng)品格,盡管史學(xué)研究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學(xué)術(shù)流變,呈現(xiàn)著不同的特色,但揭示史實之真相卻是史學(xué)之所以為史學(xué)的基本特質(zhì)。
其三是構(gòu)建史學(xué)之真知。歷史學(xué)在不斷追求真知的過程中,將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規(guī)律性知識和那些被千百次研究實踐證明了的成功的經(jīng)驗進行科學(xué)抽象,建構(gòu)起史學(xué)的學(xué)識真知,以指導(dǎo)人們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史學(xué)研究建構(gòu)歷史的同時,也是史學(xué)知識體系的建構(gòu)。就史學(xué)而言,每一次重大的變革都意味著其知識體系的變革,也意味著史學(xué)知識體系在不斷求真過程中的自我完善。不斷揚棄偽識和建構(gòu)真知,是史學(xué)社會功能的體現(xiàn)。辨?zhèn)吻笳媾c實事求是,是史學(xué)學(xué)科知識體系建構(gòu)的內(nèi)在價值。
其四是洞悉歷史之真理。處理史料以了解史實,須通過解釋始能達成。史學(xué)研究的終極目標(biāo)或者其學(xué)科魅力之所在,就在于對于人類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不竭探求和獲取。
如何在新時代的劇烈變動與在不斷創(chuàng)新的學(xué)術(shù)追求中,始終堅持歷史學(xué)求真的宗旨,是我們必須堅守的學(xué)科原則。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達致“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xué)的基礎(chǔ),承擔(dān)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習(xí)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xué)大會的賀信》)的學(xué)科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