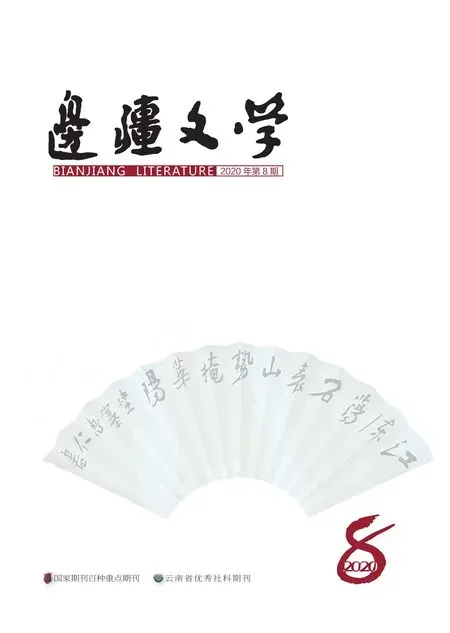祝立根近作閱讀札記
☉谷禾
祝立根是云南詩歌群落近年來為詩壇貢獻出的獨具個性的青年詩人,雖然出道時間不長,但作為當下漢語詩歌寫作的新生力量,祝立根的寫作已經在詩壇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說,祝立根已經是一位從云南邊陲走向全國的詩人。在此我也代表《十月》雜志對祝立根詩歌作品研討會的舉行表示衷心的祝賀。
祝立根的詩歌寫作之所以能取得豐沛的創作成績,源于他自身的不懈努力。我注意到祝立根是一個不愛熱鬧的詩人,我和他不止在一次詩歌活動上相遇過,他不太扎堆,尤其在云南的活動,總是默默地為大家服務,不但研討會上話也很少,平時在微信朋友圈里很少露面和發言。在快節奏、碎片化的互聯網時代,能安靜的閱讀和寫作,已經變成一種稀缺品質。從這次研討會提供的立根談詩的文章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對中國古典文學和哲學,中外現當代詩歌都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涉獵和研究性閱讀,形成了自己的思考、見解和主張。這對年輕詩人來說是相當難得的。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扎根,它有力地保證了祝立根詩歌寫作源泉的豐富性和有效性。
有一段時間,有人把我拉進了一個影響比較大的微信群,發現群里的詩人一有新作貼出來,群友馬上紛紛贊其“杰作”,甚至“每一首都是杰作”。我不反對天才,但天才畢竟鳳毛麟角,即便天才的杰作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這樣的稱贊如果不是無知和盲目,一定是廉價的奉承。我相信更多的寫作者是通過后天的不斷學習、積累成長起來的,哪怕已經入了互聯網時代,我還是更信任相信有漫長學習期的詩人。祝立根這樣的涉獵和研究性閱讀,已經和正在為他取得更大的創作成就奠定深厚基礎。
但祝立根并不是一個書齋型的詩人,從他所提供的這些鮮活的詩歌文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不是在對世界冷眼旁觀,而是投入了極大的生命熱情,他有著用腳步丈量世界的雄心和時間,他把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都交付給了天地自然,從而保證了詩歌寫作的豐富性、現場性和田野氣息。這是一條正路,也只有這樣,你寫下的詩歌文本才能“思接千載,視通萬里”,有人間冷暖,有世態炎涼,有眾生歌哭。他才能“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詩歌作為一種古老的語言文明,才有資格記錄和見證我們的時代。
從祝立根詩歌新作里,還能夠讀到祝立根發現和處理處理日常生活的詩意的嫻熟技藝。祝立根自己也在文章中反復強調日常事物的重要性,指出“這些我們看見、聽見、聞見,用手指觸碰,撞上我們身體的日常的事物,是詩歌的基本的源泉之一”。這讓我想到了大詩人杜甫。杜甫之為歷代所推崇,除了他的集大成和繼往開來,他的家國情懷之外,我覺得不容忽視的一點還有他是真正的寫日常的大師,我們甚至可以說,有了杜甫之后,中國古典詩歌才有了日常的屬性,后世讀者才從詩歌里看到被各種歷史教科書所忽略的另一種歷史,“詩史”也才名副其實。所以在我看來,尤其在當下,對詩歌寫作的對日常性的呈現不足是需要擔心的,因為更多的詩歌和詩人仍然漂在天空中,活在虛無中,在寫著不著邊際的所謂的詩。
這里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日常生活如何入詩?是不是只需要呈現碎片化、故事化、段子化的所謂的事實?可能有人會說,事實當然重要,正是無數的碎片化的事實才構成了我們身處的現實。但在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一種被表象和塵埃遮蔽的日常現實,它仍然需要寫作者去像卡夫卡那樣,透過重重遮蔽看到本質,找到并呈現出日常生活的詩意的核心。
回到祝立根的詩歌,祝立根的詩歌寫作是仍然處在一個動態的變化中的,但不管怎樣變化,我們總能在他的文本里看到鮮明的云南元素,看到地域文化在詩人成長過程中留下的鮮明烙印。他觀察和思考世界的立足點和視野里,都有云南詩歌這個源頭在。這是祝立根之所以成為祝立根的核心。
也說兩點建議。云南詩歌傳統不是某一個人,甚至他自己,也是這一傳統的組成部分,我們能從他的詩歌里看到前輩云南詩人的影子,這種影響作為營養給詩人帶來教益,從另一個角度講,也帶來了局限。對于祝立根,我覺得他從現在開始,就有必要嘗試著從這些影子里走出來。這一過程,也是他最終成為成為獨一無二的漢語詩人祝立根的過程。還有一點,我覺得祝立根詩歌文本里大詞的使用有些多。我不是說大詞不能用,而是大詞在當下的詩歌文本內外已經成為爛俗,其內在很難再生成新義,使用應該慎之又慎。真正杰出的詩人有自己的辭海,有重新發明和建設全新的詩歌語言的能力。在這一點上,我也相信終有一天,祝立根會給他的讀者不斷帶來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