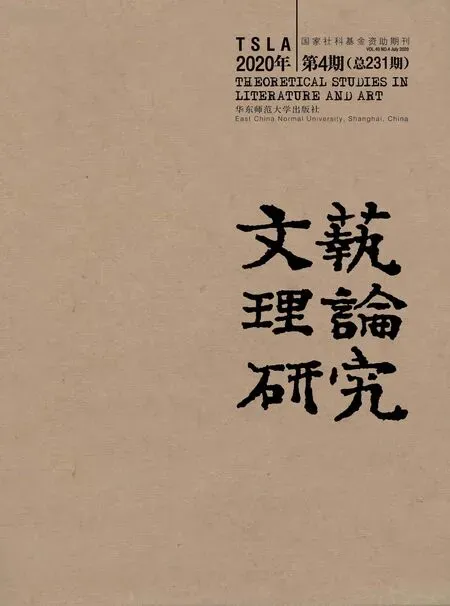頌神背后的瀆神: 奧維德流放詩歌中的皇族形象
李永毅
如學者米拉爾所言,在古羅馬詩人中,唯有奧維德是真正意義上的“奧古斯都詩人”(Millar1)。我們從奧維德的自傳詩(Ovid,P.OvidiNasonisTristia4.10)中得知,他出生在公元前43年,屋大維正是在這年正式進入羅馬政治圈的核心,此前一年,愷撒遇刺身亡,標志著羅馬共和國進入了最后的掙扎期。屋大維于公元前27年成為羅馬皇帝,公元14年去世,此后僅三年,奧維德也撒手人寰。和前半生經歷了殘酷內戰的賀拉斯、維吉爾等人不同,奧維德是在所謂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之下長大的,他的一生幾乎與屋大維的統治期完全重合。另外,和深受屋大維賞識的那兩位大詩人不同,奧維德與皇帝有一段直接的恩怨。公元8年,他因為《愛的藝術》(ArsAmatoria)和“某個錯誤”(P.OvidiNasonisTristia2.207)被屋大維流放到黑海之濱的托密斯(今羅馬尼亞康斯坦察),一直到死都未獲得屋大維和其繼任者提比略的赦免。①因此,奧維德對待屋大維的態度自然成了學者們關注的一個焦點,其相關爭論從未止息。
一
米拉爾認為,奧維德的流放詩歌表達的絕不是“顛覆性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情緒”,而是一位“皇權的忠實擁護者發出的憤懣之聲”(Millar1),因為詩人居然被自己心儀的政權拋棄,并且始終不得寬宥。在這位評論者看來,奧維德覺得羅馬才是自己理所應當的居住地,因此身處托密斯的詩人既是被拒的“局內人”,又是邊疆的“局外人”,流放詩中的情感便在這樣的矛盾中展開(Millar16)。在此基礎上,加拉索提出,奧維德不僅相信屋大維從情理上必須赦免自己,而且他還主動提出了交換條件: 一旦回到羅馬城,他就會改變此前曖昧的詩風,專心做歌頌奧古斯都政權的御用詩人。加拉索舉出的例子包括慶祝提比略凱旋的《黑海書簡》第2部第1首、慶祝執政官龐佩烏斯和格萊奇努斯就職的《黑海書簡》第4部第4首和第7首。雖然這些詩與奧維德原來的作品在風格上有延續性,但就內容而言卻是新的城市頌歌。在《黑海書簡》第4部第13首中,奧維德曾告訴朋友加茹斯,他用當地的蓋塔語作了一首贊頌屋大維的詩。加拉索的解讀是,即使在遙遠的蠻域,奧維德仍是“維護皇室價值觀和利益的代言人”(Galasso205)。哈比奈克認為奧維德不僅在一般意義上忠于屋大維,更卷入了“羅馬帝國主義的計劃”(Habinek152),是帝國邊疆一位自覺的“文化同化者”(161)。最早對奧維德流放詩歌做整體研究的埃文斯態度相對溫和,但他也認為,這些作品并沒有諷刺屋大維政權,我們的理解不應違背字面的意思(Evans7)。
然而,另一些學者深信,奧維德詩歌的藝術性主要就體現為反諷,字面的意思恰恰最不可靠。巴齊艾西在《詩人與君主: 奧維德與奧古斯都話語》的第二章通過細讀揭示,奧維德早期作品的輕浮和詼諧在流放詩歌中仍然普遍存在,他將屋大維塑造成揮舞雷霆的神也有多重的反諷意味,甚至受到了盧克萊修《物性論》的影響(Barchiesi52—77)。克拉森也發現,在這些作品中,詩人借助內容和語氣的不一致制造出反諷效果。她注意到,奧維德對皇室的多處影射都是極不恭敬的,夸張的奉承正是為了掩蓋傲慢的幽默。她也為詩人的僭越態度作出了心理解釋: 奧維德或許從一開始就預感到屋大維絕不會寬恕他,所以并不打算通過降低身段來消除對方的怒氣(Claassen,ThePoet29—51)。
雖然反諷廣泛存在于奧維德的流放詩歌中,但若據此聲稱,奧維德對屋大維一貫持抵制態度,那么這樣的說法也并不能讓人信服。因為《哀歌集》和《黑海書簡》中的大量作品證明,奧維德的確在盡最大努力爭取皇帝的赦免,至少希望后者能把他改判到離羅馬更近的流放地。事實上,在朋友馬克西姆斯的斡旋下,屋大維對奧維德的態度的確有所緩和,然而公元14年馬克西姆斯和屋大維先后去世,奧維德的夢想徹底破滅,因為繼任的皇帝提比略和他母親利維婭都憎惡奧維德。除了馬克西姆斯,奧維德求助的對象還包括布魯圖斯(他的文學代理人)、阿提庫斯(評論家)、與皇子提比略親近的梅薩里努斯和科塔兄弟、皇子日耳曼尼庫斯和色雷斯國王柯蒂斯,他甚至強迫自己給向來厭惡的提比略寫凱旋頌歌(Ovid,P.OvidiNasonisExPonto2.1)。可以看出,奧維德確實在積極地為改變自己的處境而努力。
奧維德的努力之所以屢屢受挫,與他的性格有極大關系。如前所述,奧維德是在屋大維統治下長大的,他無需像維吉爾和賀拉斯等人那樣在共和與專制之間作出選擇。對政治無甚興趣的他作出的是一個藝術選擇——棄政從文。然而在詩歌內部,他仍然必須選擇,或者主動融入奧古斯都文化秩序,或者順從自己的心性。他選擇了后者,在他自己看來,這樣的選擇或許算不上選擇,就如同他出口成詩一樣自然。但在皇帝的眼中,這樣的選擇就是站在了政權的對立面。屋大維選擇隱忍不發時,奧維德似乎享受著著名詩人的光環,但一旦皇帝抓住機會反擊,他便立刻跌落云端。當他流落天涯的托密斯時,他與屋大維一個是罪犯,一個是皇帝,有天淵之別。按照正常的理解,奧維德唯有示弱才有希望獲得赦免,他心里當然也明白這一點。但是藝術家的倔強和對藝術邏輯的執著卻讓他情不自禁地觸龍鱗、犯忌諱。
所以,奧維德流放詩歌真正令人驚奇的是,情境的弱勢和修辭的強勢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永遠忠于藝術而不是忠于權力的他即使在最艱難的處境中、在最卑微的地位里也不忘以藝術的手段反擊他的迫害者。雖然從政治上來說,這種反擊是幼稚的、情緒化的,絲毫不能改變他的處境,但從讀者的角度來說,它卻讓這些作品的主題得以深化,并讓旁觀者洞察到羅馬政治和羅馬掌權者的性質。他的藝術直覺往往超越了他的政治直覺,他的作品比他自己更具透視的本領。換言之,本無明確政治立場的奧維德因為藝術的執拗,成了一位“被動”的反對派。他在總體上或許并無抨擊政權的設計,但創作的習慣和情不自禁的想象卻讓他的作品具備了難以壓制的顛覆性。在最被人詬病的神化皇族的“阿諛”之處,這種顛覆性往往最突出。
奧維德對羅馬皇族最犀利的諷刺就藏在最為評論者所不齒的《黑海書簡》第2部第8首中。在詩的開頭,他向朋友科塔表示感謝:“馬克西姆斯,我最近收到你寄來的像章,/你給我的神,愷撒在愷撒身旁,/為了讓你的禮物有一個完滿的數字,/利維婭也和愷撒出現在一起。/幸運的白銀,比所有的黃金更有福分,/原是粗糙的錢幣,現在已通神!/即使你給我一堆財寶,也不如這厚禮——/你送至這片海岸的三位神祇。/能夠看見神,感覺他們的存在,仿佛/與真神一起交談,的確很幸福。”(P.OvidiNasonisExPonto2.8.1—10)②奧維德對屋大維、提比略(兩人都被稱為愷撒)和利維婭像章的頂禮膜拜讓最同情他的學者都難以忍受,例如埃文斯就聲稱,奧維德“將所有對皇權的常規奉承元素聚合、重組,造出了他放逐詩歌中最周詳的一首贊美屋大維和皇室成員的詩,甚至在整個奧古斯都文學中也獨一無二”(Evans26)。我們若要為奧維德辯護,其實不用考慮奧古斯都時代普遍的獻媚風氣或者自古希臘以來的將君主奉為神的傳統(Dodds236—69),只需專注于文本就足以發現詩人設下的機關。“仿佛”(quasi)一詞無論是否有諷刺意味,都消解了皇室“真神”的地位。第21—22行針對屋大維的設問句“這是錯覺嗎,還是他真的透出憤怒,/表情隱隱有一種嚴厲和冷酷?”也暗示皇帝并不仁慈。第29行將皇后利維婭稱為屋大維“在世上完美的伴侶”,恐怕整個羅馬都沒人相信。她與屋大維的丑聞人盡皆知,兩人為了成親,前者與提比略的父親尼祿閃電離婚,后者在第二任妻子產女當日拋棄了她,兩人結婚三月后利維婭便誕下了皇子德魯蘇。第31—32行說屋大維和提比略“同為美德的典范”,后者的“品格顯然是”前者的“翻版”,然而提比略無論在他的時代還是后世都遭人憎恨,絕無美德可言,古羅馬大規模的告密政治也從他開始。如果他是屋大維的翻版,屋大維的“美德”也可想而知。奧維德向提比略的像章祝愿道:“愿你的父親與涅斯托爾比壽,母親/與西比爾齊齡,讓你長久侍奉。”(P.OvidiNasonisExPonto2.8.41—42)據荷馬說涅斯托爾活了三代人的壽命,羅馬先知西比爾相傳活了不少于一千年,如果皇帝和皇后真活這么長,就是人中之妖了,作為屋大維繼子和皇位繼承人的提比略也絕不會高興。接下來詩人又對利維婭祝福:“愿殘酷的日耳曼從你身邊奪走的德魯蘇/成為你此生中喪子的唯一悲劇。”(2.8.47—48)利維婭的次子大德魯蘇于公元9年在日耳曼前線夭折,奧維德的話看似祝愿,效果卻是用舊痛刺激皇后,甚至隱隱有不祥之意: 利維婭一共兩個兒子,如果再一次喪子,就絕后了。在接近末尾的地方,奧維德說自己無法回羅馬面見皇族:“既然命運決不肯給我這樣的機會,/我只好拿工匠制造的肖像來敬拜。/人們也這樣認識高天隱匿的諸神,/膜拜的不是朱庇特,是他的替身。/最后,求你們關注,別讓這些我永遠/珍藏的形象留在可憎的地點。”(2.8.59—64)“替身”(forma)呼應著前文的“仿佛”,暗示了神靈之說的虛妄。細讀全詩之后,我們還會認為奧維德在皇室“諸神”面前是奴顏媚骨嗎?
二
由于處境的艱難,奧維德晚期作品的諷刺有時的確埋得很深,需要學者做一番偵探的工作。哈斯齊對《哀歌集》第3部第1首中地理空間的政治解讀令人稱賞(Huskey 17—39),可以作為一個精彩的樣例幫助我們領略奧維德深藏不露的精妙技藝。③在這首序詩里,奧維德讓一位羅馬人帶著自己的詩集穿過羅馬城,去尋找可以棲身的圖書館。哈斯齊敏銳地發現,在奧維德呈現給我們的羅馬景觀中,某些重要的地標消失了或者只有幽靈般的存在。他認為,至少有三處遺漏是故意的。首先,在描繪羅馬廣場時,奧維德沒有提到任何一座愷撒或屋大維修建的公共建筑物,例如元老院大廈、埃米利亞會堂、尤利亞會堂、大講壇和愷撒神廟。但他卻提到了羅馬第二代國王努瑪的宮殿和維斯塔神廟。哈斯齊指出,公元前29年后,沿圣道(via sacra)向東走的人無法直接看到奧維德在這里介紹的兩處建筑,因為愷撒神廟擋住了視線。要看到它們,需要沿著愷撒神廟南面的一條支路走,并穿過奧古斯都拱廊,然后右邊才是維斯塔神廟,左邊是努瑪宮殿。奧維德完全不提必經的愷撒神廟和奧古斯都拱廊,應當不是無心的(Huskey18—21);而他著意突出的兩座建筑在羅馬漫長的宗教傳統中無疑占據著中心位置,因為努瑪是羅馬宗教制度的創立者,而維斯塔圣火則是羅馬國運的象征。
這兩處建筑也將我們的目光引向被奧維德藏匿的另一處景觀。按照羅馬的傳統,大祭司的總部在努瑪宮殿,而他的居處就在維斯塔神廟旁的“公家”(domus publica),即使愷撒就任大祭司后也未曾違背這一規定。但屋大維成為大祭司后,卻將自己在帕拉丁山的宅邸當作了羅馬的宗教中心。他將宅邸的部分空間用作大祭司的辦公場所,并在里面建了一座維斯塔神祠,以與原來的宗教傳統相一致。然而,當擬人的詩集來到屋大維的住所前面時,奧維德完全沒有借它之口提及這座宅邸的宗教功能。故意忽略帕拉丁山上的大祭司建筑,卻突出羅馬廣場上的努瑪宮殿和維斯塔神廟,等于抹除了屋大維將傳統宗教據為己有的努力。詩中導游對這兩座古老建筑的認可也代表了與奧維德相同的民間立場。
還有一處隱匿的地標則是羅馬城精神上的地理中心——卡皮托山,這似乎令人驚訝,但奧維德無非借此凸顯了羅馬城的一個政治現實,那就是皇帝的宅邸已經取代卡皮托山成為了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Edwards71)。原本存放于朱庇特神廟的西比爾預言書也被轉移到了帕拉丁山上的阿波羅神廟里。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座新的卡皮托山和一位新的朱庇特誕生了。奧維德說這座建筑“仿佛是神的府邸”(digna deo),按照紐蘭茲的看法(Newlands66—67),詩人是在暗引《埃涅阿斯紀》中圣哲埃凡德爾告誡埃涅阿斯的話:“異鄉人,要敢于鄙視財富,也要讓自己/堪與神媲美(dignum deo)。”(Virgil8.364—65)既然收養屋大維的愷撒家族自稱是埃涅阿斯之子尤盧斯的后代,屋大維修建豪奢宮殿的行為就是背叛了先祖的美德。然而,無論是皇帝用建筑重塑羅馬價值觀的企圖,還是在舊宗教上移花接木的伎倆,對于底層人而言都沒有取得效果。詩中的導游依然將羅慕路斯修建的最古老的朱庇特神廟視為“羅馬城的根”(Ovid,P.OvidiNasonisTristia3.1.32)。整首詩的地理空間安排強烈地傳達了這樣的訊息:“雖然他權勢熏天,雖然他有神圣之名,雖然他能改變城市的物質和宗教景觀,這位皇帝畢竟不是朱庇特。”(Huskey32)
除了高超的空間敘事,奧維德也非常善于挖掘傳統詩歌資源來達到自己的藝術意圖。克拉森就注意到,音律與情感在他的流放詩歌中有隱秘的聯系(Claassen, “Meter and Emotion”351—65)。從卡圖盧斯以來,在愛情哀歌中用化名表示女主人公就已經成為慣例,例如卡圖盧斯的萊斯比婭(Lesbia)對應于現實中的克勞迪婭(Clodia),后來加盧斯的呂柯麗絲(Lycoris)對應于庫特麗絲(Cytheris),提布盧斯的黛莉婭(Delia)對應于普拉尼婭(Plania),普洛佩提烏斯的辛提婭(Cynthia)對應于霍斯提婭(Hostia)。這種對應關系建立在音律的對等性上,要求兩個名字的格律特性一致。克拉森指出,從音律上說,Livor(妒忌)和皇后的名字Livia(利維婭)是等價的,所以奧維德兩次(P.OvidiNasonisTristia4.10.123;P.OvidiNasonisExPonto4.16.47)向擬人的“妒忌”呼告時,有可能是在影射他的皇族迫害者。同理,在《哀歌集》第5部第1首第53行,根據暴君帕拉里斯的名字(Phalaris)在行中的位置,也可判定它與屋大維的封號“奧古斯都”(Augustus)在音律上對等(“Meter and Emotion”354)。
奧維德是將哀歌體運用到極致的古羅馬詩人,他善于用這種體裁的各種傳統元素來暗中傳遞自己的信息。以《哀歌集》第1部第2首為例,學者英格哈特發現,如果我們保持對詩歌體裁尤其是哀歌體的高度敏感,就會從詩中讀出許多隱藏的含義(Ingleheart73—91)。這首詩描繪了詩人在流放途中遭遇的海上風暴,作為緊接著序詩出現的作品,它具有為奧維德流放詩歌定調的重要性。詩的開頭有強烈的史詩色彩:“海神與天神(除了禱告我還有什么?),/別讓我備受顛簸的小船碎裂,/我也求你們,別煽動強大愷撒的憤怒!/時常一位神逼迫,另一位佑護。/伏爾甘反對特洛伊,阿波羅支持特洛伊,/維納斯襄助,帕拉斯卻充滿敵意。/朱諾為圖爾努斯而憎惡埃涅阿斯,/他卻平安無虞,因為有維納斯。/兇狠的涅普頓數度向尤利西斯索命,/密涅瓦卻一再相救,與伯父抗衡。/盡管我遠不如這些英雄,可誰能阻止/某位神為我抵擋另一位的恨意?”(P.OvidiNasonisTristia1.2.1—12)。評論者都意識到,奧維德在這里顯然借用了《埃涅阿斯紀》和《奧德賽》中的類似情境,激活了海難與神意之間的聯系。④然而,詩人卻突出了一點差異,那就是在史詩的神話世界里,至少還有部分神可能庇佑遭難者,而在屋大維統治的現實世界里,卻沒有任何與皇權對抗的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哀歌體的維納斯是唯一出現兩次的神,她讓諸神之間的爭斗變成了史詩體和哀歌體的對峙。
哀歌體的色彩在下文不斷強化。奧維德寫道:“駭人的南風卷走了我的禱告,嚴禁/它們飛向我心中祈求的慈神。”(P.OvidiNasonisTristia1.2.15—16)英格哈特提醒我們,風站在屋大維一邊迫害詩人的形象影射普洛佩提烏斯《哀歌集》的開頭(Propertius1.17),在那里,劫后余生的詩人聲稱風在海難中幫他的情人辛提婭折磨自己。這樣,屋大維就與情愛詩中反復無常、折磨情夫的女主人公等同了(Ingleheart80)。如此的置換看似滑稽,卻也符合真相。奧維德這位“繾綣情愛的游戲者”不正是因為《愛的藝術》遭到皇帝流放嗎?在此框架下,對風暴中舵手的描寫便具有了雙重意味:“舵手已茫然,不知什么該躲避,什么/該追逐: 面對此亂象,‘技藝’也無措。”(P.OvidiNasonisTristia1.2.31—32)“亂象”的拉丁原文是“ambiguismalis”(變幻無常的災難),但“ambiguis”也可能暗示,詩句的含義是曖昧的。擬人的“技藝”(ars)可能也指“Ars”(奧維德在流放詩歌中反復提及的《愛的藝術》)。因此,舵手的形象也是奧維德自己的形象,他因為《愛的藝術》帶來了未曾預料的災難而驚惶無措。如果這樣,詩中的船便象征著哀歌體的情愛詩,詩中的神屋大維便代表了羅馬帝國所倡導的為皇族鍍金的史詩,它決意摧毀這種不肯被納入國家秩序的體裁。
三
在奧維德所寫的全部流放詩歌中,屋大維的形象始終是與朱庇特糾纏在一起的,很多時候更是完全重合。《哀歌集》和《黑海書簡》采用了整體式的神話化策略,與此框架相配合,讓屋大維扮演朱庇特,讓利維婭扮演朱諾,讓皇族成為神族,這是一種方便的藝術手段。當然,朱庇特和朱諾的文學形象也拓展了奧維德探討權力、公義、創傷等主題的空間。
在塑造屋大維形象時,“在否定中肯定”是奧維德的常用策略,在陳述層面否定的內容,常被他在意象層面加以肯定。他如此安撫那些因恐懼而不敢幫助自己的朋友:“并非埃特納荒穴里的波呂斐摩斯/或者安提法忒斯聽你的說辭,/而是一位父親,和藹,仁慈,寬容,/他時常不動電火,只響雷霆,/做出嚴酷的決定,他自己也會悲傷,/懲罰別人時,他時常把自己捎上。”(P.OvidiNasonisExPonto2.2.133—38)雖然詩人聲稱皇帝不是兇殘的獨眼巨人波呂斐摩斯或者食人族頭領安提法忒斯,他卻故意在提及屋大維時讓我們聯想到二者的形象。不僅如此,他在流放詩歌中反復描繪的朱庇特是一位隨時可能降下雷霆、奪人性命的神。這樣一幅可怖的畫面早在《哀歌集》第1部第1首中就已經定格。詩人極力形容自己劫后余生的驚恐:“愿威嚴殿宇和威嚴諸神饒恕我!雷霆/就是從那里降下,落在我頭頂。/我記得,居住圣所的諸神都分外仁慈,/但受過他們傷害,我難免怵惕。/鷹啊,你翅翼的微小振動都會驚嚇/鴿子,若它曾傷于你的利爪;/羊羔也不敢遠離圍欄,如果它曾經/從野狼貪婪的牙齒間死里逃生;/帕厄同即使沒死,也會避開天空,/愚蠢渴望的馬車,絕不肯再碰。”(P.OvidiNasonisTristia1.1.71—80)因此,讓詩集替自己向皇帝說情時,奧維德一再提醒要小心: 要注意運氣、時機、皇帝的心情和言辭,“要小心,別為了幫我,反而害我——/我雖存希望,心里的恐懼倒更多。/千萬別再煽起他已趨熄滅的憤恨,/再給我添加新的罪名,小心!”(1.1.101—104)對妻子和朋友的類似警告貫穿流放詩歌的始終,制造出一種“壓抑的、充滿焦慮的氛圍”(Casali84)。
倘若恐懼僅限于詩人自己,或許無損皇帝的仁慈形象。然而,在流放途中和流放的前幾年,奧維德寫給朋友的書信體詩(五部《哀歌集》)都沒有點出收信人的姓名。這部分是由于詩人的擔憂,部分也是因為朋友的要求,他只能通過某種心照不宣的描寫暗示收信人的身份。雖然這種做法未必能保護此前與他過從甚密的朋友,但作為一種修辭手段,它無疑突出了“懷疑”在詩集中的“策略性中心位置”(Oliensis176),從側面暗示了奧古斯都時期壓抑的政治氣氛。即使在已公開絕大多數收信人姓名的《黑海書簡》中,奧維德仍在費力勸說某位匿名的朋友去相信他的名字出現在自己的詩里不會招致危險:“可是你,當人民生活在如此的賢君統治下,/竟相信安慰放逐者值得害怕?/若布西里斯或那位喜歡用銅牛烤死/犯人的國王當政,你或可如此,/別用沒來由的恐懼玷污仁愛的靈魂,/為何在平靜的海里為暗礁憂心?”(P.OvidiNasonisExPonto3.6.39—43)然而,奧維德越是聲稱屋大維對朋友不構成威脅,就越說明朋友的感覺正好相反。他說這位皇帝不是暴君,效果和《黑海書簡》第2部第2首里說皇帝不是食人者如出一轍。傳說埃及國王布西里斯在被海格力斯除掉前,總愛將異鄉人作為犧牲殺死;西西里僭主帕拉里斯則喜歡將囚犯裝進銅牛,活活烤死。將這樣的典故與“賢君”屋大維連在一起,難免不讓人心生疑慮。因此,在竭力打消朋友的“迫害妄想”的過程中,奧維德的頌歌“同時發揮了贊美和批評的功能”(Oliensis179)。由于他在字面上否定了自己文本所建構的屋大維的反面形象,他就總可以扮作“忠誠的臣民”,辯稱自己對皇帝毫無惡意(Williams367)。
貫穿所有流放詩集的一個重要主題也足以拆穿屋大維的仁慈假象,那就是他對奧維德才華的唾棄和摧殘。《哀歌集》和《黑海書簡》曾經長期被西方的古典學者忽視,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相信,這些作品的藝術性遠不如他此前的詩歌,⑤也即是說,他們相信了奧維德對自己的流放詩歌的“評價”。當代的眾多學者早已為《哀歌集》和《黑海書簡》的藝術質量平反,但詩才的衰退確實是奧維德在這些作品中反復哀嘆的“現象”。這個“現象”是不是“事實”,對于奧維德來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需要保持這種悲情的姿態。他總是一面抱怨作品質量嚴重下降,一面為自己辯護。衰退的表征之一是題材極其單調,然而“我的處境既堪憐,我的詩歌便憂郁,/基調當然應該與題材相符”(P.OvidiNasonisTristia5.1.5—6);表征之二是語言粗糙,可是“長期忍受苦難,我的天賦已磨鈍,/舊日的活力沒有一絲留存”(5.12.31—32)。更可怕的是流放地的環境完全不適合詩歌生長:“這里沒有書,沒有聽我朗誦的耳朵,/我說的任何話,也沒有一人理解。/到處充斥著野蠻的言語、野獸的叫聲,/到處彌漫著對喧囂敵人的驚恐。/在我的感覺里,拉丁語已經被我拋下,/我已經學會蓋塔話和薩爾馬特話。”(5.12.53—58)在孤絕的境況中,詩人甚至失去了打磨作品的興趣:“我甚至沒修改,以便紀念這個誕生地,/它們再糙野,也不會超過這里。”(5.1.71—72)他還擔心自己失去了拉丁語的純正語感(3.1.17—18),蠻語已經侵入了自己的詩歌(3.14.49—50)。奧維德的自我貶低是完全真誠的嗎?不如說這種自我指控實際上是在指控皇帝的殘忍,“他不僅破壞了奧維德的物質生存,還摧毀了他的天才”(Luck243)。
在特別激憤的時候,奧維德也會撕下一切偽裝。《哀歌集》第4部第8首被肯尼稱為“對神靈任性妄為的沉痛思索[……]而在奧維德的處境里,神靈的任性妄為其實就是人的任性妄為”(Kenney44)。在談及自己終老羅馬的夢想時,奧維德說:“年輕的我曾希望這一切都會兌現,/我也有資格如此安度余年。/諸神卻另有打算,他們驅趕我翻山/越海,直至薩爾馬特人的地盤。”(P.OvidiNasonisTristia4.8.13—16)“諸神卻另有打算”是對皇族毫不掩飾的斥責。在同一首詩中,他警告朋友,絕不要觸怒朱庇特(屋大維),否則下場將和自己一樣悲慘:“無物如此堅固,即使綁滿了鉆石,/能抵抗朱庇特極速閃電的威力;/無物如此尊崇,高蹈于危險之上,/能超越這位神,蔑視他的權杖。/雖然我受這些苦,部分是因為我的錯,/更多的災難卻由于神的怒火。/但是你要從我的遭遇中汲取教訓,/恭敬侍奉與天神同等的人。”(4.8.45—52)在這里,奧維德一反平時的說法,將自己放逐天涯的主要責任歸咎于皇帝濫用權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50行的“神”(numinis)在詩末決然地變成了“人”(virum)。語義的斷裂產生了強烈的反諷效果(Miller371)。
四
對于他一直試圖緩和關系的屋大維尚且如此,對于他向來不喜歡的皇后利維婭,奧維德的諷刺就更加尖刻了。多數時候,利維婭只是皇帝的陪襯,但詩人總是以捧殺激活流言的聯想。例如在《黑海書簡》中順帶提及她時,奧維德寫道:“他的皇后平安守護著神圣的婚床。”(P.OvidiNasonisExPonto2.2.69)對于熟知利維婭過往的羅馬人來說,這句贊辭無疑是一句笑話。詩人集中塑造皇后形象的詩則是《黑海書簡》第3部第1首。這首詩不僅是奧維德寫給妻子的最長的書信體詩歌,也是《黑海書簡》前三部最長的作品,因而特別值得關注。奧維德有意戲仿了早年的愛情哀歌,假扮情愛導師的角色,他給妻子提的如何向皇后說情的建議幾乎是他年輕時教男士如何勾引女人的那些竅門的翻版(Colakis210—15)。與《愛的藝術》最接近的一段是:“輪到你直接面對朱諾的時候,牢記/你應該扮演的角色,不要偏離。/別辯護我的行為,忌諱的話題不可碰,/哀切的請求就是唯一的內容。/打開淚水的閘門,失魂地癱倒在地,/向那雙天神的足伸出手臂。/然后只求她讓我遠離殘忍的蠻夷,/讓我只忍受時運這一位仇敵。/我還想到許多,卻亂作一團,我害怕,/就這些你顫抖的聲音都難以表達。/我猜這么做不會傷害你,她會感覺/在她的威儀下,你如何謙恭畏怯。/如果你的話被啜泣打斷,那也無妨,/眼淚經常有與話語相當的分量。”(P.OvidiNasonisExPonto3.1.145—58)這并非只是簡單的調笑,《愛的藝術》典型情景的復現讓我們警覺: 奧維德是為那部給自己帶來污名的作品真心悔過,還是以借尸還魂的方式表達自己挑釁的態度(Williams348)?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奧維德妻子替他求饒時只是“扮演”一個“角色”,奧維德在流放詩歌中向皇室示弱的姿態是不是表演?而且,如達維森所說,奧維德將利維婭比作朱諾或許是因為后者以強烈的嫉妒心和復仇心聞名,在奧維德的其他作品中朱諾也一直是這樣的形象(Davisson331—33)。
朱諾的名字還出現在前面奧維德對利維婭的“盛贊”中:“她的美德確保了我們時代的純潔/不會被任何古代的世界超過;/她有維納斯的美貌,朱諾的品格,天底下/配與愷撒同享圣床的只有她。/你為何害怕靠近她?既不是普洛克涅,/也不是美狄亞,等待你的勸說。/她不是埃及王的兒媳,或阿伽門農的惡妻,/或者斯庫拉,西西里海域的妖異,/或者喀耳刻,生來能讓人形幻化,/或者用毒蛇盤繞頭發的梅杜薩,/而是最杰出的女人,她證明時運女神/也能看見,誤擔了眼盲的罪名。/除了愷撒,整個世界,從最東到最西,/沒有誰的光芒能與她相比。”(P.OvidiNasonisExPonto3.1.115—28)關于利維婭的“美德”,羅馬人最熟悉不過。說一位七十一歲的老婦人有“維納斯的美貌”,只能引發訕笑。此外,奧維德雖然在字面吹捧利維婭,卻將她與神話中七位可怕的女人并置在一起,再次使用了“在否定中肯定”的手段。普洛克涅為替被強暴的妹妹向丈夫特柔斯報仇,殺死了兒子伊堤斯,做成菜肴給他吃;美狄亞為了報復丈夫伊阿宋背叛舊愛,謀殺了他們兩人的一對兒子;“埃及王的兒媳”指達那俄斯的四十九位女兒,她們與自己的堂兄結婚,在新婚之夜,奉父親之命殺死了新郎;“阿伽門農的惡妻”指與情夫一起謀害親夫的克呂泰墨斯特拉;斯庫拉是西西里海域的食人女妖;喀耳刻是老太陽神赫利俄斯的女兒,曾將尤利西斯的同伴變成豬。這些恐怖形象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意義場,可以輕易扭曲任何表面的贊美。
對于皇室“三位一體”中的另一位——提比略,奧維德的基本態度是盡力回避。在屋大維執政后期,提比略已經成為皇儲。然而,無論就能力、人品和聲望而言,他都遇到了弟弟大德魯蘇的挑戰。大德魯蘇在日耳曼取得了一系列大捷,但公元前9年意外從馬上跌落,一個月后去世。他的兒子日耳曼尼庫斯同樣有英俊的外表、出色的軍事才能和崇高的聲望,甚至被羅馬人視為亞歷山大大帝一樣的人物。迫于屋大維的壓力,提比略將這位侄子過繼成了自己的養子,但心里一直懼怕和仇視他,擔心他奪走自己的親生兒子小德魯蘇的皇位繼承權。屋大維去世前的幾年,羅馬權貴開始在提比略分支和大德魯蘇分支之間選邊站隊。奧維德堅決地站在了大德魯蘇的兒子日耳曼尼庫斯一邊,他原本打算獻給屋大維的《歲時記》就是后來獻給日耳曼尼庫斯的(P.OvidiiNasonisFastorumLibriSex1.3)。公元12年,提比略在羅馬舉行了凱旋儀式,奧維德輾轉得知消息后,卻將祝賀的詩獻給了日耳曼尼庫斯。在慶賀提比略的作品中,詩人強調的卻是日耳曼尼庫斯攻城奪寨的功勛,甚至極不合時宜地預言后者未來的榮光:“愿諸神佑你長壽!余下的你都靠自己,/只要有時間,你必將彪炳后世。/我的預言會應驗——詩人常說出神諭——/祈禱時,神也給了我吉祥的證據。/你也將征服歸來,登上山頂的神殿,/羅馬將歡迎你,馬車綴滿花環,/父親將觀賞兒子終成大器的盛景,/體會到自己曾給家人的喜慶。”(P.OvidiNasonisExPonto2.1.53—60)這個預言的確應驗了,日耳曼尼庫斯在公元17年也享受了凱旋的待遇,然而“父親”提比略卻絕不會高興,他心中的“兒子”只有小德魯蘇。
在給薩拉努斯的信中,奧維德毫無保留地贊美了日耳曼尼庫斯雄辯的口才:“無愧于尤利亞之名的青年便站起身來,/猶如啟明星升起,在東方的大海。/他沉默地立著,姿勢和表情與宗師無異,/優雅的長袍預示著精妙的言辭。/很快,他不再等待,發出如天界的聲音,/你會發誓說,神就應如此辯論。”(P.OvidiNasonisExPonto2.5.49—54)奧維德稱他“無愧于尤利亞之名”也是犯忌諱的事,因為屋大維的繼承人提比略事實上是克勞迪亞家族的成員,只是因為他被屋大維收養,才成為名義上的尤利亞家族成員,日耳曼尼庫斯被提比略收養,才與尤利亞家族發生關聯。而倘若大德魯蘇真是屋大維的親生兒子,那么皇位之爭就是克勞迪亞家族和尤利亞家族之爭,奧維德的說法就更危險了。最可怕的話出現在詩末:“祝愿他繼承皇位,用自己的韁繩統御/世界,這是我和所有人的祈福。”(2.5.75—76)當奧維德開始創作第四部《黑海書簡》時,原來的皇儲提比略已經登基,他意識到,自己深深地得罪了新皇帝,絕無返回羅馬的可能了,但他仍不肯違心地向后者獻媚。他在給女婿蘇利烏斯的信中,用了近60行的篇幅直接贊美日耳曼尼庫斯,特別指出,他不僅有君主的美德,也是杰出的詩人:“若沒有皇室召喚你追求更偉大的理想,/你早已成為繆斯的無上榮光。”(4.8.69—70)
五
奧維德對待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庫斯涇渭分明的態度表明,他對皇室的諷刺并不盲目,而是基于自己對具體人物的獨立判斷。但從總體上說,遭流放以來的經歷讓他對先后掌權的屋大維和提比略持負面評價,對幕后的實權人物利維婭也頗多腹誹。雖然他在流放詩歌中經常將他們稱為神,卻總在提醒他們,人神之間終歸是有分別的。前文分析過的《哀歌集》第3部第1首、《哀歌集》第4部第8首、《黑海書簡》第2部第8首都隱含著這樣的信息。《哀歌集》第2部更表明,朱庇特只是比喻,屋大維并非朱庇特:“每次人犯錯,如果朱庇特都降下閃電,/用不了多久他就會赤手空拳。/事實上,他總是先用雷聲震懾世界,/再用暴雨還天空干凈的顏色。/所以他理當被尊為諸神的父親和君王,/理當在廣闊的宇宙里至高無上。/既然你也是羅馬國家的君王和父親,/就應該效法有相同頭銜的神。”(P.OvidiNasonisTristia2.33—40)這里,朱庇特不再是動輒降下雷霆的暴戾之神,而是節制用權的化身,奧維德將他用作了教訓皇帝如何做人的工具。在《哀歌集》第5部第11首中,他對屋大維說:“因此,無論我的詩多卑微,都應盡情/稱贊你,你也配得上這樣的熱忱;/我也應求諸神仍然向你關閉天界,/盼望你為神,卻要與你暫別。”(5.11.23—26)詩人的話意味著至少皇帝現在還不是神,他死后是否可以擢升為神,也取決于天神的意愿。
在奧維德的作品中,即使作為神王而非屋大維比喻的朱庇特也是修辭建構的結果。雖然詩人一生都在寫神話,《變形記》和《歲時記》更是窮形盡相地描繪了一個多彩的神話世界,但這些詩作卻經常暗示,奧維德并不相信神話。例如,在《哀歌集》第4部第7首里,他對朋友說:“我的禱告當然是真的。我寧可相信/毒蛇的頭發盤在梅杜薩的雙鬢;/處女的腰間有狗環繞;喀邁拉存在,/由母獅和兇蛇組成,被火焰隔開;/有四足怪物,胸膛與人的胸膛相連;/有三具身體的人,也有三頭犬;/有斯芬克斯、蛇足巨人、鳥身女妖、/也有百臂的古阿斯、人牛米諾陶。/我寧可相信所有這些,也不信你變了,/親愛的朋友,再也不肯關心我。”(P.OvidiNasonisTristia4.7.11—20)奧維德的決絕語氣等于否定了這一系列神話形象的存在。在《黑海書簡》第1部第1首里,奧維德更微妙地揭示了神話和宗教的虛妄。他如此諷刺伊西斯神廟外的斂財行為:“若有人在神母前吹奏彎曲的角管,/誰會拒絕施舍他幾枚銅錢?/我們知道狄安娜不允許這樣的行為,/但她的先知也不缺生活的花費。/天神的力量總是能攪動我們的靈魂,/即使輕易被蠱惑,也不丟人。”(P.OvidiNasonisExPonto1.1.39—44)神母庫柏勒和月神狄安娜出現在這里似乎令人困惑,但埃及神伊西斯于公元前3世紀進入羅馬宗教后,迅速與多位神(包括庫柏勒和狄安娜)融合,神廟遍及帝國各地(Witt138)。所以奧維德在這里沒有區分伊西斯、神母和狄安娜。如果將愷撒和屋大維也看作神,那么他們“蠱惑”人們“輕信”他們編造的各種神譜世系,不過靠的是“力量”,這兩行的顛覆性呼之欲出。但奧維德質疑的不只是皇族的造神運動,他的劍鋒直指傳統的諸神。他接下來寫道:“我曾見某人坐在伊西斯的神祠前,懺悔/自己冒犯穿亞麻的伊西斯的天威;/另一人因相似的過錯而失明,站在路中央,/高喊自己就該有如此的下場。/天神喜歡這樣的告白,證人如道具,/正可以顯示他們的法力非虛。”(P.OvidiNasonisExPonto1.1.51—56)在伊西斯的敬拜儀式上,祭司和信徒都必須穿亞麻,但用“穿亞麻的”形容伊西斯總是不倫不類,更怪誕的是,奧維德用自古以來常見的街頭騙局作例子來證明神的法力,這恰恰消解了他們的神圣性。
如果在奧維德眼中連神都是可疑的,那么將皇族比作神也與諂媚無關。僅僅因為詩人在流放詩歌中系統地將屋大維和其他皇室成員神化,并且多有程式化的贊美之語,便認定他一貫擁護皇權,或者在受到懲罰后變得卑躬屈膝,無疑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理解。如前所述,奧維德并非一位自覺的“反對派人士”,他被流放到遠離文化中心的天涯,迫切希望返回羅馬,所以也的確有向皇族示弱換得寬恕的現實需求。但是他在藝術上的執拗和無辜受難的義憤往往壓制了“得體”的算計,文字的誠實和藝術的邏輯讓諷刺的聲音頑強地沖破“頌神”的表象,變成“瀆神”。麥克戈萬認為,《哀歌集》和《黑海書簡》具備矯正和療治苦難的力量。他指出,奧維德在流放期間,無論在空間上還是地位上都處于帝國邊緣,這使得他成了屋大維及其政策的獨特評論者和批評者。對他而言,寫詩具備了一種與政治迫害相抗衡的力量(McGowan204—205)。也正因如此,他在后世眾多偉大作家(如但丁、彌爾頓、曼德爾施塔姆)眼中,不僅是一位情愛詩人,更是一位流放詩人。
注釋[Notes]
① 關于奧維德這個錯誤的內容和性質,學界的論著汗牛充棟,僅J.C. Thibault于1964年出版的專著TheMysteryofOvid’sExil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就列出了200余位學者的文獻。但這不是本文關心的話題。
② 文中所引奧維德詩歌譯文均出自奧維德: 《哀歌集·黑海書簡·伊比斯》,李永毅譯注。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
③ 近年來,文學地理學逐漸進入古羅馬文學的研究領域,代表性的著作有: Edwards, Catherine.WritingRome:TextualApproachestothe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Boyle, A.J.OvidandtheMonuments:APoet’sRome. Bendigo: Aureal, 2003; Welch, Tara.TheElegiacCityscape:PropertiusandtheMeaningofRomanMonument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④ 例如: Claassen, Jo-Marie. “Ovid’s Poetic Pontus.”PapersofLeedsInternationalLatinSeminar6(1990): 65—94; Hardie, Philip.Ovid’sPoeticsofIllu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285—86.
⑤ 對流放詩歌的負面評價可以參考最初發表于1955年的奧維德研究經典著作: Wilkinson, L.P.OvidRecall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rchiesi, Alessandro.ThePoetandthePrince:OvidandAugustan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Casali, Sergio. “Quaerenti Plura Legendum: On the Necessity of ‘Reading More’ in Ovid’s Exile Poetry.”Ramus26.1(1997): 80—112.
Claassen, Jo-Marie. “Meter and Emotion in Ovid’s Exilic Poetry.”TheClassicalWorld82.5(1989): 351—65.
- - -.ThePoetinExile. London: Duckworth, 2008.
Colakis, Marianthe. “Ovid as Praeceptor Amoris in Epistulae ex Ponto 3.1.”TheClassicalJournal82.3(1987): 210—15.
Davisson, Mary H.T. “Magna Tibi Imposita Est Nostris Persona Libellis: Playwright and Actor inEpistulaeexPonto3.1.”ClassicalJournal79.4(1984): 324—39.
Dodds, Eric Robertson.TheGreeksandtheIrration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Edwards, Catherine.WritingRome:TextualApproachestothe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Evans, Harry B.PublicaCarmina:Ovid’sBooksfromExil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Galasso, Luigi. “Epistulae ex Ponto.”ACompaniontoOvid. Ed. Peter E. Knox. Oxford: Blackwell, 2009.194—206.
Habinek, Thomas N.ThePoliticsofLatinLiterature:Writing,Identity,andEmpireinAncientRo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Huskey, Samuel J. “Ovid’s (Mis)Guided Tour of Rome: Some Purposeful Omissions in ‘Tr.’ 3.1.”TheClassicalJournal102.1(2006): 17—39.
Ingleheart, Jennifer. “Ovid, ‘Tristia’ 1.2: High Drama on the High Seas.”GreeceandRome,SecondSeries53.1(2006): 73—91.
Kenney, Edward John. “The Poetry of Ovid’s Exile.”ProceedingsoftheCambridgePhilologicalSociety11(1965): 37—49.
Luck, Georg. “Notes on the Language and Text of Ovid’sTristia.”HarvardStudiesinClassicalPhilology65(1961): 243—61.
McGowan, Matthew.OvidinExile:PowerandPoeticRedressintheTristiaandEpistulaeexPonto. Leiden: Brill, 2009.
Millar, Fergus. “Ovid and the Domus Augusta: Rome Seen from Tomoi.”JournalofRomanStudies83(1993): 1—17.
Miller, John F. Rev. “Publica Carmina: Ovid’s Books from Exile.”ClassicalPhilology82.4(1987): 367—71.
Newlands, Carole E. “The Role of the Book inTristia3.1.”Ramus26(1997): 57—79.
Oliensis, Ellen. “Return to Sender: The Rhetoric of Nomina in Ovid’s Tristia.”Ramus26.2(1997): 172—93.
Ovid [Publius Ovidius Naso].P.OvidiNasonisExPontoLibriQuattuor. Ed. J.A. Richmond. Leipzig: Teubner, 1990.
- - -.P.OvidiiNasonisFastorumLibriSex. Eds. E.H. Alton, D.E.W. Wormell, and E. Courtney. Leipzig: Teubner, 1985.
- - -.P.OvidiNasonisTristia. Ed. J.B. Hall. Leipzig: De Gruyter, 1995.
Propertius [Sextus Propertius].ElegiarumLibriIV. Ed. Paolo Fedeli. Leipzig: De Gruyter, 2013.
Virgil [Publius Vergilius Maro].AeneidosLiberⅫ. Ed. A. Sidgwi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75.
Williams, Gareth. “Ovid’s Exilic Poetry: Worlds Apart.”Brill’sCompaniontoOvid. Ed. Barbara Weiden Boyd. Leiden: Brill, 2002.337—81.
Witt, R.E.IsisintheAncient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