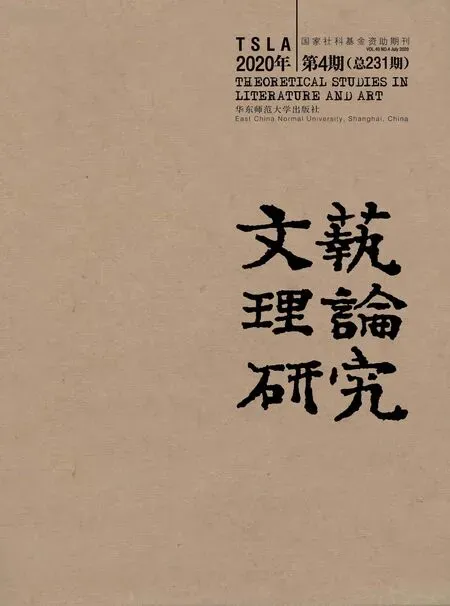窺視與勸誡: 笛福的文學生產實踐
胡振明
18世紀英國小說的興起是現代生產在意識形態延展的產物。馬克思在《經濟與哲學手稿》(1844年)中指出:“宗教、家庭、國家、法律、道德、科學、藝術等等是生產獨有特定形式,遵循生產的普遍規則。”(Marx,EarlyWritings156)在他看來,生產不僅是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的共有驅動力,而且是洞悉社會關系與意識形態本質的有效途徑。生產成就了人類的物質存在,生成了社會關系,催生了與之匹配的諸社會關系的抽象理想表述,如理念、范疇等等。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是文學生產理論的依托,先后啟發了后世法國文學理論家馬舍雷(Pierre Macherey)及英國文學理論家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等人。經過他們的系統論證,文學生產從最初的理念逐步豐富,并發展成為理論,為解讀文本與社會互為建構關系提供了有益視角。追溯文學生產理論的肇始,我們必須了解18世紀英國小說家笛福具化于文學生產的實踐。笛福先后開設內衣店、經營煙酒、從事羊毛業和制磚業,這些實踐使其成為第一位具有現代生產意識的作家,也使其成為第一位將讀者閱讀需求與作者創作意圖、個人主體性與社會公共性、窺視與勸誡融合于文本之中的小說家。笛福的文學生產實踐成就了18世紀英國小說,也論證了文學生產理論的合理性。
一、 笛福與18世紀文學生產
笛福涉獵廣泛,經商、從政、辦報刊;他勤于筆耕,撰寫時評,發表小說,有生之年身兼時政新聞記者、諷刺與哲學詩人、經濟理論家、道德與社會評論家、小說家等多重身份。豐富的閱歷造就了他非凡的洞察力。笛福敏銳地意識到,版權制度日漸完善,印刷出版日益便捷,閱讀市場逐步成形,這些因素合力重塑了作者-作品-讀者三者之間的關系。版權制度保障了作者的經濟利益,使個人創作更有動力。作品通過印刷出版,以商品的形式進入閱讀市場,供讀者購買消費。閱讀市場為讀者、作者提供交易場景,讀者購書,作者獲利。如是經濟行為也改變了文學創作的邏輯。作者從閱讀市場的反饋,以及讀者參與的公眾輿論中汲取創作靈感,了解閱讀期待,進而將其結合到個人書寫之中,以作品的形式向讀者銷售、傳播。讀者購買、閱讀作品,了解作者的創作思想,并以參與評論、傳播的方式對作品進行評斷,這為作者的新創作帶來啟示。此時的文學創作已具備生產、流通、消費等經濟特性,與普通勞動生產別無二致。①有著極強經濟意識的笛福因勢利導地挖掘閱讀市場的需求,著手文學生產,寫出的作品總能成為暢銷書,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笛福并不滿足于此,他有意借助個人書寫參與社會共識建構。他筆下的作品在啟發讀者個人思考的同時也發揮凝練社會共識的作用。笛福雖為一介布衣,但憑著文學生產而出的作品成為公眾輿論的引領者、社會變革的推動者,為“被稱為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18世紀早期英國政治理念自由公開交流體系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Richetti, “Introduction”2)。
在18世紀的歐洲,啟蒙思想逐步瓦解了專制思想的禁錮,個人主體性與創造性得到尊重,這激發了普通民眾的勞動生產熱情,社會財富也隨之發生轉移,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勞動者成為財富的擁有者。在個人日益成為商業主角,逐步推動經濟發展的背景下,代表型公共領域開始向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轉型。轉型引發了社會話語的重構,在哈貝馬斯看來,“公共領域說到底就是公眾輿論領域”(哈貝馬斯2)。社會話語的重構催生了事關個人主體性的文學創作需求:“作者、作品以及讀者之間的關系變成了內心對‘人性’、自我認識以及同情深感興趣的私人相互之間的親密關系。”(54)隨之而來的結果就是,18世紀的敘事處于“迫切與渴望兩股張力之間,即創建事關個人自主的新穎且令人信服之話語的迫切,以及弘揚社會責任與因果理念的渴望”(Flint36)。這可謂需求與供給的合力結果。18世紀敘事謀求個人主體性與社會公共性之間的最佳平衡,既要用鮮明的人物個性吸引讀者,又要以明確的社會道德意圖統領文本。積極參與社會話語建構的笛福意識到自己需要一個新敘述策略。他著手對流行于16、17世紀的流浪漢敘事進行內容與形式的改造,使之成為反映資產階級價值觀念的現代小說,成為再現資產階級個人追求及道德旨趣的最佳載體。經過他的改造,小說這個新文類更便于人物個性塑造,更貼近閱讀期待,更能啟迪讀者思想,更大程度地引發公眾輿論,成就社會共識。笛福因此被后人譽為現代小說先驅。在他及同時代其他作家共同努力下,小說逐步取代詩歌與散文,成為社會話語與共識的重要建構力量。
細讀笛福的所有小說,我們不難發現他似乎提前掌握了文學生產流水線的精髓: 書中主角無不面臨精神的內在危機,并在自我意識引領下,努力闡釋、理解生活的外在道德寓意,最終使自我與社會、精神與世俗之間實現某種平衡,進而重新界定生活的價值與意義(Richetti,TheLife237)。笛福模式化系列創作實踐事實上是私人化經歷“隱藏、揭示其公共參照物”(McKeon716)的過程。私人行為的不可測、人物個性的復雜多樣激發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公共參照物的社會性推動著作者的道德闡述。小說為讀者的窺視意圖,以及作者的勸誡目的提供了一個實施載體。換言之,笛福的小說將窺視與勸誡融為一體,讀者窺視書中個性主角成長的每個階段,作者則借助書中主角的個人醒悟予以勸誡。窺視的愉悅與勸誡的意圖成為推動故事發展的兩股張力,共同構成作品中的戲劇沖突,這既是笛福的敘述策略,又是其小說的敘事特點,在他涉及18世紀英國女性生活狀態的兩部作品《摩爾·弗蘭德斯》(1722年)與《羅克珊娜》(1724年)中尤為突出。這兩部回憶錄式自傳小說聚焦英國女性在遵循叢林法則的金錢社會中的現實生存,為當時的讀者們提供了窺視美麗女性受困、墮落、自救的獨特經歷的窗口,也令作者提供了基于書中兩位女主角真誠懺悔的勸誡實例。笛福有意讓自己虛構的“故事情節與既有道德寓意范式相符”(Bender48),這是根據讀者閱讀期待與閱讀市場需求而組織的文學創作實踐。他所取得的成功為后來馬克思、馬舍雷、伊格爾頓等人提出的文學生產理論的逐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也可以說,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文學觀在18世紀英國小說中得以印證。
二、 文學生產理論與實踐
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是關于人類經濟社會活動歷史的系統思考,物質生產是其中重要內容。最初,物質需求催生了有形的商品生產;伴隨著文明的進程,精神需求推動了無形的文學創作,在包括版權制度、圖書市場及銷售渠道在內的經濟與技術支持手段保障下,無形的文學創作最終以有形物質的方式成品,并作為待售商品進入流通領域,具備社會生產全部要素。這也為后期意識形態建構奠定了物質基礎與實現途徑。馬克思注意到了這個過程。一方面,他強調,人類是“自己觀念與理念的生產者”,是借助“思想生產方式”獲得“自身思考的產物”(Marx and Engels39),人類是在融于物質生產的意識建構中成就了個人主體性;另一方面,“藝術的客體,如任何其他產品一樣創造了欣賞美的藝術公眾”(Marx,TheGrundrisse26)。藝術客體是具有個人主體性的創作者之作,是美的具化,在贏得公眾認可的基礎上成就了共同的藝術品味,塑造了共同意識形態,社會公共性得以成形。盡管馬克思關于文學的評論只是稍有提及,散見于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論述中,沒有形成專題體系,然而他的文學洞見先后啟發了盧卡奇、葛蘭西、本雅明等人,在他們的繼承、發展、豐富的努力下,馬克思辯證唯物論文學觀成為文學批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文學觀不僅關注文學社會學,而且關注作品如何在歷史維度中得到更充分的闡釋。這突破了長久以來作者-作品-讀者單向線性的文學認知慣例,把作品-市場-社會的新維度納入,將多面、立體、復雜但統一的批評世界呈現在后人面前。馬舍雷用自己提出的理論將這個批評世界具化。1966年,他在總結馬克思“藝術生產”理論以及前人思考的基礎上,出版了《文學生產理論》一書。他指出,文學文本不是作者意圖的產物,而是生產過程的產品,“如今的藝術不是人類的創造,而是產品;生產者不是專注于自己創作的主體,而是某個情境或體系中的元素”(Macherey77)。在他看來,藝術是居于文本內外各元素互為建構的結果。作者與作品不只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而且是市場需求與創作動機的關系;作者與讀者不只是供應與消費的關系,而且是閱讀期待與創作題材選擇的關系;作品與讀者不只是商品與消費的關系,而且是市場認可與社會價值實現的關系。馬舍雷的文學生產理論把線性關系豐富、發展成為雙向建構,成為馬克思辯證唯物論文學觀的應用闡釋之一。
馬舍雷的文學生產理論論述令伊格爾頓受益匪淺。他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1976年)一書中,專辟一章論述“作為生產者的作家”。在他看來,專事意識形態建構的作家,也是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者,因為作家的意識形態輸出過程,是將可參與市場流通的作品/商品形式具化,并從中獲利。他是這樣概述的:“我們可以視文學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種社會活動,一種與其他形式并存和有關的社會、經濟生產的形式。”(Eagleton56)伊格爾頓把馬舍雷論述的作品-市場-社會、作者-作品-讀者文本內外維度融合為生產過程的一體兩面。藝術/作品成為商品,既是作者個人勞動成果,又是市場/社會價值載體;作者集精神主體與物質客體為一身,既能主動選擇、決定個人創作,又不得不被動接受、順應市場需求,獲得物質受益;讀者身兼消費主體與物質客體兩職,既被動接受、消費現有作品/商品,又能借助作品最終的銷售成果主動引導作者創作與市場供應。伊格爾頓把辯證唯物論文學觀進一步深化,把物質生產、藝術創作、意識形態建構揉為一體,把無形的思想與意識、預期收益的期待、閱讀與消費預期合在一處,通過已成為共識的生產、流通、消費三個經濟活動步驟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結果就是,文學表述與文學閱讀的過程得以重塑,一個以個人主體性與社會公共性、隱藏與揭示等等辯證關系為核心,在文本內外維度,在作者-作品-讀者、作品-市場-社會層面共同呈現的文學生產過程成為我們洞悉唯物論文學觀的有益視角,而這也恰是文學發展的內動力。
馬克思、馬舍雷、伊格爾頓建構的文學生產理論意在揭示有形經濟與無形意識之間的辯證關系,如是理論上可在18世紀小說興起過程中找到印證。瓦特指出,小說的興起取決于兩個條件:“社會必須高度重視每一個人的價值,由此將其視為嚴肅文學的合適的主體;普通人的信念和行為必須有足夠充分的多樣性,對其所作的詳細解釋應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小說的讀者)的興趣。”(瓦特62)他認為,以笛福為代表的小說家們在創作實踐中,緊扣個體價值特殊性與社會道德普世性,逐步發展了“形式現實主義”的敘述策略,最終使小說有別于其他文類。應該看到,印刷技術的發展、版權制度的完善、閱讀市場的成形,以及流通渠道的建立,為18世紀小說家們提供了不同于前人的創作思維。作者需要創作足夠吸引潛在讀者的作品,要為他們帶來“新”“奇”“特”的閱讀愉悅,同時要確保自己借助現有印刷技術與版權制度,以實現智力成果的充分回報。也就是說,他的作品越符合社會共識和期待,就越有市場,個人收益越豐厚。人數逐漸龐大的讀者們雖出于對有異于自己的他人經驗的興趣而選擇某部作品,但他們往往是在符合自己社會認知與道德預期的前提下獲得閱讀愉悅。過于背叛社會主流道德的作品并不能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可。當作者與讀者在創作題材、敘述方式、作品寓意等方面達成某種默契共識后,小說先驅們據此紛紛推出新作,讀者們有充分的閱讀選擇,多樣的閱讀興趣獲得保障,進而激發更多的消費意愿。在此良性互動下,閱讀市場日益繁榮。借助作者、讀者、市場之間的互動,一部優秀的小說作品往往能夠建構某個社會共識,這在18世紀尤為明顯。可以說,一部在個人主體性與社會公共性之間實現最佳平衡的小說,也是在閱讀市場需求與社會道德共識之間拿捏到位的力作。在這方面,笛福堪稱楷模。他率先在小說創作中運用窺視/勸誡的模式,把作者創作意圖轉化為讀者窺視他人生活的閱讀期待,把讀者獲得的閱讀愉悅提升為作者苦心孤詣設置的道德勸誡。窺視與勸誡成為文本的兩極,戲劇沖突在此間作鐘擺狀,窺視他人越深入,閱讀愉悅就越強,道德勸誡就越有力。笛福在《摩爾·弗蘭德斯》與《羅克珊娜》中運用的模式事實上也是18世紀及之后小說創作的慣例。他秉承的創作邏輯是可用生產、流通、消費等經濟要素予以概述的工業化流程,是文學生產理論得以佐證的依據。
三、 文學生產中的窺視策略
物質生產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文學生產則以閱讀期待為指向。1715年至1725年,倫敦城內犯罪激增,社會風化問題嚴重,民眾為此憂心不已。從事過新聞工作的笛福意識到存在三重閱讀期待。首先是民眾的好奇心。身陷犯罪與社會風化之事的人顯然有與眾不同的經歷,民眾普遍對此有強烈的興趣。其次是民眾的代入感。犯罪與社會風化行為是非常之事,并不是每個人都愿意親身經歷。但民眾愿意通過閱讀代入,把自己想象成當事人,有驚無險地經歷,以獲得愉悅。最后是民眾的認同感。大多數民眾愿意看到文學想象與現實生活保持著某種程度的一致性。因此,讓罪犯與有傷社會風化的當事人遭受懲罰,或懺悔改過是此類作品獲得民眾普遍認同的重要方式。笛福根據這三重閱讀期待,巧妙地借助窺視策略滿足民眾的好奇心與代入感,用勸誡策略滿足民眾的認同感。需要注意的是,笛福一方面充分了解、分析民眾的閱讀期待,另一方面從真實犯罪中汲取靈感,將相關素材納入自己的小說《摩爾·弗蘭德斯》與《羅克珊娜》中(Black78)。借助作者創作意圖與讀者閱讀期待、文學想象與現實素材的融合,笛福為讀者提供了獨到的窺視愉悅。
笛福的這兩部作品屬于罪犯自傳。始于17世紀中葉的罪犯自傳早已有之,但相對成形較晚,是在18世紀逐步確立自己的鮮明特色的(Faller4)。笛福明白,人們對禁忌之事、違法之人既畏懼又好奇,因勢利導固然能實現某種程度的閱讀市場開發,但也有潛在風險。關于犯罪與社會風化的作品一經出版成書,就具備廣泛的傳播性,隨之而來的就是道德性與合法性的問題。笛福為此選擇的敘述策略是,將作品中的人物個性塑造限定為特殊樣例,不具備普世性,以此規避因此類作品傳播而引發的道德風險。也就是說,笛福突出摩爾的“個人自主性”,以此解讀她的犯罪行為(Swaminathan193)。羅克珊娜則帶著諷刺批判的自覺意識描述自己的過往經歷,時刻提醒讀者與其保持一定距離。通過這些方式,笛福的小說“避免了傳奇范式的可預知傷感與情色煽情”(Richetti,AHistory163)。笛福既要讓讀者獲得窺視罪犯、有傷社會風化人士的愉悅,又要消除他們隨之而來的道德焦慮。在別人看來矛盾、難以調和之事,笛福則通過讀者閱讀期待與人物特殊性的融合巧妙化解了。笛福筆下的虛構敘事者都是對現狀不滿,不愿受制于現有制度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因此,這些特殊事例值得讀者關注,這些虛構人物的獨特性與獨立性因自身悖逆社會的行為(常常是犯罪行為)而得到強化(Richetti,TheLife235)。也就是說,因為這個特殊性,讀者才有窺視的意愿。也因為這個特殊性,讀者并不會因為窺視而受道德內省的影響。窺視者與被窺視者之間有一道安全的隔離墻。
摩爾·弗蘭德斯與羅克珊娜各自擁有兩個標簽身份,前者是女性與罪犯,后者是女性與交際花。雙重身份的疊加強化了她們兩人主體性的特殊之處。在18世紀語境中,身為女性,意味著對既有社會顯性與隱性規則的尊崇;身為女罪犯與交際花,則意味著對社會法律、道德秩序的違逆。有學者指出,根據傳統標準,女性犯罪尤為嚴重,因為這被視為“‘標準的’性別化行為的偏差”(Walker75)。另一方面,羅克珊娜憑借自己的美色走出困境,先后成為英國珠寶商、德國親王、荷蘭商人、英國國王的情婦,進而擁有巨額財富。她成為交際花的經歷更是顛覆了當時男主女從的社會規則,是依靠自己決定命運的明證。當摩爾與羅克珊娜先后擺脫男性,通過不同方式,實現個人獨立的共同目的時,她們所犯的罪愆“似乎特別與社會秩序的缺陷有關”(Rietz186)。若不是社會秩序存在缺陷,何以讓原本順從的女主角背離職責,走上違逆之路,對現有社會共識產生沖擊呢?對讀者而言,女性與社會秩序的決裂,這具有顛覆性之舉既強調了當事人的特殊性,又使得她們的未來選擇更具多樣性與危險性。也正因為如此,摩爾與羅克珊娜的故事更具吸引力,讀者愿意通過閱讀來窺視后續發展。摩爾出生于倫敦的新門監獄。她的母親犯下盜竊罪,在被遣送到弗吉尼亞之前把女兒留給了別人。羅克珊娜則是逃難到英國的法國人后裔,家境優越。從小寄人籬下的摩爾曾立志成為自食其力的“貴婦人”(《摩爾》7),而此時年方十四的羅克珊娜“有任何一個青年女子所渴求的種種討人歡喜的優越條件,在我自己看來,我的前途也是一片幸福”(《羅克珊娜》3)。然而,這兩位身世迥異,最初內心向善的女性卻都走上了或為盜為娼,或周旋于富人之間出賣色相、不為世人所容之路,但她們又都實現了經濟獨立,過上了體面生活。可以想象,這兩人的獨特經歷對大多數開始借助閱讀獲得外部世界知識,期冀通過個人努力實現趨上社會流動性的讀者而言,會有多大的吸引力!激發18世紀讀者更強窺視欲望的是摩爾與羅克珊娜走出困境的過程,這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讀者的現實生活參考指南。摩爾違逆不公的社會法則,力圖同時擁有男性的決斷意志、思想自由,以及女性的特有品質、社會職責,在個人意愿與現實境況中尋求妥協平衡,以此“主宰自己當下及最終命運”(Krier410)。羅克珊娜則明確地與男性主導的社會規則決裂,不想再陷入名為妻子,實為奴仆的困境,寧愿成為聲名狼藉但獨立自主的情婦。她的故事成為一個范例,即“一位自由個人,在理解社會必須的情況下可以實現何等程度的精準自由”(Richetti,Defoe’sNarratives225)。
在為讀者提供窺視兩位女性成長的機會的同時,笛福一針見血地指出她們獲得經濟自由,彰顯個人主體性的過程在于個人財富問題的解決。她們的故事是“身份與財富關系”的具化,是“把男性對社會與經濟變革的焦慮文本化”(London2—3)。社會與經濟的變革迫使每個人都要相應調整自己的生存策略,伴隨著經濟個人主義的發展與社會流動,“資本累積與個人欲望超越了血緣關系與家庭忠貞”(Borsing118)。摩爾與羅克珊娜的一生為此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參考。摩爾的墮落始于寄居家庭大兒子的誘騙。她正值十七八歲的妙齡,除了有天真、虛榮、驕傲的弱點,也展示了醉心于個人財富積累的優點。大少爺每次尋歡都會給摩爾一大筆錢,此時的她有時也對自己的未來有所擔心和思考,“但想到的只是他對我說的那些甜言蜜語和他給我的金幣。至于他到底是否真的想娶我,我卻感到無所謂”(《摩爾》19)。原本擁有幸福生活的羅克珊娜因為自己丈夫的不辭而別陷入困境,沒有工作能力以及生活來源的她不得不開始接受自己的房東——英國珠寶商的恩惠,逐步淪為他的情婦。她一度很是猶豫,直到對方出示了一份寫明若他背叛將賠款七千英鎊的書面契約,以及一張他死后三個月支付給她的五百英鎊的證券后,這才堅定了羅克珊娜的信心:“他取出一個裝著六十幾尼的緞子錢包,往我的裙兜里一扔[……]他對我的這種愛情,我早已有了大量的證據。”(《羅克珊娜》40)摩爾與羅克珊娜盡管分別因他人引誘與被人遺棄而墜入生活深淵,但她們都借助財富使個人命運呈現出另一種可能。摩爾在第一任丈夫病故之后,個人思想有了極大的轉變。對她而言,情感已是風輕云淡之事。她的個人生存動力就是不斷地財富積累。她的人生經驗簡化為“數字、度量及金錢價值”(Ghent39)。在這方面,羅克珊娜有更直接到位的表述:“婚姻契約的實質就是要女人把自由、財產、權力等一切東西都交給男人。”結婚對已實現經濟獨立的她而言不再是首選,因為“用這樣一筆錢(兩萬英鎊)來為自己買一個住處,未免太昂貴了”(《羅克珊娜》149)。摩爾與羅克珊娜成為了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
窺視的愉悅并不只在于滿足讀者對奇人異事的好奇心,而且在于讀者借助代入感獲得對現實社會、真實自我的新認知。加斯認為,小說人物既是獨立個人,又是社會成員;“具有現代性與現實性的人物”塑造在于真實自我是在社會語境中實現的(Gass111)。摩爾的犯罪、羅克珊娜的有傷風化雖然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這是社會合力的結果。現實生活中,權貴人士的欺騙與傷害、人性的寡薄與市儈、生存的艱辛與無奈不正是令無數個曾經有意自食其力的摩爾、一度天真善良的羅克珊娜墜入泥潭的根源嗎?摩爾嘆言:“貪婪是萬惡之源,貧困也是萬惡之源,而且更是一個可怕的陷阱!”(《摩爾》175)羅克珊娜自我辯解:“貧困是我的陷阱,多可怕的貧困!”(《羅克珊娜》36)貪婪是個人之過,貧困則是社會之過,它們始終伴隨著摩爾與羅克珊娜的命運起伏,成為商業社會自身缺陷誘人犯罪的實證。笛福窺視策略的過人之處在于,他用獨特的人與事激發讀者的窺視欲望,讀者在窺視之中,看到的是真實自我與現實社會的折射。這兩部“關于自我與他者辯證關系的描述”(Richetti,Defoe’sNarratives96)的小說一方面讓讀者窺視自我與他者、自我與社會的關系,另一方面讓讀者作好接受勸誡的心理準備。
四、 文學生產中的勸誡策略
物質生產是在消費中檢驗產品價值,文學生產則在讀者閱讀中實現終極意義。閱讀實踐是“一種對話,即每部特定作品傳遞的‘文本標記’與主導其接受的集體共有‘期待視野’之間的關系”(Chartier275)。笛福明白,特定作品只是激發讀者的窺視欲望,它的成功在于集體共有“期待視野”的滿足。在為讀者提供虛擬體驗女罪犯、交際花特有生活的同時,需要借助道德說教為讀者提供某種社會共識的凈化,消除潛在的不良影響。閱讀愉悅是窺視與勸誡合力的結果。笛福在《摩爾·弗蘭德斯》中借編輯之口指出:“如果能好好讀一讀本書,讀者可以從中獲得許多道德上的教益,宗教方面的啟示,以及生活中的教訓。”(《摩爾》15)在《羅克珊娜》中,他借女主人公之口說道:“我回顧自己過去的罪過,感到很厭惡。”(《羅克珊娜》129)顯然,笛福的勸誡策略以滿足民眾的社會道德認同感為指歸。笛福的勸誡策略要面對這么一個事實: 小說閱讀是個性化行為,讀者的個人理解并不受作者左右,他是基于個人經歷與視角來解讀文本的。馬舍雷就明確指出:“作品超越其最初意向讀者的禁囿,自發的閱讀是無限的。”(Macherey80)笛福意識到,如果不能一以貫之地影響讀者,那么就讓小說呈現故事邏輯的多樣性,把勸誡內容拆解,將其嵌入故事發展的若干專題,讀者自行解讀,自行決定道德教益。笛福認為,被拆解、分散的勸誡內容要比傳統的單一說教更有效,對讀者理解能力的尊重能更好地達到勸誡效果。事實上,摩爾與羅克珊娜的故事是18世紀英國社會的縮影,小說所涉及的女性境況、婚姻以及犯罪問題不能簡單評斷、臧否。在地位與財產正在經歷變革的社會中,道德評價本身就具有復雜性(Borsing131)。
勸誡策略直面18世紀女性境況及她們的存在價值。此時的商業經濟發展無疑強化了財產對于個人的重要性,提升了它在社會中的支配力。這自然讓無緣參與社會生產,獲得個人財富的女性處于更為不利的境況。唯利是圖的社會風氣沖擊了現有道德準則,女性的社會地位進一步弱化。然而,笛福并不是讓筆下的女主角成為社會不公的被動承受者,而是以積極自救者的形象進行勸誡。笛福通過這兩位女性的經歷告訴讀者:“女性方式是與特定權力安排相宜的唯一策略。”(Kay100)摩爾與羅克珊娜意識到,女性社會地位的降格因身處利益交換中的不利地位而起,那么運用女性方式揚長避短,獲得個人財產才能占據主動。笛福有意讓筆下的這兩位女主角擁有過人美貌,讓她們在運用女性方式時具有先天優勢。經歷過一些事情之后,她們對自己有清楚的認識,有理性的決斷,以及已有的、可維持自己較高生活品質的財富,這些因素匯聚起來,讓她們足以挫敗各種利益婚姻算計,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摩爾始終居安思危,即便成為一位富有紳士的情婦,衣食無憂,她也仍然想方設法攢錢。她把婚姻簡化成一種謀生手段或獲利方式,在確保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從容左右事態發展。受制于婚姻,意味著接受社會規則;此時可以主導婚姻的摩爾,卻是借此對社會行使權力(Richetti,Defoe’sNarratives114)。羅克珊娜則更進一步,她把不受婚姻約束的情婦類比成一個社會主導者,“現在我已由一個放蕩的女人變成一個女實業家,還是一個很大的女實業家”(《羅克珊娜》131)。有學者指出,諸如笛福這兩部作品的此類敘事事實上探討了日益活躍的商業市場文化中個人(男性或女性)的經濟經驗(Rosenthal7—15)。勸誡始于對新型經濟經驗問題的應對。
對18世紀女性而言,婚姻極為重要,但又極具傷害性。婚姻是當時絕大多數女性的唯一終身職業,是物質與情感生活的雙重融合。但如果愛情與婚姻無關,物質利益高過情感需求,婚姻的基礎就遭到了破壞,這對處于弱勢的女性而言極為不利。笛福借書中的一位小姐之口這樣說道:“只有財產,才會使女人值錢!男人娶女人,就是看重女人手里的財產!”(《摩爾》14)摩爾則以自己聯手制服一位傲慢的船長,使其成為好友百依百順的丈夫一事為例,提出如是勸誡:“如果男人在婚姻上能占女人的便宜[……]那全是因為女人缺乏勇氣,不敢維護自己的地位,擔當起女人的角色。”(《摩爾》65)社會道德的淪喪迫使女性作出相應的調整。對摩爾而言,婚姻不再是地位與財富的必然搭配,而是男女雙方智力與能力的匹配。她的算計也就有了合法性,甚至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盡管其后果是,婚姻成為一份經過協商而議定的、明確男女雙方責任權利的商業合同(Yahav-Brown30)。與此同時,羅克珊娜洞悉不平等婚姻的實質,認識到“婚姻契約的實質就是要女人[……]僅僅是一個奴隸”(《羅克珊娜》149),但她仍然以各種秘密婚姻形式與自己的情夫們建立穩定的社會關系,生兒育女。笛福讓摩爾與羅克珊娜謀求建立在個人財富基礎上的自由選擇,同時渴望得到社會既有制度,即婚姻的保障;她們期待社會公平,與男性同享應有權利,同時利用女性優勢換得個人便利;她們既有挑戰舊有意識的決心,同時對新生事物心有怯意,兩人匯聚了“對自由與限制,對平等與順從的矛盾欲望”(Flynn73)。這種矛盾貼近讀者的現實境況,也就使勸誡更能深入讀者內心。
笛福最重要的勸誡策略是把摩爾及羅克珊娜的墮落與社會腐化建立起邏輯關系,通過社會批判獲得讀者的認同感。18世紀初期,圖書市場上大量涌現的,關于竊賊、海盜的所謂真實歷史或秘史一方面是讀者閱讀興趣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讀者對這些罪犯的某種認同。摩爾與羅克珊娜的故事則更進一步,因為“女性道德腐化的重要意象成為18世紀初期男性的經濟理想”(Smith30)。作為虛構人物的她們,以墮落方式獲得的財富正是現實生活中的大多男性窮盡畢生努力也未必能達到的成果。由此可見,這兩位女性在犯罪、出賣色相的路上越大獲成功,就越反襯現實社會清白做人、勤勞致富何其艱難。笛福再三借摩爾、羅克珊娜之口說自己的墮落因貧困而起,是窮盡合法生存手段之后的無奈選擇,以此“強調引發犯罪與不當行為的環境、社會、體制原因”(Hammond and Shaun61)。需要看到的是,笛福讓這兩位女主角的生活具有足夠的社會代表性。她們特有的經歷使其接觸到上至貴族名流、下至窮苦百姓的各個階層的生活,在為讀者提供多個維度窺視、洞悉摩爾及羅克珊娜個人墮落與社會動因之間內在關系的同時,也讓讀者相信,她們的經歷并不是特定群體的特殊事件,而是具有社會公共性的,是墮落社會滋生的惡之花。如是認同是笛福勸誡策略的基調。當然,笛福不能免俗地用更加直白的語言道出自己的勸誡終極目的,讓摩爾講述完自己堪稱犯罪大全與指南的一生后,轉身就道出勸世良言。當羅克珊娜的美貌、幸運、個人財富無出其右,堪稱眾人艷羨對象之時,笛福卻生硬地以“正像我的罪過只帶來了我的不幸,而我的不幸只給我帶來了懺悔”為結尾(《羅克珊娜》327)。勸誡終歸還是要與社會公共性、主流道德融合才好。
《摩爾·弗蘭德斯》與《羅克珊娜》是文學生產的成品,是從作者-作品-讀者線性創作邏輯向作者-作品、作者-讀者雙向建構邏輯轉變的范例,是窺視與勸誡融合的實踐。笛福順應因18世紀商品經濟發展而興起的閱讀市場需求,從讀者的閱讀期待出發,選擇身兼女性與罪犯/有傷社會風化者雙重身份的摩爾與羅克珊娜作為小說的主角,即其個人故事的敘事者。這既滿足了讀者對當時犯罪問題的切身關切之想,又滿足了他們由此而生,針對罪犯獨特經歷的窺視好奇心。笛福并不想把這兩部罪犯自傳寫成部分讀者熱衷的獵奇之作,而是要使它們適應更廣泛的讀者群體,為此,他增添了這兩部小說的勸誡說教功能。笛福將早年豐富經歷造就的經營意識融于個人書寫之中,進而使小說集其本人對犯罪現象,尤其是對女性犯罪的思考,及對社會道德建構的熱忱于一體。讀者閱讀這兩部小說,從摩爾與羅克珊娜的個人講述中獲得替代經驗,并從中深受教益。可以說,從創作到成書,再到閱讀的完整文學生產過程是以個人主體性與社會公共性的互為建構為驅動力的。作者需以創作思想與虛構人物的獨特性為特點,這樣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足夠吸引潛在的讀者。同時,作者需要選取廣大讀者共同關心的話題作為創作基礎,以此擴大作品的受眾面。讀者選擇具有獨特性的作品為閱讀對象,以此實現閱讀愉悅。需要看到的是,無論作品內容如何獨特,它都應與社會共識與道德保持內在一致性,從而確保作品能被更多讀者接受。基于作者創作動機與讀者閱讀期待,作品也就集個人主體性(作者創作/讀者閱讀)與社會公共性(作者的創作目的/讀者的理解基礎)于一體。文學生產在推動了小說發展的同時,還賦予讀者更大的參與公眾輿論建構的自主性。也正是在作者有意引領、讀者有意參與的氛圍中,集窺視與勸誡于一體的《摩爾·弗蘭德斯》與《羅克珊娜》成為引發公眾輿論的文本載體,也成為文學生產的實踐樣例,這為馬克思、馬舍雷、伊格爾頓所發展的文學生產理論提供了有力實證。
注釋[Notes]
① 參閱胡振明:“作品、市場、社會: 文學公共領域形成初探”,《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2018): 211—21;“作者、作品、讀者: 18世紀歐洲文學公共領域的建構”,《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2019): 189—98。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ender, John.ImaginingthePenitentiary: Fiction and theArchitectureofMind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Black, Joel. “Crime Fiction and the Literary Canon.”ACompaniontoCrimeFiction. Eds. Charles J. Rzepka and Lee Horsley. Oxford: Blackwell, 2010.76—89.
Borsing, Christopher.DanielDefoeandtheRepresentationofPersonal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Chartier, Roger. “Reading Matter and ‘Popular Reading’.”HistoryoftheReadingin the West. Eds. Guglielmo Cavallo and Roger Chartie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9.269—83.
丹尼爾·笛福: 《摩爾·弗蘭德斯》,郭建中譯。南京: 譯林出版社,2003年。
[Defoe, Daniel.MollFlanders. Trans. Guo Jianzho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3.]
——: 《羅克珊娜》,定九、天一譯。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
[- - -. Roxana. Trans. Dingjiu and Tianyi.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
Eagleton, Terry.MarxismandLiteraryCriti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Faller, Lincoln.CrimeandDefoe:ANewKindof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Flint, Christopher.FamilyFictions:NarrativeandDomesticRelationsinBritain, 1688—179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Flynn, Carol Houlihan. “Defoe’s Idea of Conduct: Ideological Fictions and Fictional Reality.”TheIdeologyofConduct. Eds. Nancy Armstrong and Leonard Tennenhouse. New York: Methuen, 1987.73—95.
Gass, Joshua. “MollFlandersand the Bastard Birth of Realist Character.”NewLiteraryHistory45.1(2014): 111—30.
尤爾根·哈貝馬斯: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 學林出版社,1999年。
[Habermas, Jürgen.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 Trans. Cao Weidong, et al. Shanghai: Xuelin Press, 1999.]
Hammond, Brean, and Shaun Regan.MakingtheNovel:FictionandSocietyinBritain, 1660—1789. New York: Palgrave, 2006.
Kay, Carol.PoliticalConstructions:Defoe,Richardson,andSterneinRelationtoHobbes,Hume,andBurk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Krier, William J. “A Courtesy which Grants Integrity:ALiteralReadingofMollFlanders.” ELH 38.3(1971): 397—410.
London, April.WomenandPropertyintheEighteenth-CenturyEnglish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cherey, Pierre.ATheoryofLiteraryProduction. Trans. Geoffrey Wa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Marx, Karl.EarlyWritings. Ed. and trans. T.B. Bottomo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3.
- - -.TheGrundrisse. Ed. and trans. David McLell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TheGermanIdeology. Ed. and trans. R. Pasc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7.
McKeon, Michael.TheSecreteHistoryofDomestic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Richetti, John.Defoe’sNarratives:SituationsandStructur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 - -.TheLifeofDanielDefoe. Oxford: Blackwell, 2005.
- - -. “Introduction.”TheCambridgeCompaniontoDanielDefoe. Ed. John Richett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1—4.
- - -.AHistoryofEighteenth-CenturyBritishLiteratur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7.
Rietz, John. “Criminal Ms-Representation:MollFlandersand Female Criminal Biography.”StudiesintheNovel23.2(1991): 183—95.
Rosenthal, Laura J.InfamousCommerce:ProstitutioninEighteenth-CenturyBritishLiteratureandCul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Smith, Sharon. “Defoe’sTheCompleteEnglishTradesmanand the Prostitute Narrative: Minding the Shop inMrs.ElizabethWisebourn,SallySalisbury,andRoxana.”JournalforEarlyModernCulturalStudies15.2(2015): 27—57.
Swaminathan, Srividhya. “Defoe’s Alternative Conduct Manual: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Female Networks inMollFlanders.”Eighteenth-CenturyFiction15.2(2003): 185—206.
Van Ghent, Dorothy.TheEnglishNovel:FormandFunction. New York: Harper, 1961.
Walker, Garthine.Crime,GenderandSocialOrderinEarlyModern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伊恩·瓦特: 《小說的興起》,高原、董紅鈞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
[Watt, Ian.TheRiseoftheNovel. Trans. Gao Yuan and Dong Hongj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Yahav-Brown, Amit. “At Home in England, or Projecting Liberal Citizenship inMollFlanders.” Novel:AForumonFiction35.1(2001): 2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