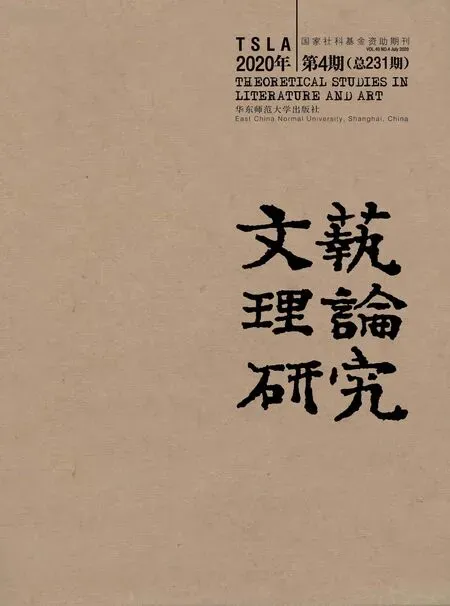過渡與協調: 十八世紀英國小說中的不可靠敘述
王 悅
作為當代敘事學的一個基本范疇,不可靠敘述(unreliable narration)的研究存在修辭方法與認知方法兩種路徑。與修辭方法將不可靠敘述定義為“隱含作者與敘述者規范不一致”(Booth 159)的作者修辭策略不同,認知方法將不可靠敘述視為“在框架理論的語境下,讀者用敘述者的不可靠性來解決語意模糊和文本不一致的一種投射”,是“被稱之為‘自然化’的解釋策略或認知過程”(Yacobi113—26)。這一方法彌補了修辭方法對于讀者接受層面的忽視,也在與修辭方法的爭論與交流中不斷修正自身的局限,已經成為研究不可靠敘述的重要理論參照。
近年來,運用認知方法對敘事(不)可靠性進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 讀者在為“解決語意模糊和文本不一致”進行不可靠性的解讀時,自身所攜帶的歷史文化身份不可避免地參與了進來,它在多大程度上對敘事可靠性的判定產生了影響?以何種方式產生了影響?換言之,歷史文化潮流與不可靠的敘事形態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系——成為了一個研究熱點。對此,布魯諾·澤維克(Bruno Zerweck)在《歷史化的不可靠敘述: 虛構敘事中的不可靠性和文化話語》一文中作出了詳細闡述:“由于不可靠敘述是解釋策略的產物,它是具有歷史和文化變數的。它反映了哲學、自然科學、心理學、社會學或美學話語在過去兩個世紀內許多顯著的歷時和共時的發展。不可靠敘述因此可被認為是界于倫理學和美學之間、文學和其他文化話語之間的一種現象。而且,如果我們把歷史和文化層面置于不可靠敘述的理論中,不可靠敘述的概念最終會成為文化研究的廣闊領域中的一項重要策略。”(Zerweck151—52)基于這樣的理念,澤維克等敘事學家將不可靠敘述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而不僅是一種敘事手法來看待,提出不可靠敘述研究需要第二次轉型——歷史和文化轉向。①
這樣一種觀念的轉變為不可靠敘述研究中的許多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思路,比如: 為什么同一個敘事文本的(不)可靠性會在后世不同時代的解讀中出現極大差異?為什么在某些時期、某些文化背景下不可靠的敘事作品會集中大量出現,而在另一些歷史時空中則非常少見?不可靠的敘事形態對文化思潮的演進產生了哪些推動力?這些問題既涉及讀者的闡釋認知,也涉及作者的修辭方式。因此,筆者認為,對于不可靠敘述的歷史文化考察并不是認知方法的專屬,而是二者綜合的運用。本論文擬從這一思路出發,就18世紀的英國小說來探討不可靠的敘述現象與其背后的歷史文化因素之間的關系,分析不可靠的修辭及闡釋與轉型期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對不可靠敘述的歷史文化研究作一個初步的嘗試。
一、 “傳奇”與“歷史”之間
在18世紀的英國,傳奇文學仍舊在敘事文學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從法國流入的英雄傳奇,在王政復辟后的英國上流社會大行其道。因此,英國早期小說作家大多把與傳奇劃清界限作為建構自己小說理論的重點,在敘事作品中強調自己講述的是真實事件,以與講述虛構離奇故事的傳奇相區分。當時以笛福為代表的許多作家在新聞與小說寫作中“兩棲”生存,極盡細節記錄之能事來證明自己所寫的內容是“千真萬確”的(Baker136);許多小說的標題以“歷史”命名,如菲爾丁的《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TheHistoryofTomJones,AFoundling),作者以“真實”歷史的記錄者而非故事的創造者自居。大部分小說家如理查遜所言,盡管“知道它(故事)是虛構”,卻認為維護小說的“真實可靠的外觀”和讀者“對其歷史真實性的信賴”至關重要(McKillop,TheEarlyMasters42)。
事實上,關于“事實”與“虛構”的界定,18世紀的英國與現代已普及的觀點并非完全一致。邁克爾·麥基恩(Michael McKeon)在其名著《英國小說的起源: 1600—1740》中詳述了當時許多文人名士對各文類的區分,傳奇、傳記、游記等敘事類型常常被放在“歷史”條目,與現代人認同的歷史作品歸為一類。這種分類標準體現了當時的人們對于“事實”與“虛構”之間界線的模糊,也反映出認識論轉型時期的思想沖突——關于“在敘事中如何講述真實的兩種不同觀點(傳奇/歷史)之間的對峙”(麥基恩53)。
在麥基恩看來,小說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解決早期現代社會文化中出現的“類型不穩定”(problems of categorial instability)問題,這一問題背后是科學發展推動下對歷史真實性的推崇以及由此產生的認識論危機。②當時以法國英雄傳奇為代表的傳奇文學受到了影響,不再在敘事中單純追求虛構性,而開始依據亞里士多德的“或然性”(probability)原則向逼真性邁進(Green285—95);傳奇因此被公認為小說文體的前身,在“小說(novel)”的稱謂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奇的、新穎的”與傳奇特征的明顯關聯。但與此同時,小說是以真實歷史的姿態從傳奇中脫胎出來的,歷史真實性與逼真性看似相近卻并不兼容,在逼真性發展成完善的現實主義范式之前,歷史真實性主張在整個西方小說的起源階段占據主導地位(麥基恩95),這種文類類型的不穩定——“傳奇”與“歷史”在早期小說中的共存與對抗,是導致18世紀英國早期小說中存在諸多不可靠敘述的原因之一。
以菲爾丁的《湯姆·瓊斯》為例。盡管菲爾丁對于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在小說中追求歷史真實性的努力,但他同時又無法讓尚未發展成熟的小說與傳奇劃清界線。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其小說中的主人公的身世問題。類似傳奇中為主人公設置神秘出身的套路,菲爾丁小說中的主人公身份也常常帶有一種先天的不確定性——《約瑟夫·安德魯斯》《湯姆·瓊斯》和《阿米莉亞》等作品中都是如此,“出身”問題在情節推進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如同瓦特所說,這一重要性“幾乎相當于笛福作品中的金錢或理查遜作品中的道德”(瓦特311)。
在《湯姆·瓊斯》中,關于主人公身世的敘述本身就是不可靠的。湯姆·瓊斯作為一個來歷不明的棄兒,被人偷偷放在鄉紳沃爾華綏的臥室床上,沃爾華綏在收養這個孩子之前派人去查證了他的身份。查證工作異乎尋常地順利,嫌疑人詹妮坦率地承認了自己是孩子的生母;孩子的父親也在稍后被人指認,經由治安官沃爾華綏的審判,確認是理發匠兼私塾教師帕特里奇。至此,主人公瓊斯的身份似乎已經明了——一個窮私塾教師與女仆的私生子。瓊斯的出身決定了他不能得到沃爾華綏財產的繼承權,不能與鄰居鄉紳之女索菲婭結婚,甚至不能得到周圍稍有身份的人的尊重——但同時他作為養子又深受沃爾華綏先生的寵愛。因此,瓊斯的身份帶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地位的高低與否取決于沃爾華綏對他的認定,小說的基本情節都圍繞這一身份問題展開: 卜利非等人出于嫉妒和利益紛爭毀謗瓊斯,導致瓊斯被沃爾華綏趕出家門,踏上一連串的冒險旅程;與索菲婭的愛情因為等級差異不被家庭接受,導致索菲婭隨后也離家出走,瓊斯的后半段旅程都在追尋索菲婭,魏斯頓和沃爾華綏等人也出于聯姻的緣故齊聚倫敦。
在整個故事的推進過程中,第三人稱敘述者一直以歷史學家的身份自居,聲稱自己只是歷史的記錄者而非創造者,如他在談到沃爾華綏去倫敦辦事時說:“他辦的究竟是什么事,我可不知道。只是他多年來離家外出從來沒有超過一個月,這回卻走了這么久,足見事情相當重大。”(菲爾丁8)。這種“不充分報道”(underreporting)③的修辭大大地拉近了敘述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讓讀者信服于敘述者所謂的歷史真實性,然后在“可靠”的偽裝背后猛然將讀者帶入“不可靠”的陷阱里。
這種不可靠性直到讀者讀完整本《湯姆·瓊斯》后才能意識到。當故事結尾表明瓊斯其實是沃爾華綏的妹妹白麗潔小姐的私生子時,讀者才會發現前面建立在對瓊斯身世誤判基礎上的大量不可靠敘述。首先白麗潔小姐這一人物形象被顛覆,所謂“白麗潔小姐對于高貴婦女稱作貞操的那種美德,一向非常重視,她本人平時操守也十分嚴謹”(菲爾丁14)原來是尖酸的諷刺,敘述者采用多處這類不可靠的評論來制造白麗潔小姐貞潔、古板的假象,使讀者產生了錯誤的判斷;同樣,在詹妮、帕特里奇、沃爾華綏和卜利非等人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主人公身世反轉后帶來的人物形象的重構,作者借由不可靠敘述賦予筆下人物更豐富的內涵——詹妮的“好學”比不過“愛財”,帕特里奇看似有罪實則無辜,沃爾華綏一直都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卜利非的惡毒出于嫉妒,更出于對財產的貪欲,等等,這使得我們對于作者給小說定下的主題——“人性”有了更深的認識。
從主人公身世而來的不可靠敘述典型地體現了傳奇與歷史對早期小說的雙重影響。一方面,身世謎團本就是傳奇的慣用情節,作者在最后關頭揭示身世真相,可以制造信息懸置型的不可靠敘述;另一方面,作者將傳奇類型的故事放在“歷史”的背景下,使得敘述者的身份發生一種分裂: 當敘述者旁觀式地講述“事實”時,他可以被看作他自稱的歷史學家;而當他刻意隱藏、扭曲事實(即進行不可靠的敘述)時,他又從歷史學家的身份中跳脫出來,轉而成為虛構文學的作者。歷史學家與作家的身份矛盾顯示出過渡時期的小說在“如何在敘述中講述真實”這件事上的猶疑,而不可靠敘述——這一主動“說謊”的敘事手段卻恰恰起到了戳破小說的“歷史”外衣,還原其虛構本質的作用,客觀上推動了現實主義范式的確立。
不僅如此,不可靠敘述在促進小說與傳奇分離方面同樣功不可沒。盡管早期小說作家們大多打著“反傳奇”的名號進行創作,但我們仍可以看到他們的敘事作品中有大量傳奇遺留的痕跡。如《湯姆·瓊斯》的基本情節是男女主人公的戀情受到父輩阻隔而被迫分離,共同踏上冒險旅程,遭受一系列艱難考驗而終于澄清真相、締結婚姻,有學者認為其明顯受到了古希臘“赫里奧多羅斯式小說”(也被稱作希臘傳奇)的影響:“它的情節模式通常是由兩個己經訂婚并進行偽裝(通常是兄妹)的戀人的旅程構成。他們的旅程通往一個目的地,在那里身份被揭露并得以完婚。”(Lynch16)但菲爾丁只是借用了傳奇的框架,以一種舊瓶裝新酒的方式表達自己對現實的關照,如杜鵑在研究菲爾丁小說的倫理敘事時所說:“一方面,他充分借鑒英雄傳奇的敘事結構,借助人物的‘英雄’行為展現英國社會的道德狀況;而另一方面,他又通過對‘英雄’涵義的反諷式運用,表達了一種強烈的道德審判意識。”(杜鵑44)這里的“反諷式運用”,也是以一種不可靠的敘述方式來進行的。如敘述者對于主人公瓊斯的不可靠評價,說他“荒唐胡鬧、調皮粗野”(菲爾丁119),“來到世上就是為了上絞刑架的”(97),把瓊斯放置在一個做“壞事”的角色中——偷盜、欺騙、縱欲等等,然而即使在世俗眼中這些罪名成立,讀者卻依然能清楚地感到隱含作者對于瓊斯的喜愛之情。作者一面站在自然人論的角度為瓊斯辯護,④一面采用不可靠敘述的方式展現世俗眼中所謂道德的說辭,使小說邁出超越英雄傳奇模式、深化道德反思主題的關鍵一步。如同哈特菲爾德所說,菲爾丁筆下主人公的犯罪是用以“反映由‘普通人而非哲學家’所構成的世界中絕對道德范疇的片面,以及自己對道德復雜性的贊賞”(Hatfield24),這種充滿著不可靠敘述的“道德復雜性”幫助小說從傳奇的框架和歷史的姿態中脫離出來,成為反映時代熱點的主流文學樣式。
二、 “宗教”與“世俗”之間
小說作為一種新型敘事文學樣式的發源與社會文化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伊恩·瓦特在《小說的興起》中將小說興起的時間認定為18世紀,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在于這一時期的敘事文學體現出了迥異于傳統敘事體裁的個人主義經驗。如他所說:“小說的基本標準對個人經驗而言是真實的——個人經驗總是獨特的,因此也是新鮮的。因而,小說是一種文化的合乎邏輯的文學工具,在前幾個世紀中,它給予了獨創性、新穎性以前所未有的重視,它也因此而定名。”(瓦特6)相對于傳統敘事文學將“現實”對應于普遍真理、一般概念(7),小說中的現實圖景建立在對獨特個體經驗的反映之上,這種現實主義范式的轉化背后是文化思潮的大變革,小說敘事的方式則是凸顯這一文化演變的符號表征。
特羅爾采曾指出:“真正永久性的個人主義的成就,應歸因于一種宗教的而非世俗的運動,應歸因于基督教改革運動,而非文藝復興運動。”(Troeltsch328)自16世紀以來的基督教改革運動中,以加爾文宗為代表的新教取消了教會作為上帝代言人的身份,轉而“推崇一種控制范圍滲透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所有領域的一切行為的控制形式”(韋伯28),鼓勵教徒在不間斷的內省中感知神意,確信自己已經蒙受天恩。這種內省使得日常世俗活動被賦予了宗教意義,個人而非教會成為執行神意的工具,從而確立了個體經驗在精神升華過程中的重要性。18世紀的小說大量體現了這種宗教自省在世俗生活中的影響,如《魯濱遜漂流記》的主人公時刻在自己的點滴生活中尋求神意的指引,《帕梅拉》《克拉麗莎》等書信體小說以日記和靈魂自白的形式與上帝對話,都在無形之中將宗教意識與個人獨特性的塑造聯系在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這種帶有資產階級理念的宗教觀在18世紀的英國小說中既堂而皇之地掌控了主流話語權,又常常莫可名狀地發生與其他情節內容的抵牾,以至于相關敘事的可靠性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以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為例: 主人公魯濱遜·克魯索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上升期資產階級的典型,經濟個人主義的特性在他身上展露無遺——對金錢的追求是人生的首要事情,重視賬簿和契約法則,以商品價值衡量一切人際關系。但在這樣一個“經濟人”身上,同時還存在著尋求宗教救贖和信仰指引的一面,對上帝的懺悔和神意的體悟占據了第一人稱敘述者心理世界的核心。雙重的價值體系賦予了主人公立場不明的敘述聲音,以至于他的敘述經常看起來不那么可靠。
比如,小說開頭談及航海一事時說:“除了航海以外,我對別的一概都不樂意干,[……]這種偏執的性格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不幸,終于使我未來的生活直接落到悲慘的境地。”(笛福4)這種懺悔在流落荒島之后更加深刻:“由于當初我堅決不顧自己原來的身份,不聽我父親的具有遠見卓識的勸告,反對他的勸告,我可以說,是犯了原罪。”(191)魯濱遜在荒島上對于原罪的懺悔與他開始認真領受上帝旨意的行為同步,父親的身份在這里有了上帝的隱喻——違背父親(上帝)即是原罪。然而,在主人公離島之后,他卻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懺悔:“我自己一向有出海的愛好;加上他再三勸說,終于動心了,就以個體商人的身份,登上他的船,去東印度。”(301)基督徒的身份在“我”回歸世俗生活后隱去,堅持經濟個人主義的資產者成為主人公唯一的人格標簽。鑒于小說敘事的時間晚于被敘述的故事時間,在小說開頭時“我”已經經歷完所有的事件,那么他有關航海的種種懺悔的說辭是否可靠呢?綜觀全書,隱含作者對于故事核心——航海一事究竟認定為合理還是罪過,應該還是不應該,竟難以下判斷。
瓦特曾把《魯濱遜漂流記》與《浮士德》《唐璜》和《堂吉訶德》一起并稱為“我們個人主義社會里具有獨特共鳴的重要神話”,因為它們“展示了主人公對部分現代西方人向往的典型目標一心一意的追求”,“代表或象征了所處社會的某些最基本價值理念”(Watt ix-xii)。18世紀啟蒙運動影響下的英國正處于傳統社會向個人主義社會的轉型期,基督教信仰對于個人既意味著在世俗生活中服務上帝的新教倫理,也遺留著原始宗教觀中對現實欲望的壓制和禁錮,世俗生活與宗教信仰的關系既相輔相成又彼此排斥。魯濱遜作為敘述者,試圖在敘事中整合“自我奮斗”與“精神自傳”兩個故事,但是在書寫“精神自傳”時,無數“奮斗”的細節跳出來暴露這種宗教自省的不可靠: 他發現島上可能有野人出現時,“我的害怕攆走了我的一切來自宗教信仰的希望”(笛福155),當他發現大麥生長只是他抖落了雞飼料的緣故,“我從宗教的立場出發,對上帝保佑的感謝也化為烏有了”(82);而在書寫“自我奮斗”時,精神內省的敘事又阻止了對自我奮斗的肯定——將荒島生涯解讀成上帝對自己靈魂的救贖,只能推導出航海歷險是罪過的結論。
兩個故事之間的矛盾使多處敘述中的不可靠顯而易見,但問題在于: 小說的隱含作者究竟持何種觀點?讀者該從何種角度理解這種不可靠性?在馬克思看來,魯濱遜并不具有一種虔誠的宗教意識,主人公只是把祈禱“當作消遣來看待”(馬克思 恩格斯86);那么如果隱含作者的立場也是如此,則敘述者關于宗教懺悔的敘述就是不可靠的;反之,如果隱含作者保持了與敘述者的距離[諾瓦克曾通過分析笛福的社會評論等非虛構性作品,指出他的真實道德觀與小說中的道德觀并不相同(Novak198—204)],則小說中世俗與宗教的矛盾沖突就成為作者想要反諷的主題,如瑞凱提所認為的,這種矛盾是個體與世界之間復雜矛盾關系的反映,體現了“對絕望的控制和對控制的絕望”的辨證結構(Richetti67)。
事實上,歷來對《魯濱遜漂流記》的解讀都離不開對其敘事中不可靠之處的闡釋——它是站在“世俗”的立場上談“宗教”不可靠,還是站在“宗教”的立場上論“世俗”不可靠?或是認為兩者都不可靠?抑或作者根本就無意制造不可靠的敘述,所謂不可靠是后世讀者闡釋的結果?最后一種觀點以瓦特為代表,他認為魯濱遜對兩個故事的敘述可能都是相當真誠的,只是由于時代的原因,笛福本人并沒有意識到這種沖突(瓦特84);讀者在小說中感受到的種種不可靠之處,可以解釋為作者觀點中的“一種未解決的、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的沖突的產物”(139)。
瓦特的觀點實際上是從認知角度對這部小說進行不可靠敘述的解讀——不可靠性并非從作者的修辭策略中來,而是來自讀者對“語意模糊和不一致的一種投射”;作者和讀者對于敘事中“不一致”的意識差別,則可以歸因于文化思潮的轉變。在18世紀的英國,物質生產的快速發展使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出現世俗化的傾向,但正如施耐德所言,“信仰很少變成懷疑,它們變成的是儀式”(Schneider98),對于當時的許多人來說,宗教與世俗的對立甚至是不存在的。這或許恰恰是這一時期的英國小說中頻頻出現此類型的不可靠敘述的原因:“宗教”與“世俗”尚未分化成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小說家在進行時代體征的刻畫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共存的二者作為故事的意識形態背景,而這種共存之下的沖突與差異則需要在文化的轉型期結束之后才能被人們充分認識到。
之所以一個文本的不可靠敘述能夠出現這么多樣化的解讀方式,根源還是在于文化語境的動蕩不安——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融匯充滿矛盾與妥協,作為個人經驗發聲的小說,其隱含作者無法在意識形態領域尋找到一個穩固的支撐點,這使得讀者面對文本中的不一致時,與隱含作者的理解相距甚遠。從另一面來講,文本中不可靠敘述的多義性也是《魯濱遜漂流記》作為經典的價值所在,它的隱含作者與敘述者之間飄忽不定的距離在取締了敘述可靠性的同時,準確地傳達出個人主義價值觀構建過程中的困惑與兩難。
三、 “教化”與“娛樂”之間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英國小說興起的18世紀,文學讀者數量相對于以往有明顯的增長,其中占據主流的是商人、店主等資產階級群體,女性是重要的組成部分。⑤相對于古典文學對讀者知識背景和審美品位較高的要求,18世紀的小說更傾向于給讀者提供一種簡易輕松的閱讀體驗。“它不需要大量的思想勞動,也不需要運用理性才能便可以被領會,只需活躍的想象力便可奏效,幾乎不必或完全不必增添記憶的負擔。”(Croxall14)讀者平民化使小說從一開始就不可避免地被賦予了休閑娛樂的功能,而書商取代恩主成為作者的主要經濟來源也使得小說不得不傾向于資本市場,對于大眾讀者(特別是女性讀者)趣味的迎合必不可少。
從受讀者歡迎的角度而言,理查遜的《帕梅拉》是個非常杰出的代表。這部小說問世后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反響,一年再版五次,仿作續作不斷,成了最暢銷書。女性讀者占據了小說受眾的很大一部分,尤其女仆讀者是其中一個很引人注目的群體,用蒙塔古夫人的話說,帕梅拉在婚姻上的成功使她成為“世上所有的侍女為之歡呼的對象”(Thomas, ed200)。有意思的是,伴隨小說的暢銷而來的是讀者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把它捧上了天,另一派對之嗤之以鼻”,“特別是在女性中間出現了兩大陣營,即帕梅拉派和反帕梅拉派。[……]有的人認為那個年輕處女是淑女們該效法的榜樣;有人甚至毫不遲疑地在講道臺上推薦這部羅曼司。另一些人則恰恰相反,他們在書中看到的是一個虛偽狡猾、精于誘惑之道的女子”(Gooding109)。
讀者態度的分歧與作者為小說預設的道德教化功能不無關系。18世紀的英國處于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新興的資產階級迫切需要在文化政治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將符合本階級訴求的價值理念滲透進全社會的意識形態中。小說家們積極地參與了這一過程,如理查遜就以“美德有報”作為《帕梅拉》的副標題,企圖在虛構文學話語中建構起忠貞、虔信、勤儉等資產階級道德標準,教導讀者(尤其針對文化水平不高的讀者)棄惡揚善、走上正途。其他作家如菲爾丁、笛福等,也都在小說中開宗明義地強調小說的道德啟迪功用,以文學創作的方式參與到清教徒倡導的道德改良運動中來。
一方面是塑造資產階級新道德觀的“教化”需要,一方面是迎合讀者大眾的“娛樂”要求,這雙重屬性根植于早期英國小說的發展模式之中,同時也因為彼此的差異在敘事形式上留下了“不可靠”的裂痕。就《帕梅拉》而言,這是一個身為道德楷模的“灰姑娘”的故事。女仆帕梅拉通過與少主人B先生的婚姻實現了階級躍升,但這份成就并不僅僅是靠帕梅拉的美貌或個人魅力,而是更多地源自帕梅拉的道德原則,集中體現為貞操觀。在《帕梅拉》成書的時期,“貞潔不僅是眾多德行之一種,而且趨向成為最高尚的德行,它既適用于女人,也適用于男人”(瓦特172)。這種將抵制肉體欲望視為主要美德的倫理觀帶有清教主義的色彩,帕梅拉的行為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被認為是正義的、神圣的,是為捍衛基督教原則和社會道德秩序而進行的一場斗爭。
可以看出,道德原則對于帕梅拉的意義是雙面的——既是用來與B先生作斗爭的武器,也是實現自身階層攀升的階梯。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都處于劣勢的帕梅拉,在與B先生的抗爭中主要借助的就是權威的道德秩序。基督教義是她反抗的底氣。“我將永遠相信上帝的恩澤,它將會保護我,我將依靠這來頂住!”(理查森74)她時刻不忘在信中援引“全能的主”,占據道德高地來譴責和說服B先生,聲稱“貞潔將永遠是我生命所引以為豪的東西”,“當我去世的時候,它將成為我最大的安慰,那時候全世界的財富與虛榮,將比乞丐所能穿的最低劣的破布更值得鄙視”(69)。以這種方式確立自己與B先生相比人格上的優越地位。
但與此同時,這種將道德原則作為抗爭武器的敘述也充滿了不可靠性。比如,帕梅拉在敘事中一直堅稱要脫離B先生的“魔爪”,但當她終于獲得了許可離開,卻又借口“職責所在”,在B先生家里逗留多日,不時出現在B先生面前,還為他精心縫制了一件背心(37—40);她對B先生的拒絕永遠恰到好處,既不同意做外室又讓他明白自己并無其他意中人;更加難以自圓其說的是,她一直以“邪惡”“卑劣”“歹毒”“下作”等貶義詞來評價B先生,但當他終于向她求婚時,她卻似乎完全忘記了所有的不幸,并馬上陷入了“愛情”(292)。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帕梅拉的敘事很容易讓讀者質疑其可靠性: 她以道德為武器是真的源自高尚與正義嗎?還是另有目的?
瓦特認為:“作為一個小說家,理查遜能夠保持相當大的客觀性;但很清楚的是,作為一個自覺的道德家,他是完全站在帕梅拉的立場上的,他的小說的最嚴重的缺陷正是由此而生。”(瓦特187)換言之,從作者意圖的層面來看,《帕梅拉》的隱含作者與敘述者的規范是一致的,即作者想要通過敘述者展開的是可靠的敘述。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敘事文本的可靠性可以由此得到保證。事實上,當理查遜試圖通過敘述一個因德行而獲利的故事來倡導道德時,就已經使道德遠離了原本的純粹——它同時包含著抵御物質誘惑與追求現實福祉兩重意味,“既是中產階級抗拒、改造上層社會腐敗道德的工具,又是和上層社會達成妥協,得到認可,從而分享社會權力的途徑”(胡振明119)。這種矛盾暗中消解了敘事的可靠性,使敘述者帕梅拉的形象在讀者眼中變得可疑,卻又同時完美地體現了新興資產階級對于“道德”涵義的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帕梅拉》中的不可靠敘述正是這部小說能夠在市場上大獲成功的必要條件,它巧妙地將小說的娛樂功能與教化功能融合在一起,反映了這個時代對待道德的微妙態度。一方面,小說中與利益綁定的“道德”順應了商品社會逐利的特性,迎合了轉型期社會中的許多人想要“往上爬”的心理,讓讀者在道德的外衣下收獲一種代入的快感;另一方面,小說又通過給予道德利益回饋證明了道德的力量,客觀上起到了引領社會價值導向的作用,以致小說在成為暢銷文學的同時還成為“講道臺上的范本”。關于道德充滿歧義的、難于定論的敘述或許正是《帕梅拉》最大的魅力所在,它所引起的巨大的爭議也是這個時代新舊文化交替的縮影。
如托馬斯·凱默所說,這部小說的“人物性格以及動機的論爭表象所掩蓋的是在傳統意識越來越受到質疑與挑戰的時代里更為激烈的沖突與詰問[……]《帕梅拉》不僅是部小說,而且也是意識形態角逐的戰場”(Keymer Peter, edsxvii-xix)。傳統意識的衰微在小說中首先體現為B先生對于傳統道德信條的態度——身為統治階級一員的B先生對于帕梅拉口中的“上帝”“貞潔”“榮譽”態度是輕佻而不以為然的,傳統信條已經失去了它作為意識形態話語的權威性;而一直將其奉為寶典的帕梅拉卻又在利益兌現后對B先生態度大變。那么結局的成婚到底是傳統價值信條的勝利,還是摻入利益考量的資產階級道德觀的勝利?
就18世紀的英國小說而言,意識形態的角逐演變與小說敘事的不可靠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趙毅衡說過:“由于文學最根本的機制是更新語言,創造新的表意方式,它必然破壞既成的語言規范與意識形態規范,文學的生成與釋義就很可能成為對既定價值的挑戰,就很可能迫使‘意識形態萬能’這拋光的表面展開裂縫。”(3—4)這種“裂縫”通常出現在一種文化面臨危機的時候——原有的意識形態話語開始落后于時代的發展,敘述者的世界難以用舊的敘述秩序自洽,因此表現出的不可靠性既是文化沖突的結果,也是推動價值觀念革新的力量。
在《帕梅拉》的例子中,“帕梅拉派”和“反帕梅拉派”表面上爭執的是帕梅拉的敘述話語是否可靠: 她到底是純潔還是虛偽?根源上則是新舊道德觀念的分歧: 道德是否可以與功利捆綁在一起?怎么界定道德與功利的關系?《帕梅拉》最著名的批判者菲爾丁就是從文化保守主義的觀念出發指責功利的道德觀是不道德的;而理查遜,這個身兼印刷業主的文學家,在小說創作中一直有著迎合大眾品味(特別是女性品味)的傾向,他給友人的信里說:“如果我過于神圣化,我懷疑除了老奶奶以外,我還會吸引什么人。”(McKillop,SamuelRichardson62)道德教化與休閑娛樂的功能在作者初創的構想中就已經結合在一起了。這種寫作思路在文學史上甚至開創了先河——生成了一種用婚姻來為道德解圍的通俗文學模式,足見從中同時滿足了讀者正義感與功利心的不可靠敘述有它流行的必然;只是隨著時代浪潮的推移,休閑娛樂的功能更多地在小說中占了上風,以至于與功利融合的道德敘述似乎很難再引起“不可靠”的爭議了。
從敘事的角度綜觀18世紀英國的經典小說作品,不難發現不可靠敘述現象的普遍存在。新生的敘事體裁——小說從“傳奇”與“歷史”中脫胎而出,承載著新舊價值觀念的交融與分歧,尋找自身在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中的位置,在敘事手法上留下“不可靠”的印跡。笛福、理查遜、菲爾丁等小說家敏銳地捕捉到文化的革新與社會的轉型,他們筆下的不可靠敘述既反映了時代精神的過渡更迭,也起到了在沖突中協調價值差異、構建新型文化樣式的作用。用盧卡奇(Georg Lukcs)的話說,“小說是被上帝拋棄了的世界的史詩”(61),那么18世紀英國小說中不可靠的敘述,則是史詩中被賦予文化轉折痕跡最明顯的篇章。
注釋[Notes]
① 關于不可靠敘述的歷史文化轉型,拙文《〈湯姆·瓊斯〉中的不可靠敘述與早期現實主義語境: 一種文化敘事學視角》(《外國文學》2019年第3期)中有進一步的論述,這一研究方向已經引起了國內外不少學者的關注和討論。參見王悅:“《湯姆·瓊斯》中的不可靠敘述與早期現實主義語境: 一種文化敘事學視角”,《外國文學》3(2019): 43—51。
② 麥基恩認為小說的興起源于解決兩種“類型不穩定”問題: 一種是“文類類型”,另一種是“社會類型”。前者反映出認識論危機,即如何在敘述中講述真理的認識態度上的文化轉變,稱之為“真理問題”(questions of truth);后者體現出如何將外在社會秩序和民眾內在道德狀態結合起來的文化危機,稱之為“道德問題”(questions of virtue)。此處主要探討的是“真理問題”。
③ 修辭方法的代表人物費倫區分了不可靠敘述的六種亞類型: 事實/事件軸上的“錯誤報道”和“不充分報道”,價值/判斷軸上的“錯誤判斷”和“不充分判斷”,知識/感知軸上的“錯誤解讀”和“不充分解讀”。參見: James Phelan,LivingtoTellaboutIt(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49—53.
④ 菲爾丁將瓊斯的性格特點定義為“natural gentility”,認為“自然”本身符合道德的真義。自然人論在18世紀的啟蒙文化語境中受到追捧,菲爾丁在小說中也將“自然”作為道德的核心詞匯。
⑤ 參見: Marjorie Plant,TheEnglishBookTrade(London: Allen & Unwin, 1939),445; John Tinnon Taylor,EarlyOppositiontotheEnglishNovel(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43),25; Laura Brown,EndsofEmpire:WomenandIdeologyinEarlyEighteenth-CenturyEnglishliteratur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1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ker, Ernest A.TheHistoryofEnglishNovel. Cabin John: Wildside Press, 2010.
Booth, Wayne C.TheRhetoricofFi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Croxall, Samuel.ASelectCollectionofNovelsandHistories. Farmington Hills: Gale Ecco, 2010.
丹尼爾·笛福: 《魯濱遜漂流記》,鹿金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8年。
[Defoe, Daniel.RobinsonCrusoe. Trans. Lu J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杜鵑: 《論亨利·菲爾丁小說的倫理敘事》,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Du, Juan.EthicalNarrative:AStudyofHenryFielding’sNovels. Ph.D. Dis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8.]
亨利·菲爾丁: 《湯姆·瓊斯》,黃喬生譯。南京: 譯林出版社,2004年。
[Fielding, Henry.TomJones. Trans. Huang Qiaoshe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4.]
Gooding, Richard. “Pamela, Shamela,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amela Vogue.”Eighteenth-CenturyFiction2(1995): 109—30.
Green, Frederick C. “The Critic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French Novel.”ModernPhilology3(1927): 174—87.
哈貝馬斯: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 學林出版社,1999年。
[Habermas, Jürgen.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 Trans. Cao Weidong, et al. Shanghai: Xuelin Publishing House, 1999.]
Haller, William.TheRiseofPuritan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8.
Hatfield, Glenn W. “The Serpent and the Dove: Fielding’s Irony and the Prudence Theme of Tom Jones.”ModernPhilology65(1967): 17—32.
胡振明: 《對話中的道德建構——十八世紀英國小說中的對話性》。北京: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7年。
[Hu, Zhenming.MoralConstructioninDialogue:DialogisminEighteenth-CenturyEnglishFictions. Beij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2007.]
黃梅: 《推敲“自我”: 小說在18世紀的英國》。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Huang, Mei.Debatingthe“Self”:Fictionsin18th-CenturyEngland.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Keymer, Thomas, and Peter Sabor, eds.ThePamelaControversy.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Press, 2001.
盧卡奇: 《盧卡奇早期文選》,張亮、吳勇力譯。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Lynch, James J.HenryFieldingandHeliodoranNovel:Romance,Epic,andFielding’sNewProvinceofWriting. Rutherford: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馬克思 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SelectedWorksofKarlMarxandFriedrichEngels. Vol.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邁克爾·麥基恩: 《英國小說的起源: 1600—1740》,胡振明譯。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McKeon, Michael.TheOriginsoftheEnglishNovel,1600—1740. Trans. Hu Zhenmi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5.]
McKillop, Alan Duglad.TheEarlyMastersofEnglishFiction.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56.
- - -.SamuelRichardson:PrinterandNoveli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Novak, Maximillian E. “Conscious Irony in Moll Flanders: Facts and Problems.”CollegeEnglish3(1964): 198—204.
塞繆爾·理查森: 《帕梅拉》,吳輝譯。南京: 譯林出版社,1997年。
[Richardson, Samuel.Pamela. Trans. Wu Hui. Nanjing: Yilin Press, 1997.]
Richetti, John J.Defoe’sNarratives:SituationsandStructur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Schneider, Herbert Wallace.ThePuritanMin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Thomas, W. Moy, ed.TheLettersandWorksofMaryWortleyMontagu. New York: AMS Press, 1970.
Troeltsch, Ernst.SocialTeachingoftheChristianChurches, Trans. Olive Wy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31.
Watt, Ian.MythsofModernIndividu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伊恩·P·瓦特: 《小說的興起》,高原、董紅鈞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
[Watt, Ian.TheRiseoftheNovel. Trans. Gao Yuan and Dong Hongj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馬克斯·韋伯: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馬奇炎、陳婧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Weber, Max.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 Trans. Ma Qiyan and Chen J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Yacobi, Tamar. “Fictional Reliability as a Communicative Problem.”PoeticsToday2(1981): 113—26.
Zerweck, Bruno. “Historic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Unreliability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Narrative Fiction.”Style1(2001): 151—78.
趙毅衡: 《苦惱的敘述者》。成都: 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
[Zhao, Yiheng.TheUneasyNarrator.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