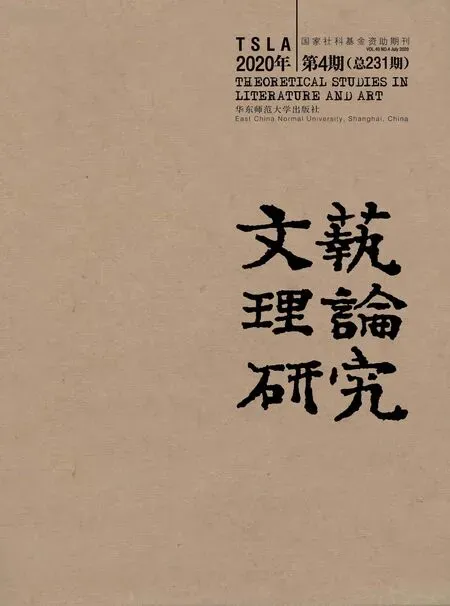文學的審美與意識形態
——基于當代西方文論中“審美意識形態論”的討論
湯 黎
在當今西方文學理論的討論中,意識形態問題一直處于中心地位。這是因為,在人類所有的活動和交往中,意識形態都是不容回避的,即意識形態是人類對其生存條件的真實關系和想象關系的統一體(Althusser202—203)。在人類精神探索的進程中,文學是最為悠久的一種審美形態,而文學所內含的觀念在歷史階段中從來都發揮著意識形態功能。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不容置疑。所有的文學文本本身就可以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都在具體的語境中通過形式產生意識形態效用(杰洛瑞128)。毋庸置疑,文學是審美的,是在歷史和社會現實中實踐的一種方式。具體的審美形式通過感性和看似主觀性的話語,均表達了某種抽象理性和政治意蘊。鑒于審美可以彌合現代社會中主體的分裂,在碎片化的社會中建構精神家園,起到現實的政治功能,因此,審美意識形態論對于討論文學與意識形態、審美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保持著闡釋的有效性。
國內學界審美意識形態論的產生背景,是讓文學研究脫離以往將文學只視為意識形態反映和政治話語工具的簡單甚至庸俗化取向,重新重視文學的美學功能但又不脫離其政治語境。早在20世紀80年代,為了破除之前將文學簡單化為政治工具的思想,錢中文、童慶炳等學者開始提出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論。此理論基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從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屬性出發,認為文學是意識形態的反映,同時也具有審美屬性。然而由于時代和針對的主要問題所限,當時的審美意識形態論是基于“審美反映”之上,且未對文學和意識形態的物質性進行深入探討。這受制于當時整個的文論語境,也同中國美學傳統有一定的關聯。在這一理論誕生之時,也有不少學者對審美意識形態論提出質疑: 他們或認為文學是審美而非意識形態,或堅持只關注文學的美學價值,或聲稱文學只是意識形態的反映。這些質疑的觀點或將意識形態視為單一、固定和封閉的系統,甚或等同為政治意識形態;或將美學視為感性的、無功利的概念和范疇。在筆者看來,這些觀點在對意識形態和美學各自的涵義以及這兩者的生成和運行機制等的相關理解上失之偏頗,帶有精英主義和本質主義色彩,并且,這樣的討論仍然囿于二元體系的范式。提倡審美意識形態論并非要削弱任意一方的簡單化理解;而是將兩者有機結合;且這種結合并非簡單的“一加一”疊加。文學的審美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本身就是交互發生、相互作用、相互實現的;這兩者之間的關聯不可割裂。有鑒于此,本文將試圖在當代西方文論的視閾中,厘清意識形態和美學的內涵和范疇,以及這兩者同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關系,剖析當代西方文論界對審美意識形態的論爭,從而對西方學界的審美意識形態論進行全面闡釋,在分析國內學界審美意識形態研究的現狀與癥結之后,提出幾點建議,以期為國內文論界審美意識形態論的拓展方向提供參考。
一、 意識形態與文學及文學理論的關系
意識形態這一具有200余年歷史的哲學范疇容納了互不相容的多種涵義。伊格爾頓曾對“意識形態”這一錯綜復雜的概念“社會生活中的意義、符號和價值的生產過程”“權力與話語的結合”“個體的賴以同社會結構構成各種關系的媒介”等多種定義(Eagleton1—2;轉引自段吉方95—96);以上定義可以被概括為“作為一種生活關系而不是一種經驗描述的意識形態”(Eagleton 30;轉引自段吉方96)。雷蒙·威廉斯把意識形態的定義概括為標志著某一特殊階級或集團特點的信仰體系;或虛幻的信仰體系;或意義和觀念產生的一般過程(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55)。意識形態是穿越一切社會生產場域的唯一形式;“是一個文化假設系統,或一系列相互關聯的話語,支持或反對社會秩序的相關信仰或價值,或者隱藏或壓制社會和經濟型中的矛盾因素的思想結構”(沃爾夫萊129)。它無處不在;調和主體及其社會角色以及主體之間、主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從意識形態與藝術的關系來看,葛蘭西所提倡的“有機意識形態”(organic ideologies)是一種“在藝術、法律、經濟行為和所有個體及集體生活中含蓄顯露出來的世界觀,它廣泛分布于哲學、宗教、民間傳說等各層次意識形式中”(孟登迎770)。阿爾都塞將意識形態同主體建構、勞動力再生產等結合起來闡釋,展現了意識形態的物質因素和體制因素。這些因素體現在主體的自我建構、國家機器和社會機構的教化功能這幾個方面。他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詞來指“制度或機構,如教會和宗教、學校制度、法律、政治、媒體和交流,以及文化,不管是文學、藝術還是體育,都是這些‘機器’生產,是話語和社會實踐,它們鼓勵個體參與并支持這些話語和實踐”(沃爾夫萊136)。由此可見,主體性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考量的重要部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對主體進行質詢,賦予主體的社會身份。它是政治無意識所依附的物質基礎,是規訓個體以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領地。此概念在某種意義上打破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區分,表明了主導話語霸權對個人領域的滲透和宰制。意識形態體現了權力運作的展開方式;主體受到意識形態召喚,被意識形態所建構。意識形態效應可存在于在感性的個體體驗和規訓個體的霸權話語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中,并且與社會經濟狀況密不可分。意識形態不僅是主導政治話語的體現,也有著反主導政治的烏托邦色彩。
“文學語言就是形成意識形態效應的媒介。”(杰洛瑞57)語言是一種社會實踐;由語言所構筑的文學不能獨立于社會實踐而存在。文學是寫作的社會實踐。阿多諾認為:“藝術既為自己同時也為社會而存在,始終既是自己同時又是其他的某種東西,批判性地從歷史中疏離出來,但并不采取一個超越歷史的優勢點”(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351)。任何藝術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同歷史和意識形態纏繞,文學也不例外。文學的歷史與社會在文化的維度上歷史共存,這是威廉斯的基本觀點。他提出的“社會的文字和學習之間的不平衡”(unevenness of literacy and learning)表明,所有寫作的社會實踐都處在社會特權和民主分級的復雜過程之中,處于專業化和播散之中、教育的特權和剝奪之中、排除和重新適應之中(Williams,WritinginSociety46)。文學誕生于實際語境,但又被不斷闡釋和重新銘刻,而這樣的闡釋和銘刻受限于一定的意識形態。因而,“‘文學’本身永遠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伊格爾頓,《瓦爾特·本雅明》162)。作為形塑思想文化的一個平臺,意識形態對文學文化的生產有著巨大的參與作用。文學在公共權力領域往往采取批判的姿態;由于此種姿態,文學又成為了形成新的公共輿論的場域。因而,文學的孕育和悖離、滋養和變異,都處在意識形態之中。文學的生產脫離不了它所處的主導意識形態,但它又能夠超越對其進行宰制的霸權話語。統治階級利用文學來構建自身的意識形態體系,而往往在該意識形態體系成為主導意識形態后,一些文學和藝術就從中悖離,以其先鋒性和對現實桎梏的打破而批判地超越了其產生的場域。文學悖離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在于“文本中出現的社會現實已非歷史原貌,而是社會規范、傳統的變形,進入文本后便喪失了原有的實用性和權威性,被脫去了神圣的面罩,使人們對它的合法性產生疑問。而原本遭到主流意識形態壓抑的邊緣成分則趁機顯露出來,對權威提出挑戰并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伊瑟爾9)。可見,文學既是意識形態的反映,又是反意識形態壓制的敘述力量。
同樣,文學理論的政治性與意識形態也是互相孕育和互相構建的。從詞源學上可見,“理論”(theoria)一詞的希臘文字之源頭包含多重意義: 既指劇場觀眾觀看角度的儀式性再現和認知事物的意義,也有從仔細觀看、審視而延伸至深思的指涉;這兩層意義都指向“對公眾事務的見證”這一含有政治意味的涵義。“理論就是‘批評之批評’或‘元批評’。它體現了一種批評意識(對意識形態的批評),一種對文學的反思(反觀批評,自我意識或自涉)。”(孔帕尼翁13)理論的反叛性不僅體現在它對現實的批判、對意識形態的批判,甚至還體現在它對自身的批判上。理論關乎意識形態和語言學分析,“意識形態批評是對語言幻覺(認為語言和文學天生如此的觀念)的揭露: 唾棄理論之人者強調其天性,文論揭示其代碼與規約”(孔帕尼翁17)。概言之,“文學理論一直就與種種政治信念和意識形態價值標準密不可分”(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196—97)。
就理論中的意識形態批評而言,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將文學放進包括政治和經濟在內的社會關系網絡來進行理解,因而能夠闡釋文學與意識形態、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語境等之間的關系。在意識形態批評中,文學的生產傳播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意識形態的效果用圍繞文學本身的概念產生,也就是說,圍繞作為文學作品傳播手段的話語/機構形式而產生。”(杰洛瑞127)杰洛瑞把審美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結合,提出“價值的雙重話語”。詹明信在《政治無意識: 作為社會象征行為的敘事》(ThePoliticalUnconscious:NarrativeasaSymbolicAct, 1981)中,通過對歷史敘事的解讀解析了文化文本中的政治無意識因素;在文學闡釋中,社會象征行為和其中的意識形態內涵得以被挖掘。在《理論的意識形態》(TheIdeologiesofTheory, 1988)中,他再次聚焦于文本的歷史維度和政治解讀,通過對文本的闡釋來展現了意識形態中的烏托邦色彩。伊格爾頓認為,意識形態的作用是尋求思維和世界、語言和存在之間差異的調和,消除語言概念和感知直覺之間的區別。諸如馬舍雷、伊格爾頓等馬克思主義文論家認為,文學生產以意識形態為原料,由社會歷史進程決定。文學可以被理解為亞權力的一種意識形態形式。“解讀文學文本必須根據它們的不穩定性;一種意識形態實踐向意識形態行為亞層面的轉化是不穩定的,它會導致對其自身意識形態內容進行內在批判。”(格洛登 克雷斯沃思 濟曼主編986)文學在揭示和解釋意識形態的畸變性上,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作為一種文學批評范式,意識形態批評不僅關注文學的社會政治內容,更致力于發掘文學的意識形態意義同其實現之間的關系。
西方文論傳統在如何對待意識形態上持兩種不同的態度: 一種是將文學視為意識形態的反映,另一種是將文學視為顛覆意識形態的論述。前者將文學視為封閉的世界和壓制的手段;后者則主張,意識形態是封閉、壓抑的力量,文學則是解放的力量。自柏拉圖以來,西方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傾向之一便是把文學作品視為對社會文化價值的反映。然而,如果“把文學貶低成僅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反映而已,這些理論實際上傾向于把文學的作用限制為消極反映,成了現實的權力趨勢的一種不自覺的畸形寫照”(米勒,“文學理論在今天的功能”125)。如前所述,文學在傳達意識形態和支撐霸權秩序上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與此同時也是逃離霸權控制的重要途徑。文學理論也處于同樣的悖論當中: 它包含了一個時代的“階級統治觀念”,也就是主流意識形態;然而,與此同時,它也是對意識形態的批判以及自我批判的表征。文學和文學理論的內在理念離不開一定的政治批判立場和政治實踐態度(塞爾登 威德森 布魯克124—25)。從文學理論是被壓抑的意識形態的釋放這一層面來看,文學因其對情感等感性因素的強調而反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壓迫。從文學理論的社會實踐性來看,文學理論在各個層面上的權力活動實為文學-學術制度與整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權力-利益之間的權力關系問題之體現,服務于社會意識形態的需要(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206)。在理論對文學研究界產生的巨大影響中,理論的審美取向和理論的意識形態性都占據了重要角色。
二、 西方文論界關于審美和意識形態關系的論爭
德曼對文學理論中審美和意識形態的關系有著這樣的論述:“我們所謂的意識形態恰好就是將語言現實同自然現實相混淆,將語言的指稱同現象論相混淆。其結果是,研究文學性的語言學,比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其他任何形式的探究,都更突出地成為一種揭示意識形態偏差方面的強有力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以及一種解釋這些偏差發生原因的決定性因素。那些譴責文學理論忘卻了社會和歷史(亦即意識形態)現實的人,只不過是在訴說他們自己的擔憂,擔憂這一正受自己貶損的工具會揭穿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的神秘現象。”(De Man11)文學理論對意識形態有著強有力的揭示力量,對主導意識形態的霸權話語起到祛魅和質詢的作用。“理論對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構成了挑戰,因為它揭示了意識形態的運作模式;理論也違反了美學家們的哲學傳統,對文學經典提出了質疑,模糊了文學和非文學話語的界限。”(De Man11—12)從某種層面而言,德·曼此番對意識形態的闡釋反映了支持與反對文學的意識形態性的批評家之間的沖突。
文學理論應該對所處的意識形態進行反映并參與其構建,還是應該完全脫離意識形態而專注于文學性的研究,這是理論的支持派和反對派所爭論的焦點之一。此分歧可謂體現了文學及文學理論的審美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之間的矛盾。不少學者號召文學理論的審美回歸,反對將文學理論同意識形態聯系在一起。部分反對文學理論的意識形態性的文學批評家認為,意識形態傾向只代表一種霸權話語,從而壓制了其他的聲音。而實際情況是,在文化中存在多種聲音,每個聲音都代表一種意識形態,每種意識形態在追尋權力時都尋求按照一個特定的方向指引行動(柯理格28—29),因此不可能將人們的思想限制在單一的向度當中。另一方面,反意識形態的批評家認為,文學的顛覆力量能夠擺脫意識形態的桎梏。文學文本自身遠非封閉,因而其反意識形態論述能夠削弱任何意識形態敘述的整體性(35)。然而,對意識形態的過于反對有可能陷入“否定的意識形態”的狀況,成為“抗拒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從社會學批評的角度來看,反意識形態的各種理論,也來源于意識形態領域(162)。反對將意識形態同文學理論聯系起來的批評家認為,將文學作品的概念視為一個僅僅只具政治功能的事物,實為剝奪其作為文學批評之客體的功能。跟隨這一邏輯,文學理論死亡的結論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毋庸置疑,這一只承認文學審美功能而否定其社會功能的邏輯顯然是不成立的。作為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文學不斷參與社會意識形態的構建,文學理論也就相應地是具有行動力的社會實踐活動。理論話語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其政治實踐的完成。伊格爾頓認為,文學理論都帶有某種政治傾向。他將文學理論視為當代政權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化的一部分,是政治意識形態的體現。理論的重要實踐功能是揭露、批判和挑戰主流的價值觀。因而,文學理論不應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譴責;應受譴責的是其對自己政治性的掩蓋或無知(《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197)。當代文學理論體現出與社會和歷史現實的脫節,另一方面又在逃離意識形態的舉動之中暴露出與之的同謀關系。“文學理論的問題在于,它既不能戰勝又不能加入后期工業資本主義的種種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201)這說明,單純地依靠意識形態并不能讓文學理論的實踐作用得到有效實施。
從美學層面來看,號召單純回歸文學理論的審美功能的批評家,實際上對美學的定義過于狹窄。審美認知介于理性與感性之間,既有對主體經驗的感性關注,又有對社會文化機制等因素的理性思考。美學的現代觀念的建構與現代階級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建構是密不可分的。然而與此同時,美學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也持有質詢和挑戰的態度。在現代社會中,美學不僅能調和并加強權力運作,也能夠對意識形態的構成因素進行批判和超越。正如米勒所言,文學理論是唯一一種避免將文學封殺在唯美主義范圍中的形式(《重申解構主義》246—47)。部分左翼批評家將美學的內在復雜性簡化為直接的意識形態功能,這也是對當今理論功能的片面化理解。德曼道出了文學理論受到抵制的根本原因:“文學理論的什么東西這么嚇人,以至于激起如此強烈的抵制和攻擊?它由于揭示出意識形態的運轉機制,而傾覆了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它反對美學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強大哲學傳統;它瓦解了文學作品既定的經典,模糊了文學和非文學話語之間的界限。言外之意是,它也可能揭示出意識形態和哲學的聯系。”(de Man103)文學和文學理論都沐浴在其所處的社會意識形態和美學傳統中,這同時也是逃離意識形態控制和傳統美學桎梏的方式。審美活動對主體和主體所處的社會所產生的啟蒙力量是隨著文學生產而不斷被激發的,因此,從文學的審美價值而言,社會實踐和政治實踐是不能割裂的。顯而易見,過分強調文學和文學理論的審美性或意識形態性都是不可取的。理論的審美功能和社會功能之間需要調和以達到一個平衡點,過于強調或忽略一方都失之偏頗。
自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以來,整個西方知識界和思想界都被埋下了批判反省的種子。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早期法國理論的沖擊不僅是一個理論革新,同時也引發了學界文學理論的范式轉換。之前并未開展理論闡釋的批評家開始將文學批評和意識形態緊密結合起來,這一轉變使得“理論”一詞比起其文學闡釋層面上的意義而言,更偏重于意識形態上的意義。1968年之后,在批評理論的旗幟之下聚集的各種理論是支配某些學術環境的自由意識形態。推崇“文化政治批判”的“新左派”知識分子既想擁有政治話語權,又想在社會文化語境中推行審美關懷。左翼批評家致力于文本的外化,試圖將意識形態分析等更為廣泛的話語涵蓋進文學話語當中。在文本分析的具體操作上,文本的文化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經濟、政治體制和歷史基礎等,也被納入了研究范圍,形成整體化分析模式。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在西方的文學研究傳統中,意識形態傳統同美學傳統的沖突帶有否定理論的意識形態性傾向。此可謂當代西方社會文化種種顯性或隱性、理論或實踐、集體或個人的焦慮的表征。實質上,文學的學術批評從一開始就由一系列的理論爭端構成。這些爭論不僅限于對作為一門學科的文學之本質的討論,還包括探討文學研究這門學科存在的必要性,甚或文學存在的必要性。正是這些理論爭端豐富了文學研究的學科性。當下理論的種種困境促使今日的學者在更多的維度上反思意識形態、文化霸權以及國家機器之間的種種矛盾與沖突。唯有考察意識形態的深層次內涵,深刻洞悉文學的美學價值和意識形態價值的生成和運行機制,才能獲得理論化深思所需的縱深與距離感,才能堅持理論的實踐性。理論的實踐性與文學的審美性、意識形態性密不可分;若要恢復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理論、美學、意識形態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不得不仔細考量的問題。文學話語和文學實踐都體現出文學是一種特殊的審美意識形態。文本生產是一種意識形態生產;而意識形態生產是復雜而隱蔽的精神活動和意識過程。各個主體通過意識形態產生共鳴;這是一個復雜的集體無意識過程,其中包含了情感、心理等各種美學因素,也與意識形態的物質層面脫不了干系。在文學體制的進程化當中,文學作為文化資本的表征,承擔著審美話語和政治話語的雙重功能。
三、 文學理論中的審美意識形態
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是能解決文學的美學和意識形態這兩種功能之間沖突的方式之一。如伊格爾頓所言,文學是一種審美的社會意識形態,具有實踐功能。他提出“審美意識形態”這一概念,認為審美話語具有意識形態的內涵。伊格爾頓在《批評與意識形態》(CriticismandIdeology, 1978)和《美學意識形態》中都強調了審美與政治和權力的關系。在《美學意識形態》中,他駁斥了把美學視為中立和無功利性的觀點,闡釋了現代社會中美學和意識形態的一致性。他認為,維護社會秩序的最根本力量,如風俗習慣、情感、愛等,有著審美化的成分。“美學著作中的現代觀念的建構,與適合于那種社會秩序的人類主體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導言3)他反對統一的、整體的意識形態觀念體系,希望在對差異性的強調中找尋審美話語的政治蘊含和理論的批評性功能。
自康德以來,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形式,其與認識論和倫理學的聯系被埋沒在美學理論之中。在其起源和發展過程中,美學成為了哲學本質的領域,而非語言哲學的領域。美學理論也未能成功地以一種綜合判斷的形式來統一認知、欲望和道德層面。以席勒、馬克思、馬爾庫塞等為代表的左翼美學家認為,藝術作為主客體關系的調和方式,作為對處于社會中被異化的人的批評,作為個體和社會之間和諧關系的想象,與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是互相纏繞的。“由于美學的整體性概念被疑惑地解釋為現代社團國家所要求的公民必須順從的某種壓迫性意識形態的投射,所以,對許多批評家來說,展示截然相反的一面也就成了他們的政治責任[……]。”(Baldick165;轉引自格洛登 克雷斯沃思 濟曼主編68)在福柯看來,“政治壓迫的權力在本質上也是審美的,由它自己的自我享受、自我膨脹所掩蓋起來”(《美學意識形態》388)。威廉斯注重文化與社會分析,阿爾都塞注重意識形態文化實踐,本雅明強調文學批評的“革命”精神,伊格爾頓提出了“以意識形態生產”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生產美學”(段吉方113),這些觀念都體現了審美與意識形態結合的可能性。可見,審美可謂意識形態的范式;在某種程度上,美學可被視為內在的“抗拒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主體在美和意識形態中既取得精神上的崇高感,又在無意識中受制于權力。“文化領域是一個非強制性一致的領域;審美判斷的本質恰恰在于它們是不可能被強制的。”(《美學意識形態》87)審美意識形態是一個矛盾的概念,但其有效性正是體現在這種矛盾當中:“如果意識形態想要有效地運轉,它就必須是快樂的、直覺的、自我認可的: 一言以蔽之,它必須是審美的。然而,在此鮮明的悖論中,這恰好就是威脅要損耗其客觀力量的東西。把意識形態更深入地置于主體中去的行動終以意識形態的瓦解而告終。”(《美學意識形態》30)可見,美學對于意識形態霸權又有著強有力的挑戰。因而,不能把美學的內在復雜性與矛盾性簡化為簡單的意識形態功能。
審美意識形態是對審美話語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這種深層次聯系的揭示。同意識形態一樣,審美也充滿悖論和復雜性。美學的矛盾性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美學中存在著反抗權力的力量,而權力又規約著美學。審美話語在反映其所處的意識形態語境的同時又對其進行挑戰。它的解放力量體現在,它“例證了自律和自我決定的新形式,改善了法律和欲望、道德和知識之間的關系,重建了個體和總體之間的聯系,在風俗、情感和同情的基礎上調整了各種社會關系”(《美學意識形態》16)。通過把情感、風俗等感性因素深深鐫刻進主體,審美意識形態隱蔽地實施了社會統治。從某一層面而言,審美體現了政治無意識,是主體無意識中將意識形態銘刻在內心的一種方式。正如伊格爾頓所言:“美學是道德意識通過情感和感覺以達到重新表現自發的社會實踐之目的所走的迂回道路”(28)。美學以一種感性和柔性的方式傳達著理性和剛性的意識形態內涵和政治話語,通過對主體的內化來悄無聲息地形塑著人們的觀念、社會的規約。“審美保證了主體之間自發的、直接的、非強制性的一致,提供了防止社會生活的異化的情感紐帶。”(89)在審美的感召之下,主體自發自愿地形成了具有凝聚力的集體無意識。處于社會中的主體和他者在審美和意識形態的平衡和制約中獲取和諧相處的方式,實為在審美基礎上的意識形態建構。這正如席勒所提出的“審美的心理調節”這一觀念:“如果人類想要在實踐中解決政治問題,就必須通過審美教育的途徑,因為只有通過美人類才能走向自由。”(95)齊澤克將文學和意識形態同語言、欲望的無意識構建結合起來,注重主體心理和文化實踐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現代意識形態系統通過結構與主體之間固有的距離發生作用(齊澤克29)。正是這種距離讓審美能夠在主體和社會之間發揮調停的功能。同時,主體在無意識中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控制和侵染,盡管從憤世嫉俗的立場來對待主流意識形態和權威話語,在行為上還是受它們控制。“美和崇高都是意識形態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人文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問題在于如何將意識形態的中心性和撫慰與必要的尊敬和主體的服從統一起來。”(80)通過審美意識形態,倫理和政治責任被內化,深入主體性中。審美意識形態能讓主體在擁有個體獨特性的同時,對意識形態體系有歸屬感,獲得一種雙重意識形態的效果。審美話語中的無意識政治因素在此種悖論中能得到展現。
意識形態批評具有對現實的實踐效應。體現這一理論有效性的方法之一是將理論的意識形態功能與審美功能結合,尋求審美價值與文化政治融合的途徑。此種途徑要求將文學置于社會文化語境之中,在重視對文學生產、傳播等各個環節研究的同時,進行審美和哲學上的深度反思。文學不可避免地處于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系當中,體現審美話語中的意識形態內涵。文學有其物質性,其研究包括文學的生產和流通等環節;文學也有其審美屬性,體現著情感、心理等感性層面。意識形態本身既是上層建筑和權力話語的體現,又參與社會生產和文化資本的構建。意識形態具有審美幻想的象征內涵,有其在社會現實中的實踐功能,也有著建構主體的功能。因而,如何把審美的感性層面同其意識形態屬性以及意識形態生產結合起來,是把審美意識形態運用于實踐的關鍵。詹明信認為,對文學作品的閱讀應當從純粹美學和形式的問題開始,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尋找政治、社會、歷史的意義(詹明信7)。從美學的層面而言,應當把在狹義上將文學僅當作藝術作品來理解,轉移到從寫作的社會實踐來理解。寫作的社會實踐表明了文學在公眾中的形式,而內在形式的美學經驗同樣包含在公眾之中。因此,文學的社會和審美問題通過公眾領域的體制化而相遇。文學理論的審美功能和社會功能之間既保持距離又亦步亦趨。通過審美解決政治問題的設想在理論的發展史上也屢見不鮮。現代和后現代的思想家,包括席勒、尼采、馬爾庫塞、本雅明甚或福柯,他們的思想都對審美與意識形態所代表的政治權力關系進行了闡發,強調審美話語的批判張力的實現。而伊格爾頓的“審美意識形態”概念更多地是作為一種批判性的政治概念而出現,強調審美意識形態在批判的同時也具有建構上的意義。這不失為在當代左派批評陷入困境之后,文學理論的美學功能和社會功能結合的一種批評實踐方式。概言之,文學的審美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張力是可以調和的。文學理論并非只有“政治化”和“去政治化”這兩個選項,而是可以將審美功能和社會功能融為一體,從文學概念的社會維度和美學維度來進行綜合研究。
審美意識形態既有基于主體經驗的美學的感性、情趣、鑒賞,又有從個體體驗聚合而成的共識性的集體無意識,在意識形態層面達到抽象。理解審美意識形態的發生機制和實現機制有助于更為深層次地理解審美的本質和意識形態的內核。后現代所推崇的日常生活審美化,使得審美意識形態能夠通過日常生活的無意識來實踐政治話語。作為個體的人既具有審美的知覺,也有著在社會中獲得權力話語的愿望。在傳統理性走向危機之時,審美意識形態的崛起表明了主體的權力話語的實現需要通過深層和感性的個體經驗,才能彌合個體意識形態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使主體對抗宏大的話語霸權,獲取真正的解放力量。
四、 國內文論界“審美意識形態論”的反思與展望
1982年,錢中文提出,“文藝是一種具有審美特征的意識形態”(“論人性”92)。他認為,文學的本質特性是多層次的;其第一層次的本質特性是審美的意識形態性。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邏輯起點是審美意識而非意識形態,審美意識作為人的本質的確證是建立在長期文學實踐的基礎之上的(《文學發展論》86)。童慶炳將審美意識形態論定為文藝學的第一原理,他倡導審美意識形態論的實踐效用,指出實踐是“審美”與“意識形態”結合的中介,“人的情感在審美實踐中直接生成審美意識形態”(“實踐是‘審美’”16)。文學“審美反映論”和“審美意識形態論”是整一性的復合結構(“新時期文學”64)。自童、錢二學者之后,王元驤等也大力提倡審美意識形態論。王元驤堅持把文學藝術視為意識形態的一種特殊形式,堅持審美、政治、道德理想的交匯(“我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的理解”6)。他認為,文學是作家審美意識的物化形態(《文學原理》25);提出在“特殊性的層面上以‘審美的’來規定文學藝術的‘意識形態’特性”,“有助于內化為自己的思想人格”(“我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的理解”12)。他的此種觀點可謂與西方學界審美意識形態論中審美和意識形態對主體的建構功能有一定的相似性。
國內文論界的審美意識形態論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基礎上,發掘并整合了中國審美傳統對人本主義的重視,并將其同新的歷史語境結合在一起,由此,傳統美學就具有了當下的實踐力,以及學理上的創新性。中國學界的審美意識形態論基于中國的美學和文學現代性語境。由于文學傳統、美學傳統和社會文化語境等的不同,國內學界所提出的審美意識形態雖然受西方文論界審美意識形態觀念的影響,但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其的反映和跟隨,而是“本土產”與“本土化”相結合的一種發展。縱觀國內審美意識形態論三十余年來的發展,相比其誕生之時有了一系列理論上的推進。錢中文把文學的社會文化屬性和美學屬性結合起來考量,注重意識形態的物質性和產生過程。童慶炳的“文化詩學”借用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提倡人文主義和歷史理性(吳子林227)。王元驤指出,需要把現有的審美意識形態論進一步向文藝本體論和人學本體論拓展,把以往的文藝形式批評整合到審美意識形態論當中(“對審美意識”160—65)。然而,國內學界的審美意識形態論還是基于精英主義視角,如童慶炳、王元驤等,對將精英文學同大眾文化等同和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理論走向頗為質疑。近年來,國內學界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的討論更偏向于呼吁審美意識形態對社會文化的建構功能和政治參與功能,以及對審美日常化的關注。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所關注的,是當代國內文論界審美意識形態論的基本問題和理論指向,如何立足于闡釋當代大眾文化的審美基礎,并由此深入研究審美日常化同文學藝術與意識形態的特殊關系(王杰13—21)。此外,也有學者呼吁從“審美意識形態”進行“文化轉向”的話語修正(李艷豐148—55)。
與西方的審美意識形態,尤其是伊格爾頓的審美意識形態論相比較,當下國內學界的審美意識形態論對文學的生產、傳播、接受以及由此對主體建構方面的研究,以及對差異性的強調等,還有待進一步拓展。然而與此同時,國內的研究更為注重中國的美學傳統和審美價值取向。國內不少學者提倡審美意識形態論中的“人學”,這和當代西方文論中所提倡的意識形態和美學對主體的建構有趨同性,同時也有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學”的特色。不難看出,相比20世紀80年代最初提出之時國內學界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的討論提出了新的呼吁;期待的拓展方向從美學和意識形態只是單純反映社會文化拓展成為社會生產和主體建構,從最初的精英主義傾向拓展為將文學文本外化的審美日常化傾向,從文學的審美和意識形態反映論轉為反映和建構雙向并重,加強了審美意識形態論的實踐功能,提升了其時代效應,具有能夠包容多種取向,重視社會文化語境和文化生產的傾向,體現多元并置和注重差異化的取向。諸種討論的變化和轉向體現了國內學界同西方學界的交流和接軌,也是國內學者對國際文論界熱點問題的積極參與和回應的體現。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該論題的拓展和深入展現了國內學者的問題意識、自省精神;也體現了中國文論界學術在國際文論界的話語創新力量。
審美和意識形態這兩者都是流動的、具有多種內涵的范疇;文學與文學理論也是開放和發展的話語體系。審美和意識形態是文化構建以及社會中的主體建構的重要因素,其實踐功能和闡釋有效性是持續的。中國當代文論中的審美意識形態論在歷經三十余年的生長后,在學理上有所推進。在當今社會文化語境中,文學的文化轉向進一步加劇,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邊界逐漸消失,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國內學界的審美意識形態論需要繼續深化和拓展以保持其闡釋有效性和實踐效能。在具體的途徑上,首先,國內的文學和文論研究應當關注文學生產的問題體系,從文學生產同經濟生產的聯系角度來關注審美意識形態的物質性,擴展研究視野。由于文學生產深陷于商品生產的結構之中,因而會隨商品生產結構的改變而改變。近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生產結構的轉型帶來了社會文化結構的轉型,文學話語生產機制由此發生嬗變。基于此種變化,當今國內的文學研究應該注重不斷演變的文學話語生產機制的文化資本層面;其中,資本的構成和形式等文化場域要素都應該被囊括進研究的范圍,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學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物質性。其次,由于意識形態的構成因素包括物質的和象征的生產,和日常生活不可分割,所以國內學界對文學生產的研究應該重視意識形態實踐的日常層面。在審美日常生活化的今天,美學經驗已經滲入了社會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以中國傳統美學觀念來看,“在世”品格同生活美學以及日常生活審美化具有共通性。由于審美意象的構建是一種心靈自由的活動,所以唯有通過貼近生活層面,注重現世關切,才能找尋打破束縛心靈的力量。這不僅是對西方當代文藝美學潮流的呼應,也是對中國傳統美學的傳承。因而,在國內學界的文學研究中,提倡日常生活審美化和生活美學,挖掘生活原有的審美品質,能夠更好地把文學和文論還原到日常的生活感受和生活體驗當中,避免文學文論同日常生活經驗的斷裂而導致的學術僵化。當下的研究應從日常生活審美現象中提煉出多樣化的意識形態和美學觀念,推進更具有實踐效力的審美意識形態,并以此來參與和構建大眾的文化生活,提高對現實生活的闡釋有效性。第三,要關注日常的意識形態,就應該注重文學中所反映的差異化的個體感受,而非整體性和宏大的意識形態觀念。通過把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同當下的語境緊密結合,注重文學所傳達的個體經驗和情感之美,沖破傳統的審美自律論或以往的政治工具論的藩籬。注重審美意識形態的物質性,注重文學的生產、傳播和接受,從某種層面而言,是對微觀政治和差異化社會的認同。在理論和實踐當中存在一個意識形態的自由度,因而,將文學文本放進文化場域中進行理解,分析其中異質性、互不兼容的個體論爭,有助于對宏大敘事進行消解。當今,國內文化意識形態的格局是多元共生的;在差異化和文化間性的場域中,審美意識形態論的功能有著充分展現自身的可能性。審美的差異化和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在主體意識和主導意識形態之間的距離更能產生批判和超越的力量。學界應充分注重個體意識和意識形態的雙向建構性,對文學中所反映的主體的審美經驗和意識進行探討,在承認審美體驗和意識形態多樣性和復雜性的前提下進行研究。
當今的國內文論界,對文化研究這一批評范式從最開始的較為排斥逐漸轉為了接受和認同,這也為審美意識形態在學界的新發展提供了土壤。國內學界的審美意識形態若要有進一步的推進,應將美學、意識形態和政治社會綜合起來進行研究。在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的研究方面,學界若能把文學文本同當前機制下的文化客體、社會結構、政治無意識和經濟體系等聯系起來進行綜合分析,通過對社會關系結構和主體認同活動的分析來考慮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性,重視審美和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的、有現實功用的物質性存在,在強調其人文精神的同時又注意避免其成為脫離政治的空中樓閣,將能較大地推動文藝美學的發展。國內文論界如能在汲取傳統美學精華的同時,跳出經典美學的自律和精英化的限制,致力于融入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在碎片化和差異性的社會中討論意識形態的多樣化態式,使得審美意識形態注重當下性和時效性,則能更有效地反映和回應時代。
結 語
學界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的爭論,都有著明顯或暗含的政治取向和意識形態意蘊。不同文學理論或“非理論”之間的爭論所涉及的問題,實為現代社會中文學研究對抗其各種命運的意識形態策略。審美和意識形態都是充滿悖論的,錯綜復雜的,包容差異性的,帶有烏托邦色彩同時又具有功利目的性的;感性和理性、物質與精神、意識與無意識、主體與客體、反映與構建、規訓與解放等以往二元論的概念在這兩者身上都同時并存和同時呈現。審美意識形態可以對公共領域進行重新構建,讓個體在社會語境中獲取心靈自由的途徑。即使在文學理論的文化轉向以及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等同的大背景下,文學理論的審美意識形態的實踐作用仍然是顯著的、亟待實現的。當今的各種“小理論”和亞文化所構筑的流動、多變、多元的意識形態也在不斷更新審美的范疇、實踐方式。在此背景下,文學研究更需要注重批評的文化實踐功能,在堅持文學理論的社會實踐性與批判性的同時,追求其審美旨趣。當今國內文學界匯集了多種文學生產方式和話語模式,既有受西方美學話語影響的創作,也不乏遵循傳統美學范式的作品;對文學觀念有著多維度的探討。在此種眾生喧嘩的態勢之下,審美意識形態論有利于關注個體敘事和主體經驗,因而是貼近日常生活的,而不是與大眾文化脫節的上層建筑。在當下的語境中,國內學界審美意識形態論如能在注重文學的意義播散和多重闡釋、審美和意識形態的物質性、日常生活審美化、主體建構等方面有所推進,將在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更具滲透性,更匹配文化的異質性和多樣性,將在社會文化實踐中有不竭的生命力。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lthusser, Louis Pierre.EssaysonIdeology. Trans. G. Lock.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4.
Baldick, Chris.CriticismandLiteraryTheory,1890tothePresent.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安托萬·孔帕尼翁: 《理論的幽靈: 文學與常識》,吳泓緲、汪捷宇譯。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Compagnon, Antoine.TheDemonofTheory:LiteratureandCommonSense. Trans. Wu Hongmiao and Wang Jieyu.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de Man, Paul.TheResistancetoTheory.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段吉方: 《意識形態與審美話語——伊格爾頓文學批評理論研究》。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
[Duan, Jifang.IdeologyandAestheticDiscourse:AStudyonTerryEagleton’sTheoryofLiteraryCriticism.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0.]
Eagleton, Terry.Ideology:An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1.
特里·伊格爾頓: 《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 -.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 Trans. Wu Xiaom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美學意識形態》,王杰、付德根譯。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
[- - -.AestheticIdeology. Trans. Wang Jie and Fu Dege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4.]
——: 《瓦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評》,郭國良、陸漢臻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5年。
[- - -.WalterBenjamin:Or,TowardsARevolutionaryCriticism. Trans. Guo Guoliang and Lu Hanzh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Gramsci, Antonio.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邁克爾·格洛登 馬丁·克雷斯沃思 伊莫瑞·濟曼主編: 《霍普金斯文學理論和批評指南(第2版)》,王逢振等譯。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
[Groden, Michael, Martin Kreiswirth, and Imre Szeman, eds.TheJohnsHopkinsGuidetoLiteraryTheoryandCriticism(SecondEdition). Trans. Wang Fengzhen, et a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1.]
約翰·杰洛瑞: 《文化資本: 論文學經典的建構》,江寧康、高巍譯。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Guillory, John.CulturalCapital:TheProblemofLiteraryCanonFormation. Trans. Jiang Ningkang and Gao Wei. Nan 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沃爾夫岡·伊瑟爾: 《怎樣做理論》,朱剛、谷婷婷譯。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Iser, Wolfgang.HowtoDoTheory. Trans. Zhu Gang and Gu Tingti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詹明信: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僑等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年。
[Jameson, Fredric.TheCulturalLogicoftheLateCapitalism. Trans. Chen Qingqiao,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默里·柯理格: 《近代美國理論——建制·壓抑·抗拒》,單德興譯。臺北: 書林出版社,1995年。
[Krieger, Murray.TheIdeologicalImperative:RepressionandResistanceinRecentAmericanTheory. Trans. Shan Dexing. Taipei: Shulin Publishing House, 1995.]
李艷豐:“文化轉向與中國當代審美意識形態理論的‘合法性’考察”,《文藝理論研究》5(2013): 148—55。
[Li, Yanfeng. “Cultural Turn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The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 Ideology.”TheoreticalStudiesinLiteratureandArt5(2013): 148—55.]
孟登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西方文論關鍵詞》,趙一凡、張中載、李德恩主編。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767—74。
[Meng, Dengying,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KeywordsinWesternLiteraryTheory. Eds. Zhao Yifan, Zhang Zhongzai and Li De’e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767—74.]
希利斯·米勒:“文學理論在今天的功能”,《文學理論的未來》,拉爾夫·科恩主編,程錫麟、王曉路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121—32。
[Miller, Hillis. “The Fun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Today.”TheFutureofLiteraryTheory. Ed. Ralph Cohen. Trans. Cheng Xilin and Wang Xiaol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3.121—32.]
——: 《重申解構主義》,郭劍英等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 - -.RestateDeconstruction. Trans. Guo Jianying,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8.]
錢中文:“論人性共同形態描寫及其評價問題”,《文學評論》6(1982): 82—93,124。
[Qian, Zhongwen. “A Discussion on the Description of and Evaluation on the Common Form of Humanity.”LiteraryReview6(1982): 82—93,124.]
——: 《文學發展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 - -.OntheDevelopmentofLiterature.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5.]
拉曼·塞爾登 彼得·威德森 彼得·布魯克: 《當代文學理論導讀》,劉象愚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Selden, Raman, 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eds.AReader’sGuidetoContemporaryLiteraryTheory. Trans. Liu Xiangy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童慶炳:“實踐是‘審美’與‘意識形態’結合的中介——對近期‘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質疑的三點回應”,《文化與詩學》2(2009): 3—18。
[Tong, Qingbing. “Practice is the Agent of Combining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Three Responses to Recent Doubts on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Ideology of Literature’.”CultureandPoetics2(2009): 3—18.]
——:“新時期文學審美特征論及其意義”,《文學評論》1(2006): 64—74。
[- - -. “On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and Its Significance.”LiteraryReview1(2006): 64—74.]
王杰:“當代中國語境中的審美意識形態理論”,《文藝研究》8(2006): 13—21,166。
[Wang, Jie.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Ide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text.”Literature&ArtStudies8(2006): 13—21,166.]
王元驤:“我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的理解”,《文藝研究》8(2006): 4—12,166。
[Wang, Yuanxiang. “My Understanding of ‘Aesthetic Ideology’.”Literature&ArtStudies8(2006): 4—12,166.]
——: 《文學原理》。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
[- - -.LiteraryTheory.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9.]
——:“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的再反思”,《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2009): 160—65。
[- - -. “Reflections on Aesthetic Ideology.”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5(2009): 160—65.]
Williams, Raymond.Marxismand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 -.WritinginSociet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4.
于連·沃爾夫萊: 《批評關鍵詞: 文學與文化理論》,陳永國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Wolfreys, Julian.CriticalKeywordsinLiteraryandCulturalTheory. Trans. Chen Yongguo.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吳子林:“中國審美學派——理論與實踐: 以錢中文、童慶炳、王元驤為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2009): 217—41。
[Wu, Zil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Aesthetic School: Centering on Qian Zhongwen, Tong Qingbing, and Wang Yuanxiang.”ResearchonMarxistAesthetics2(2009): 217—41.]
?i?ek, Slavoj, ed.MappingIdeolog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4.
斯拉沃熱·齊澤克: 《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光茂譯。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
[- - -.TheSublimeObjectofIdeology. Trans. Ji Guangmao.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