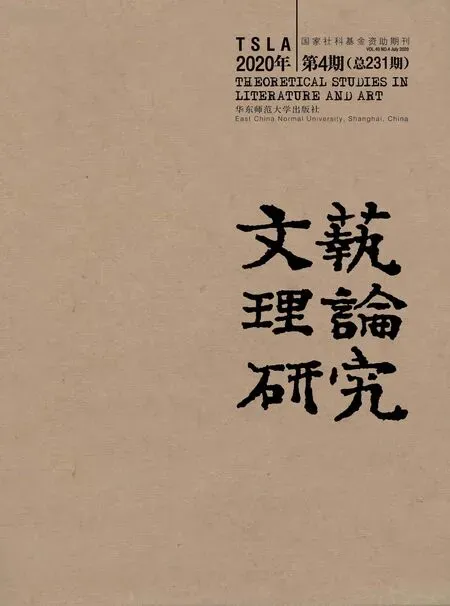從創作到制作: 網絡新媒體視域下文學生產方式轉型
李靈靈
中國大陸的當代文學地圖又變了。自王曉明撰文《六分天下: 今天的中國文學》,①距今已十年,今日之文學版圖格局,大致呈三足鼎立之勢: 嚴肅文學、暢銷書文學和網絡文學。前兩者可歸為紙面文學,嚴肅文學延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期刊文學,繼承了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現代文學”傳統;暢銷書文學是商業圖書出版機制下,以打造暢銷書為目標的紙面文學;網絡文學又可細分為原創文學網站機制下的網絡類型小說、自媒體文學以及跨媒介平臺的文學存在。三者各自適用于不同的市場邏輯。
王國維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十年前網絡文學已占半數,如今更以燎原之勢,成為這個時代的文學主角。其中以網絡類型小說和自媒體文學為甚,較之嚴肅文學和暢銷書文學,這是完全不同的文學類別,在文學生產方式上與傳統紙面文學有本質的區別。
網絡文學的商業化和產業化,催生了一大批網絡職業寫手和職業作家。2006年,體制內作家洪峰為聲討文化局不發工錢,展示了一場“作家乞討秀”。2009年,《南方人物周刊》策劃了“網絡文學”專題:“寫小說賺大錢”。兩相對比,更顯嚴肅文學的“凄涼”。大批以文為生的寫手作家們,紛紛從傳統紙面文學轉陣網絡文學。艾瑞咨詢《2018年中國網絡文學作者報告》顯示: 自2015年起,中國網絡文學作者數量一直保持30%的高速增長,到2017年底,網絡文學作者規模達到了784萬人(艾瑞咨詢6)。
習慣了傳統文學創作的作家們轉向網絡的過程并不容易。較早從文學期刊轉向網絡寫作的作家比如打工作家,他們為早已市場化的文學期刊撰寫面向打工者的打工文學,對市場變化比較敏感。當媒介變遷之際,打工作家走向分化,一部分轉向體制內嚴肅文學,一部分轉向網絡文學市場。②最初轉向網絡文學的作家們處處碰壁,他們發現: 這個新生的文學市場上,已經找不到他們的讀者了。他們的寫作題材和寫作手法,都和網絡文學格格不入。“移民”網絡的作家要改變寫作策略,因為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學生產。
有兩種作者不受新媒體帶來的文學生產方式轉型的困擾。一種是一開始就在網絡上寫作的作家,比如方舟子、蔡智恒、今何在等等,有意思的是: 在網絡文學領域最先崛起的作家都不是中文系出身,如方舟子是生物學博士,蔡智恒是水利工程博士。因沒有經受嚴肅期刊文學的“審美規訓”,其作品語言鮮活,想象力豐富,思想大膽。另一種是新生代網絡作家,幾乎沒有接觸過“期刊文學”,沒有太多的顧慮和桎梏。新生代知識儲備、知識結構和前輩作家不同,他們一開始就生活在網絡世界,讀著網絡小說長大,熟悉新生代的語言,相比之下,這些90后、00后更熟悉同齡人的審美情趣。
網絡給文學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只是變換了發表和傳播的媒介”(何平1—3),還意味著和此前完全不同的文學書寫。“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劉勰407),網絡新媒體時代的文學不僅受到審美代溝和審美趣味差異的影響,③也受到新媒體文學生產機制的制約。和紙面文學傳統相比,新媒體文學生產機制要求作家在文學生產方式上實現轉型,至少面臨三個方面的轉變: 從寫“我”到為受眾寫,從類型化寫作所要求的知識“層累化”到反類型化,從文學小作坊到大規模的模式化生產。這種根本性的時代轉型,將影響和造就文學范式的根本性轉型,塑造一種新的文學生活。
一、 從寫“我”到為“分眾”寫
網絡文學出現之前,與之相區別的是肇始于19世紀末的“新文學”或“現代文學”傳統,及已經形成秩序化的審美規范、評價機制和生產傳播方式等(何平1—3)。這個傳統幾乎影響了20世紀中國的整個百年文學進程,在網絡文學前產業化階段,網絡精英或草根的自由寫作也深受其影響。2003年,起點中文網首創VIP收費閱讀制度,這個開創性的制度將網絡文學推向市場,陳村感慨網絡文學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④從此,網絡文學在產業化之路上狂飆突進,一去不復返。
“現代文學”傳統的誕生以“啟蒙”為口號,由少數精英來“教化大眾”,而網絡文學寫作卻越來越呈現協商機制、互動文化特點。⑤網絡作家首先要滿足受眾的需要,與受眾“共同寫作”。原創文學網站的文學生產機制中,在線連載的網絡類型小說形成一個互動的文學空間: 網絡文學讀者不需要作者有多高深的寫作技巧,不需要多精妙的語言表達,高明的讀者都自帶吐槽模式,在評論區的評點、調笑和怒罵中,作者經由讀者“指引”合作共同完成小說,“在沒有邊界的討論中,所有參與人員都成為延續話題的生產者”(許苗苗130—37)。
新媒體特有的互動屬性,使文學生產脫離了印刷媒體時代創造一個完美文學典范的愿景,文學的“歷時性”意義被打破,網絡類型小說的生產更像是在空間意義上基于情感、審美、交際的粉絲文化。作家不再是孤獨的創作者,他(她)有了更多陪伴者同行;但作家在20世紀“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權威、神圣光環不再,從“啟蒙精英”轉變為文學“明星”、文學“大神”。更多時候,作家要照顧粉絲受眾的閱讀期待。網絡作家高樓大廈接受周志雄采訪時說:“不管是學生還是成人,現實生活中都有太多的猶豫[……]如果主角猶豫,我會很難受,我會把主角塑造得更果斷一些,更多的是讀者要求果斷,倒不是因為作者,所以有的時候其實不想果斷,但是這個確實是為了迎合市場。”(周志雄編29)在新媒體文學交際場域中,粉絲受眾是衣食父母,網絡文學生產不可能“自說自話”,“明星作者-粉絲受眾”的新型文學互動關系,打破了傳統相對封閉的文學生產和文學消費(何平1—3),而轉變為由印刷媒體時代“作家中心”轉向新媒體時代“讀者中心”的文學生產活動。⑥
嚴肅期刊文學時代單向傳播,把受眾假想為趣味單一的整體,與其審美趣味的單一供應相比,網絡文學場域具有審美趣味分化和審美群落化特點。網絡類型小說自帶審美差異,趨向多樣化的豐富類型,自媒體細分市場和自媒體文學具有“垂直”屬性。⑦這意味著作家需要滿足細分后的受眾需要——專門為某一類讀者的獨特趣味而寫,傳媒行業稱之為“分眾”,網絡文學受眾也具有“分眾”屬性。網絡作家一旦開始從事網絡文學寫作,他(她)首先要定位,為哪一部分讀者而寫,該類讀者喜歡什么樣的題材。這與純文學“決不為取悅讀者而寫作”的路子大相徑庭。
作家首先要作充分的市場調查。網絡作家孔二狗以寫《黑道風云二十年》一舉成名,他說自己正式寫作這本小說之前,花了兩年時間考察各個中文論壇,用專業商業咨詢的眼光挨個分析,最后鎖定“天涯雜談”,因為這里“有最多的高級知識分子,也有最多的普通人”,他把“商業策劃與創作熱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寫之前,我否定了無數的題材: 《我的童年》——一個80后的歷史,不行,關注的人太少了。
[……]然后想寫我的奶奶,一個經歷過張作霖、偽滿洲國、國民黨、共產黨[……]寫一個農村老太太歷史,沒別的意思啊,就是覺得我在農民這個階層紅不太可能,應該是我紅了以后寫比較好。
我有3個關鍵詞: 黑道(題材足夠新穎)、風云(矛盾沖突激烈)、20年。矛盾沖突不缺、精彩程度不缺、社會意義不缺,這樣的書不紅,沒天理。
我這么處心積慮地以專業市場咨詢業人的眼光做文化產品,不成功沒道理。(張歡28—31)
孔二狗的個案頗具代表性,他以管理咨詢顧問出身,把網絡小說當成一個文化產品來運作,這與當下影視文化產品制作具有異曲同工之妙。SMG影視劇中心助理李捷文在《頭腦風暴》節目中談到韓國編劇十二法則,其中針對女性觀眾,又將她們細分為“看電影的女觀眾”和“看電視劇的女觀眾”,為她們提供不同的影視文化產品。⑧新媒體時代的文學寫作越來越向影視文化產品制作靠攏,作家也自覺地迎合受眾的審美需求。嚴肅期刊文學和網絡文學市場“冰火兩重天”,孔二狗解釋為:“因為我們踩著地的,接著地氣,比如我、當年明月,每天浸淫在網上,知道大家的關注點是什么,傳統的高高在上的作家,早就不愿意了解人民想要什么。”(張歡28—31)網絡作者選擇文學題材時考慮的因素是什么?艾瑞咨詢的數據也印證了: 星級越高的作者選擇題材時更關注讀者喜好(艾瑞咨詢8)。
進入IP階段后,網絡文學衍生的文化產業鏈決定了網絡文學的腳本性質,網絡作者不僅要考慮差異化的小說受眾,更要考慮“長尾”意義上的影視、游戲受眾。這意味著不僅在題材上,并且要在寫作手法、語言上對紙面文學傳統進行改裝。“許多小說在與游戲簽約后,內容有了新變化,角色更豐富、性格更鮮明、情節更復雜。這并非寫作者的意圖,而是適應游戲市場用戶喜好,方便改編的伏筆。”(許苗苗130—37)有了粉絲基礎,才能被改編成影視、游戲、動漫,讓更多人看見。而由于商業需要,能被改編成游戲、影視,決定了某些種類的類型小說能被拓展到整個文化產業鏈: 比如玄幻小說、科幻小說和游戲競技小說等。網絡作者在寫作中為了配合改編需要,也自覺地采用“翻譯畫面”的手法: 用更形象化的語言來寫作,文字更具有畫面感等等。這一切是為了拓展更多網絡文學受眾及其衍生文化產品粉絲受眾的需要。
總之,新媒體視域下文學生產的重心已經轉移: 由寫“我”到為“受眾”而寫。作家的“個體經驗”和私人冥想不再是文學的表達核心,個性化的表達受阻。要想在網絡文學市場生存下來,作家不能任性、率性到只寫自己。由于審美代溝和審美群落化差異,傳統作家在網絡碰壁,學院派在市場碰壁;同齡人更了解同齡人,50后至70后無法理解90后、00后的世界,不太容易提供滿足“網生代”的網絡文學產品。在令前輩瞠目結舌、眼花繚亂的各種“功法”、二次元、腐女充斥的世界中,90后、95后年輕作家快速崛起,逐漸成為網絡文學寫作主流,30歲以下作者占了七成(艾瑞咨詢36)。同一審美圈更理解同一審美圈,酷愛玄幻、軍事的理工男不理解女生為何向往《魔道祖師》《花千骨》里的愛情,網文作者寫作題材偏好性別分化更嚴重。不是圈內人沒法理解溝通,更無法提供滿足這個圈子需求的文學產品。文學場域從“計劃文學”到“商業文學”的時代真正到來。媚俗化也好,⑨“審美衰減”也好(何平1—3),作家個性和主體性的滑坡,⑩是一個事實,受眾崛起的時代已經到來。
二、 類型化套路、機器人寫作與反類型化
以受眾為中心寫作,意味著提供受眾喜聞樂見的通俗文學產品,而通俗化的往往是類型化和模式化的。從新媒體時代越過印刷媒體回溯到口頭文學時代,流傳于民間的童話故事和民間故事就是類型化、模式化文學的代表。研究民間故事的學者都熟悉故事學的經典概念工具: 芬蘭學者阿爾奈(A. Aarne)發現民間故事的敘述情節模式大致相同,按情節類型(type)對民間故事進行編排著有《故事類型索引》;美國學者斯蒂·湯普森(Stith Thompson)發現流傳于整個歐洲、亞洲、南美、澳洲等地的民間故事都有類似的情節敘事單元母題(motif),其《民間文學母題索引》(1932年)展示了世界各地故事成分的同一性或相似性;另一位知名學者普洛普(Vladimir Propp)則探索故事的敘事結構,發現這些故事都有大致的結構特點,其《民間故事形態學》被認為是20世紀具有獨創性的文學研究典范。我國民間文學研究者劉魁立對中國民間故事的生命樹研究,彌補了世界民間文學中缺少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的遺珠之憾。
中國文學傳統中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只是一個小小分支,在厚重綿長的古典“詩文”傳統中一直是被壓抑的。胡適曾著《白話文學史》,提倡重視鉤沉了近兩千年的白話文傳統;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分子也致力于搜集民間歌謠,以期用“活的文學”來對抗強大腐朽的“山林文學”“廟堂文學”。這一切和今天中國文學處境竟依稀類似,不同之處在于,五四精英知識分子是從上而下“教化大眾”,他們構建“新文學”傳統的資源多來自西方,而不是民間通俗文學傳統;今日新媒體時代的網絡文學卻是從下而上自發崛起的通俗“民間”文學,雖有附著于新媒體的新特點,但本質上,網絡文學仍然是以普通受眾為中心的通俗暢銷文學。
由網絡文學二十年發展史可見: 20世紀90年代興起于北美留學生群體的華語網絡文學和2003年前處于自由創作階段的網絡文學,都帶有“現代文學”傳統的精英氣質,少有類型化、模式化的痕跡;而當網絡商業文學機制形成(VIP付費閱讀)之后,網絡文學隨即急轉為暢銷文學,迅速分化出網絡類型小說,開啟了類型化和模式化套路。拉長歲月跨越媒介來看,網絡文學中的各種“梗”:“女主跳崖脫胎換骨”梗,“少年被退親受辱、勵志發憤圖強”梗,和民間文學中的敘事情節單元母題、類型頗為相似。網絡文學的當紅創作者“唐家三少”“天蠶土豆”“我吃西紅柿”的粉絲們都很清楚: 他們創作的小說看了一部就不用看其他了,因為都是一個“套路”。盡管如此,粉絲們仍然忍不住圍觀大神新作,架不住新成長起來的青年源源不斷加入網絡文學入口。“廢柴”少年一路升級打怪(煉器煉級)逆襲得道(得正果、得成功、贏得美人歸)的故事套路“深入人心”,跨越了時光和文化隔閡,只需看看《西游記》《魔戒》的流行就知道了。
通俗暢銷的文化產品之所以類型化和模式化,概因人類共同的“審美心理機制”使然。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假設: 自己認為美的,也希望別人能引起相似的普遍性的審美認同(共通感)(康德57—59)。在什么樣的文化產品能暢銷流行這點上,美國編劇深諳人的“審美心理機制”: 暢銷的都是模式化的。好萊塢影視大片自不必說,其電影小說敘事模式有固定的三幕結構:“第一幕介紹英雄所面臨的問題,以危機和主要沖突的預示來結束。第二幕包括主人公與他或她面對的問題進行的持續斗爭,結束于英雄接受更為嚴峻的考驗這一節點。第三幕所呈現的應是主人公對應問題的解決。”(趙勇95—106)中國大陸的中文系素稱“不培養作家”,美國大學卻有各種各樣的寫作課程和編劇課程,教授人們如何創作出暢銷小說。嚴歌苓曾在美國接受編劇課的訓練,據說她接受馮小剛邀請寫作《芳華》時表示: 不受電影劇本的規訓,要寫一部“抗拍性”的小說。結果學者發現她的小說和電影敘事三幕結構大體對應,是按照劇本化的影視思維模式和結構方式操作的,“雖然《芳華》用小說技法掩飾得非常成功,給人一種嚴肅文學的錯覺,但實際上卻是按照某種配方生產出來的‘電影小說’”(趙勇95—106)。某種“配方”當然是指類型化和模式化的寫作套路,參照“配方”能制作出暢銷流行的文化產品。日本動漫和韓國影視的文化產業體系成熟發達,他們也建立了一套類似的文化生產法則。網絡類型小說和民間文學、通俗文學一樣,都是類型化和模式化的文學品種,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網絡文學也因此喚起了人類普遍的“審美心理”,走紅于海外,與美國好萊塢大片、韓劇、日漫相媲美,成為新媒體時代全球粉絲文化的重要一極。
既然故事元素早已根植在人類普遍的審美心理結構中,民間故事中的母題有一百多個,“神奇故事”的敘事結構也有固定的套路和公式,那么,作家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口頭文學時代,民間文學沒有作者,作者是“廣大人民群眾”,“作者”和“作家”概念是印刷媒體時代伴隨版權保護應運而生的。進入新媒體時代,作家面臨的危機可能還不是“為受眾寫”導致自身獨創性被抑制、主體性被消解,而是類型化和模式化的文學產品對作家個體的倚賴越來越小,受眾只關心“梗”,不關心誰是最先發明了這個“梗”的人。很多時候說不清哪些是作家獨創的“私人梗”,哪些是網絡文學資源庫里共享的“公共梗”,網絡文學知識產權保護越來越困難。這也從側面說明: 新媒體時代,與民間文學具有類型化本質的網絡文學,正在慢慢遮蔽作者。
更嚴峻的挑戰還不止于此。網絡類型小說是眾多以同一題材為創作內容的同質化作品,“同一題材”和“同質化”內容,加上與嚴肅文學相區別的模式化特點,以及網絡文學資源數據庫和網文寫作軟件的便捷,決定了網絡類型小說更容易被抄襲改裝: 不僅能被人類同類“抄襲”取用,也能被人工智能作家(AI)輕而易舉地“抄襲”組裝。丁帆曾憂心青年作家“在體制與資本構成的文學秩序中如何生存和發展”(丁帆1—3),沒有料到的危機是: 當下作家還面臨著機器人寫作的挑戰。微軟詩人小冰已經出版了第一部人工智能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IBM詩人偶得能隨意組合各類五言、七言古體詩。模式化極強的網絡類型小說極易被人工智能改編。試想在類型小說題材庫中輸入:
男一: 花樣大叔。女一: 野蠻妹。配角: 任意。類型: 愛情/懸疑。場景: 海島/都市。主情調: 憂傷。宗教禁忌: 無。主情節: 愛犬/白血病/隕石撞地球。語調: 任意[……](韓少功,3—15)
一部網絡類型小說可以在幾分鐘內“定制”而成。智能寫作以編程的形式“用典”或“用梗”,將來的人工智能會制作出各種語言風格的瓊瑤體、淘寶體、魯迅體……智能寫作軟件的“數據庫式寫作”,使得文學“創作”這門需要作家匠人精雕細琢的“手工藝術”,直接跨入了信息產業時代(邵燕君等37—42),文學產業化制作大生產成為可能。
那么作家意味著什么?怎樣證明作家個體還“活”著?智能寫作軟件一出世便擁有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文學經典資源數據庫,最不擅長遣詞造句、最不會編故事的“小白”作者,也能憑借機器人創作出“像樣”的故事,作家個體比拼不過計算機算法。可能的出路,就是為文學經典資源數據庫貢獻“知識份額”: 新媒體時代的作家,一方面要遵循類型文學的“審美心理機制”,要懂“套路”;另一方面又要突破類型化的寫作,開創新的原創類型,在類型化寫作和反類型之間走鋼絲。但這一切需要時間、錘煉和積累,資本的力量推動文學向前,恐怕并沒有給作家留出太多積累時間。
三、 資本的力量: 批量文學生產和團隊寫作
網絡文學生產方式轉型不僅包括以“受眾”為中心的類型化寫作,還包括與新媒介革命匹配的一整套新的文學生產機制,將文學帶入工業化大生產的快車道。邵燕君研究了多年文學期刊后得出結論: 傳統文學生產機制是壞死的,當代文學應寄希望于網絡等新型機制(邵燕君12—22)。的確,網絡文學吸納了大量的文學青年,贏得了資本的青睞,一路開疆拓土,連體制內文學生產者、研究者和學院派研究者,也不得不提出“向市場學習”。那么由網絡文學市場來教作者寫作又當如何呢?
首先,無論是原創文學網站還是自媒體平臺,都有一整套市場化的作者培育機制,從某種意義上激發了民間原創文學力量的爆發。網絡文學三大巨頭閱文集團、阿里文學和百度縱橫文學,在網站主頁都打出了誘人的寫作獎勵計劃和優質培訓廣告。比如閱文集團針對作者所處的不同階段,提供定制化的扶持計劃,涵蓋了從“一星作家”到頂尖“白金作家”的培養體系,在籠絡“老作者”的同時,保證其文學生產有源源不斷的“新作者”注入。培養體系包括: 作者定制化方案,為作者和作者能提供的內容定位;幫助作者塑造品牌,并提供針對性的營銷支援,通過諸如電視節目、新聞發布會等方式提升曝光率;通過大數據分析發現潛力作者,為他們提供粉絲運作和用戶分析;通過系列線下作者培訓和研討會、線上編輯互動、專題寫作講座等活動培育作者。2017年,阿里文學在北京召開“文學即世界”首屆作者年會,承諾借助阿里集團淘寶閱讀、UC書城、阿里影業等多渠道分發優勢,使作者迅速積累粉絲和名氣,打造全鏈路衍生模式(艾瑞咨詢27—30)。
與嚴肅文學期刊和紙面商業文學出版相較,原創文學網站幾乎涵蓋了文學活動的各個環節。其機制囊括了文學生產、文學渠道、文學銷售、文學宣傳、文學閱讀、文學評論(主要是讀者粉絲的評論互動)、評價系統(大數據分析)和文學全產業鏈開發,使之兼具生產機構、發行渠道和版權經紀人等多種角色。
自媒體文學平臺同樣有一整套類似的文學生產機制。剔除新聞類、行業類自媒體,自媒體文學網羅了網絡類型小說(此類由原創文學網站承包)之外的文學品種,比如散文、隨筆、微小說、雜文等。無論是微信公眾號、頭條號、簡書、大魚號、企鵝號還是百家號,都有一套針對作者的培訓、獎懲計劃,以控制整個內容生產。
面對這樣龐大的由資本力量構筑的具有強勢話語權的文學體系,網文作者一旦進入,就如同鏈條上的一環,幾乎沒有太多自由操作的空間,文學活動的一切都在龐大體系下運行。
網文體系首先要求作者精準定位,這是精細化模式化大生產的第一步。入駐平臺首先要確立個人品牌標識: 原創文學網站要求選擇玄幻、科幻、都市還是言情類寫作,自媒體平臺要求選擇娛樂、情感還是讀書類別的個人號。自媒體平臺對寫作領域細分要求更為嚴格: 內容必須垂直,專注于某一個領域進行深耕細作。百家號將垂直細分度納入新手作者轉正的考核評分標準,頭條號、大魚號等也針對垂直細分程度決定是否將文章推薦給更多的讀者。也就是說,如果作品的類型細分辨識度不高,寫得再好,沒有推薦,就不會被更多讀者看到。這種機制滿足了“分眾”閱讀需求,也提高了作者在某一個專業領域的“知識積累”標準,畢竟著文者都是該領域的“高手”,也有被高手養刁了胃口或本身就是行家的讀者。這種寫作方式頗似大工業化生產中的專業分工,作者被分配到一個個指定的工位,進行流水線上某個動作的熟稔操作。
網文體系的精細化模式化生產還體現在寫作培訓理念上。在傳統文學觀念中,文學創作是很難教的。文學網站和自媒體的寫作培訓以及市場上各路內容生產“大神”所開設眼花繚亂的寫作課程,更偏重“術”的層面,即便有“道”,也是從心理學、營銷學、傳播學等角度闡發如何讓讀者更好地接受、如何吸粉等營銷之道。比如17K小說網曾舉辦“網文大學”,簡書有“簡書大學堂”,教新入門作者如何寫作: 從如何起標題,到某種類型的文章如何開頭、如何架構、如何結尾,起承轉合,要避免哪些雷坑,都有詳細的講解。寫作講師們總結出每一種類型怎么寫才受歡迎的固定套路,想靠業余寫作實現財務自由的作者們趨之若鶩。初嘗甜頭的作者們發現: 原來寫作并沒有那么神秘,不需要多少高深的知識和文學修養,寫作不過是模式化的套路。
原創文學網站和自媒體平臺還要求批量化、大規模、持續性的文學內容生產。一方面是因為資本的逐利屬性,比如某個文學網站設立的“全勤獎”: 一個月內每天5000字合格更新,月獎金500元,一個月內每天1萬字合格更新,月獎金1000元。獎勵金額和寫作字數相關,高強度的更新導致寫作成為一個“體力活”:“每天醒了就寫,寫累了就吃,吃完了再寫,寫不下去就想后面的情節。做夢都是故事。”另一方面還因為新媒體平臺機制下,粉絲的注意力是稀缺資源,一不留神就會被讀者取消“關注”打入冷宮,非如此不能在這個體系中生存。因為更新不及時被讀者怒罵調笑者不在少數,唐家三少曾在節目中透露自己連續九年未有一日停更,有一次高燒到40度,晚上10點以后堅持爬起來寫了8000多字才休息。
在這種機制下,作家們是文學藝術家還是文字匠人,或者說是“金錢的奴隸”?現有的網文平臺機制把作者當成奶牛,不停地催奶。作者的知識累積很快被“壓榨”殆盡。為了對抗這種機制,作者們抱團合作,以團隊生產來運作,建立維護一個具有人格化標識的作者品牌。這種“團隊寫作”手法在紙質商業出版領域早已見怪不怪: 書商操作一個系列小說,為方便打造作者品牌標識,將所有作者署為一個作者名,而這個名字有可能是虛擬的。
新媒體時代的團隊寫作顯然更受文學生產機制驅動。原創文學網站的類型小說動輒幾百萬字,按照起點中文網的簽約條件,作者前20萬字免費供讀者閱讀,更新了20萬字之后才獲得簽約資格。20萬字在紙媒出版中已經是一部長篇小說的規格,而在網文中才剛起了個頭。面對洋洋灑灑卷帙浩繁的類型小說體量,一個人的精力和知識累積已經不夠用,用團隊合作來抵御知識累積所需要的時間差異便成了公開的秘密(這也是智能寫作軟件流行的原因之一,團隊伙伴有可能是機器人)。許多知名大神背后,有可能是團隊創作,“三五個寫手輪番上陣,一部動輒百萬字的網絡長篇半年就完成”(許苗苗130—37)。自媒體平臺因為其媒介屬性更強,有時需追熱點、保持時效性,要持續穩定的內容生產必得采用團隊“作戰”方式,比如知名自媒體六神磊磊等公眾號的運作。我們似乎又回到了口頭文學時代,只知有《荷馬史詩》《詩經》,而不用理會其“真正”的作者是誰。不同之處在于,今天為了打造作者品牌IP,必須要有一個符號意義上的作者。
這種適應新媒體文學生產機制的新的文學生產方式,更像是文學工業化大生產。文學更像是產品,而不是作品;新媒體的商業機制下,作家成了制作者,寫作變得更像是制作,而不是創作。文學自古就帶有商業化的特質,商業化并不是網絡文學區別于古典文學傳統、現代文學傳統的根本特性。商業資本和新媒介疊加所帶來新的文學生產機制、新的文學生產方式,才真正重塑了當下的中國文學。
以原創文學網站和自媒體為平臺的網絡文學活動對應著信息文明時代,正在造就一次徹底的文學范式轉型,這次轉型可能比中國現代文學相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范式轉型更具有顛覆性。從寫“我”到為“分眾”而寫、類型化模式化寫作套路的適應與超越、大規模批量文學和團隊寫作,只是文學生產方式轉變過程中呈現出的幾個鮮明特點。從中可見: 1.“作家”真正面臨“死亡”的危險。羅蘭·巴特說作家“死”了,是從文本接受角度消解作者的“霸權”。在新媒體時代為受眾寫、類型化套路、團隊寫作中,作家個體的獨創性“死”掉了。特別是原創文學網站小說類型化、機器人寫作迎合的模式化需求,掩蓋了作家的“個性”,這是從文本生產的意義上來說作家“死”了,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個體“作家之死”。2.從創作到制作,文學成為文化產業鏈的源頭活水,成為游戲影視動漫的腳本,需要大規模的批量生產。文學終于也面臨本雅明所說“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的命運: 審美“靈韻”退化。3.文學產業化最大限度地釋放了文學的活力,激發了民間原創文學力量的興起,但文學也在產業化中消解著自身,或者說變成了另外一種形態。和“現代文學”傳統相比,網絡文學更接近民間文學或口頭文學的類型化、模式化套路,產業規模需要批量化、規模化的文學生產。但是網絡文學一直在變化,文學的“靈韻”如何在這種轉型中延續、保存,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文學史已經或將要跨入一個新紀元(王侃1—3)。
注釋[Notes]
① 參見王曉明:“六分天下: 今天的中國文學”,《文學評論》5(2011): 75—85。昔日王曉明將中國文學地圖分為: 嚴肅文學、反抗的文學、新資本主義文學、網絡文學、博客文學等。
② 參見李靈靈:“媒介變遷與作家群落分化: 以打工作家為例”,《文藝爭鳴》5(2016): 155—63。
③ 參見陶東風:“以記憶傳承超越審美代溝”,《人民日報》,2018年11月20日第24版。
④ 參見程千千、章曉莎:“‘榕樹下’與網絡文學20年: 網絡文學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上海市作家協會與上海網絡作家協會聯合舉辦的“當年榕樹下——網絡文學20周年回顧”主題討論會,邀請榕樹下首任藝術總監陳村參與。澎湃新聞2017-12-6.2020-3-3
⑤ 參見許苗苗:“游戲邏輯: 網絡文學的認同規則與抵抗策略”,《文學評論》1(2018): 37—45。
⑥ 參見單小曦:“‘作家中心’·‘讀者中心’·‘數字交互’——新媒介時代文學寫作方式的媒介文藝學分析”,《學習與探索》8(2018): 156—62。
⑦ 寫作內容要“垂直”指專門從事某一領域的專業內容撰寫。
⑧ 由第一財經傳媒開辦的全新演播室談話類節目《頭腦風暴》,《笙簫可以不再沉默》,2015年第314期。
⑨ 參見胡友峰:“消費社會與電子媒介時代文學的生長背景”,《小說評論》6(2014): 58—63。
⑩ 參見張文:“媒介與百年中國作家身份的建構”,《蘭州學刊》12(2016): 43—50。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丁帆:“青年作家的未來在哪里”,《文藝爭鳴》1(2017): 1—3。
[Ding, Fan. “Where is the Future of Young Writers.”ContentioninLiteratureandArt1(2017): 1—3.]
韓少功:“當機器人成立作家協會”,《讀書》6(2017): 3—15。
[Han, Shaogong. “When Robots Establish Writers’ Association.”Reading6(2017): 3—15.]
何平:“再論‘網絡文學就是網絡文學’”,《文藝爭鳴》10(2018): 1—3。
[He, Ping. “A Second Discussion on ‘Internet Literature is Internet Literature’.”ContentioninLiteratureandArt10(2018): 1—3.]
艾瑞咨詢網.“2018年中國網絡文學作者報告”.艾瑞咨詢研究院.2018-9-17.2020-3-3
[IResearch Website. “2018 Report on Chinese Writers of Internet Literature.” IResearch Institute. 2018-9-17.2020-3-3.
康德: 《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年。
[Kant, Immanuel.TheCritiqueofJudgement.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劉勰: 《文心雕龍譯注》,王運熙、周鋒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Liu, Xie.Translationof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withAnnotations. Ed. Wang Yunxi and Zhou Fe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4.]
邵燕君等:“直面媒介文明的沖突,理一理‘文學的根’”,《南方文壇》4(2017): 37—42。
[Shao, Yanjun, et al. “Confronting the Conflict of Media Civilization and Fixing ‘the Root of Literature’.”SouthernCulturalForum4(2017): 37—42.]
邵燕君:“傳統文學生產機制的危機和新型機制的生產”,《文藝爭鳴》12(2009): 12—22。
[- - -.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Mechanism of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Mechanism.”ContentioninLiteratureandArt12(2009): 12—22.]
王侃:“最后的作家,最后的文學”,《文藝爭鳴》10(2017): 1—3。
[Wang, Kan. “The Last Writer, and the Last Literature.”ContentioninLiteratureandArt10(2017): 1—3.]
許苗苗:“作者的變遷與新媒介時代的新文學訴求”,《文藝理論研究》2(2015): 130—37。
[Xu, Miaomiao. “Changing Authorship: The Evolution on Literary Practices and Theory.”TheoreticalStudiesinLiteratureandArt2(2015): 130—37.]
張歡:“孔二狗: 哥寫的不是黑社會,是時代”,《南方人物周刊》33(2009): 28—31。
[Zhang, Huan. “Kong Ergou: What I Write Is Not Gangdom, but the Time.”SouthernPeopleWeekly33(2009): 28—31.]
趙勇:“從小說到電影: 〈芳華〉是怎樣煉成的——兼論大眾文化生產的秘密”,《文藝研究》3(2019): 95—106。
[Zhao, Yong. “From Novel to Film: On the Production ofFanhua(Youth) and the Secret in the Production of Popular Culture.”Literature&ArtStudies3(2019): 95—106.]
周志雄編: 《大神的肖像: 網絡作家訪談錄》。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
[Zhou, Zhixiong, ed.ThePortraitsofCelebrities:InterviewswithInternetWriters. Jinan: Shandong People’s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