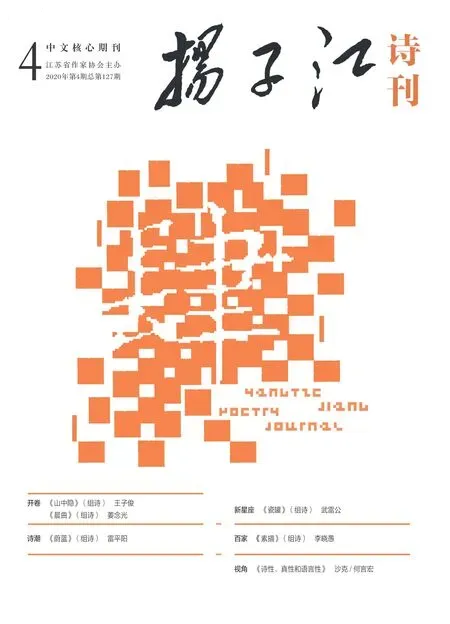便簽集(組詩)
蔡天新
芝加哥的云
白色大廳是酒店的名字
在東特拉華街一零五號
離開密歇根湖大約半英里
客房窗前有一對單人沙發
街對面是一幢高層車庫
不時有紅色的尾燈閃過
當初秋的陽光高高升起
照射到那堵白色的外墻
室內的光線驟然變得明亮
少頃,一團白云飄過天空
天色轉而幽暗,隨后它飄走
如此反復,始終未見到云
我們的人生也有許多時刻
快樂無比,或傷感莫名
出于某種難以言說的緣由
愛荷華河
昨夜一場特大的暴風雨
襲擊了愛荷華的東部地區
河水猛漲,流速遽然加快
可是仍不發出任何聲響
對岸有個少年騎著單車
吹著我年輕時吹過的口哨
追著漂流在河中央的樹枝
朝著密西西比河的方向
水面與橋梁愈來愈接近
只有單槳皮劃艇可以通過
遠處有我向往的小鎮舊宅
雖說主人早已經離開故鄉
流水逝去了我原地不動
而當我離開以后水流仍在
正如時光逝去了生命尚在
而當生命逝去時間仍未停滯
美國哥特
一個是畫家的妹妹
終身沒有結婚
一個是畫家的牙醫
執拗是職業的天性
兩人站在畫家屋前
并肩成為他的模特
質樸、謙遜、笨拙
手握一支三叉鐵耙
此畫被安放在田間
或機場的候機大廳
成為故鄉的風景線
也是風城的鎮館之寶
魚與貓
在女子詩社成員后頭朗誦
我應該向她們表示敬意
那就念一首關于魚的詩吧
魚與女子有著天然的聯系
聽眾大笑,像波浪傳到后排
而旅店的白色便箋上寫著
一行埃德加·愛倫·坡的詩句
——但愿我能寫出貓的神秘
大海與沙漠
維珍的飛機一路向東偏南
被午前和午后的日光推送
澳洲的城市大多坐落在海邊
猶如埃及人定居尼羅河畔
古老的和現代的港口
一樣的和不一樣的沙漠
藍天是它們共同的邊界
也是天空的胸膛和綬帶
紙與筆
白色的信箋,可以握在手心
一支小鉛筆斜放在上面
像一根細細長長的竹竿
可以撐動劍河上的平底船
銀色的削筆刀躲在角落里
悶聲不響,像一枚船尾舵
當筆尖上下或左右移動
它不動,靜觀萬物的變化
村莊與道路
一支白色的長長的線段
看起來可以穿過任何針孔
但它可能是一條高速公路
連接著你的故鄉和首都
村莊像大小不一的繩結
在古老而明亮的陽光底下
樹葉脫落融化在藍天里
像地上地下老人的牙齒
書籍與視頻
書籍像高低不一的房屋
靜臥在梯形的小桌板上
灰色的大地一片蒼茫
一場傾盆大雨從天而降
更多的人帶著耳機觀看視頻
讓人生又一出戲在方寸間展開
平日里他們是群眾演員
如今被天空賦予了閑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