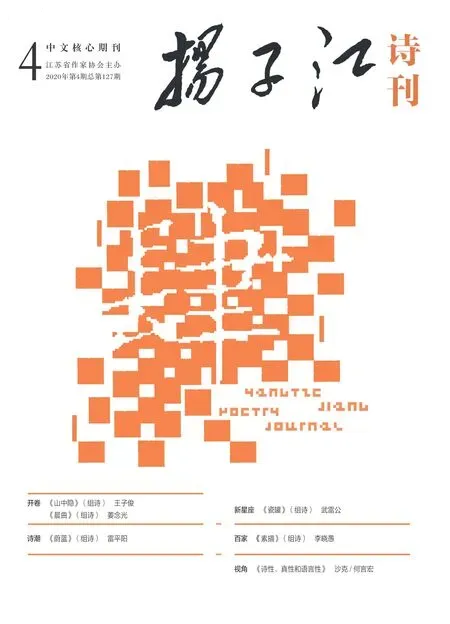瓷 罐(組詩)
武雷公
傍晚,以及鳥鳴
已經很久忘記自己是一個父親了
此刻,我坐著
目光在一團白云里睡著
而那顆心臟意外地帶領孩子們
去郊野,采集遍地
那傍晚的寧靜
也已忘記在那兒滯留多久
群鳥的鳴叫帶路,是夕陽的
余暉銜著的小哨子吹響
引領的,只是我一顆回家鼓蕩的心
孩子們,伏在桌子上寫作業
神色疲倦,而我
像一面密不透風的墻
面無表情地立在他們周邊
回到母親家里
手腕上測了體溫
走出小區
一個人穿過兩條小城街道
又測了四次體溫
終于拐進了母親的庭院
我摘下口罩面對著她坐下
我不想讓一層薄薄的口罩
把我們母子隔離
已經很久沒陪母親了
坐在小院的屋檐下抽煙
她遞來一杯我喜歡的普洱茶
坐那兒看著我,看著
她面容漸老的兒子,她就那么
一動不動地坐著,沉默寡言
庚子年二月初一的時光
就這么熱氣騰騰地在我們周邊流淌
但我分明在母親的臉上
瞥見了漾著世上最巨大的滿足
這是多么靜謐的時刻啊
陽光的花粉在這個小院
在一個母親和她滿面滄桑的兒子周邊
悄悄釀著一種蜜
瓷 罐
那么小小的一個瓷罐,送給誰
都會被當作無用之物拋棄
我卻對它不離不棄
母親從舊貨攤把它買回來,送給了我
讓它伴隨著我
母親知道我時常無端頭痛
用它在額頭上拔火罐,很適宜
于是去異鄉之地,我不忘
在隨身的包里,帶著它
有時一個人在雨夜
倍感風聲颯颯之時
我會拿出火罐,拔在額頭
在陌生的旅舍,不知不覺睡去
而體內多日勞塵的凄風
也會被小小的瓷罐
慢慢吞噬
次日睡醒,也會頓覺神清氣爽
身體變得輕盈,額頭
顛沛異鄉時,仿佛
也多了一個深色的唇印
晚 風
你陪著我,像一塊安靜的麥田。偶爾
像鳥雀撲棱掠過的你的語言
又像郊外的油菜花甜得淌蜜
而我坐在陽臺的椅子上,被風吹著
像剛停歇的火車。街燈亮了
如果你陪我再久一點兒
會聆聽到我胸中的山谷,有溪澗,淙潺不息
而我還會為此掛出眼中的燈籠
晚風,吹啊吹
你夢中的孩子都打開了窗戶
我還在那里……扶著欄桿
抽著煙像個老邁的漁夫等著夜闌中
駛來的船只
植樹者
注定一生忙碌不歇
這足以證明我還沒有
在這個世界撤離
每時每刻,光陰的血管流動
都在耗費著我的心力
當小鎮的燈火漸次熄滅
而我一個人會扛著鐵鍬遠行
假如我沒有向誰透露我的行蹤
誰也不會想到我在層層的云天
獨自栽樹。云朵的沃土
有極多暗藏的星子碰撞鐵鍬
并發出“哐啷——哐啷”刺耳的銳響
有時,會驚擾一個曾經
與我揮手別離的人
假如,午夜時下雨,閃電是我
用鐵鍬引來灌溉幼樹的溪流
看到的人,你不要驚慌
冬天的我是玻璃
在時間的灰燼里我透明得有些尖銳
雪花引來采蜜的冬天
飛行的骨骼有流水的衰老在嘩響
冬天的我是玻璃
你看過我就會看到雪地留下尖銳的劃痕
停在林地邊緣的雪橇
裝滿了像禮物一樣沉甸甸的過往
最好甭提命運把動機不良的日子
安插在我們越冬的路上
盡管這個世界仍嫌我不夠透明光滑
但我還是愿意把它叫作兄弟
月亮下的草原
如果月亮不是這春風中最涼的花瓣
那么,讓我
在草葉的音符上把它喊圓
我在大漠孤煙的嗓音里,遲到了多少年
……而在蒼鷹的天涯里
白羊白得茫茫無邊
作為一個慵懶的遲到者
至今我才被風的故鄉輕輕打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