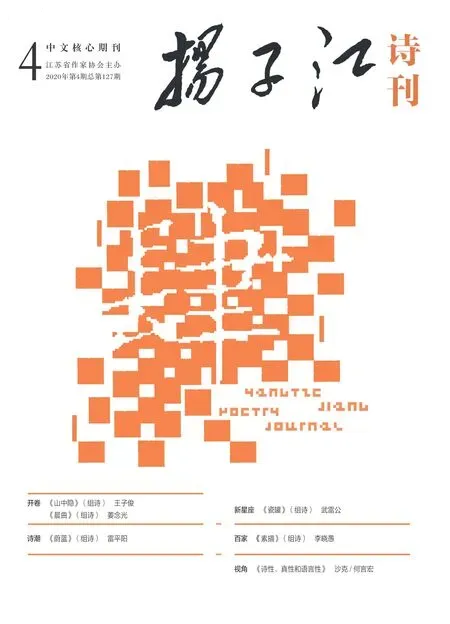旋轉木馬(組詩)
王徹之
卡呂冬狩獵
來自大都市的希臘神像們
缺少它的幽默。海閃爍釉光,
拉奧孔的蛇纜索般,垂入地平線
拖拽著這顆冰冷行星;
而半裸的維納斯,如水手觀測著風,
通過她在海浪陰影下
咸濕的目光想象群島有多遠,
如何與大陸保持間性聯系,
盡管斷斷續續,風格卻必須
連貫;像批評家們對我們的歡樂
呼出的泡沫偏愛泰然處之——
可無論是對你從它隕石般的臉上
瞥見的那無數因狂喜而戰栗的流星,
還是在公里的加速消亡中,
對它生活波浪上魚躍的呼喊
和馬刀般彎曲的臀線,以及原始風度來說,
美,和它的悲劇性,一旦被確認,
就必然認同我們既是觀眾,又是它的發生之地。
旋轉木馬
雖然圣誕集市結束得
比去年更早,但在集市盡頭
小蒙古包似的木馬棚下,
幾匹錯落有致的、上下移動
而彼此沉默無聲的馬,其感情
似乎全靠軸承相連。在夜晚
鼻翼吐著熱氣,在上釉的前腿筋腱,
光滑得讓人想到愛奧尼式立柱,
與佯作奔跑的后腿間,它們的鎖子甲披風
幾近潰爛,殘破如視力損壞的漁網。
從它們鱈魚似的小腹刺入
然后冷冰冰地,在既定的法則下
圍著星空旋轉的遙桿,看起來
就像騎手在風中解綁的心靈
由于戰爭來得太快,而來不及
與之達成共識的小天使手中搶來的。
而當木馬停止了,它們也不肯
在你輕易踏出圓圈半步前失去亮度,
反而在冷風中,讓四蹄的黝黑
消耗在激情遠超其忍耐的空氣里。
激情在這里是無意義的,像海灘的木馬。
當習慣這種驚奇,它的感情
仿佛木馬里的士兵泄出,
趁夜晚占據你的身體,然后四散奔逃,
以至于許多年后,你走下來,
竟然還可以感到,你的雙腿仍然
間或顛簸在它的感性不能持續的天真中。
馬戲團
這些天雨大得仿佛
能將日子的牢籠沖毀。
思念像馬戲團的野獸退場,
踮腳穿過它尖酸而不熟悉的客廳。
出于對暖氣的蒼白臉色以及
其合乎禮儀地放棄熱情的尊重,
冬天即將過去,但電燈泡的噴嚏
幾乎再次讓所有的事物變暗。
在比你更好理解的事實中,車站
像一片雪花一樣站立,在兩座小山間
把窗戶的標本,插在河流縱橫的
標記灰色心碎和托爾金的地圖冊上。
幸運的是,它準備好失去的
比已經失去的更多,如同水電費賬單。
和圓珠筆滔滔不絕的彈簧類似,
兩個月以來,作為自我的售票處,
這僅有的戲劇感并不來自時間
標點似的雨,后者以其擊傷大腦的散文
不斷敲打我的圍欄,而是完全
取決于時間中,雨對自身的厭倦
如何平復,又如何在你的心中化為烏有。
搬 家
再也不會睡在相同的地方,
擁有角度相同的風景,和鄰居,
連室內墻壁的白色也不會相同,
但這遠非旅行。即使去海邊,
或者城堡周圍,也用不著
憑意志拋下所有,從一座城市
和自己的咳嗽飛到另一座城市,
并試著接納新的交通規則,道路,
和以前幾乎被你視作野蠻的
凌駕另一種語言之上的語氣。
搬家用不著這樣枉費心力,
沒有什么東西跟蹤你,那些雜物
全都沒意愿進入你的生命,
盡管你曾經對它們消耗激情。
別去翻那本已然殘破,像老奧登
溝渠縱橫的臉的詩選,也不用
收起它旁邊,撂下農活的打印機,
鯨魚似的嘴張著,像波士頓
退休的觀鯨船拴在碼頭上
疲憊而無所事事。
每次我去海邊,
像跛腳的海鷗,水蚊子般大小,
趔趄在風暴中,我都感到某種
在體內鐵索般作響的
同樣的疲憊,也許帶著懷疑,
將自身置于風浪的中心,
如同碼頭清潔工,隨時準備
彎腰撇清大海的白色浮沫。
我知道,下次冒雨出門的時候
如果我什么都不會帶走,
這就相當于說,我沒有完成工作,
待在原地,等沒人注意我會搬去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