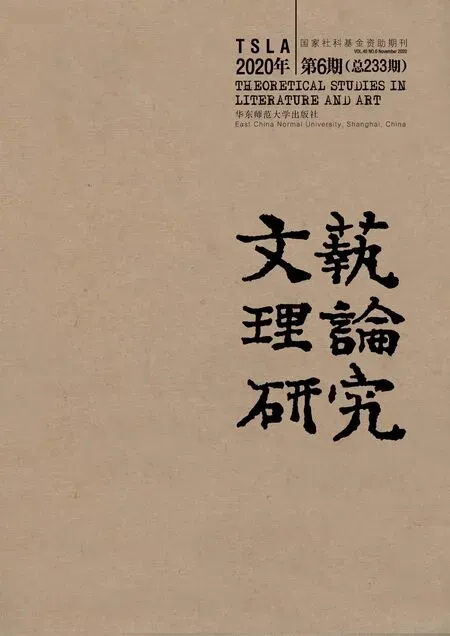經驗在信息時代的貧乏及其出路
——以本雅明思想為線索的一個考察
孫 斌 張艷芬
本雅明在20世紀30年代,或者說,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里,面對這個時代所興起的一種新的傳播形式即信息,流露出了對經驗的憂慮。①就經驗是一個到處得到使用并因此而為我們所熟知的概念而言,我們似乎很能明白本雅明的憂慮意味著什么。然而,事情毋寧是反過來,即,正是我們對這個概念的熟知使我們不能明白本雅明的憂慮,因為,就像黑格爾說的那樣,“一般說來,熟知的東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東西,正因為它是熟知的”(黑格爾 20)。至少就其作為一個哲學詞匯而言,經驗有著太多的不確定與不明晰之處,以至于奧克肖特慨嘆道:“在所有哲學詞匯當中,‘經驗’是最難以駕馭的一個詞語。每個魯莽的作者如果試圖使用這一詞語來避免它所含有的模糊之意,那么他的這種作法是一種野心。”(奧克肖特 9)詞匯是一個作者由以存在于世與返回自身的方式,因此,我們謹慎地把經驗這個詞的源始意義同本雅明及其時代的問題結合起來。我們這么做,不是因為我們知道這樣就能避免奧克肖特所說的魯莽與野心,而是因為我們不知道還有什么別的辦法可以分擔本雅明的憂慮——我們的時代依然彌漫著本雅明的憂慮,如果說這種憂慮沒有加重的話。
一、記憶被廢除了嗎?
經驗所指認的東西是極其廣泛的,認識、情感、欲求等諸如此類在康德看來屬于內心不同能力的東西現在恐怕都可以在一般的意義上被視為各種經驗模式。事實上,康德本人也正是從經驗開始他的批判哲學的研究的。我們知道,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導言”的開頭就是:“我們的一切知識都從經驗開始,這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因為,如果不是通過對象激動我們的感官,一則由它們自己引起表象,一則使我們的知性活動運作起來[……]那么知識能力又該由什么來喚起活動呢?所以按照時間,我們沒有任何知識是先行于經驗的,一切知識都是從經驗開始的。”(康德 1)盡管康德接下來指出經驗乃是復合物以便對其中的“我們固有的知識能力”(康德 1)方面作出闡述,但是他在這里把經驗的首要方面指認為感官的激動對于我們來說卻同樣重要,因為把經驗歸結到感覺正是我們可以追溯到的一個古老傳統。至少,亞里士多德就表示,“求知是人類的本性。我們樂于使用我們的感覺就是一個說明[……]動物在本性上賦有感覺的官能,有些動物從感覺產生記憶,有些則不能產生記憶[……]現在,人從記憶積累經驗;同一事物的屢次記憶最后產生這一經驗的潛能[……]經驗為個別知識,技術為普遍知識,而業務與生產都是有關個別事物的;因為醫師并不為‘人’治病,他只為‘加里亞’或‘蘇格拉底’或其他各有姓名的治病,而這些碰巧都是‘人’。倘有理論而無經驗,認識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涵個別事物,這樣的醫師常是治不好病的;因為他所要診治的恰真是些‘個別的人’”(亞里士多德 1—2)。也就是說,一方面,盡管經驗可以被歸結到感覺,但是必須以記憶為中介,另一方面,經驗所指向的東西是個別的,而不是普遍的。由以對經驗作出基本刻畫的這兩個方面也構成了我們接近本雅明的經驗概念的重要進路。
不過,這種接近只有在另一個問題得到處理之后才會成為可能,這個問題就是知識。我們發現,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經驗都是在知識的標題下來加以討論的。相應于這樣的討論,作為感覺與經驗之間中介的記憶就被要求精確地再現前者所指向的可感物的性質。那么,知識是討論記憶的唯一標題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首先要考察一下知識與記憶的關系,也就是說,知識是否需要或者說基于這種精確再現意義上的記憶。而考察的結果是,知識所需要或者說基于的乃是精確再現,而不是記憶,確切地說,不是與人的經驗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記憶。如果說精確再現與記憶的這種拆離在很長時間里似乎并不存在或者至少并不明顯的話,那么作為這個時代的新的傳播形式的信息改變了這一點。之所以這么說乃是因為,得到現代技術支持的信息,較之古老的記憶來說,能夠完美地執行精確再現的任務以至于毋庸置疑地取代了曾經擔負這項任務的記憶。事實上,我們看到,今天,就像龐德斯通說的那樣,“智能手機把互聯網的答案放到了你的手指下;在這種隨時都能便利地獲取答案的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人,似乎有必要重新評估一下記憶事實的重要性了”(龐德斯通 17)。如果考慮到,一方面,互聯網使得無論多么龐大的信息都能以數據的形式存儲在云端,另一方面,像智能手機這樣的移動終端可以隨時隨地便捷地獲取這些信息,那么,在這種重新評估中,記憶似乎就成為了一件完全沒有必要的事情。
而實驗也證明,這的確是一件沒有必要的事情。比如,我們看到,“2011年,哈佛大學的丹尼爾·韋格納(Daniel Wegner)發起了一項實驗,給志愿者看一份含有40樁瑣事的清單——就是一些短句,如‘鴕鳥的眼睛比腦子大’。按照指示,每人要把所有這40句話輸入計算機。一半的志愿者被要求記住這些事實,而另一半沒有被這樣要求。此外,有一半的人了解自己的工作將被存儲在計算機上,而另一半則被告知任務完成后輸入內容會被即刻清除。隨后,志愿者接受了跟所輸入事實相關的測驗。按指示被要求記住信息的人得分并不比另一半人更好,但那些認為自己的工作很快就會被清除的人得分就比另一半人高得多。因此,分數高低與是否試圖記住事實無關”(龐德斯通 20—21)。這個實驗表明,能否記住這些瑣事的決定性因素不是志愿者是否想要記住它們,而是他們是否知道它們得到外部存儲。一旦他們或者說他們的大腦得知要記住的這些事實可以在計算機上得到存儲,那么大腦會自動地把這項工作交給計算機;反過來,如果大腦知道,除非自己記住,否則所記的內容將會被清除,那么大腦就會積極地把這項工作承擔起來。所以,實驗的結論是:“能在網上找到的信息,大腦會自動遺忘。”(龐德斯通 21)簡單來說,精確再現是知識曾經需要記憶的理由,同時也是它現在不再需要記憶的理由。這意味著,如果記憶在知識的標題下來討論,那么記憶將會不可避免地被取消和廢除。
記憶的這種困境或者毋寧說絕境逼迫我們從前面所提及的那種拆離來作出考慮。杜威沒有看到,可能也沒有想到,記憶會在云端信息的時代陷入如此不堪的境遇,不過這并不妨礙他注意到這種拆離并進而指出一個事實,即,知識不僅不是討論記憶的唯一標題,而且甚至也不是主要標題。他一方面接過了從亞里士多德以來的那個傳統,即把經驗同記憶聯系在一起,他說:“人之所以不同于較低的動物,乃是因為他保存了他過去的經驗。過去發生的事情在記憶中又活了起來。”(Dewey 80)另一方面,他又明確摒棄了這個傳統將記憶置于知識的標題下來討論的做法,他說:“然而,記憶的復活很少是照實的。我們自然記得那使我們感興趣的東西,因為它使我們感興趣。過去之所以被回想起來,不是因為它本身,而是因為它加到現在上去的東西。因此,首要的記憶生活與其說是知識的和行動的,不如說是情感的。”(Dewey 80)唯其如此,記憶的生活或者說過去的經驗就不是精確的再現,而只是出于興趣和情感編織出來的故事和戲劇,即杜威說的:“既然人之所以復活他過去的經驗乃是因為興趣,即那種被加到現在否則就空虛的閑暇之上的興趣,那么原初的記憶生活乃是一種幻想和想象,而不是精確的回想。畢竟,它只算作是故事、戲劇。”(Dewey 81)這樣的故事和戲劇,就其是幻想和想象而言,顯然不像知識的標題下所討論的東西那樣現實,但它們卻是一個集體由以成為一個集體的情感紐帶和社會規范。杜威進一步說道:“[……]故事變成了社會的遺產和財產;啞劇發展為規定的儀式。[……]詩歌固定下來并系統化。故事變成社會規范。再扮演情感上重要經驗的原始戲劇被制度化為祭儀。”(Dewey 84)簡單來說,像故事這樣在記憶中得到保存的經驗,給出了一個集體得以被刻畫為這個集體的某樣東西,而這樣東西是知識所無法給出的——知識給出的是普遍的而非個別的東西。
這樣東西被本雅明考慮為傳統,他說:“記憶創造了傳統的鏈條,它使發生的事情代代相傳。[……]一個故事系著下一個故事,正如偉大的特別是東方的講故事的人向來表明的那樣。每一個故事中都有一個謝荷拉查德,每當她的敘述停下之際她就記起新鮮的故事。”(Benjamin 98)既然發生的事情是在記憶中代代相傳的,那么它們就只是故事,并且正因為是故事,它們得以在代代相傳中不斷生成新鮮的故事——或者毋寧說,不是“生成”,而是“記起”,因為這一切從頭到尾都是在記憶之中發生的。杜威意義上的回想所指向的東西是可能,甚至可以說是一定會被我遺忘的,因為那些東西就其僅僅聯系于公共的或者說外在的知識和行動而言,與我這個個人無關。記憶則不同,它是我由以成為這個個人的東西,因此,它無法被我遺忘,正如我無法不是作為這個個人的我。換句話說,我以知識和行動的方式所占有的東西都可能或者說一定會失去,但只要我還是我,那么有一樣東西是我至死都不會失去的,這就是記憶。唯其如此,本雅明借著援引帕斯卡給出了他的斷言:“‘沒有人,’帕斯卡說,‘死的時候是如此之貧窮以至于他身后什么也沒有留下。’記憶無疑也同樣如此——盡管它們并不總是能找到后嗣。”(Benjamin 98)之所以不貧窮,乃是因為,任何一個個人都是攜著記憶中滿滿的一生經驗死去的。而且,這樣的個人,亦即那在口口相傳的故事中度過一生的個人所擁有的經驗并不是孤獨的,而這完全是由于講故事的人的緣故——“因為他當然追溯整個的一生(附帶提及,這個一生不僅包含他自己的經驗,而且包含不少他人的經驗;講故事的人把他從傳聞中得知的東西歸為他自己的)。他的天賦便是敘述他的一生的能力;他的特性便是能夠說出他的全部的一生。講故事的人: 他是能夠讓他生命的燈芯被他故事的柔軟火焰完全燃盡的人”(Benjamin 108-109)。恐怕正是本雅明這里所說的講故事的人,使我們明白了前面援引的杜威的那個判斷,即“故事變成社會規范”。
故事之所以變成社會規范,不是因為它們成為了得到頒布的條文,而僅僅是因為有人還一直在講述它們;講故事的人的記憶中所保存的他自己的經驗其實就是那個集體的經驗,他以他的一生來做這件事情——這恐怕也是本雅明借著他描述的講故事的人的天賦所道明的東西。事實上,本雅明直接就說:“經驗確實是一樁傳統的事情,既在私人的生活中也在集體的生存中。”(Benjamin 157)而經驗之所以可以在講故事的人那里編織自身,并進而在故事的口口相傳中成為規范和傳統,乃是因為故事能夠以本雅明所說的“有所指教”的方式使人受益并得到規范。本雅明這樣寫道:“故事或公開或秘密地包含有用的東西。在某一情形中,這種有用性可能是道德上的;在另一情形中,是實用的建議;還有的情形中,則是諺語或格言。在每種情形中,講故事的人都是一個對于他的讀者來說有所指教的人。但是,如果今天‘有所指教’開始變得過時,那么這是因為經驗的可傳性正在降低。結果,我們對于自己和他人都無所指教。畢竟指教更多地不是對于問題的回答,而是關于一個正在展開的故事如何延續的建議。[……]講故事的藝術正在走向它的盡頭[……]。”(Benjamin 86-87)這是令人遺憾和極其悖謬的,亦即,就在我們借著本雅明的分析弄清楚杜威所考慮的故事如何變成社會規范的時候,卻發現這樣形成的社會規范在今天已經由于講故事的藝術的失去而變得無效了。事實上,我們很容易看到,龐德斯通所說的“能在網上找到的信息”正是包含各種各樣的指教,這些指教比本雅明所列舉的還要多、還要廣,它們形成了處理各種相應事務的規范。然而,不同的是,這些東西既不來自任何一個追溯其自身經驗的個人,也不去向任何一個發展其自身經驗的個人——人們無需也不必如此追溯和發展,因為那些東西沒有也不會進入記憶。作為結果,本雅明所說的問題在今天會得到無比迅速而有效的回答,但是恐怕不會再有任何故事可以得到展開乃至延續了。
換句話說,盡管,如前所述,精確再現與記憶可以拆離開來,并且這種拆離在杜威那里得到了辯護,但是現在,這種訴諸情感的記憶似乎隨著它所復活的經驗和編織的故事的走向盡頭而走向盡頭了。記憶的這次走向盡頭無論如何比它在知識的標題下所遭到的那次取消和廢除要更為嚴重,也更令人憂慮——這種憂慮對于本雅明來說同時就是對經驗的憂慮。
二、信息是如何運作的?
記憶的兩次致命危機特別是第二次所引發的經驗和傳統的困境,逼迫我們不得不對造成這些令人憂慮的情況的原因作出追問和思考。就其直接性和現實性而言,這個原因恐怕就是我們前面討論的信息。信息旨在揭示事情的本質,而講故事的人及其故事無疑會由于粘附于其中的個人經驗而遮蔽事情的本質,或者至少使事情無法得到透徹的說明。這就是本雅明所比較的:“講故事不像信息或者報道那樣旨在傳達事情的純粹本質。它使事情沉浸于講故事的人的生命中,以便為了把事情從他身上再次拿出來。因此,講故事的人的印跡粘附于故事上,其方式就如同陶工的手印粘附于陶土器皿上。”(Benjamin 91-92)既然如此,那么為了獲得事情的純粹本質和透徹說明,信息必須終結故事。事實上,本雅明正是在這個線索上對信息運作的實質作出了考察。盡管他當然不知道信息后來會隨著網絡技術而發展成比如龐德斯通所描述的那種狀態,但是他的這些考察卻使我們看到了這種狀態的真實根源。他這樣說道:“[……]我們承認,隨著以印刷出版為其在高度發達資本主義中最重要工具之一的中產階級的完全控制,一種傳播形式出現了[……]這種新的傳播形式就是信息。[……]然而,信息要求即時的可驗證性。首要條件是它顯得‘就其本身而言是可以理解的’。[……]聽似合理對于信息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由于這一點,信息證明與講故事的精神不相容。如果講故事的藝術變得稀有,那么信息的散播在這種情況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每天早晨我們都能看到全球的新聞,但卻缺乏值得注意的故事。這是因為沒有哪件事來到我們身邊不是已經得到了透徹的說明。換句話說,到現在,任何事情幾乎都不益于講故事;幾乎一切東西都有益于信息。”(Benjamin 88-89)在這里,使記憶和經驗遭受致命打擊的原因得到了揭示,這就是信息的即時可驗證性,或者簡單地說,即時性。事情的本質和透徹的說明現在都歸諸即時性之下,因而不僅沒有任何東西會被遮蔽,而且也沒有任何東西會被延遲。
本雅明在比較信息的即時與故事的延遲時這樣說道:“信息的價值無法活過它為新的那個瞬間。它只活在那個瞬間;它必須把自己徹底交付給那個瞬間,并且抓緊時間向那個瞬間說明自己。故事則不同。故事并不耗盡自身。故事保存和集中它的力量,并能夠甚至在很長時間之后釋放。”(Benjamin 90)如果結合前面所說的“全球的新聞”,那么可以說,在這里,信息之所以無須也無法延遲,乃是因為它在它存活于其中的那個瞬間完成了對全球的透徹說明,或者說反映。信息的這種運作,仿佛使人的中樞神經系統在瞬間延伸到全球,并就在這個瞬間獲得了對于全球的整體印象。在這一點上,熱衷于討論人的延伸的麥克盧漢為我們提供了更為生動的描述,他說:“電子時代一個主要的側面是,它確立的全球網絡頗具中樞神經系統的性質。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不僅是一種電子網絡,它還構成了一個統一的經驗場。正如生物學家所指出的,大腦是各種印象和經驗相互作用的地方,印象和經驗在此相互交換、相互轉換,使我們能作為整體對世界作出反映。”(麥克盧漢 428)盡管這里所說的和印象彼此交換及轉換的經驗與講故事的人的意義上的經驗并不相同,甚或正好相反,但是,顯然,這種經驗模式成為講故事的藝術走向盡頭之后的基本經驗模式——或者,毋寧反過來,正是對這種經驗模式的追求以及與之相應的技術發展把講故事的藝術帶到了盡頭。作為結果,這種訴諸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的經驗被等同于信息,相應地,經驗的獲得被等同于信息的貯存,確切地說,即時而整體的貯存,因為只有這樣,故事的延遲才能被完美地剔除——反諷的是,這種剔除恐怕也正是對本雅明所考慮的經驗的剔除。對此,麥克盧漢的表述是:“既然我們的新興電力技術并不是肢體的延伸,而是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所以我們把一切技術——包括語言——看成是加工經驗的手段,看成是貯存和加快信息運動的手段。”(麥克盧漢 423)在這個意義上,前面提及的本雅明的那個判斷“幾乎一切東西都有益于信息”可以被進一步解讀為“幾乎一切東西都有益于信息的貯存和加快”。接下來,如果考慮到麥克盧漢所說的“和經驗相互作用”的“印象”在哲學以及心理學上得到的界定和比較,那么可以說,這個進一步解讀甚至并不僅僅是技術層面上的。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信息的貯存及其運動的加快現在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即,曾經被作出并被堅持的那種關于印象和觀念的區分變得不再必要了——因為即時性使得一切東西都可以直接呈現于心靈。比如,我們知道,休謨非常明確地表示:“人類心靈中的一切知覺(perceptions)可以分為顯然不同的兩種,這兩種我將稱之為印象和觀念。兩者的差別在于: 當它們刺激心靈,進入我們的思想或意識中時,它們的強烈程度和生動程度各不相同。進入心靈時最強最猛的那些知覺,我們可以稱之為印象(impressions);在印象這個名詞中間,我包括了所有初次出現于靈魂中的我們的一切感覺、情感和情緒。至于觀念(idea)這個名詞,我用來指我們的感覺、情感和情緒在思維和推理中的微弱的意象[……]”(休謨 13)然而,隨著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我們對于一切的遭遇從未像現在這樣強烈和生動,以至于休謨這里所區分的作為“微弱的意象”的觀念幾乎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因為一切都已成為了印象。作為“最強最猛的那些知覺”的印象是當下直接的東西,它不需要以思維和推理為中介,并且特別不需要以記憶為中介——不管這個記憶是杜威區分的知識和行動意義上的還是情感意義上的。事實上,我們不難發現,龐德斯通說的“能在網上找到的信息”所給予我們的正是這樣的印象。而本雅明,盡管對網絡技術一無所知,卻早已在他所關注的印刷出版中發現了這一點,即,信息給予我們印象,而印象在它即時地、直接地、強烈地、透徹地向心靈呈現自身的同時,把經驗和傳統隔離出去了。本雅明這樣說道:“如果印刷出版的意圖乃是使讀者把它所提供的信息同化為他自己經驗的一部分,那么它是不會實現它的目的的。但它的意圖正好相反,并且已經得到了實現: 把所發生的事情同它能于其中對讀者經驗產生影響的領域隔離開來。新聞信息的原則(新聞的新鮮感、簡潔度、可理解性,以及尤其是,單個新聞條目之間沒有聯系)為此做出的貢獻同頁面排版以及文章風格所做的貢獻一樣大。[……]信息同經驗隔離開來的另一個原因是,前者進入不了‘傳統’。”(Benjamin 158-59)簡而言之,本雅明對印刷出版所作的這些分析透露了一個事實,即,信息的運作乃是以即時提供直接印象的方式隔離經驗和傳統。
到這里,可以說,無論從哪個層面上來講,本雅明所說的經驗似乎都被信息不可避免地終結了。然而,事情恰恰也正是在這里出現了轉機。休謨大概不會想到,印象有可能會如此之強烈和生動,以至于對它以最強最猛的方式進入其中的意識,形成挑戰和威脅。而本雅明正是在這一點上作出了考察。他說:“在弗洛伊德看來,意識[……]卻有另外一種重要的功能: 防止刺激。‘對于一個活的有機體來說,防止刺激是一個幾乎比接受刺激更為重要的功能;防護屏配有其自身的能量儲備并且必須首先努力保護能量轉換的特殊形式,這些在防護屏中起作用的形式抵御著外部世界中運作的過多能量的影響,這些影響傾向于潛能的均衡并因而傾向于破壞。’來自這些能量的威脅乃是震驚的一種。”(Benjamin 161)這意味著,信息給予我們的印象,就其如本雅明所描述的那樣是新鮮、簡潔、可理解的而言,乃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上的,即,意識憑借其防護機制而沒有遭到外部世界的過多能量的破壞,或者簡單來說,沒有遭到震驚的破壞——一旦遭到破壞,那么意識尺度上的新鮮、簡潔以及可理解性就蕩然無存了。然而,對于印象來說,這樣的前提恰恰是不存在的,亦即,這樣的防護恰恰是遭破壞的。對此,本雅明隨后對比性地援引瓦萊里的分析作出了闡述:“‘人的印象和感覺’,瓦萊里寫道,‘實際上應歸入驚奇的范疇;它們是人身上的一種不足的證明[……]回想乃是[……]一種基本的現象,它旨在給我們以時間來組織我們原先所缺乏的對于刺激的接受’。對于震驚的接納由于應付刺激的訓練而獲益,而且,如果需要的話,夢和回想也可以被征募。”(Benjamin 161-62)言下之意,印象突破了意識的尺度,并因此而必須歸于震驚。弗洛伊德與瓦萊里的這種關聯某種意義上源于本雅明自己在大城市的生活經驗,這就如同基洛赫所說的:“[……]本雅明畢生對大城市的強烈迷戀導致其大量著作是用于闡明現代都市生活的獨特經驗和集中趨勢:‘震驚’、加速度和過度刺激,碎片感、迷失方向……”(Gilloch 7)無論如何,如果印象是在震驚而不是在意識的標題下得到討論的話,那么那種與信息聯系在一起的事情的本質或透徹的說明就消失不見了,因為震驚意義上的印象恰恰不是即時的和直接的,而是必須,就像瓦萊里說的那樣,通過回想來組織對它的接受。就此而言,經歷了致命危機的記憶似乎獲得了某種得救的契機。
這個契機存在于與意識不同的另一個系統中。本雅明援引并分析道:“[……]‘意識和留下記憶印跡乃是同一個系統中彼此不相容的兩個過程。’毋寧說,記憶碎片‘在留下它們的事件永遠進入不了意識的時候常常是最有力和最持久的’。用普魯斯特的術語來說,這意味著,只有那些尚未被明確地和有意識地經驗到的東西,那些尚未作為經驗發生在主體身上的事情,才能成為非意愿記憶(mémoireinvolontaire)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據弗洛伊德,‘作為記憶基礎的永恒印跡’對刺激過程的貢獻,乃是為那必須被認作不同于意識的‘另外系統’所保留的。”(Benjamin 160-61)那些沒有進入意識或者說意識無法接受的東西,以記憶碎片的方式在有別于意識的另外系統中持久地活躍著,這個另外系統就是普魯斯特這里說的非意愿記憶。并且,正是這種使記憶碎片或者印跡持久活躍的非意愿記憶,為非即時的震驚印象提供了對之加以組織接受的時間,這個時間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經驗在主體身上生成的時間——因為經驗缺乏由以即時生成的即時印象。那么,非意愿記憶究竟是怎樣的,以至于可以擔當如此重任?本雅明寫道:“對于普魯斯特來說,柏格森理論的純粹記憶變成了非意愿記憶。普魯斯特使這種非意愿記憶直接面對一種意愿記憶,后者服務于理智。其巨著的頭幾頁就被用來澄清這種關系。在提出這個術語的反思中,普魯斯特告訴我們,多年來,他對畢竟在那兒度過一段童年時光的貢布雷鎮的回憶是多么貧乏。一天下午,(他后來常常提及的)一種叫作瑪德琳的蛋糕的味道把他帶回過去,然而,在那之前,他一直受限于一種服從注意力要求的記憶的提示。他把這叫作意愿記憶,而它的特點正是在于,它所給出的關于過去的信息并不保有過去的印跡。”(Benjamin 158)意愿記憶之所以服務于理智,乃是因為,它的功能僅僅在于為注意力指向某樣東西給出提示,而這種提示跟被指向的東西是否屬于過去并無關系。簡單地說,意愿記憶使過去的東西離開過去,從而作為一種不帶有過去印跡的東西置身于注意力的面前——此時這樣東西無非是關于過去的信息。作為結果,我們沒有也無法以這樣的記憶回到過去,而這樣的記憶也因此而對我們顯得貧乏。改變這種狀況的是非意愿記憶,它并不使我們的注意力獲得關于過去的信息,而是把我們帶回過去,就像關于瑪德琳蛋糕的記憶把普魯斯特帶回過去那樣。
也就是說,震驚印象因為有著過多的能量,所以打破了意識的防護機制,并進而打破了信息的即時運作。這樣一來,由即時信息和直接印象所形成的對于經驗和傳統的隔離就發生了松動,人們從而被非意愿記憶帶回過去。一個人的非意愿記憶就如杜威所說“保存了他過去的經驗”,而不是保存了他的注意力指向的提示。當然,在這一點上,本雅明給出了比杜威更多的考察與闡明。
三、經驗變得貧乏了嗎?
然而,這似乎并不能緩解本雅明對經驗的憂慮。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非意愿記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基洛赫在解讀本雅明對普魯斯特的評論時這樣說道:“非意愿記憶乃是一種將私密的、迷人的經驗概念化的企圖: 最為瑣碎和短暫的感覺的力量——普魯斯特的例子包括瑪德琳蛋糕浸在茶里的氣息與味道以及各種灌木和花朵的氣味——出乎意料和難以言明地喚醒對童年經驗的長期休眠的記憶。”(Gilloch 218)將私密而迷人的經驗概念化,或者說,將瑣碎而短暫的感覺把握住,這是一種本領。我們在瑪德琳蛋糕上看到了普魯斯特對這種本領的諳熟和運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毫不費勁地擁有這種本領。事實上,在本雅明看來,這種本領很大程度上歸屬于講故事的藝術,可是我們知道,本雅明認為“講故事的藝術正在走向它的盡頭”。他寫道:“信息對更為古老的敘事的取代[……]反映了經驗的日益萎縮……故事使自己嵌入講故事的人的生活中,以便把自己作為經驗傳給那些聽故事的人。故事因而承載著講故事的人的標記,就如同陶土器皿承載著陶工之手的標記。普魯斯特的八卷本著作表達了一個想法,即它要把講故事的人的形象努力地恢復給現在的一代人。普魯斯特以宏偉的一致性來承擔這項任務。這從一開始就使他潛心于以復活他自己的童年為首要工作。在說問題能否得到根本解決乃是運氣之事時,他充分展示了它的困難。他結合這些反思鑄造了非意愿記憶這個措辭。”(Benjamin 159)在這里,這個曾在《講故事的人》中出現的陶器之喻同普魯斯特的工作聯系在了一起。盡管普魯斯特在他的工作中提出了非意愿記憶,但是若要以這種本領來恢復講故事的人的形象,恐怕希望渺茫,因而只能像普魯斯特說的那樣交付給運氣。惟其如此,直到1939年,我們還是可以從以上這些出自《論波德萊爾的幾個主題》的文字中讀到本雅明至少從1933年的《經驗與貧乏》就開始表達出來的對經驗的憂慮。他在那里寫道:“誰都很清楚,什么叫經驗: 總是年長者把它們傳給年輕人。[……]而現在這些都哪兒去了?哪兒還有正經能講故事的人?[……]又有誰愿意試圖以他的經驗來和年輕人溝通?沒有了。很清楚,在經歷過1914—1918年的這一代人身上,經驗貶值了,這是世界史上一次最重大的經歷。”(本雅明 252—53)這段描述經驗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發生顯著貶值的文字,幾乎一字不差地再次出現在1936年的《講故事的人》中。
因此,必須考慮其他的可能,也就是說,考慮除非意愿記憶或者講故事藝術之外的其他可能。那么,這個考慮從何處入手?就前面關于信息和故事的討論而言,這個考慮可以繼續從震驚這一對信息的即時運作的破壞入手。只不過,現在,隨著講故事的藝術的衰落,事情不在于比如“抒情詩如何能夠把一種以震驚經驗為其標準的經驗當作它的基礎”(Benjamin 162),而在于一種新的震驚形式。本雅明以照相機和電影來考慮這種新的震驚形式,他說:“現在手指的輕按就足以把一個事件固定為無限的時段。可以說,照相機給出了死后震驚的瞬間[……]因此技術使人的感覺中樞服從于一種復雜的訓練。這一天到了,即,電影滿足了對于刺激的既新且急的需要。在電影中,以震驚為其形式的知覺被確立為一種正式原則。”(Benjamin 175)在這里,曾經同為信息的反面的非意愿記憶和震驚被剝離開來了,而這兩者之前在故事中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處于平衡狀態。本雅明也明確承認,像照相機和電影這樣新的震驚形式擴大了意愿記憶的范圍,“如果我們把靈韻指定為一種精于非意愿記憶并傾向于緊緊環繞知覺對象的聯想,那么它在實用對象情形中的類似物就是留下熟練雙手印跡的經驗。建基于照相機使用以及后來類似機械裝置使用之上的技術擴大了意愿記憶的范圍;借助這些裝置,它們使得這樣一件事情成為了可能,即一個事件隨時都能在視聽方面得到永久記錄”(Benjamin 186)。不難發現,由照相機等裝置所引發的意愿記憶的這種擴大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就是非意愿記憶的衰退,這種衰退同時也是靈韻的衰落。我們知道,就在本雅明寫作《講故事的人》的1936年,他還寫作了《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他在后者中專門討論了靈韻的衰落以及之后的情形。兩者形成了一種對照,即本雅明在為經驗憂慮的同時也在思考和尋求出路,而這種出路正是建立在他自己對靈韻的拆除之上的,換句話說,他無非是要以他對靈韻的衰落的分析來告別講故事的藝術以及非意愿記憶。所以,難怪伊格爾頓要說:“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講故事的人》中,本雅明卻大力贊揚了他用另一只手拆除的靈韻。故事或民間傳說就是這一靈韻的光源,因為它散發著睿智的回憶之光,閃耀著連綿不斷的傳統所積累的成熟‘經驗’之輝。”(伊格爾頓 78)如果說本雅明在1936年指出“講故事的藝術正在走向它的盡頭”,并在同一年開始探索靈韻衰落之后的狀況,那么1939年借著非意愿記憶對普魯斯特的任務——即努力恢復講故事的人的形象——所作的分析則告訴我們,講故事的藝術已經抵達了它的盡頭,并且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這些工作足以使本雅明擺脫普魯斯特對意愿記憶的抱怨或者說對靈韻衰落的不滿而繼續前行。“普魯斯特抱怨他的意愿記憶所呈現給他的威尼斯意象貧瘠而缺乏深度,他注意到‘威尼斯’這個詞使得豐富的意象對他來說像照片展覽那樣索然乏味。如果說從非意愿記憶所升起的意象的區別性特征是在意象的靈韻中被看到的,那么攝影術就定然密切關聯于‘靈韻衰落’的現象。”(Benjamin 187)不過,要擺脫普魯斯特的抱怨或不滿恐怕首先要弄清楚它們究竟意味著什么。對于這個問題,伊格爾頓的分析或許提供了線索,他說:“在感知過程中,只有那些不能被意識警覺記錄的刺激才會進入大腦的無意識層面,并留下記憶的印跡;而這些記憶印跡一旦被激活,則成為靈韻的根源。因而,充分清醒地‘親歷’某一事件,避開刺激的震撼,而非讓刺激滲入大腦深處,其實對‘靈韻’傷害極大,正如兇殘者之于浪蕩子,機械復制品之于‘真品’。”(伊格爾頓 45)在這里,伊格爾頓似乎并沒有比前面關于意識防護機制的討論說出更多的東西,亦即,非意愿記憶未被意識警覺記錄從而進入無意識的層面,這不同于避開震驚的意愿記憶在意識層面上的清醒親歷。然而,如果我們考慮到前面提及的兩點,即照相機和電影既屬于震驚形式又屬于意愿記憶,那么就必然得出結論說,照相機和電影盡管是意愿記憶,但是就其為震驚形式而言卻又和非意愿記憶一樣,如伊格爾頓所描述的,“讓刺激滲入大腦深處”。這樣一來,機械復制品就其作為復制作品缺乏真品“在它碰巧所在的那個地方的獨一無二的存在”(Benjamin 220)而言,的確異于真品并傷害了靈韻,但是,就其可以作為震驚作品“進入大腦的無意識層面”而言,卻又像真品那樣“留下記憶的印跡”從而“成為靈韻的根源”。因此,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的工作與其說是對靈韻衰落之后的狀況的考察,不如說他現在無需靈韻概念也可直接考察比如電影這門震驚藝術在無意識層面的運作了——盡管這門震驚藝術就是一門機械復制的藝術。
事實上,本雅明正是繼續援引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來對電影展開分析。他說:“電影豐富了我們的知覺領域,其方法可以用弗洛伊德的那些理論來闡明。50年前,一個口誤或多或少未加注意地被放過了。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這樣的口誤才會揭示一次表面上看似按照正常程序進行的對話的深度之維。自《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以來,事情發生了改變。這本書使得此前一直在知覺的寬闊河流中不被注意地漂浮的東西分離出來并成為可分析的。對于視覺以及現在還有聽覺的全部范圍來說,電影帶來了一種相似的統覺深化。”(Benjamin 235)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電影更多地乃是在無意識層面上改變和深化我們對事物的知覺方式,而不是僅僅為我們提供普魯斯特意義上的服務于理智的意愿記憶的材料。比如,就視覺方面而言,即便說電影是一種對于實在的再現,這種再現也是對實在的滲透與重組——在這個意義上,電影就像杜威所描述的記憶一樣,并不提供知識所要求的精確再現。對此,本雅明通過比較繪畫和電影對實在的再現作出了闡釋:“畫家在他的作品中與實在保持一段自然的距離,而攝影師則深深地滲透到了實在的織體之中。他們獲得的畫面極其不同。畫家的畫面是一個總體的畫面,而攝影師的畫面則由按照新的法則裝配起來的多重斷片所組成。因而,對當代人來說,電影對實在的再現有著畫家的再現所無法匹敵的重要性[……]”(Benjamin 233-34)。也就是說,如果說畫家讓我們看到了我們由于種種原因而沒有看清或看到的東西,那么攝影師讓我們看到了我們從未也無法看到的東西——當然,這一切都是就肉眼而言的。簡而言之,電影再現的實在并不是已然存在于某處的現成的東西,而是需要“按照新的法則裝配起來”的不現成的東西。那么,這個新的法則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它服務于無意識層面上的知覺,亦即,根據它所裝配起來的東西構成了一個為無意識所滲透的空間——一個永遠無法為有意識的探索所觸及的空間。本雅明這樣陳述道:“借助特寫鏡頭,空間擴大了;借助慢鏡頭,運動延長了。快照的放大照片并不是簡單地使盡管不清晰但無論如何看得見的東西變得更加確切: 它揭示了題材的完全新的結構形成。因此,慢鏡頭也不僅呈現了為人熟悉的運動性質,而且揭示了其中完全不為人所知的性質,‘它們遠不像受阻的快速運動,而是產生了異常滑行、漂浮、超自然移動的效果。’顯然,一種不同的自然對著攝影機而不是肉眼打開了自身——只是因為人有意識地探索的空間被無意識地滲透的空間所取代了[……]攝影機以其下降和上升、中斷和隔離、延伸和加速、放大和縮小的辦法來進行介入。攝影機把我們引入無意識的光學,就像精神分析把我們引入無意識的沖動。”(Benjamin 236-37)本雅明這里的陳述也許會遭到質疑,即,攝影機的這些操作方式及其拍攝手法都可以在技術上得到透徹的說明,因此根本不需要再借助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從無意識來解釋。本雅明當然明白這一點,不過他的重點并不是在這里,亦即,他的那些無意識層面上的分析并不是指向攝影機的操作方式及其拍攝手法,而是指向它們所提供的影像借助深化人的統覺而在人們心理上產生的效果——“異常滑行、漂浮、超自然移動的效果”就是這樣的心理效果。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對著攝影機而不是肉眼打開了自身”的東西,從根本上來說恐怕就不是造成某種視覺效果的景象——不管這樣的景象看似平常還是非同尋常——而是產生某種心理效果的“無意識的沖動”。我們無從知曉,對于本雅明來說,電影是否可以借此而成為這個時代復活或者說策動經驗的新的力量。在這一點上,對電影抱有可疑樂觀態度的本雅明并沒有直率地表達自己的態度。不過,斯蒂格勒的態度倒是直率的,在他看來,從心理效果上作用于人的情緒的電影使我們對生活重新有了期待。他這樣說道:“電影的職責針對的是我們的煩惱,它將我們的煩惱轉化為新的精力,轉移了該煩惱的實體。針對我們周日午后‘什么也不想做’的那種可怕的、近乎致命的情緒,它做了一些事。電影使我們重新擁有了對某些事物的期待,這些事物總會到來,將要到來,將要來到我們身邊,它們源自于現實生活: 也就是以非虛構性為特征的生活,是當我們走出電影放映廳的黑暗、陷入白晝的光明之后所處的那種生活。”(斯蒂格勒 11—12)可是,就在我們試圖以這個態度來為本雅明的憂慮考慮出路時,我們突然發現電影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死了,確切地說,在這個隨時可以在移動終端上看電影的時代,斯蒂格勒描述的那種我們由以在走出黑暗與陷入光明之際重新期待生活的電影已經死了。這是因為,我們現在總在黑暗之中,或者說,總在光明之中——按照黑格爾的想法,這兩者是一樣的,其結果都是,什么也看不見。②
到這里,亦即到電影這里,由本雅明的憂慮所引發的這個關于記憶、信息以及經驗的思考和追問不得不暫時中止了。這當然不是因為電影中止了本雅明所憂慮的經驗的貧乏,盡管電影無疑在很大程度上使這種貧乏變得更為復雜了;而僅僅是因為,本雅明所熟悉或者說所理解的電影已經死了。③不過,這個電影已死無非意味著,隨著無意識的光學而來的無意識的沖動已經滲透并作用于移動終端的每一個人的每時每刻。這迫使我們不得不就在中止的同時再次返回那些問題,亦即重新思考和追問記憶、信息以及經驗對于生活在移動終端的人來說意味著什么,或者毋寧說,對于作為移動終端而生活的人來說意味著什么。這些問題本文或許已略有觸及,但它們顯然更適合在另一篇文章中得到充分的展開。
注釋[Notes]
① 這種憂慮出現在《經驗與貧乏》(1933年)、《講故事的人》(1936年)、《論波德萊爾的幾個主題》(1939年)等文獻中。
② 黑格爾的原話是:“這個有視覺的人在純粹光明中與在絕對黑暗中,皆同樣什么也看不見[……]”(黑格爾 98)。
③ 對于電影之死的問題,學術界今天已經獲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思考,比如保羅·謝奇·烏塞: 《電影之死: 歷史、文化記憶與數碼黑暗時代》,李宏宇譯。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André Gaudreault, and Philippe Marion,TheEndofCinema?:AMediuminCrisisintheDigitalAge. Trans. Timothy Barn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等。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亞里士多德: 《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5年。
[Aristotle.Metaphysics. Trans. Wu Sho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本雅明: 《經驗與貧乏》,王炳鈞、楊勁譯。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
[Benjamin, Walter.ExperienceandPoverty. Trans. Wang Bingjun and Yang Jing.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
- -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Dewey, John.TheMiddleWorks1899-1924.Volume12: 1920.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伊格爾頓: 《沃爾特·本雅明: 或走向革命批評》,郭國良、陸漢臻譯。南京: 譯林出版社,2005年。
[Eagleton, Terry.WalterBenjamin:Or,TowardsaRevolutionaryCriticism. Trans. Guo Guoliang and Lu Hanzhen.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Gilloch, Graeme.WalterBenjamin:CriticalConstell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黑格爾: 《精神現象學》上卷,賀麟、王玖興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1981年。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ThePhenomenologyofMind. Vol.1. Trans. He Lin and Wang Ji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休謨: 《人性論》(上冊),關文運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6年。
[Hume, David.ATreatiseofHumanNature. Vol.1. Trans. Guan Wenyu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康德: 《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年。
[Kant, Immanuel.CritiqueofPureReason.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麥克盧漢: 《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0年。
[McLuhan, Marshall.UnderstandingMedia:TheExtensionsofMan. Trans. He Daoku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奧克肖特: 《經驗及其模式》,吳玉軍譯。北京: 文津出版社,2004年。
[Oakeshott, Michael.ExperienceandItsModes. Trans. Wu Yujun. Beijing: Wenjin Press, 2004.]
龐德斯通: 《知識大遷移: 移動時代知識的真正價值》,閭佳譯。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Poundstone, William.HeadintheCloud:WhyKnowingThingsStillMattersWhenFactsAreSoEasytoLookUp. Trans. Lü Jia.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斯蒂格勒: 《技術與時間: 3.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方爾平譯。南京: 譯林出版社,2012年。
[Stiegler, Bernard.TechnicsandTime:CinematicTimeandtheQuestionofMalaise. Vol.3. Trans. Fang Erp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