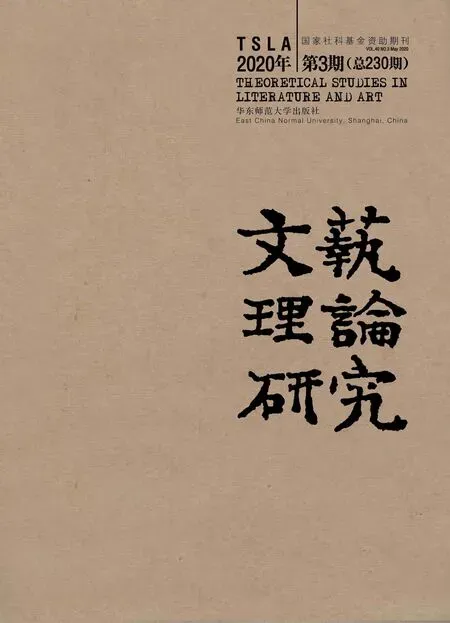論六朝文論中的“文匠”說
楊冬曉
六朝文論典籍中開始廣泛出現將作家比喻為“匠”的現象。具體分為兩種: 一是直接以“匠”稱呼作家,如《文賦》中的“意司契而為匠”(陸機2)、《文心雕龍·神思》中的“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范文瀾493)、①《顏氏家訓·文章》中的“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顏之推109)等;二是用某位工匠的名字,如“匠石”“輪扁”“班倕”等來類比作家,如《文心雕龍·事類》中“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范文瀾617)、《南齊書·文學傳論》中“輪扁斫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蕭子顯264)以及《抱樸子·辭義》中“非班匠不能成機巧;非英才不能收膏腴”(楊明照393)等。這樣的運用十分廣泛,并在后世文論中產生深遠影響。這促使我們思考:“工匠”這種勞動者的身份與行為,是怎樣進入六朝文人的思考范圍的?又是怎樣反映出六朝文學觀的特點的呢?眾所周知的是: 六朝盛行的老莊思想多有對“工匠”(如“郢匠”“輪扁”等)文化意義的特殊理解。但筆者認為,僅以老莊哲學的形而上思辨去理解文學創作的具體行為,中間會有較大隔閡。因此本文意欲從“匠”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六朝文人非常熟悉的藝術技巧行為入手,分析六朝文論“文匠”說的具體含義與后世影響。
一、 “匠”的意義衍變: 社會身份、藝術范疇與文論概念
古代文化中的“匠”本是對普通勞動者的稱呼。《周禮·考工記》云:“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黃公渚注99)早期的“匠”指的是從事木器制造的工人。后來“匠”又演變為手工勞動者的統稱,《說文解字注》云:“匠,木工也。從匚從斤。以木工之稱引申為凡工之稱也。”(許慎635)而詳查先秦兩漢的文獻典籍,會發現有時“匠”還能邁出具體身份的稱謂,擁有更豐富的含義。比如《楚辭·天問》云“女媧有體,孰匠制之”(董楚平譯注78);《淮南子·要略》云“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劉安533)。這里的“匠”就擴展為對創造、制作行為的普遍稱呼。而同時,古人對“匠”所代表的制造行為還有一些具體特征的認定。
第一,“匠”與規則、法度緊密相連。《孟子·告子上》云:“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楊伯峻譯注273)《墨子·天志》亦云:“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圜之別矣。”(吳毓江321)作為生產活動的必要條件,工匠會使用名為“規”或“矩”的工具來劃定準繩、制型模范。所以“規矩”一詞逐漸成為準則、制度的代稱,與“匠”的制作行為密不可分。
第二,“匠”以精巧的技藝為優勢和特征。《呂氏春秋·似順》云:“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 匠不巧則宮室不善。”(594)作為制造者的匠人不僅要遵守規矩,更需技藝純熟、手段精巧,才能攻堅克難、完成人人稱贊的作品。《韓非子·定法》中就有“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483)的說法。精巧的手藝逐漸成為優秀工匠的標志。
由此可見,先秦兩漢典籍中的“匠”字基于對勞動者身份和制造行為的描述,又與“規則”“技藝”等概念緊密相連,是一個運用廣泛、內涵豐富的詞匯。但是“匠”畢竟是對普通勞動者的稱呼,而古代階級觀念里的確有對勞動階層的輕視與隔離。如《孟子·滕文公下》中說:“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歟?”(楊伯峻譯注146)先秦文獻中的“匠”的確較少和文化階層的活動發生關系。那么到了六朝時代,這個誕生于勞動實踐的詞匯,是如何逐步進入文論術語之中的呢?除老莊之學的影響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在六朝時期“匠”所代表的制造、規則和技藝等行為有了新的表現方式,即六朝士人十分熱衷的藝術創作行為。
《說文解字注》釋“藝”云:“周時六兿。字蓋做埶,儒者之于禮樂射御書數,猶農者之樹埶也。”(許慎113)在古人認識中,“藝”一方面是士大夫的必備技能與身份象征,另一方面卻又源于生產勞動,是制造行為的“雅化”形式。到了六朝時期,“藝”對于士階層的意義又有了新的提升。潘天壽曾說:“(漢魏六朝)人民即苦于死亡離亂之頻仍,當局者亦疲于驅夷御敵之無策,致相率逃于清靜無為,形成厭世之風尚,聰明才智之士,因多攻藝事以為消遣。”(潘天壽28)六朝士人為了應對政局動蕩、儒道淪喪的社會困境,除潛心玄佛思想外,很多人兼善甚至專攻某項技藝,以之為價值依托和心靈慰藉。像音樂、繪畫和書法,毋庸置疑是六朝士人最喜好的藝術類型。文人名士中阮籍善嘯,嵇康擅琴,顧愷之以畫聞名,王羲之書法冠絕一時。我們可以推測,這些兼善藝術與詩文的名士,會不會在工匠技藝——藝術審美——文學創作間構筑一條橋梁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很多藝術類型在先秦時代屬于技術工匠的職業,因此六朝士人的藝術實踐不僅是一種審美探索,更包括對前人技藝經驗的學習。如潘天壽所說,六朝時代一些原本“多屬被豢養之工匠”(潘天壽29)的藝術類型,如繪畫、音樂和書法等,開始“蹈入自由制作之境地”(29)。在不少名士眼中,藝術創造一方面是高尚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又落實為精巧的技藝制作。比如書法家王羲之就以腳踏實地的態度說道:“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學無及之。”(王羲之41)《顏氏家訓》則云“畫繪之工,亦為妙也,自古名士,多或能之。”(顏之推209)視藝術為一種神功妙技并認真學習,這是六朝名士提高修養、充實生活的風雅方式。所以史料中有王獻之為練字染盡十八缸水、顧愷之討論繪畫“竟夕忘疲”(張彥遠181)的故事。不論這些名士是否將藝術創作與工匠的勞動等同,其中鉆研規范、勤學技藝的思想都是一致的,這就構成了“工匠”技藝精神與文化階層溝通的渠道。
另一方面,六朝流行的華麗文風推崇文學創作的技巧性,并力圖讓文學呈現出藝術品一般的審美效果,這就強化了藝術技巧與文學創作的關聯。六朝時期力求“形似”的山水、詠物詩大量出現,而文字對仗、韻律和諧的駢體更是文學形式的主流。《文心雕龍·物色》曾說:“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范文瀾694)《麗辭》也說:“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韻俱發。”(588)這些將文學寫作類比為音樂、繪畫或雕刻的做法說明: 當六朝士人將藝術視為一種高雅技能時,對文學也有類似的看法。陸機《文賦》就將文學創作的過程描述為“辭程才以效伎”(陸機2);《詩品》則云:“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鐘嶸66)將文學視為精妙的語言技巧,是六朝文論的一個典型特征。
可見,對“技藝”的強調和追求是六朝藝術觀與文學觀的連接點。而代表“規則”和“技巧”的“匠”在此時大量出現于文學理論中,則為我們借助藝術理論了解文學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在六朝藝術技巧論的參照下,我們不僅可以系統解讀“文匠”說的豐富含義,還能準確把握六朝文學技巧論的本質特征和深遠影響。接下來讓我們逐層解讀六朝“文匠”說的含義。
二、 “文匠”說的基本含義: 規矩文法與精研辭采
六朝以“匠”論文的現象逐漸增多,但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中仍是零珠碎玉式的存在,其理論關聯并不明顯。不過從文獻梳理來看,“匠”自從出現在文論中,就往往與文學和其他藝術技巧的比較有關。東漢《論衡》就說:“能剒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坎,謂之土匠;能雕琢文書,謂之史匠。”(王充76)到了六朝時代,這種類比依然常見。《文心雕龍·原道》說“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范文瀾1),將華麗文辭的作者隱喻為繪畫或織錦的工匠;而《書記》則云“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范文瀾458),直接將某一文體的寫作比喻為工藝品的制作。在這種認識背景下,通過與六朝藝術技巧論的對比,我們就可以對六朝“文匠”說進行系統整理與特征歸納:
一、 “镕范之匠”。《文心雕龍·定勢》云:“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镕范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逾越。”(范文瀾530)劉勰認為文學創作要像鑄模陶范一樣,在規則指導下調配篇章、運用字句。這里的“司匠”一詞,與“難得逾越”的寫作規范有著明顯的意義呼應。同樣,前文中顏之推“世俗準的,以為師匠”一語,稱幾位“師匠”級作家是文學創作的“標準”,似乎也在強調“文匠”與“規矩”的關系。而若對比六朝藝術創作的技巧理論,會發現此時對“規矩”的要求的確無處不在。
六朝時代迎來了“中國藝術徹底的覺醒”(陳傳席7),其表現形式千姿百態。比如書法領域一方面有“飄若游云,矯若驚龍”的神妙墨寶,另一方面書論著作中卻隨處可見循規蹈矩、步步為營的學習策略:
夫書不貴平正安穩,先須用筆,有偃有仰,有攲有側,或小或大,或長或短。(王羲之41)
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衛恒29)
我們可以對比一段文學創作的論述: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文心雕龍·定勢》;范文瀾530)
不管是書法還是寫作,在學習之初按照“規矩”逐步訓練,都是進入化境的必備階段。而“規矩”作為藝術品基本形態與審美特征的準繩,又是必須遵守、不可逾越的。阮籍《樂論》中提及:
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鐘之氣,故必有常數[……]其物系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陳伯君校注86)
也許音樂本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但從創作角度來看,特定的樂感體驗一定要有固定的音律搭配,隨意改動就會破壞相應的美學效果。相應在文學中亦有嚴格的寫作規范:
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抑滯必揚,言曠無隘。(《文心雕龍·詮賦》;范文瀾136)
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文心雕龍·頌贊》;范文瀾158)
六朝文體劃分不只是形式之別,還有實用價值和審美風格的嚴格區分。為避免《文心雕龍·序志》所說“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范文瀾726)的后果,理論家須不斷完善文體規范的細節。《文心雕龍·書記》云:“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460)這種觀點和此時樂論、畫論一樣,都在強調創作過程中不可逾越的技術法則。在文成法立的六朝時代,文論中“匠”字的運用不僅呼應了工匠重視“規矩”的原始含義,亦與此時藝術領域中強調規范的風氣形成了共鳴。
二、 “斫刻之匠”。《文心雕龍·隱秀》篇云:“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工辭之人,必欲臻美[……]譬諸裁云制霞,不讓乎天工;斫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周振甫譯注554)文學不同于其他藝術之處是以語言為素材,但拋開素材之別,兩者又都需要精雕細琢的技藝才能塑造完美的形象。《文心雕龍·事類》曾云:“夫山木為良匠所度,經書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筆。”(范文瀾617)文之“良匠”善于“工辭”,正如六朝藝術家往往是精通技術的巧匠。
以繪畫為例,不少人認為六朝繪畫以“傳神”“氣韻”為重,但陳師曾卻說:“六朝繪畫雖其畫風巧致,尚存漢時古拙之余。至于寫生之技能,則遠勝于前代。”(陳師曾9)內在神韻固然重要,但繪畫的基本表現依然是形象描摹。《山水松石格》中說:
素屏連隅,山脈濺渹。首尾相映,項腹相迎。丈尺分寸,約有常程。樹石云水,俱無正形。樹有大小,叢貫孤平;[……]或難合于破墨,體向異于丹青。隱隱半壁,高潛入冥。插空類劍,陷地如坑。(蕭繹21)
六朝山水畫往往要展現自然景物中的玄妙之道。但具體創作過程中卻需窮盡各種技術手段使景物形象歷歷在目,這正和此時詩歌領域“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鐘嶸36)的風氣隱隱呼應。且看《文心雕龍·物色》關于山水詩的寫作方法:
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 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范文瀾693—94)
不論是文學還是其他藝術,高深的審美體驗都必然依托于精細的審美形象,而形象塑造又離不開技巧運用。六朝藝術家苦練技術的例子不勝枚舉: 書法家鐘繇曾說:“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鐘繇12)畫家張僧繇則是“手不釋筆,俾畫作夜,未嘗倦怠。數紀之內,無須臾之閑”(張彥遠239)。相應在文學領域里,劉勰也以“嘔心吐膽,不足語窮;鍛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于庸目;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周振甫譯注554)的目標鼓勵作家鉆研文術。在不斷精進的過程中體會創作的意義與技藝的精髓,這種境界是六朝藝術與文學創作的共同追求。
綜上,我們梳理了“文匠”說的兩條基本內涵: 規矩文法與精研辭采。這正與先秦兩漢文化中“匠”強調“規則”“技巧”的內涵彼此呼應。但相比于前代,六朝美學與文學都經歷了質的飛躍。倘若局限于先秦文獻中“匠”的基本義,僅將“文匠”的工作與言辭組合相連,那就不僅忽視了六朝文學理念的進步,也錯失了六朝藝術美學的精髓。接下來讓我們繼續挖掘“文匠”說的深層意蘊。
三、 “文匠”說的深層意蘊: 獨抒性靈與變通適會
六朝“文匠”說強調了文法規則和辭采技巧的重要性。但全面研讀六朝文論中“匠”的用法,會發現它的含義遠不止于此。《文心雕龍·事類》云:“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范文瀾617)《神思》則云:“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493)這似乎證明真正獨具慧眼的“工匠”不只有手頭的技術操作,還會深入“意”和“思”的層面。另一方面,若說“文匠”需嚴守規矩,那么陸機《文賦》云:“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陸機2),似乎又表明以“意”為尚的“文匠”根本不受規范的束縛。如此看來,六朝“文匠”說還另有深意。且讓我們繼續分析:
一、 “性靈镕匠”。《文心雕龍·宗經》贊文云:“性靈镕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群言之祖。”(范文瀾23)正文又說:“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21)這似乎說明要洞達文章寫作的真諦,“文匠”就必須參透“性靈”的奧秘。而對比六朝藝術理論,會發現對“匠”的這種要求完全在情理之中。
六朝流行的“神韻”說源自繪畫,卻深刻影響了各個藝術門類。具體到創作領域,其核心觀念則認為: 外在藝術手段需與內在情感相連,才能創造出超凡脫俗的藝術珍品。比如王羲之有“意在筆先”之說:
意在筆前,字居心后,[……]何也?筆是將軍,故須遲重。心欲急不宜遲,何也?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王羲之41)
不管掌握多么熟練的技術,高明的書法家都明白: 創作之初如箭鋒般脫穎而出的是敏銳的審美感悟,要以“心意”指揮筆劃運作,才能創造出絕佳作品。我們可以對比一段文學創作觀:
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結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文心雕龍·情采》;范文瀾538—39)
寫作絕非單純的文辭拼湊。以內心情感指導篇章雕琢,這才是“為情造文”的作家進行創作的基本動力。而從鑒賞角度講,只有飽含情感的技巧才能塑造動人的形象。嵇康樂論中說:
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蕩心志,而發泄幽情矣。(《琴賦》;嵇康105—06)
正如畫家顧愷之所說:“神儀在心,而手稱其目者,玄賞則不待喻。”(顧愷之,“畫評”5)高明的藝術技巧一定是心手結合的產物,以精美的形式傳遞豐富的情感,才能讓藝術品在觀者眼中散發無窮魅力。相似的鑒賞論也出現在文學中:
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文心雕龍·總術》;范文瀾656)
高明的“文匠”與藝術家一樣,能夠將“性靈”與“技藝”融為一體,使文辭技巧成為情感蘊藉與審美體驗的載體。這既是對六朝藝術技巧論的借鑒,也是六朝文學創作論與鑒賞論的突破。
二、 “隨變適會”之匠。《文心雕龍·章句》云:“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范文瀾570)這不僅指出文學之“匠”擅于雕琢辭章,似乎還說明這種技藝是變通無礙、隨心所欲的。類似語句也出現在《神思》中:
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后闡其妙,至變而后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范文瀾495)
“伊尹”和“輪扁”均是古代巧匠。而他們的技藝如《莊子·天道》所言:“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陳鼓應注譯358)都說工匠必依“規矩”行事,但此處例證似乎說明只有躍出規矩之外,在變通中頓悟自由創作的精髓,才是“文匠”臻于化境的標志。事實上,“變通”觀念不只出現在六朝文學領域,亦是此時藝術創作中的典型思路。顧愷之曾說:
用筆或好婉,則于折楞不雋。或多曲取,則于婉者增折。不兼之累,難以言悉,輪扁而已矣。(顧愷之,“魏晉勝流畫贊”6)
為了表現千姿百態的審美形象,藝術家的表現手法需隨時調整,所以顧愷之有“臨見妙裁,是達畫之變也”(顧愷之,“畫評”5)的總結。而這與陸機的文學觀頗為相似: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陸機3)
面對“為物多姿,為體屢遷”的表現對象,以“窮形盡相”為目標的作家就要像“輪扁”一般參透相時而動的道理。然而除審美對象的多姿多彩外,六朝藝術對于規則的“變通”還另有深意。成公綏的書論提到:
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成公綏15—16)
固定的“規矩”與常態的“適變”成為創作的必然現象,其核心原因是“應心隱手,必由意曉”這個原則的存在。內在意蘊的豐富多變才是藝術家自由發揮的原始動力。我們可以對比文論中的觀點:
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范,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蕭子顯264)
高水平的“文匠”以情感表現作為技藝的終極旨歸,而自由豐沛的情感抒發不會被條條框框的規則所束縛的。因此《文心雕龍·定勢》云“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范文瀾529);《隱秀》云“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周振甫譯注632)。正如《莊子·天道》對“輪扁”技藝精神的解讀:“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陳鼓應注譯358)“文匠”與其他藝術巧匠一樣,手中的技藝不是刻板的操作條例,而是自由抒情的媒介、玄妙之理的載體。既要遵守文體寫作規范,又能以深刻的審美感悟指導文辭技藝的自由發揮,這就是六朝文論家對于“文匠”的高標準要求。
綜上,我們梳理出六朝“文匠”說的深層意蘊: 文學之“匠”不僅掌握寫作技藝,還要在精美的言辭組合中融入豐富的生命感悟,在成熟的文體規范中體現變通無礙的自由發揮。六朝“文匠”說繼承了先秦兩漢“工匠”文化對于規范與技巧的重視,又深受六朝“緣情”“神韻”“新變”等審美觀念的影響,是一個層次豐富、意蘊深厚的概念。“文匠”說在六朝之后依然有巨大的生命力,那么六朝“文匠”說在后代文論中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四、 六朝“文匠”說的歷史發展: 褒貶互現與技道合一
六朝之后的古代文論中,以“匠”論文仍是常見現象。比如明代呂天成評湯顯祖、沈璟說:“此二公者,懶作一代之詩豪,竟成千秋之詞匠,蓋震澤所涵秀而彭蠡所毓精者也。”(呂天成37)而胡應麟則評七律詩的做法:“一篇之中,必數者兼備,乃稱全美。故名流哲匠,自古難之。”(胡應麟79)在這些例證中,我們感覺“工匠”之稱基本是對作家的褒揚。但事實上古代藝術和文學理論中的“匠”不一定都是贊美之稱。清代孫衍栻在《石村畫訣》中說:“畫中人物、房廊、舟楫類,易流匠氣。獨出己意寫之,匠氣自除。有傳授必俗,無傳授乃為雅。”(孫衍栻977)把描摹物象的畫稱為“匠氣”,與缺乏“意”、偏于“俗”聯系起來,明顯帶有貶義。明代王夫之則評六朝詩歌說:
詠物詩齊梁多有之,其標格高下,猶畫之有匠作,有士氣。征故實,寫色澤,廣比譬,雖極鏤繪之工,皆匠氣也。(王夫之152)
齊梁詠物詩善于描述物象細節。但王夫之卻鄙薄其像“匠氣”畫一樣格調低下。古代藝術和文學領域的“匠氣”“匠作”等語,確有可能是貶義詞。陳傳席曾解釋繪畫領域對“匠體”的輕慢:
文人士大夫是不愿和工匠平列的。他們既要掌握這門由工匠發展起來的技術,又要和工匠相區別,“跨邁流俗”“橫逸”“逸才”“高逸”都是和“輿邑”(俗工)相對立的[……]唐之后士大夫作畫,言必稱士體了。(陳傳席115—16)
階級偏見認為工匠出身勞動階層,只知手工操作,不懂得文化階層所欣賞的高逸之情、玄妙之理。在這種誤解下,一些人認為藝術領域細致的形象刻畫、文學領域精美的辭采編排,都是“匠”知“技”不知“道”的體現,并冠以“俗氣”“淺薄”的帽子。但如前分析,在六朝相對自由開放的環境里,一些士人淡化階級偏見,將深邃的文化內涵與精細的藝術技巧合二為一,開拓了“匠”的語義內涵。那么它是否會影響到后世“文匠”說的用法及詞義色彩呢?答案是肯定的。
六朝之后的“文匠”說,其基本義仍是寫作規范與言辭技巧的指稱。清代劉大櫆說:
譬如大匠操斤,無土木材料,縱有成風盡堊手段,何處設施?然即土木材料,而不善設施者甚多,終不可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劉大櫆434)
作為“大匠”的文人一方面需要知識和經驗作為“材料”,另一方面則需掌握“成風盡堊”的妙技。這強調了文辭技藝對于寫作的重要性。但若拘泥于“規范”與“技巧”,就會成為文學發展的桎梏。明代李東陽說:
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規矩之謂,而其為調,則有巧存焉。茍非心領神會,自有所得,雖日提耳而教之,無益也。(李東陽29)
若只懂亦步亦趨而不知領悟真諦,只懂賣弄文辭而不知心領神會,阻礙了情感的自由抒發和文體的與時俱進,這樣的“匠”就不一定是正面形象。那么古代文論中出于褒義的“匠”又有哪些共同特點呢?
首先,必須是能將情感與技巧融會貫通的上乘之“匠”。金代趙秉文說:“上匠不師繩墨,獨自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趙秉文433)“文匠”身懷寫作妙技,但技藝運用須有助于情感的充分展現。明代袁中道云:“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出自靈竅,吐于慧舌,寫于铦穎,蕭蕭冷冷,皆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袁中道521)文之“上匠”定能心手相通、技道合一,創造辭采精妙而又情感豐沛的作品。
其次,必須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神妙之“匠”。明代徐禎卿說:“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徐禎卿13)隨著情感的自由變化與時代的文風更替,寫作技巧自應變通無礙卻又得其寰中。宋代戴復古詩云:“意匠如神變化生,筆端有力任縱橫。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腳后行。”(戴復古227)以情為先,筆隨意動,自出機杼不為規矩束縛,這才是文學領域“神工哲匠”應有的境界。因為有這種覺悟,所以古代文論中“一代宗匠”“規矩大匠”“意匠”“師匠”的稱呼均是對文學家最高的贊美。“文匠”說在歷史沿革中最終走向褒義色彩。
綜上,我們分析了六朝“文匠”說的起源、含義與后世影響。可以發現: 作為技藝與制作的代表,“匠”在古代早期并未和文學發生緊密聯系。而六朝人則逐漸意識到: 文學和其他藝術創造活動一樣,不僅是思想的反映,更是精工巧技的產物,這就促成了“文匠”說的產生。更重要的是在六朝特殊的人文環境下,文論家將深邃的哲學、美學理念與尊重工匠勞動、學習技藝經驗的精神融會貫通,既強調了寫作技巧的重要性,又以文辭技藝助推了抒情、審美功能的發揮,極大地豐富了“文匠”的內涵。它的出現代表了六朝文論家對于文學創作規律的深刻思考,并深刻影響了后代文論對于“文匠”概念的認識,使得“文匠”說成為古代文論中一個源遠流長、內涵豐富的概念。
注釋[Notes]
① 本文所引《文心雕龍》原文(除《隱秀》篇外)均出自范文瀾: 《文心雕龍注》(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其中《隱秀》篇引自周振甫譯注: 《〈文心雕龍〉譯注》(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2006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陳伯君校注: 《阮籍集校注》。北京: 中華書局,1987年。
[Chen, Bojun, ed.AnnotatedCollection of Ruan Ji’s Work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陳傳席: 《六朝畫論研究》。天津: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
[Chen, Chuanxi.AStudyofPaintingTheoriesduringtheSixDynasties.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6.]
陳鼓應注譯: 《莊子今注今譯》。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
[Chen, Guying, ed. ZhuangziTranslatedandAnnotated.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陳師曾: 《中國繪畫史》。杭州: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
[Chen, Shizeng.AHistoryofChinesePainting.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3.]
成公綏:“隸書體”,《中國歷代書論選》,潘運告編。長沙: 湖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16—18。
[Cheng, Gongsui. “Styles of Official Script.”SelectionofChineseCalligraphyTheoriesacrossDynasties. Ed. Pan Yungao.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7.16-18.]
戴復古: 《戴復古詩集》。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Dai, Fugu.CollectedPoetryofDaiFugu.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董楚平譯注: 《楚辭譯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Dong, Chuping, ed. The Songs of ChuTranslatedandAnnotated.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4.]
范文瀾: 《〈文心雕龍〉注》。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Fan, Wenlan.Annotated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高誘注 畢沅點校 徐小蠻標點: 《呂氏春秋》。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Gao, You, Bi Yuan, and Xu Xiaoman, eds.MasterLü’sSpringandAutumnAnnal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4.]
顧愷之:“魏晉勝流畫贊”,《歷代論畫名著匯編》,沈子丞編。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2年。7—8。
[Gu, Kaizhi. “Remarks on the Paintings of the Wei and Jin Celebrities.”CollectionsofPaintingTheoriesacrossDynasties. Ed. Shen Ziche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 Publishing House, 1982.7-8.]
——:“畫評”,《歷代論畫名著匯編》,沈子丞編。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2年。5—6。
[- - -. “Remarks on Paintings.”CollectionsofPaintingTheoriesacrossDynasties. Ed. Shen Ziche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82.5-6.]
黃公渚注: 《周禮》。北京: 商務印書館,1936年。
[Huang, Gongzhu, ed.RitesofZho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6.]
胡應麟: 《詩藪》。北京: 中華書局,1958年。
[Hu, Yinglin.Gathering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嵇康: 《嵇康集校注》,戴明揚校注。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Ji, Kang.AnnotatedCollection of Ji Kang’s Works. Ed. Dai Mingya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2.]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三冊),郭紹虞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8—33。
[Li, Dongyang.PoetryTalksfromtheHuailuHall.SelectionofChineseLiteraryTheoriesacrossDynasties. Vol.3. Ed. Guo Shaoyu.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28-33.]
劉安: 《淮南子》,許慎注,陳廣忠點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Liu, An.WritingsofPrinceHuainan. Eds. Xu Shen and Chen Guangzho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6.]
劉大櫆: 《論文偶記》,《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三冊),郭紹虞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434—38。
[Liu, Dakui.CasualNotesofCommentsonLiterature.SelectionofChineseLiteraryTheoriesacrossDynasties. Vol.3. Ed. Guo Shaoyu.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434-38.]
劉義慶: 《世說新語匯校集注》,劉孝標注,朱鑄禹匯校集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Liu, Yiqing.CollectedAnnotationstoThe Tales of the World. Eds. Liu Xiaobiao and Zhu Zhuyu.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2.]
陸機: 《陸士衡集 附札記》。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1—4。
[Lu, Ji.CollectedWorksofLuShihengwithNot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1-4.]
呂天成: 《曲品校注》,吳書萌注。北京: 中華書局,1990年。
[Lü, Tiancheng.AnnotatedEvaluation of Southern Dramas. Ed. Wu Shum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潘天壽: 《中國繪畫史》。北京: 團結出版社,2011年。
[Pan, Tianshou.AHistoryofChinesePainting. Beijing: United Press, 2011.]
孫衍栻:“石村畫決”,《中國畫論類編》,俞劍華編。北京: 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6年。977。
[Sun, Yanshi. “Painting Theory from the Stone Village.”CollectionofChinesePaintingTheory. Ed. Yu Jianhua. Beijing: Chinese Classical Art Publishing House, 1956.977.]
王充: 《論衡》。北京: 商務印書館,1947年。
[Wang, Chong.CriticalEssay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47.]
王夫之: 《姜齋詩話箋注》,戴鴻森箋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Wang, Fuzhi.AnnotatedPoetry Talks from the Ginger Studio. Ed. Dai Hongse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1.]
王先慎集解 姜俊俊校: 《韓非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Wang, Xianshen, and Jiang Junjun, eds.HanFeiZi.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5.]
王羲之:“書論”,《中國歷代書論選》,潘運告編。長沙: 湖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41—43。
[Wang, Xizhi. “Remarks on Calligraphy.”SelectionofChineseCalligraphyTheoriesacrossDynasties. Ed. Pan Yungao.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7.41-43.]
衛恒:“四體書勢”,《中國歷代書論選》,潘運告編。長沙: 湖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19—29。
[Wei, Heng. “Four Styles of Calligraphy.”SelectionofChineseCalligraphyTheoriesacrossDynasties. Ed. Pan Yungao.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7.19-29.]
吳毓江: 《墨子校注》,孫啟志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1993年。
[Wu, Yujiang.AnnotationstoMo Zi. Ed. Sun Qiz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蕭繹:“山水松石格”,《歷代論畫名著匯編》,沈子丞編。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2年。21。
[Xiao, Yi. “Painting Theory on Landscapes.”CollectionsofPaintingTheoriesacrossDynasties. Ed. Shen Ziche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2.21.]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郭紹虞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64—65。
[Xiao, Zixian. “Literary Theory inTheBookofSouthQi.”SelectionofChineseLiteraryTheoriesacrossDynasties. Vol.1. Ed. Guo Shaoyu.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264-65.]
許慎: 《〈說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Xu, Shen.NotestoExplanations of Characters Simple and Complex. Ed. Duan Yucai.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1.]
徐禎卿: 《談藝錄》。北京: 中華書局,1991年。
[Xu, Zhenqing.RemarksonAr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1.]
顏之推: 《顏氏家訓》,夏家善、夏春田注。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
[Yan, Zhitui.Yan’sFamilyInstructions. Eds. Xia Jiashan and Xia Chuntian. Tianjin: Tianji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5.]
楊伯峻譯注: 《孟子譯注》。北京: 中華書局,1962年。
[Yang, Bojun, ed. MenciusTranslatedandAnnotated.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楊明照: 《抱樸子外篇校箋》。北京: 中華書局,1997年。
[Yang, Mingzhao.AnnotatedOuter Chapter of the Master Who Embraces Simplici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袁中道: 《珂雪齋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Yuan, Zhongdao.CollectedWorksfromtheKexueStudio.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9.]
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
[Zhang, Yanyuan.FamousPaintingsacross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趙秉文:“答李天英書”,《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二冊),郭紹虞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433—39。
[Zhao, Bingwen. “Response to Li Tianying.”SelectionofChineseLiteraryTheoriesacrossDynasties. Vol.2. Ed. Guo Shaoyu.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433-39.]
鐘嶸: 《詩品集注》,曹旭集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Zhong, Rong.AnnotatedCritiques of Poetry. Ed. Cao Xu.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4.]
鐘繇:“用筆法”,《中國歷代書論選》,潘運告編。長沙: 湖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12—14。
[Zhong, Yao. “Techniques of Using the Writing Brush.”SelectionofChineseCalligraphyTheoriesacrossDynasties. Ed. Pan Yungao.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7.12-14.]
周振甫譯注: 《〈文心雕龍〉譯注》。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2006年。
[Zhou, Zhenfu, ed.TranslatedandAnnotated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