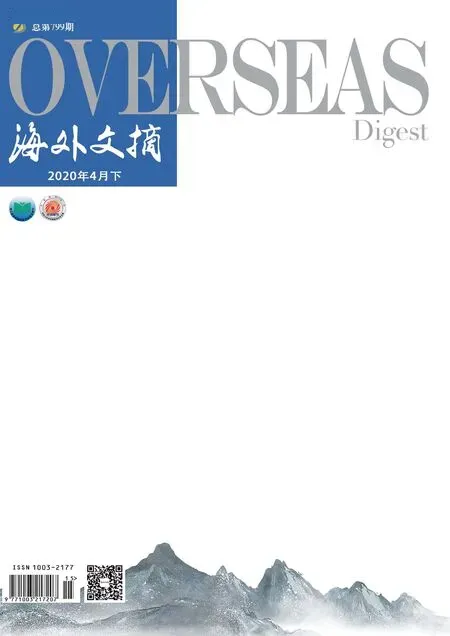基于鄧小平海洋戰略構想的啟示對破解我國西太平洋海上戰略通道安全困局和實踐的探討
應慧超
(江蘇陸軍預備役高炮某部,江蘇無錫 214000)
0 引言
習近平同志指出:海上戰略通道是關系我國經濟和民生的命脈。要想富,先修路;要想強,必通航。確保我國海上戰略通道安全無疑是實現海洋強國的重要一環,而西太海上戰略通道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鄧小平海洋戰略構想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是新時期中國經略海洋的開創之舉。
1 我國西太地區海上戰略通道的安全困局
從地理學的角度看,西太是我國走向太平洋、印度洋、南北極等海外區域重要的戰略樞紐;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以海洋和海上通道為主的西太海域戰略需求深刻影響著我國從近海走向深海的戰略實施。然而,美國的強勢介入、區域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軍事發展水平的不足,都嚴重影響了我國西太海上戰略通道安全和穩定,也不足以支撐海洋強國戰略的實施。
(1)美國的強勢介入讓西太海上戰略通道安全烏云密布。中美作為這一區域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美國一直尋求對該海域海上戰略通道的絕對控制權,積極通過各種手段排斥遏制中國。在東北亞,美國以半島危機為借口,以“硬碰硬”的方式對待東北亞安全局勢,借以保持在東北亞海域軍事存在的正當性。在東海海域,美國主動卷入中日矛盾,主張保持以有利于日本的釣魚島問題“現狀”為基礎,通過懸而未決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發揮該問題對中國的鉗制作用。在臺灣問題上,美國幾乎每次都是臺海危機背后最大的操控手,通過《日美安保條約》的不斷修訂、加強美臺合作等方式,加大對臺海局勢變化的軍事部署,把臺灣島打造成美國遏制中國第一島鏈封鎖線上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在南海海域,美國頻頻拋出“中國單方面改變海上現狀、中國違逆國際法理和規則和中國破壞海上自由航行”[1]等無理論調,通過外交鼓勵、軍備協助、安全承諾等方式不斷助推沿海國家的南海政策強硬化,無疑加重了南海海域共同開發建設的難度。在整個西太地區,美國依舊保持著70 多年前提出的“島鏈”政策,努力把住對西太地區事務的絕對主導權,不僅從軍事上扼制中國,而且在經濟、安全、意識形態等領域對中國也毫不松懈。
(2)西太地區沖突和民族矛盾由來已久。由于歷史原因,西太地區國家之間存在著各種民族、領土、宗教等矛盾,也是影響整個西太海上安全環境的關鍵所在。該區域“海上通道眾多且非常重要,也是世界公認的‘軟肋’”[2],海上安全環境極不樂觀。日韓歷史認識問題和領土之爭非常激烈,雙方就“慰安婦”遺留問題、“獨島”(日本稱為“竹島”)問題對抗都非常激烈;在矛盾對抗中,甚至出現了韓國軍艦與日本軍艦相互對峙的嚴重局面,雙方一度揚言“不惜以戰爭保衛島嶼的意志”[3]。東南亞“六國七方”海權之爭,對南海油氣資源、海島資源、航道資源的爭奪依然十分激烈;同時,東南亞各國的軍備競賽也愈演愈烈,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2019 年年鑒數據顯示,2014—2018 年之間,亞洲和大洋洲進口武器占全球進口武器的40%,其中東南亞國家占9%;數據還顯示,2018 年僅亞洲就有7 個國家發生了武裝沖突:印度尼西亞、緬甸、菲律賓、泰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值得注意的是,海上恐怖主義沉渣泛起,南海、馬六甲海峽附近海域已經成為了恐怖襲擊、海盜等恐怖行動的頻發區。這些都為我國維持“走出去”戰略下的海上戰略通道安全埋下隱患。
(3)遠海能力薄弱與近海建設良性互動不足。從全球來看,中國海洋能力建設的目標在遠海,建設在全局。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仍然處在起步階段,各國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倡議并沒有表現出與中國對應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各國對于中國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援建的方式所帶來的主權、安全等問題的疑慮依然存在。同時,中國在海外依然面臨著維權軍事斗爭、海上局部戰爭、低烈度武裝沖突、境外打擊恐怖主義、海外非戰爭軍事行動等嚴峻挑戰。2018 年6 月1 日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吉布提海外保障基地正式啟用,主要在海外護航、維和、人道主義救援等方面給予重要保障。但是,這樣的戰略支點,依然面對著戰略線短、布局孤立的嚴重問題,無法形成完整的運輸保障線、全球支援網。
2 鄧小平海洋戰略構想及特點分析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際海權呈現出斗爭形勢日趨復雜化、實現手段逐步多樣化和海軍發展高科技化等特點,毛澤東同志始終以維護海上利益、發展海上力量為目標,不斷維護我國海洋權益,鄧小平同志繼承和發揚毛澤東海權思想,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原則,通過維護海洋國土、發展海洋經濟、建設海上力量來構建其海權思想并付諸實踐。
(1)加快對外開放沿海城市發展海洋經濟。向海而興、背海而衰。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提出有先后次序的“差異化、有序化、梯級化”發展思想,優先開放發展沿海城市,在中國東部沿海部分地區率先設立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大力促進沿海城市和區域的發展,帶活了我國海洋經濟的發展。1984年5 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將天津、上海、廣州等十四座城市定為全國第一批沿海開放城市,賦予這些城市在對外經濟活動中的更多自主權利,放寬利用外資建設項目的審批權限,在稅收、外匯管理上給予“三資”企業優惠待遇。1985 年2 月,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門-漳州-泉州三角地區被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 年3 月,又進一步擴大了經濟開放區的范圍,把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環渤海等地區的一些沿海城市開放為經濟開放區。鄧小平同志通過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來經略海洋,歷史和實踐證明,這為中國發展海洋強國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經驗和戰略支撐。
(2)通過“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緩和爭端經略海洋。自古以來,中國堅持和倡導“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20 世紀80 年代,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東海、南海領土爭端難以解決的形勢下,鄧小平提出了“擱置主權,共同開發”超凡的戰略思考,繞過地區分歧爭執點,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加強與東北亞、東南亞國家的合作交流,促進地區之間的互利互信,同時也為我國經略海洋爭得寶貴的國際環境。“擱置主權,合作開發”這一思想的提出,核心在主權屬于我國,精髓在共同開發。由于歷史原因,中國在西太地區政治、安全處境極為不易:南海“六國七方”資源之爭形勢嚴峻,東海中日兩國釣魚島之爭,美國積極介入亞太安全事務,使得這一片本該和平的區域成為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一個主要熱點地區。在如此復雜的情況下,鄧小平同志敏銳嗅到時代的主題由“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所轉變,主動提出擱置爭議,以合作共贏的積極態度尋求與周邊沿海各國共同開發海洋資源。
(3)加快建設海軍戰斗力提升海洋軍事存在。海軍強、海權強、國運昌。海上力量是海洋權利實現的工具。近代中國的慘痛教訓更是告誡我們,西方列強都是憑借堅船利炮通過海上入侵中國的[4]。1975 年6月26日,鄧小平視察海軍106艦為海軍題詞時指出:“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為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而努力奮斗”。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中國海軍已經逐漸走出‘淺海’,走進‘深海’,過去十年邁進海洋的旅程達到了之前30 年的30 倍。”[5]鄧小平同志從海軍建設戰略目標、海軍現代化建設、海上指揮作戰能力等方面著手,“給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規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對現代戰爭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軍隊”[6],中國海軍實現了建國后由“近岸防御”向“近海防御”的轉變。
3 鄧小平海洋戰略構想對構建我國西太海上戰略安全通道的啟示
“海洋關系國家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必須突破重陸輕海的傳統思維,高度重視經略海洋、維護海權。”[7]鄧小平海洋戰略構想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應對海洋新挑戰、解決海洋新問題的智慧結晶,啟示著我們,只有堅持發展、開放、合作,建設陸權和海權兼具的強國,才能建成真正的世界強國。
一是堅持陸海并重,實施海洋強國戰略,著力打造海上交通線上的軟硬實力。國強則海權強,國弱則海權弱。
(1)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加大海洋開發力度,特別是南海海域、東海海域開發,加強對周圍海域資源的開發,推動海洋產業結構轉型發展,形成陸海聯動的開放格局和新型產業鏈模式。2011 年到2018 年,中國海洋經濟發展指數(OEDI)年均增速3.5%,2018 年指數達到131.3,比上年增長3.2%,總體表現穩中向好。
(2)培養高端海洋人才,發展海洋高端科技。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充分發揮好海洋研究院所、海洋高校資源的平臺優勢,做好人才培養和儲備;同時,強化海洋前沿科學研究與技術難題的研發和攻關,突破涉海關鍵技術的攻關,不斷取得海洋高科技術的突破。近年來,“蛟龍”、“深海勇士”探海、“雪龍”探極、“藍鯨1 號”南海試采可燃冰、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等涉海關鍵技術和重大項目建設取得突破,對海洋強國建設的支撐能力明顯增強,拓展了我國開發利用海洋的空間疆域。
(3)推進軍民融合發展,提升海上交通線遠程保護能力。面對錯綜復雜的近海海上戰略通道環境,中國有必要尋求海上交通線遠程保護能力。這是一項系統性工程,主要包括:證明有重要反潛能力的附加核動力攻擊潛艇的建造和配置,航母的建造,專門海軍船舶造船廠的建立,海軍輔助艦隊,獲得(如在印度洋)可靠的海外基地,高水平中國人民解放軍學說,訓練水平和人員作戰能力的成熟度等[8]。2018 年4 月,習近平在南海海域海上閱兵時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努力把人民海軍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軍”[9]。
二是堅持開放合作,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建設共享安全的海上戰略通道。海洋命運共同體包含著相互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觀的高深智慧。
(1)發揮“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優勢,加強與周邊國家的良性互動。合作方能共贏,在東亞地區尤為如此。區域各國應當放下歷史矛盾,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面向未來,加強海域共同合作開發,依靠自己建設安全共享的安全環境。同時,要善于利用東北亞國家、東盟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使中國在東海、南海問題上占據主動性。同時,中國在這些海域中要采取更加靈活而堅定的政策和立場,比如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推進南海島礁建設,更好地實現國家主權主張和戰略布局。
(2)堅持走出去戰略,加強與世界各國在海洋的共同開發。中國戰略利益遍布世界各地,海上戰略通道是溝通起來的橋梁。中國應當主動走出去,積極與世界各國加強在海域的合作開發,要推進我國相關法規的立改廢釋工作,同相關國際法和駐在國法律搞好對接,加快有關行動法規制度的體系建設;發揮好吉布提中國軍事基地的模范作用,在印度洋、太平布局有效的戰略支點,共同與大陸建立完整、連續的戰略支援線。2019 年9 月,所羅門群島與中國建交,基里巴斯與中國復交;中國還與多數太平洋島國簽署基礎設施發展規劃。這些都是成功的戰略舉措。
三是開展大國外交,加強與美海上安全合作,降低中美海上交通線摩擦帶來的沖突風險。未來幾年中國主要戰略能源海上交通線安全選擇,依舊是維持與美國的友好關系,免費依靠美國海軍保護的重要能源供應路線。美國對西太海上戰略通道的控制中,一方面尋求與中國之間的有限合作,另一方面與區域其他國家積極展開軍事交往以遏制中國發展。但中美兩國在該區域具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在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領域都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1)推進中美務實性軍事合作。建立“戰略安全對話”“防務磋商”“軍事安全磋商”等海上軍事磋商和互信機制,建立各種直接涉及改善安全環境的機制,建立一系列海上安全細則;針對當前該海域嚴重泛濫的海盜事件和海難救助,建立海上安全應急共享、預警和聯合護航機制,推動中美軍事交流與合作,擴展在 “環太平洋聯合軍演”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
(2)展開多維度多領域的安全合作與交流。與正式的軍事安全對話和磋商機制相比,非官方、非政府或半官方的“第二軌道”軍事交流形式更為靈活。發揮好香格里拉對話、中美安全問題研討會、退役高級將領非正式軍事會晤等第二軌道在雙方交流中的積極作用,加強雙方在海上聯合搜救演習、建立人道主義救援和減災定期磋商機制等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推動中美安全合作常態化和機制化。
(3)建立解決海上沖突的危機管控機制。近30 年的中美海上爭端表明,中美之間的軍事競爭沒有贏家。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區具有廣泛的共同的戰略利益,雙方應當降低軍事競爭水平,構建“互信、合作、不沖突、可持續”[10]的新型中美軍事關系。不斷優化中美海上合作形式,中美兩國國防部于2014 年簽署了《關于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諒解備忘錄》和《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諒解備忘錄》,成為兩國加強危機管控、預防風險的重大成果。中美兩國應當共同努力,保持溝通機制的暢通和連貫性,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國防部工作磋商機制、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國防部熱線電話等現有平臺和機制運轉,保證在出現重大矛盾的溝通和處理渠道。中美應當彼此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不斷增進互信,加強合作,妥處分歧,管控危機,共同努力推動中美新型軍事關系不斷向前發展。
4 結語
未來已來,經略海洋、發展海軍、走向深藍已是我國當前刻不容緩的戰略目標。構建西太海上戰略通道安全,是我軍走向深藍的第一步,也是我國實施“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的關鍵所在。鄧小平同志“發展、合作、開放”的海洋戰略構想,拋棄零和思維,展現了大國領導人的大國氣度。中國的海洋戰略實施需要自身實力作堅強后盾,合作是維護海上安全的最有效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