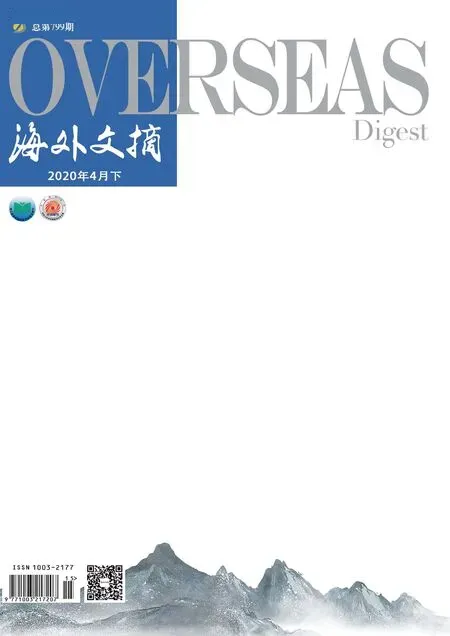宗法制視角下的冥婚儀式運行機制與合法性分析—以晉東南J 市的冥婚習俗為例
劉淵 劉尚麟 李若彤 張千禧 郭子宇
(吉林大學,吉林長春 130012)
冥婚,亦稱陰婚,是為死去的人找“配偶”的一種習俗。人們總以為未婚而死,是人生的不幸,所以即使在冥間,亦須為未婚者覓“配偶”,使已死的男女結成婚姻并合葬。通過冥婚讓他們結成“夫妻”,夭亡者便可過繼子嗣,由此香火得以延續。冥婚現象自古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直到現在,冥婚習俗在山西、陜西等地的農村地區仍然存在。在高速發展的當代社會,冥婚逐漸形成了獨有的非法買賣市場和利益關系鏈。不正當的冥婚買賣催生并導致了一系列違法犯罪行為,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國家法治建設。
冥婚之俗由來已久,但對于冥婚問題的學術研究在近現代才逐步興起。已有研究成果多從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來研究古代冥婚現象和冥婚歷史,以冥婚的內容、類型、儀式、發展變化狀況、社會根源以及相關文學作品為切入點進行研究[1-3]。也有少數學者進行了田野調查考察當代的冥婚現象,然而大多在使用現有的理論進行解釋,對于冥婚運行機制和合法性沒有更深入的探索[4-6]。綜合來看,目前既有的研究一方面對當代冥婚問題的分析解釋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也缺乏對華北地區冥婚問題的關注。
本研究以宗法制為考察視角,對冥婚盛行的晉東南地區冥婚進行了田野考察。研究團隊的田野點選定為晉東南J 市Q 縣H 鄉S 村,地處中條山谷中,主要姓氏(氏族)為Z 氏。由于地處位置相對閉塞、氏族組織相對單一等因素,當地的冥婚儀式較大程度地保留了原始風貌,較好地反映了華北地區冥婚儀式背后的宗族、宗教、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內容。研究團隊著力考察了當地某宗族所經歷的冥婚案例及其社會網絡,對該宗族內成員以及操作冥婚儀式的“靈職人員”展開了口述史料和其他訪談資料的采集,得出了以下主要發現。
1 晉東南田野調查的三項發現
晉東南Q 縣的冥婚習俗雖在不同個案間在細節上各異,但大體遵循了同一套制度邏輯,即:由家長做主,在家族間實現“聯姻”,并以事鬼神為核心目的。這一制度邏輯在家族內的縱貫結構上,表現出一套等級分明的權力關系;而在家族間的橫向結構上,則具備我國傳統生育制度的一些特征。
根據田野調查所采集的各案例,絕大部分冥婚者并非遵從逝者自身的意愿決定,而是逝者家屬將冥婚加于逝者之上。是逝者的家屬在逝者離世后,認定逝者需要一場完善的婚姻,便替逝者做主,為逝者舉辦“婚禮”。冥婚在意愿和決定權方面,與冥婚主角并無太大牽連,反而是由逝者親屬籌劃達成的一場“婚姻”。顯然,冥婚的主要動機并非滿足逝者個人對婚姻的向往,而是滿足其所在的宗族的需要。這說明,冥婚在明面上打著安息逝者的旗號,其真實目的是穩定宗族,在實施上也與宗族傳統的家庭觀念聯系緊密。因此,冥婚服務的主體并非逝者本人,而是活躍在逝者身邊的眷屬,乃至逝者所屬的整個宗族組織。這進一步說明了冥婚對于宗法制的重要意義。
其二,冥婚在生育制度方面也與宗法制有深刻關聯。經過調查發現,冥婚不僅涉及了婚配階段,更涉及到后代生育問題。在一些案例中,男女雙方(的家庭)在完成冥婚后會選擇給冥婚夫婦過繼一個子嗣,這名用于過繼的孩子往往來源于雙方家族中親戚的孩子。在男女雙方完成冥婚儀式之后,這個孩子將會被過繼給冥婚夫婦,成為他們名義下的孩子。由婚配到生育,在宗法觀念的影響下,冥婚不僅僅是為了完成“婚配”,更是通過過繼子嗣實現“家族的延續”。為冥婚夫婦賦予一個社會意義上的“后代”,體現宗法觀念中結婚生子以延續血脈、擴大宗族的含義。這種“婚姻”又與傳統的婚姻形式不盡相同,雖然它依舊存在著婚配與生育等與婚姻相似的形式,但這些形式卻僅僅存在于表面。就生育而言,冥婚只完成了子女的過繼,但是并未涉及到撫育孩子的各個環節。這樣一種形式的婚姻,更多帶來的就是對雙方宗族的穩定,且加強雙方宗族之間的聯系,其社會意義遠超過了其在人口學上的意義。
除了傳統宗法父權的影響外,冥婚與當下的婚姻現實息息相關。目前,我國社會存在婚姻擠壓(marriage squeeze)現象:我國人口中的“男多女少”導致大批男性單身無法找到配偶。這種現象在農村地區尤其明顯。所接觸到的冥婚案例中,大多數選擇主動結冥婚的是未婚而死、沒有配偶的男性,相對而言主動選擇冥婚的女性很少。在冥婚的非法“市場”中,存在著女尸供不應求的情況,女尸價格遭到了哄抬。這看似是由現實因素所引起的,但歸根結底而言,還是宗法制所導致的結果。宗法與父權導致了男尊女卑的秩序局面,要求男子成家立業的觀念根深蒂固,男方的家族也更有實現逝子“完婚”的需求,將成家娶親視為男性的一項“任務”。正是這樣濃厚的宗法制觀念和男權觀念,使得男性逝者家庭對于冥婚的需求比女性逝者家庭更為強烈。由此可見,女尸貴、男尸冥婚主動性高的冥婚現狀亦為宗法制對冥婚施加影響的結果。
2 晉東南的冥婚儀式與鬼神信仰
通過實地調查發現,與以往研究中記載的頗為復雜的冥婚儀式有所不同的是,目前晉東南地區的冥婚儀式已經大大簡化,僅為男方拉回棺材一起下葬,并由“陰陽師傅”上香、念經等。
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又譯為“過渡禮儀”)是人類學術語。法國人類學家范熱內普(van Gennep, Arnold)提到(1909),通過一種特殊的、“神圣化了的氛圍營造”,人的身份就如同“從屋子中的各房間和走廊中”發生了“通過”,在通過儀式下,參與了通過儀式的個體在社會角色上發生了躍遷,實現了社會身份的轉化[8]。例如,婚禮作為一種通過儀式,實現了婚配雙方從未婚到已婚的身份轉化;而喪禮作為一種通過儀式,則實現了逝者從家族正式成員到已經入土為安的身份轉化。作為婚姻儀式和喪葬儀式的復合體,冥婚儀式也符合這樣的定義,屬于通過儀式。通過冥婚這一過渡儀式,冥婚對象實現了在社會關系結構中從在游離孤獨的狀態到合法地被宗族體系接納的狀態轉換,而參與的宗族在世成員則實現了從“被冤魂纏身”到“宗族穩定得到了維護,冤魂得到了安撫而不再被其纏身”的身份狀態轉化[7]。
在冥婚的過程當中,“鬼魂”這一抽象的概念在未婚逝者身上實現了具體化和神圣化。一方面,抽象的“鬼魂”被具象化為了未婚逝者,被賦予了特定的人格,也因此被嵌套進入了未婚逝者在生前所處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于是,抽象的“鬼魂”與具體的生者之間展開了定向的社會互動,直到冥婚儀式完成之后這種互動方可結束,“鬼魂”也方可回歸到其原處的抽象狀態。另一方面,“鬼魂”從一種日常生活中口耳相傳的一般性的抽象事物,在未婚逝者的身上得到了神圣化,被賦予了超自然的力量(如糾纏原家族、帶來厄運)。因此,冥婚不僅僅是對未婚逝者的婚、喪兩種儀式的復合體,更是對鬼神的一種崇拜活動。所以,冥婚儀式不僅是單純的婚喪儀式,更是一種逝者崇拜,是一種類宗教的信仰活動。
3 法制化與當代冥婚習俗間的矛盾
在宗族制度興盛時期,冥婚的存在對于維系傳統秩序有著重要作用,對于國家法效果不甚的家長制管理體制來說,冥婚是合乎一家之法、一族之法的。然而近百年來,中國社會整體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社會的勞動方式由傳統手工業轉為機械化生產,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程度越來越高,社會主要組織形式和社會關系由家庭和血緣轉為職業組織和業緣。而鄉村社會在轉型過程中雖然具有相對獨立的形態,但家族制度也總體是走向沒落的,而宗族制的衰落也使冥婚的合法性不斷被削弱。隨著城市化的進程,鄉村居民的居住也不再是固定、聚居的。由于大量勞動力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熟人社會便顯得不再那么重要,“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開始有大量交集,即血緣團體和契約團體相互滲透”。當進入到城市中后,接受了更先進的觀念,伴隨著經濟發展,國家對火葬的推行以及相關部門對土葬的嚴格監管,冥婚的可能性變得更低了。
冥婚的合法性不被認同更客觀地體現在由冥婚產生的違法犯罪行為。在很多流行冥婚、需要女尸的農村地區,圍繞著女尸形成了一條產業鏈并擁有廣大市場。為了謀得利益,即使在我國刑法中明確規定“盜竊、侮辱尸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仍然有人從墳墓中、停尸間或其他地方秘密竊取尸體,高價出賣或倒賣,更有甚者,鋌而走險,為了獲取尸體而實行殺人行為后易尸逐利。近年來關于尸體倒賣的新聞時常進入公眾視野:某地發生大規模墳墓盜掘事件,某男子在火車站案件過程中被查出攜帶六具殘缺不全的女尸,某醫院院長帶頭倒賣太平間中女尸等等。由冥婚產生的種種違法犯罪行為都對社會秩序的穩定和人民生活保障構成了巨大威脅。另外,從《尸體出入境和尸體處理的管理規定》可看出,出于社會公共衛生安全的考慮,禁止買賣尸體是為了禁止尸體處理不當造成的水源污染和病毒傳播;《殯葬管理條例》中為了節約土地資源、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規定禁止隨意占用耕地或林地來做墓地[9-10]。
然而在晉西南Q 縣,女尸的價格一高再高。不僅占用耕地、林地乃至高速公路用地修建冥婚墓的現象普遍發生,女尸的交易活動也非常活躍。這引出了本研究所探討的核心問題:當冥婚本身的社會基礎(即宗法制)在社會變遷之下逐漸瓦解時,冥婚在通過什么機制來獲取合法性以維持自身的存續呢?
4 宗法制日趨式微背景下的當代冥婚問題
英國人類學家、華南宗族研究專家斐利民(Maurice Freedman)認為(1966;1970),在宗族制度背后所體現的,是一套完整的社會地位、權力與社會管理體系。斐利民提到(1958),中國的宗族結構由家(family)和戶(household)二者共同構成,植根于鄉村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其經濟生產基礎之中,具有強烈的秩序性色彩。基于這種宗族制度,中國鄉村社會發展出了一套以親疏關系為基礎的差序格局,從而建立了以宗族結構為基本結構的禮俗社會。林語堂(2013)將這種宗法制結構稱之為“家庭主義的倫理學”,并突出了其中家長的地位和作用。也正因此,雖然在各地冥婚習俗有著或多或少的差異性,但是其基本邏輯是一致的。華北的喪俗(包括冥婚)在整體上呈現出了明顯的齊一性(uniformity)特征(Naquin, 1988)。也就是說,雖然各地的冥婚在具體操作上各有不同,宗法制的基本邏輯始終貫穿著冥婚活動。在田野調查中研究者發現,晉西南Q 縣的冥婚儀式雖然和我國其他地區在流程上存在差異性,但其宗法制邏輯是一致的[11,12,14,17,20]。
斐利民認為(1958;1970),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中的經濟生產關系是維系宗族制度的基礎,即:男性負責勞動,財產在氏族內部實施有限的分享,宗族經濟收入的最終支配權歸屬家長把持。林語堂將這種“家族集體制”稱之為“中國式的共產主義”(2013)。同樣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婚姻、喪葬制度也以宗法制為基礎。類似于財產的“家族集體制”,研究者發現,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婚姻中也存在家族優于個人的情況,“中國男性的婚姻更多是出于家族的利益而非個人利益:延續香火,生育后代以繼續祖先崇拜,為家族的老母親尋找一名兒媳并最終讓其接替家族族母的位置”[15]。因此,冥婚的目標也是維護宗法制。一種主流的觀點認為,冥婚的目的是防止過世未婚家族成員的鬼魂因為沒有后代而無人祭拜,從而返回家族添亂(Martin, 1973)。在研究團隊所開展的一系列訪談中,受訪者大多都提到了“未婚家庭成員死后,其鬼魂會回到原家族作亂”的說法,也進一步印證了宗法制是冥婚儀式的基礎[13,14,16,20]。
隨著時間的推移,現代化進程破壞了宗法制的基礎。在斐利民的分析框架下,隨著現代化的展開,個體獲得了直接掌握私人財產的能力和權利,“家庭集體制”解體,從而在宗法制下壟斷了經濟生產和分配活動的男性成員(尤其是家長)不再享有經濟特權。魏婓德(Frederic Wakeman)的一篇論文(1988)證實了這一假說,他提出,新中國成立后雖然部分婚喪習俗得以保留,但其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然而吊詭的是,冥婚習俗在山西非但沒有因宗法制的式微而逐漸式微,反而在民間繼續盛行。冥婚習俗在山西的日趨盛行,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在2005 年,中國中央電視臺報導了(2015)山西一起因配冥婚而導致的謀殺案。《中國新聞周刊》(李騰,2016)報道稱,隨著冥婚習俗的日趨盛行、村民收入的提高和鄉村中“男多女寡”的人口失衡問題,女尸的價格水漲船高,山西未婚女尸價格一度達到了15 萬的“天價”。在田野調查中研究團隊亦發現,在今天的晉西南Q 縣中,冥婚已經形成了一個包括了“鬼媒人”“老法師”“陰陽師”在內的分工明確、團隊完整的一整套“產業鏈”,其中更是“女的搶手”(受訪者語)[18-19]。
雖然宗法制已經式微,然而宗法制倫理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種特殊的現象彰顯了晉西南Q 縣的鄉土社會中所面臨的一種嚴峻挑戰:在現代化大潮之下,鄉村的家庭主義倫理受到了沖擊,晉西南的鄉村社會直接站在了現代規訓與鄉村禮俗的十字路口之上。這也是冥婚儀式在晉西南所面臨的“合法性危機”:在現代主義的法律看來,為尸骨實施婚配是對逝者遺體的不尊重;然而在鄉村的地方倫理之下,為過世的子女尋找配偶恰恰是對逝者最大的尊重。如果這樣的“合法性危機”不能得到解決,冥婚的日趨盛行和宗法制式微之間的矛盾必將繼長久的在晉西南的鄉村社會中繼續發展下去。
5 結論
通過田野調查,研究團隊發現了冥婚背后所潛藏的權力關系和生育制度,認識到了冥婚作為一種特殊的通過儀式的特別屬性,并結合社會變遷的大背景對冥婚制度的新發展和合法性變革展開了一定的考察。本研究一方面努力將冥婚問題的考察視域拓展到了華北地區,另一方面也對現有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回應和補充。
冥婚的社會基礎——宗法制在我國鄉村地區已經面臨瓦解。一面是名存實亡的鄉村宗法制,而另一面是仍然活躍的冥婚活動,冥婚背后潛藏的是鄉土秩序和現代性之間的張力關系。從小處看,這是我國法律在鄉村推行所面臨的一項阻礙;從長遠看,這是我國現代化建設在鄉村地區所面臨的一塊“硬骨頭”。如何實現鄉村傳統秩序和現代化建設之間的相適應乃至互洽,是一項重大的課題。